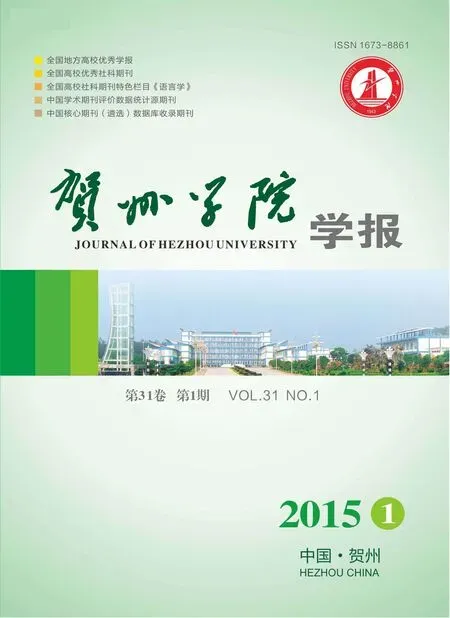《黄金时代》: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史诗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汤唯等主演的《黄金时代》从播映前便已在影视界掀起热议,播映后更是褒贬不一,引发各种争议。事实上,这部影片是以纪录片的形式通过萧红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呈现了民国那个“黄金时代”中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尤其呈现了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知识分子们随着时代动荡而沉浮不定的命运遭际与人生轨迹,建构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荧幕史诗。
一、民国历史的呈现之诗
《黄金时代》的时长为178分钟,被许多观众抱怨“冗长”“沉闷”,殊不知,正是如此的时间长度,才容纳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民国那个年代复杂的现实面貌。或许正是因此,海外对此片的反响不错,赞之为“一杯手磨蓝山咖啡”,因为这部影片是需要像品咖啡一样细细品嚼的。
《黄金时代》以萧红个人富有传奇的命运变迁为视点,呈现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段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社会的状态、景况,影片中牵动的历史人物众多、关涉的历史事件繁复,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之诗。所谓“黄金时代”,从大的时代背景而言,主要是指思想文化的自由,春秋战国、魏晋、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黄金时代,民国时期一直被称为文化的黄金时代、诗歌的黄金时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教育的黄金时代。而历史上,每一个“黄金时代”的社会景况其实都是时局动荡、民不聊生,《黄金时代》中所覆盖的历史时段亦是如此,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31年日本入侵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43,经济发展跌入低谷,绝大多数中国人均挣扎在勉强维持生存的窘迫中,时时面临失业、饥饿、死亡、病痛等困境,其实是朱自清所称的“动摇的时代”[2],周作人所称的“乱世”①,但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才使各种思想、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于是迎来文化大爆发。影片中的1931年至1942年,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年轻人可以自由追求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但对于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也是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动乱年代,《黄金时代》通过一群中国文人们的故事激活了人们对于萧红所生存的黄金时代的记忆与关注。在那一历史时段里,由于时代动荡、政局混乱的原因,许多文学青年纷纷为学业、事业和爱情而流落他乡,其中不少陷入了生死绝境。正是这种时局不稳、人心动荡的时代环境,颠沛流离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文化自由的时代氛围,使文艺青年们写出了许多传世佳作,如《生死场》 《八月的乡村》等。《黄金时代》仿佛是一个人物群像展览馆,将这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和当时的知名文人都一一呈现于影片中,如鲁迅、萧军、胡风、梅志、黄源、许粤华、端木蕻良、骆宾基、聂绀弩、罗烽和白朗等20多人都以萧红为联结点纷纷出场。
电影在造型、服装、场景等方面都充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格与气息,使影片始终萦绕着一股怀旧气息,从旗袍、棉大衣、军大衣服到貂皮大衣,从哈尔滨、上海、晋北、香港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西北战区,都符合时代感,充满历史感。
而许鞍华独特的叙述视角也为本片增加了历史感、时代感。3小时的影像时间中,20多个主配角中的大多数角色都直接面向观众“讲故事”、朗诵萧红作品中的片段、或讲述自己眼中的萧红故事,如罗烽和白朗夫妇正襟危坐地对着摄像机直陈叙述萧红的重大人生转折,等等。这些编剧和导演穿插的环节是为了制造一种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可以暂时将观众从影片的“故事”中抽离出来,而非沉浸在故事中,让观众一起参与到历史事实的纪录、再现与反思中去,如此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呈现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复杂风貌,让观众产生一种“与历史相认的乐趣”。
但影片中最呈现“黄金时代”之时代性的是萧军和萧红的选择与分手。影片巧妙地通过二萧的选择呈现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年轻人普遍的痛苦,即是“为一个人还是多数人”,这是当时那个年代许多人需要面临的选择。周作人主张“闭门读书”,废名则躲进雍和宫明哲保身,一些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精心钻研纯粹的艺术;但许多作家感召于时代,为时代而艺术,为现实而艺术,为革命而艺术。萧军与萧红的情感悲剧就是发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黄金时代》通过他们两个人在选择时的纠结、矛盾与痛苦中其实呈现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许多人面对的共同时代话题:“为一个人还是多数人”,为艺术而艺术还是让艺术为革命服务,甚至完全让艺术成为革命的武器、传声筒。丁玲此时已经从“文才子”变成“武将军”,“不爱红妆爱武装”了,实现现实中的革命投身和文艺中的革命转向了。萧军跟着丁玲留在临汾不愿转移,抛开了身怀其孩子的萧红,这是他做出的选择;而萧红只想找个地方,过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安静地写作,正如她在跟端木蕻良结婚时所言的:“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当萧军知道萧红跟端木蕻良在一起后,他对萧红说:“你跟端木蕻良结婚,我跟丁玲结婚”,这句话引得不少观众爆笑。但其实,这背后的含义是不熟悉那个历史年代的观众们难以理解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许多人奉行的文艺方针,而倡导这种文艺方针的“左翼”占据着文艺界的主流位置,丁玲则是当时的一面文化旗帜,是文艺转向的一个标志,曾经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已经在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艺方向转变。而端木蕻良是带有小资情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此萧红与端木蕻良、萧军与丁玲结婚,其实都隐含着政治意味,虽然萧军最后并未跟丁玲结婚,但那句话却折射了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特殊的政治爱情,也折射了那个历史时代。
另外,“黄金时代”本身含有反讽意味,那个年代是思想和文化的黄金时代,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每一个个体而言,其实并非“黄金时代”,时代的动荡让每个人的生活都颠沛流离,正如萧红写给萧军的信里所言的:“这真是黄金时代……只不过是在笼子中度过的。”这个“笼子”,是命运的笼子,是时代的笼子,谁都逃不掉。萧红在那个“黄金时代”,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这样平实、普通的小小愿望都没法实现,不能不充满讽刺意味。
二、民国文人的爱情史诗
影片通过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一批民国文人的爱情,谱写了一曲跌宕、曲折的爱情史诗。在那个“黄金时代”,许多年轻人都奉行“想爱就爱”的情感逻辑。萧红第一次见到萧军时便谈到爱情的话题:
萧红:“你关于爱的哲学是什么?”
萧军:“爱就爱,不爱就丢开。”
萧红:“如果分不开怎么办?”
萧军:“丢不开便任他丢不开吧。”
这一对话中萧军对于爱情的态度其实已经注定了萧红的悲剧,只是当时她意识不到。萧军的爱情观已表明他并非那种一旦爱上一个人便矢志不移的人,而是想爱就爱、不爱就丢开的人。从他的几段爱情史看,他的爱一开始都是轰轰烈烈的,毫不顾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世俗眼光,但不久便又背弃爱情,寻找新的感情对象。对于萧军而言,他一直在践行他“想爱就爱,不爱就抛开”的爱情逻辑。他的原配许氏,他不爱了,便将她和两个孩子打发回老家,并宣布与其脱离关系,命令其改嫁。对于萧红,一开始他对萧红的爱是炽热的,疯狂的,他为萧红的文学才华而折服,第二次见面就不顾萧红正身怀别人的孩子,而疯狂地与萧红发生了关系。萧红以为颠沛流离的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的人,一头栽了进去,孩子生下来也不愿意自己抚养,像丢掉一个包袱一样抛弃了孩子,以为从此没有任何负担和拖累地可以跟萧军好好恋爱,但萧军如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一旦激情燃尽,便只剩下冰冷的灰烬,他与萧红的情感出现了危机,一次又一次的婚外恋把萧红抛掷在昔日情感的死灰中,萧红只能一次次选择放逐自己,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心灵疗伤。对于第三任妻子王德芬,萧军是与萧红分手不久便与她走到一起的,接连跟她生了8个孩子,但亦并未能阻止他频繁出轨。他甚至把这些情感经历作为写作中值得珍惜的经验与素材:“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3]这或许是他“敢爱敢恨”的心理根源,影片中无法容纳那么多内容,便做了简单化和模糊化处理。
萧红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她逃婚,是她追求自己爱情的表现;她身怀汪恩甲的孩子却与萧军走在了一起,也是她敢爱敢恨、敢于超越世俗的表现。而面对萧军的背弃,她痛苦过、纠结过,但当萧军选择留在临汾打游击不愿与萧红转移后,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而跟端木蕻良在一起了。当萧军的孩子生下来后,她对这个背弃之人的孩子并无好感,当护士抱给她时,她惊恐得往后缩,至于孩子是怎么死的,影片做了模糊处理。影片中还有个细节是,萧红在端木蕻良问她要贴身多年的木杖时,她却拿着木杖去征求聂绀驽的意见,萧红与聂绀驽之间的那段对话是非常经典而微妙的。显然,萧红内心对聂绀驽存有好感,因而拿木杖和端木蕻良的话试探他。历史上,当时的文人圈都撮合萧红和聂绀驽,认为他们比较合适,但聂绀驽当时有家室,因而聂绀驽没有直接回答萧红,而是要她注意她在文坛上的位置,认为她与端木蕻良的名气、地位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可萧红是一个不为世俗所束缚的人,而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地位、名气不是她所考虑的,她考虑的是找一个爱她欣赏她的人,有个安静的地方过安静的日子安静地写东西,因此她在试探过聂绀驽而被委婉回避后选择了端木蕻良,也是她敢爱敢恨的表现。
端木蕻良同样是“想爱就爱”的。他在萧军和萧红还在一起的时候便欣赏萧红的才华,并产生倾慕之心,当他看到自己倾慕的女人过得并不幸福,在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拳脚之下委曲求全,终于在萧红转移而萧军选择留下打游击后向萧红伸出爱的橄榄枝,不管萧红是不是正怀着萧军的孩子。而当时萧军虽然没有选择跟萧红转移,虽然他与萧红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但彼此还是相爱的,萧军也并未彻底放弃萧红,他在萧红心里其实还是为自己留了退路的:“万一我死不了,我们再见,那时候如果我们还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因此影片中萧军知道萧红跟端木蕻良在一起后很痛苦、愤怒,萧红则很害怕萧军“闹事”,护着端木蕻良,但端木蕻良觉得爱了就爱了,没什么害怕的,敢于直接面对萧军,这是他“想爱就爱”的表现。
三、民国女性的悲剧史诗
萧红本身是女性,而且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女性,时代、男权思想、命运、性格等各种原因都是造成她悲剧的重要因素,因此影片无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一层内涵:通过萧红的命运呈现一代知识女性的命运,通过萧红的悲剧谱写了一篇女性悲剧命运的史诗。
萧红的悲剧首先是时代造成的。影片中对萧红“饥饿”的呈现,其实反讽了所谓的“黄金时代”。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便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而萧红作为女性,在男人尚且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地带,她们无法养活自己,无法独立,只能依赖男人。有部分女性,一方面被自由、解放的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想唤醒了,渴求独立、自由,但另一方面她们置身于男权话语依然占据绝对主流的社会,她们无法摆脱依赖男人的命运,因而注定了萧红这样的女性的悲剧。萧红对于男人的依赖性,与萧红自身性格有关,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时代不允许她不依赖,不允许她独立,她除了投靠一个又一个男人,除了依赖男人为她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别无选择。这是时代造成的别无选择的悲剧。
萧红的悲剧也来自她的女性身份。萧红自己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4]234“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5]407。虽然当时已经倡导自由、解放的女性思想,一部分女性已经觉醒了,但是男权思想依然很严重,男人并未完全“自由、解放”,依然大男子主义,依然像萧军一样以“伟人”自居,希望女人“听话”,遵守“三从四德”,懂得“为妻之道”,要求女子贤惠、伺夫。影片中萧红提米倒进缸里,米非常沉,萧红非常吃力,但萧军却翘着二郎腿旁若无人地坐在一边看书;萧红一直忙里忙外,萧军却未曾过来帮忙,这是一种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气质。更显示萧军大男子主义气质的是他的拳头,曾经共患难的妻子,萧军竟然拳头相向,有一次将萧红打得左眼有一块青肿,当梅志和许广平关心询问时萧红掩饰说是自己晚上不小心跌伤的,但萧军却冷笑地吼叫:“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昨天喝醉了打的!”这种连掩饰的机会和最基本的自尊都不给自己妻子的语言暴力显然更伤害萧红,让她身心疲惫,伤痕累累,以至萧红临死前发出了痛苦的心声:“我爱他,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5]407,这一句“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不知道凝结了萧红多少痛苦,承受了女性多么沉重的悲剧。而萧红嫁给端木蕻良,虽然经济条件好了,他却是个“逃跑主义”者,一遇到困难就先逃跑,推卸责任,从武汉撤退时只剩下一张船票,萧红让给他,让他先走,他就真的自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真的准备突围撤离;当他遇到战乱,遇到萧红病重,他都害怕得大哭,完全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样为萧红撑起一片可以安静生活的天空,也不是与萧红共患难,而是胆小怕事、自私虚伪,没有任何担当,只会“逃避”“开溜”。影片中的端木蕻良有点“懦夫”形象,萧红因此非常恨他。当然,在萧红的最后岁月里,端木蕻良或许是良心发现,回来给萧红转移医院,萧红动手术后他为她吸吮喉管里吐不出的痰,为他的“懦夫”形象稍微做了一些纠正。萧红的悲剧在于她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欣赏她、真心爱她、对她不离不弃的男人,这让人不由想起《寻找男子汉》中的舒欢,一直在“寻找男子汉”,却一直找不到。萧红也一直在寻找爱情,但她遇到的要么是汪恩甲一般的纨绔子弟,要么是萧军一样的大男子主义男人,要么是端木蕻良一样的“懦夫”,这便是她作为女性的悲剧。
萧红的悲剧还是命运的悲剧。她总是被命运捉弄,每次投入新的感情时都怀着上一任的孩子,让她的爱情与婚姻充满了讽刺。当然这悲剧根源的很大部分诱因是她个人性格的悲剧,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萧红倔强而又软弱,她一直在跟命运抗争,但在感情面前又不够冷静、坚定,过于轻率,不够独立,总是要去依靠男人,她就是出走后的“娜拉”,她用自己的悲剧人生回答了鲁迅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除了依赖男人,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虽然是身处“黄金时代”,萧红却一直是生活在“笼子”里,“男人的笼子”里,命运的笼子里,正如她自己所总结的:“我这个人不愿意受屈辱,可我这一生,总在别人的屋檐下……”[6]对于萧红个人而言,她拥有过一段暂时不用为经济发愁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相对于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艰难时段,是“舒适”的,但她依然能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黄金时代”的虚幻和短暂,“笼子”与“黄金时代”的对比,内中悲凉不言自明,这是萧红对自身命运的清醒认知与反观。
《黄金时代》通过萧红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展现了其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以及当时的一群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谱写了一曲引人深思的史诗,虽然在国内的票房没有比预期的高,评价没有预期的好,但真正好的影片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黄金时代》的实验性、先锋性以及其所反映的民国时代历史风云、其所建构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史诗内涵都将愈益为人们所发现、认识。
注释:
①周作人指出:“在现代乱世,青年只有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去,作个人类进化的见证;弱的退下来,叹息诅咒,以终天年”,“苟全性命于乱世”。
[1](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朱自清.那里走[A]//一般[C].1928年 第4卷3期.
[3]萧军.第二信上海——北京37年5月6日发(萧军给萧红的信)[J].新文学史料,1979(5).
[4]张韧.萧红故居思绪[A]//阎刚编.学者随笔[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季红真.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6]王小妮.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
——端木蕻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