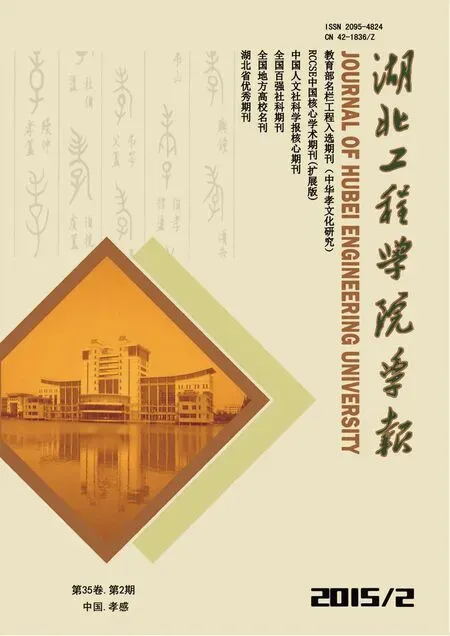神的理性与自然理性主义的重张——中世纪理性主义政治观解析
周明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神的理性与自然理性主义的重张
——中世纪理性主义政治观解析
周明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可以向前追溯到中世纪。奥古斯丁的政治观是对末世拯救一再推迟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妥协,它是带有理性色彩的;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来解释神学政治,他的政治观是自然理性主义政治的重张。正是他们孕育了近代理性主义政治的产生。
(责任编辑:张晓军)
关键词:神的理性;自然理性主义;中世纪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B503
文献标识码:码:A
文章编号:号:2095-4824(2015)02-0095-04
收稿日期:2014-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Z012)
作者简介:周明军(1975-),男,河南清丰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政治学博士。
Abstract:To be critical of the rational politic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Augustine’ s political viewpoint turned out to be one kind of Christian compromise due to the deferment of eschatological saving, and had some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quinas used the doctrine of Aristotle to clarify his theological politics and his viewpoint could be called the rebirth of natural rationalism. It was Augustine and Aquinas who gave the birth tot the modern rational politics.
二十世纪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的权威卡莱尔指出,那种关于中世纪僵化不变的观念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偏见和无知;他认为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12-13世纪那样在思想和生活的变化方面如此的迅速,所以,那种“黑暗的中世纪”的论断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读。对此,丛日云的观点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显示出鲜明的特色,从研究主题的转换到思想内容的创新等方面,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1]12并且他还认为,在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和近代自由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即前者为后者准备了思想前提,而后者则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2]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政治思想之间的距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而当代英国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的批判表明,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政治其实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对其进行批判完全可以从更早的阶段开始。因此本文将展开对中世纪政治观的考察,这里选取中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对他们政治思想的解读,本文认为,中世纪神学政治观,这样一种“追求神性的政治” 不仅含有理性的色彩,而且具备理性主义的特质,正是它们孕育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政治。
一、奥古斯丁的政治观——神的理性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并没有提到奥古斯丁,这说明黑格尔并未将奥古斯丁作为一个哲学家来看待。黑格尔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施特劳斯的继承,他认为,“奥古斯丁首先是作为一个神学家而非哲学家来从事著述活动的。他很少自称哲学家,也从不只根据理性和经验来探讨政治问题。其最高原则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圣经,他对后者的权威深信不疑,而且视之为有关人及政治事物真理的最终源泉。”[3]195从这里不难发现,奥古斯丁政治观的认识论基础是理性与信仰的对立,而且后者高于前者,即只有凭借信仰才能获得对最高真理——上帝的认识。而其政治观的理论根基则是这两点,即耶稣说的“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以及圣徒保罗在致信给罗马人时写下的《新约全书》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宣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这一理论基础又使得奥古斯丁必须重视世俗权力,这样在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他又不得不借助理性,即“就其立场的选择有赖于预先考虑这一立场的最重要的替代者而言,他需要根据独立的人类理性来认识政治哲学和政治事务”[3]195。同时,公元410年罗马城的陷落所造成的恐慌及其对基督教的质疑,基督下凡进行终极拯救的“末世审判”的一再推迟,这些问题都使得任何一个基督徒必须思考现实的政府和政治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奥古斯丁接受了历史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了将古典世俗政治哲学进行基督教化改造的任务。在本文看来,他的“双城论”毋宁说是对“末世拯救”一再推迟的一种基督教意义上的妥协,因此理性在奥古斯丁这里是占据一定分量的,也因此他的政治观本文称为“神的理性”。
奥古斯丁政治观的理论来源是《上帝之城》第19卷第15章中的关键性论述,虽然上帝创造了人,但“他没有打算让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理性动物统治非理性动物以外的东西,不是人统治人,而是人统治动物。因此,第一个义人被立为牧羊人,而不是人的国王”[4]。根据这一论述,卡莱尔和马库斯构建了二十世纪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研究的一大经典的范式。概括起来,这一范式主要有三个论点构成:第一,奥古斯丁认为政治秩序起源于人类自身的罪过,其存在是违背人类自然本性的;第二,他认为国家的作用是在尘世中惩罚和救治有罪的人类,而不是通过道德教化来使人向善;第三,他将国家这一世俗权力看成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并承认它在尘世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性。[5]
具体地讲,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在这一宇宙中各个事物各安其位,对它们来说这就是“善”的意义。可是组成宇宙的事物中总有一些不安分的种类存在,即天使和人,他们总想脱离固有的位置而疏远上帝。就人来说,由于人类始祖的原罪,由于骄傲,他们脱离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不仅使人类疏远了上帝,还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疏远。针对这样的行为,上帝不仅要实施惩罚,还要实施恩典,并最终使人类得救以进入天国。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他认为人类的生存状况先后经历了乐园、尘世与天国这三个过程,在乐园阶段人性并未堕落,之后由于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人类被逐出乐园进入尘世,但这一阶段是暂时的,上帝通过实施惩罚和恩典最终会让人类走向天国。对应这三大阶段,奥古斯丁的“双城论”也随之出炉了,所谓对上帝的爱构成了天上之城,对自己的爱构成了地上之城。但是这两座城是浑然一体的,人间的教会与国家只能是它们的代表,并非它们真正的落实。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纠正人类对上帝的疏远,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纠正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最终会导致人类在竞争和斗争中的自我毁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是高于世俗权威的,因为它是和上帝相接的。在丛日云看来,这样的国家观的逻辑结论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它所极力强调的就是国家的根本局限性,这其实就是说任何国家都难以摆脱暂时意义之上的“地上之城”的性质。[2]171-192
另外,关于奥古斯丁研究,还应注意“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古希腊的城邦已成为历史,罗马城也已经沦陷,可是奥古斯丁依然沿用了“城”这一概念,他依然习惯于以“城”的形式来看待政治社会,这说明了在当时的文化传统中,“城”依然被视为社会的基本构造和单元。罗明嘉通过考察《上帝之城》中“城”的概念指出,“城”是人类的一种理性的联合,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屡次使用的就是这个意义。而《上帝之城》这部巨著的题目本身就表达了其关键观点——“城”,是一个社会概念,奥古斯丁通过这部著作要传达的正是其关于社会生活的神学构思,“社会生活的理念,是奥古斯丁在这部著作中的一个经纬性原则,并非处于其思想的边缘,而恰是处于其晚期思想的核心”[6]。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奥古斯丁的政治观是带有理性色彩的,如果再加上前边的分析,即他的“双城论”是对末世拯救一再推迟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妥协,则他的政治观的理性色彩就更为突出了。然而真正完成认识论上信仰和理性并立,并在合理性上论述了世俗政权的是奥古斯丁去世后八百年的阿奎那。
二、阿奎那的政治观——自然理性主义的重张
对于阿奎那,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几乎是一笔带过,但是他的做法并未得到继承,比如梯利和罗素,他们就分别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阿奎那,而现在已有更多的研究证明阿奎那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作为一个神学家的地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认识论上讲阿奎那充分肯定了理性的地位,并将理性和信仰给予了平等的对待,也因此在其政治观里教权和世俗的政权之间是可以并存、且没有实质性冲突的。阿奎那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论,最主要的原因是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革命”,对此萨拜因认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对西欧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为过的。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把希腊知识生活的新视界带给了中世纪,并且使得中世纪的人们相信,理性是一把一定能够打开认识自然世界大门的钥匙。”[7]但是,在所有的中世纪思想家当中,对亚里士多德研究最深的只有阿奎那,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像阿奎那那样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概念。
在认识论上,阿奎那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突出理性的地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主要体现在其《神学大全》第十二题:论我们怎样认知天主,第十四题:论天主的知识,以及第十六题:论真理,这三篇文本中;[8]第二,来自于对奥古斯丁“原罪论”的修正。首先,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依然强调《圣经》是智慧的最高源泉,因为它最好地反射了神性的光芒,但神性之光也可以通过理性来闪耀,因此他便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他看来启示和理性同样能够成为真理的源泉。阿奎那认为,理性能力是以人的本质或者本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从感觉出发,通过理性我们能够把握世界上的事物的本性或本质。但是人的理性在实践上是有局限的,不过阿奎那认为我们不必对这样的局限过于心烦,这正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因为这样的局限并没有严重地影响我们过一种美好生活的能力。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理性的局限确实将带来很大的困难,阿奎那认为,这正是涉及上帝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依靠信仰和启示的力量,他说,“即使在关于上帝的真理能被人的理性所发现的情况下,人也需要神启的指引,这是必需的;因为理性所研究的关于上帝的真理只会被少数人获取,(这种获取)需经很长时间,并且有很多错误。”[9]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在阿奎那这里,他赋予了信仰和理性同样的地位,这两者在发现真理上是能够相容的,这就改变了奥古斯丁的理性服从信仰的观念。
其次,针对奥古斯丁的“原罪论”,阿奎那也做出了修正。具体来看,阿奎那是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或“本性”观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要取消本性,而是使本性更加完美。连同这个认识一道,阿奎那认为原罪并没有导致人的本性彻底堕落,而是使人的本性受到了伤害,这样的伤害并没有使人丧失理性的能力,在这样的能力下,无需神恩的介入,人也能在现世过美好的生活。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仅靠理性人类就能最终实现“末世拯救”、进入天堂,因为后者需要信仰和神启。这样最终我们看到,阿奎那在认识论上就完成了打通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任务,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而这样的一项工作绝不像罗素说的那样轻松,“阿奎那的独创性表现于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稍加改篡用来适应基督教教义一事上”[10]。
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之上,阿奎那论述了自己的政治观。当然,其政治观的理论基础依然来自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即阿奎那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和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描绘的基督教政体思想。首先,在政治秩序即国家的起源上,他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生成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阿奎那则指出,“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合群的生活。”[11]44因此,人就自然地会和同类一起分工协作以更好地满足生活的需要,由此他们便组成了社会。但由于人类本性的自私,每个人在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情形下必然会和他人之间发生矛盾甚至争斗,因此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和更好地分工协作,就需要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国家便由此产生。其次,在国家的目的上,阿奎那同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即认为国家是人类至善的社会团体,目的是谋取社会共同幸福,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只是在阿奎那看来,所谓的幸福生活不仅是物质的,还要包括更重要的精神层面,“人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政治社会不仅帮助他取得由一个国家的许多不同工业生产的这样一些物质福利,而且也帮助他求得精神上的幸福。”[11]156而对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来说,虽然世俗国家应该指导人们趋向这个目的,但这一目的的真正实现只能依靠上帝的引导。最后,在政体思想上,阿奎那近乎照搬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阿奎那将“公利”和“私利”作为区分政体正义与否的标志,然后他也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寡划分出了六种政体,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谓正态与变态政体的划分如出一辙。而在合乎正义的政体中,阿奎那认同的是君主制,他认为由一人来掌握政权不会产生利害冲突和意见的纠纷,从而也就避免了统治者内部的互相倾轧和纷争,他说“凡是本身是个统一体的事物,总能比多样体更容易产生统一,所以由一个人掌权的政府比那种由许多人掌权的政府更容易获得成功……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人所掌握的政体”[11]48-49。这不仅符合理性,也是最符合上帝意志的。
同时还必须看到,在论述世俗政治秩序的同时,阿奎那也论述了教会和教会秩序,即所谓的教权。在阿奎那看来,和世俗的政治秩序不同,教会不是属于“本性”或“自然”的秩序,它是属于“恩典”的秩序。因此教会的职责便和国家是不同的,它关注的不是人类的一般幸福,而是终极拯救,它的权威直接来自于上帝,它也是一个有其自身正符合法律的组织,但它的权力和世俗的国家权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说教会就肯定有高于国家的权力。因此,在阿奎那这里,教权和俗权就成了并立的了,它们之间各有其自身的活动范围,各有自己的职责要履行。而如果非要说教会的权威高于世俗政府的话,那也只是在以下这个意义上讲的:它关注的是一个更高级别的问题,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人类才能实现最终的救赎。这就是说,阿奎那是在坚持了理性和信仰同等地位的基础上,论述了关于教权的思想。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说,阿奎那的政治观是具备理性主义特质的。
三、结论
基于以上对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政治观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奥古斯丁的政治观只是带有理性色彩的话,那么阿奎那的政治观则是具有理性主义的特色了。尤其是对于阿奎那而言,由于他将一种“全新”的政治学说成功嫁接到了神学政治观之上,因此,“他的许多结论,标志着从基督教思想到理性主义的转变,也就是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1]303。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世纪的政治观孕育了近代理性主义政治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2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册[M].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4]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28.
[5]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5.
[6]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话[M].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
[7]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邓正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97.
[8]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册[M].高旭东,译.台北:中华道明会,碧月学社,2008.
[9]凯利·克拉克.托马斯·阿奎那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61.
[11]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God’ s Ration and the Rebirth of Natural Rationalism: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Rationalism in Middle Ages
Zhou Mingjun
(Departmentof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ZhengzhouInstituteof
AeronauticalIndustryManagement,Zhengzhou,Henan450015,China)
Key Words: God’ s ration; natural rationalism; medieval political view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