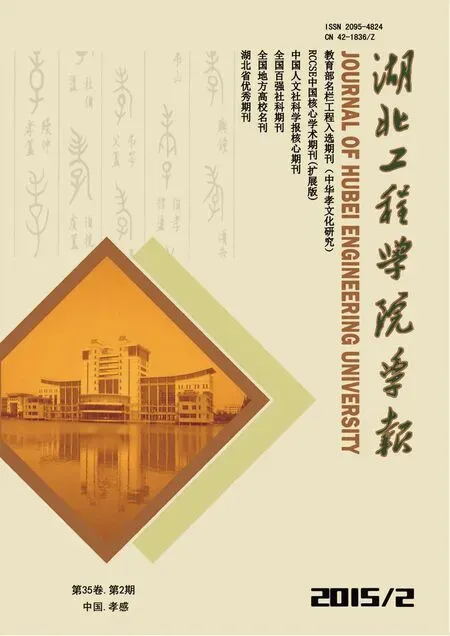梁启超情感论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
梁启超情感论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
摘要:梁启超秉持心学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循着“境者心造”的逻辑对创造世界的情感推崇备至。为此,他一面宣称情感高于理性,一面借助宗教激发人的热度情感。与此同时,梁启超重视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由此应运而生。对情感的推崇和论证构成了梁启超心学的主要内容,也使梁启超的心学具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独特意蕴。
(责任编辑:祝春娥)
关键词:梁启超;情感;情感说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码:A
文章编号:号:2095-4824(2015)02-0038-06
收稿日期:2014-12-21
作者简介:魏义霞(1965-),女,安徽濉溪人,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Abstract:Liang Qichao maintained the thinking direction and value pursu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regarded human emotions as the supreme factor of creating the world, following the logic of “circumstances being made by mind” . Hence he declared that emotion was higher than rational and also stimulated people's passionate emotions with the help of religions. Meanwhile Liang Qichao paid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oetry revolution” and “novel revolution” emerged accordingly. Admi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for emotions constituted the main contents of Liang Qichao’ s theory of mind so that it had its ow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implications.
梁启超断言“境者心造”,坚信世界、历史都是由人之心力创造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心力是宇宙间最神奇、最权威的存在,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力量。由于确信创造世界的心力是情感而非理性,梁启超由推崇心力转向推崇情感;并在情感高于理性的论证中,建构了中国近代心学中情感派的哲学形态。
一、对情感的诠释
是什么决定了人的行为,并且通过人之行为,最终创造了世界?换言之,创造世界和历史的心、心力究竟是什么?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中,梁启超沿着唯意志论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将情感、意志说成是人之行为的真正主宰。这使心力创造世界随之转换成情感创造世界,情感也随之成为最权威、最伟大的力量。
梁启超专门探讨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明确指出情感高于理性,具有超越理性的品格,更拥有理性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并借此将情感说成是决定人之行为的真正主宰,奉为创造宇宙的决定力量。按照他的说法,人的行为都是从所好、所安等情感中发生出来的。这表明,人的行为受制于情感,而与理性无关:“人生不过无量数的个人各各从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里动。所好所安,就是各个人从感情发出来的信仰。各人的所好所安,谁合理、谁不合理,那样有效率、那样没有效率,绝不是拿算学的公式、物理学的眼光所能判断。”[1]3968这就是说,人生绝非固定、呆板或僵化的,人的行为皆靠从所好、所安中发生出来的信仰来操控,究其极是个情感问题。事实上,人们做什么事全凭信仰,靠的是情感的支配。正因为如此,情感才是人之行为的主宰,一切皆与理性无关,因而不能拿数学的或物理学的眼光来判断。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进而强调,支配人之行为的情感带有神秘性,并非理性可以控制或分析的——行为人不知其所以然,旁人看来越发百思不得其解。对此,他论证并分析说,情感具有理性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权威性,如果说情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皇帝的话,那么,理性则是情感的臣仆,一切听从情感的指挥。既然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如此,结论便不言而喻:对于人的行为来说,情感是主宰,理性对之无能为力——不仅无法控制,而且无力判断。这是因为,情感这种东西带有神秘性,任何人要想用理性来解剖它,都是不可能的。秘密在于:凡是有信仰的人,对于他所信仰的事,总含有几分呆气,仿佛是鬼使神差一般如痴如醉、如癫如狂而不能自已——自己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发莫名其妙。别人要把他的信仰对象对他条分缕析地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除非他本人已经把他信仰的东西抛弃了,不然的话,任凭别人说得唇焦口敝也是无用。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梁启超举例子解释说,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位俊男爱恋一位丑女,便觉得这位丑女是天下第一美女,任你黄金分割律、美人标准,在这位恋爱中的俊男那里全不适用。有一天这位俊男变心了,才会突然发现自己眼中的第一大美女原来是一位丑女。这个例子的哲学意义在于,理性绝对不能变易情感,只有情感才能变易情感。分析至此,梁启超总结说:理性对于人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既无力促使它,也无力阻挠它;理性不能支配人的行动,真正操纵和支配人之行为的只有情感。既然如此,为了促使人的某种行为,唯一的办法便是激发某种情感。
在梁启超的视界中,情感与理性完全是两码事,由于情感的神秘性,理性无法对情感进行分析或解释,更无法对发之于情感的行为加以阻挠或推进。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理性的作用充其量只是阐明道理,判定某事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应该这样做还是应该那样做。然而,理性所讲的“应该”又总带有“遗憾”和责备的味道,因为理性最终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决定人之行为的是理性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剖析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须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该做、某件事该怎样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们既承认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对于情感这样东西十分尊重。”[1]3968
梁启超的上述论证凸显了理性的苍白无力,也证明了理性在情感面前的相形见绌。一言以蔽之,理性并不能控制人的行为,也不能对情感进行分析和判断。比如说,所好所安等情感决定了人的行为,那么,每个人的所好、所安究竟孰是孰非?谁的合理、谁的不合理?哪种有效率、哪种没有效率?这同样是一个情感问题,属于信仰领域,绝非可以诉诸理性的。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对情感寄予厚望,声称只有情感炽热、爱恋专凝才能行为果断,毅然决然,于是置生死于不顾,排除一切利弊得失而勇于进取冒险,最终成就“顶天立地的大事业”;古今中外一切英雄豪杰所以会做出震惊寰宇的壮举,秘密就在于,他们的情感达到了白热度,因而能够所向披靡,行信于天下。
进而言之,梁启超所推崇的不受理性控制、并且主宰人之行动的情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在这方面,他将王守仁所讲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相提并论,用以证明人的自由意志与生俱来;并在此基础上借助自由意志,号召人们破除心中之奴隶,做具有怀疑精神、敢于进取冒险的“新民”。
梁启超宣扬自由意志的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全新人格,而且在于将人之自由运用于历史领域,借此揭示历史进化的动力。可以看到,在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中,梁启超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无限夸大,进而否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客观规律(梁启超称之为“因果必然法则”)的制约。为此,他不惜否认了一贯推崇的因果律,以便将一切都交给人的自由意志。梁启超断言:“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费心了!”[2]4155-4156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因果律等于必然律,自由意志则是偶然的同义语;这便意味着因果律与自由意志相互抵触,人们对之只能取一弃一。在这种情况下,他认定社会、历史是由人之自由意志创造的,由人之自由意志创造的世界、历史是不受因果法则支配的。更有甚者,由于坚信历史是人之自由意志的创造品,梁启超反对在历史研究中求因果,甚至反对用归纳法求“共相”。
二、对情感的激发
基于对情感与理性的比较,梁启超得出结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他写道:“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3]3921这就是说,情感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富有情感是人充满生命活力的表现。沿着这个逻辑,梁启超指出,那些可爱而不知爱、可哀而不知哀、可怒而不知怒、可危而不知危的人由于情感麻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人性。
既然情感是人之本性的一部分,并且决定了人的行为和创造,那么,情感对于人来说,便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葆有情感,情感至诚、炽热是人创造的源泉,也是生命活力的体现,乃至是最佳的生命状态。有鉴于此,如何激发情感,使人充满生命活力成为梁启超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秸秆直燃发电厂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的同时,我国秸秆直燃发电装机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单机装机规模已从早期的12MW逐步发展到30~50MW机组。已投入运营的项目中应用较多的为30MW的机组,约占总投产项目的53%。
按照梁启超的理解,情感高于理性,并且究其极是个信仰问题。既然理性对情感无能为力,那么,只好另谋他途,以信仰激发、引导或控制情感。沿着这个思路,他由推崇情感而推崇信仰。综观其思想可以发现,梁启超一面强调情感与理性无关,一面将情感与信仰联系起来,进而归结为宗教。他这样做与对宗教的理解密切相关,更与他企图以宗教般的狂热来激发人之心力、情感的理论初衷息息相通。沿着心学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梁启超侧重从心、精神的角度来界定和理解宗教,断言白热度情感就是宗教。他声称:“情感结晶,便是宗教化。一个人做按部就班的事,或是一件事已经做下去的时候,其间固然容得许多理性作用;若是发心着手做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业,那时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仆的地位,情感烧到白热度,事业才会做出来。那时候若用逻辑方法,多归纳几下,多演绎几下,那么,只好不做罢了。人类所以进化,就只靠这种白热度情感发生出来的事业。这种白热度情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宗教。”[1]3968心学旨趣和对情感的执著使梁启超将宗教限定在情感、信仰的范围内,而轻视宗教的教仪教轨等外在或强制方面的因素。更有甚者,他给宗教所下的定义是“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将宗教完全归结为信仰。对于这个定义,梁启超逐项进行了界定:所谓“对象”,意思是说,凡为某人信仰所寄托者,便成为这个人的宗教对象。据此,梁启超将宗教泛化,断言宗教的“对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所谓“信仰”,是宗教的灵魂所在;宗教语境中的“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1]3966。梁启超强调,抓住了这两种特征,也就理解了信仰对于宗教的意义。因此,信仰的这两种特征是解读梁启超宗教观的钥匙和关键,对于梁启超所讲的宗教极为重要:第一,由于将信仰界定为“情感的产物”而非“理性的产物”,梁启超视界中的宗教具有了不受理性控制的情感的功能和作用。第二,信仰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既彰显了宗教的至上价值和权威,又印证了情感的至上价值和权威,指向了膜拜情感、讴歌情感的价值诉求和人生旨趣。所谓“各个人”,意思是说,“信仰是一个一个人不同的,虽夫妇父子之间,也不能相喻。因为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强”[1]3966-3967。这就是说,宗教是完全个人化的情感体验,既然是私秘而神圣的,也就是他人无权干涉——当然也无力强求的。可见,在梁启超的界定中,宗教便意味着绝对信仰。这样一来,由于宗教崇拜,或者说,出于宗教狂热,人皈依宗教,便有了绝对信仰;由于有了绝对信仰,人便拥有了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从而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地为了信仰的对象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表明,宗教是激发人之热度情感的不二法门,也是点燃人之激情的灵丹妙药。由此反观梁启超的宗教定义可以发现,他提倡宗教,就是为了借助信仰的绝对权威,激发人的热度情感。
鉴于情感、信仰与宗教的密切相关,梁启超由尊重信仰进而倚重宗教,试图凭借宗教控制、激发人的白热度情感。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论证上,与当初一再强调情感不受理性控制,从而彰显情感的神秘、神圣和神奇类似,梁启超突出宗教与哲学的区别,指出哲学是阐明道理的,偏重理性。因此,如果信凭哲学,则会让人在瞻前顾后的权衡和计较得失的算计中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表明,在治事方面,哲学家不如宗教家,哲学家只能空谈道理,宗教家则长于治事:“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其两思想并无之人虽尤多,然仅恃哲学以任者则殆绝也)。”[4]762分析至此,结论不言而喻:宗教是培养英雄的精神鼓动剂,英雄豪杰中有宗教思想之人多;哲学则使人精于算计,攻于功利,一事无成。因此,成就大业者有哲学思想之人少;即使有哲学思想,其英雄壮举也非出于哲学而是出于宗教。在这方面,无论是近代英国的缔造者——克伦威尔(梁启超称之为克林威尔)、引领日本明治维新的诸领袖,还是唤起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康有为、谭嗣同都是如此。
上述内容显示,梁启超一面夸大宗教的作用,一面贬低哲学的作用,目的只有一个:让人彻底摈弃理性,撇开功利,完全信凭宗教般狂热即他所膜拜的白热度情感来治事救世。因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人才能够不顾生死荣辱,不计利害得失,勇猛无畏,蹈死如饴。至此,梁启超一步步由对心力、情感、信仰的推崇,最终落实到对宗教的虔诚和狂热。他之所以寄希望于宗教,便是为了以宗教般的虔诚激发人的信仰,鼓动大无畏的救世精神和担当。
三、对情感的抒发
鉴于情感的神圣性和重要性,梁启超对待情感的基本原则和态度不是压制、压抑,而是释放、激发和表达。这是因为,“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3]3921-3922有鉴于此,他不仅在意情感的激发和至诚,而且关注情感的抒发和表达。于是,讴歌情感的伟大,激发、抒发情感成为梁启超一生的执著追求。他发起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均出于更好地抒发、表达人之情感这一初衷。
1899年冬,梁启超在赴夏威夷的海途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他之所以大声疾呼“诗界革命”,具有以诗歌来表达人之情感的强烈意图。梁启超作《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面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表达方面的资源,一面寻求表达情感的最佳方式。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他将中国韵文的发端说成是歌谣,对歌谣抒发情感的作用赞不绝口——不仅将歌谣说成是韵文的发端,突出歌谣对中国美文的引领作用,而且直接将之视为诗的“前驱”。好的歌谣感人之深有时可以驾于专门诗家之上,魅力在于:由于“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能够“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歌谣这种超越功利、不为流传而只为抒发情感的初衷恰恰使其成为最直接、最朴素的情感宣泄和表述,所以才有出奇的感人效果。这是歌谣的魅力所在,也是其胜于诗的秘密所在。与歌谣随一时情感尽量发泄不同,诗有“固定的字数、句法和调法”,难免词胜于意,有意无意间限制了情感的表达和发泄。鉴于歌谣表达情感的率直、自然和酣畅淋漓,梁启超强调:“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5]4339
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梁启超尤其对小说情有独钟。因此,继“诗界革命”之后,他发起了“小说界革命”。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申明“小说界革命”的宗旨是创作新小说,并将新小说提到了新民第一要务的高度。对此,他在文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6]884在这里,梁启超一口气提出了七个证明,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文艺、新人心和新人格,必须先新小说,难怪新小说成为新民“不可不”先新者。这使新小说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必要性,也使“小说界革命”势在必行。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小说何以具有如此力量、如此魔力?梁启超给出的说法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那么,梁启超所讲的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究竟指什么呢?
依据梁启超的剖析,小说的魅力是必然的,其秘密武器则在于以情动人,这一点与人之本性相契合。既然人的一切行为均受情感支配,而情感不受理性控制或哲学算计,那么,对于人只能以情感变易情感。这使小说在感人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由于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小说“感人之深,莫此为甚”。通过熏、浸、刺、提四种方式和力量,小说让读者对于书中的描写犹如置身其中,感同身受,从而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悲喜,共命运,产生巨大的心理共鸣和情感共鸣。这便是小说的魅力和奥秘所在。一言以蔽之,小说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之所以能够达到动人的效果,是因为小说以情动情。小说的这种感染力决不是采取说教的方式所能达到的,更非强制所能奏效的。这用梁启超的话说便是:“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6]885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除了出于“新民”的需要之外,梁启超对小说的钟爱,还有以小说抒发情感的初衷。事实上,正是由于将小说视为抒发、表达情感的利器,梁启超才奉小说为以情感人、启蒙民众的法宝。换言之,在梁启超的视界中,小说之所以能够达到“新民”的目的,在于小说的表达方式是以情感人。以情感人既是小说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性质,也是小说优越于其他文体的巨大魅力。基于对小说的这种认识,梁启超对小说十分重视,“小说界革命”应运而生。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小说的作用,他一面亲自创作小说,引领新小说的创作;一面在自己主办的报纸、杂志上大量刊载小说,提升小说的地位。当然,与对小说性质和作用的认定相一致,梁启超这样做既是“新民”、启蒙大众的需要,又是利用小说抒发、引导大众的情感,培养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的需要。
四、梁启超情感说的独特意蕴
情感说是梁启超心学的主体内容,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情感派的典型代表。梁启超的情感学说具有浓郁的中学渊源,他推崇的杨朱按照他的理解就是重情的代表。更主要的是,中国近代的重情思潮滥觞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接续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重情传统。梁启超对戴震的推崇与情感密不可分,在他的眼中,戴震哲学作为中国情感哲学的典型就是名副其实的“情感哲学”。由此,梁启超将戴震的哲学称为“重情主义”:“《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7]38-39由此可见,正是在戴震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中发现了戴震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的秘密,梁启超才对戴震推崇有加——在将《孟子字义疏证》誉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的同时,从情感入手解读戴震的思想;在将“情感哲学”视为戴震哲学立脚点的前提下,揭示戴震对宋明理学道德形上学的反动,肯定戴震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与此同时,梁启超对情感的诠释容纳了西方哲学的思想元素,特别是借鉴了唯意志论关于情感高于理性的思想。这使梁启超成为最早在哲学领域阐发唯意志论的戊戌启蒙思想家。
唯意志论是指用情感、意志或自然倾向等非理性因素解释世界的哲学派别。因此,对情感进行深入剖析且对情感推崇备至的非唯意志论莫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对情感的膜拜,梁启超对唯意志论乐此不疲。尽管如此,梁启超并不是唯一推崇、阐释唯意志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王国维、章炳麟和蔡元培等人都对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津津乐道。必须提及的是,他们对唯意志论的诠释各有侧重,彼此之间迥然相异,故而不可同日而语。王国维将唯意志论运用到文学评论之中,对《红楼梦》的研究便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章炳麟的哲学具有唯意志论色彩,总的说来,他主要是用唯意志论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在早期宣称、拥护进化论阶段,章炳麟将唯意志论所推崇的意志(“志”)与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相结合,进而说成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8]102在后期质疑进化、鼓吹俱分进化阶段,他同样以意志来解释进化,《俱分进化论》一文多次出现叔本华(章炳麟译为索宾霍尔)足以证明此时的章炳麟对进化的态度与对唯意志论大家——叔本华的推崇密不可分。蔡元培则将唯意志论运用到教育之中,试图通过美育(即美感教育)来美化意志,进而美化世界。梁启超在本体领域强调情感高于理性,并将唯意志论与康德等人的自由意志、倭铿(今译奥伊肯)的生命哲学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意识流等诸多思想相杂糅,进而推崇情感,讴歌意志自由、精神自由。与对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推崇一脉相承,梁启超在教育中提倡情育(情感教育)和意育,试图通过陶冶情操,培养兴趣,推行乐观主义、快乐主义,使人快乐无忧,无所畏惧,享有美好快乐的人生。不难看出,王国维、章炳麟、梁启超和蔡元培四个人对唯意志论进行了不同的阐发,致使唯意志论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拥有了不同的领地和样式。无论是从情感高于理性推出激发热度情感、积极创造的乐观、进取精神,还是将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与康德、柏格森和倭铿的思想相和合都彰显了梁启超情感说的独特意蕴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M]//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M]//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M]//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M]//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梁启超全集: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章炳麟.原变[M]//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Liang Qichao’s Emotion Theory
Wei Yixia
(ResearchCenterofChineseModernThinkingandCul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80,China)
Key Words:Liang Qichao; emotion; emotion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