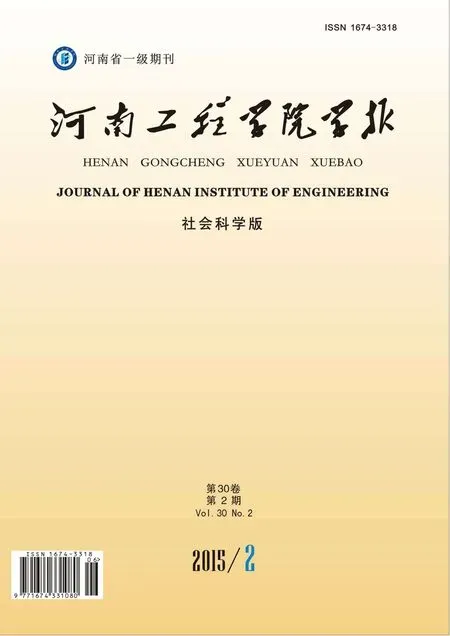论消费文化范式下张爱玲文本的电视剧改编
杨 曙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在消费社会环境下,很多名家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这样说道:“艺术品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的价值。”[1]张爱玲的小说是文学经典,在消费文化时代,很自然被导演们直接拿来并改写,在改写以后,也就产生了一定的文艺场,本文关注的就是这个文艺场。
一、张爱玲文本的原初商业语境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十分明显的消费主义时代,并带有很强的消费主义文化特征,消费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已经具备了话语权。消费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穿,而是刺激与制造欲望,并不断满足欲望。不管是基本的生活物质还是文化产品都会被这种消费气息所感染,传播媒介会大肆利用这种气息并制造强大的欲望。早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就因为其开放,娱乐、金钱、欲望等现代消费主题一开始就绑定在电影中,不管是纯文学还是纯音乐纯绘画,都或多或少沾染到大众文化的消费气息。就实际的文化场来看,大众文化与商业的密不可分也为不少当时的海派商业文人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和作品原初的本质,当他们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合谋者时,他们能完全利用大众媒介的攻势,与充满现代性的上海十里洋场大众文化融合,使得原本高高在上的雅文学出现雅俗交汇的状态。“沦陷区的作家大部分必须以稿费和版税为生,读者的反应对于他们而言即是生计的来源,米珠薪桂是任怎样超然的人也不可能超脱的现实。”[2]通俗文学从来都面向大众,没有受众也就没有文学的欣赏,文学是否有受众也就成为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尺。旧上海印刷业的发达,也使文学具备了较强的商业属性,张爱玲的文本从一诞生就进入强大的流通领域,也成为她个人谋生的工具。
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两年,自从她在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后,又连续在《万象》《天地》《古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在这两年里,张爱玲不仅发表作品的速度加快,而且密度很高,其主要作品充斥着男女婚姻,主要人物存在的价值也是为了情欲。表现情欲的作品往往流于世俗,不管是何种性别与国籍都乐于赏鉴。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的这种批量生产不仅表现在她总量的批量生产,连同她自身的作品也存在着复制性,她的一些作品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如《十八春》和《半生缘》、《金锁记》和《怨女》、《小儿女》和《哀乐中年》,这些作品主题都是差不多的;《有女同车》和《等》都是在表现女人念叨的总是男人,女人所议论的也是男人;《道路以目》和《色·戒》都是表现封锁中的情感;《私语》和《童言无忌》中的自传回忆又出现在《茉莉香片》和《十八春》中。这种文学复制性带有很强的消费意识形态性,这是张爱玲消费意识写作的明显表征,因其感受到某种叙事模式带来的神奇商业魅力,才会将这种模式继续使用。在她的笔下,商业与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交互体,让商业文化成为生产领域的重要调料。大众文化学者费斯克认为,不少大众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在与大众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大众文化的文本就是“大众文化产品同大众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大众日常经验的相关性”[3]。文学文本的消费性被二度移植到电视文本,而且把张爱玲原先诉说的家长里短表现得更加凡俗化,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与灯红酒绿得到更加普泛化的表现。“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decontexualized),在这一过程中,内容失去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aura)。”[4]
二、当代电视传媒与原初文本的合谋和消解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张爱玲的文本消费更加深入大众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大众文化水准的参差不齐,在传媒的炒作下,文学消费开始走向欲望化,大众传媒将自身的关注热点集中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方面。虽然当今的受众和20世纪40年代的受众存在很大的区别,但他们都热衷消费的本质是一样的。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影视文本,都体现了“大众文化产品同大众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大众日常经验的相关性”[3]。
与传统文字相比,影视手段往往比较直观,且具感染力和震撼力,因此,在消费社会极具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与张爱玲文本本身具备的原始消费属性产生了合谋。大众传媒在内容传播方面,较之传统的文字更能表现人的欲望。正如南帆所言:“影像撤去了文字形成的屏障;影像的空间逻辑令人感到,欲望的对象与自己同在。这极大地诱导了自居心理的发生:人们将自己想象为欲望周围的一个角色,甚至朦胧地构想自己与欲望对象的种种生动情节。”[5]从受众角度而言,影视改编给大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愉悦,人们不用读书便可进行观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了娱乐需要,必然想获得自身的快感。从大众传媒角度而言,传媒机构往往有巨大的经济压力,传媒被逼迫着在“生产—消费”模式下进行运转,使用富于商业性的文本进行影视作品改编往往也有着更高的收视率。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和20世纪40年代毕竟有着较大的文化消费差异。在一定意义上,电视文本在挑剔的受众和高压力的收视率下,会削弱原著的思想深度,更多体现出一种趣味性,表现为一种直观快感。正如安德烈·勒文孙所言:“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中,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6]电视中审美会出现与原著的背离,从观众的角度去把握电视细节,电视中往往会出现一种“匮乏与拯救”[6],也就是说,电视作品中会表现一种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匮乏的品质,转而由影像中的人物来完成这种品质,包括对爱情的忠贞、对理想的追求、对友情的负责,人们在电视中所追求的人物形象往往是至善至美的,这种完美形象完全是人们日常审美中的追求,因为人们日常缺乏,所以他们会在电视中寻求表现,以此来完成一定意义上的人生救赎。
原初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并不是人们日常审美中的完人,她平日写作就是打破传奇,解构完人。她的笔下从来没有英雄,全是世俗男女,带有种种人性的缺陷,这些人物钩心斗角、自私、胆怯,这些有着琐屑缺点的小人物,才是时代的真正代表人物。王佳芝、许小寒、曹七巧、范柳原、白流苏、葛薇龙……这些一个又一个树立在经典文学之林的人物形象并不是高大全,而是个个充满着人性的缺点,张爱玲一定要揭开每个小人物的面纱,直接从本质上揪出那真实的卑微和缺陷。
原著中的《倾城之恋》实际上讲述了一个自私女人白流苏和一个自私男人范柳原的结合。白流苏虽然外貌很好,但是本人十分工于心计,她在娘家败落和积蓄被哥嫂盘剥的情况下,就只想着依靠嫁人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找范柳原就是觉得范柳原既能给她带来收入又能给她带来面子。正如文中白流苏所言:“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7]239在这样赌博式的婚姻支配下,她自然和范柳原就没有什么感情。“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7]2552009年上演的电视剧《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却一扫那种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弱点,端庄大方,善良聪慧,对范柳原情深意切,对哥嫂忍让妥协,在战争中顽强、勇敢、有爱心,简直就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找不到任何人性缺点。小说中的宝络,是白流苏的妹妹,是个随波逐流式的人物,在哥嫂的离间下,她认为白流苏夺她所爱,与白流苏直接断掉姐妹情谊。在电视剧中,宝络是非常有主见的女子,她总是支持白流苏,和白流苏感情非同一般,战争爆发后,宝络完全接受革命的洗礼,成为一个坚强的女子。虽然这样的改动更加符合观众的期望,但是原先文本的文学张力缺失了很多,文本的主题被颠覆掉,而且文学的审美价值被削弱了很多,这种人物刻画手法是不符合现代文学的人物塑造原则的。
电视剧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造是不善表现人物丰富的心理活动的,但经典名作都善于表现人物细致的心理活动,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十分仔细。电视剧不可能表现出人的心理活动,心理描写必须依靠人物的言语及行动表现出来,如果表现不好,则会被原先文本中的心理描写局限住。张爱玲的开山名作《金锁记》,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人物形象,她原本是个有姿色的普通女孩,健康又泼辣,她以自己的爱情为代价和一个残废的少爷结婚,几十年后,她拥有了丰厚的家产,此时她心理却压抑到极点并引起心理变态,她折磨自己的儿媳,和自己儿子暧昧,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完全成了一个感情畸形的怪胎。这些心理变化过程在小说中表现得细致入微。《金锁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极高的原因之一即为该小说把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极致,人物的变态心理被十分细致地镂刻出来,一系列毒辣的心理活动让读者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感觉,这些是电视剧无法表达的。电视剧是极其通俗化的,2002年由穆德远导演的电视剧《金锁记》中,曹七巧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最后带着一颗释怀的心离世。电视剧中人物性格的艺术感染力显然大不如小说,悲剧性被降低了很多,电视剧完全是站在一种极为通俗化的角度来进行制作的,适合大众的口味,但是削弱了原著的心理描写所带来的艺术渗透力。
三、电视消费语境中的经典削弱
存在于张爱玲作品电视剧改编的大众文化,令受众感到兴奋的是改编中的符号,这种符号的存在,导致经典意义的改变。电视剧在不断地生产各种符号,受众的快感体验也在不断更新。当电视剧对经典进行再造,受众和张爱玲经典作品也就构成了不断消费的关系。媒介不断对张爱玲经典作品进行改造,大众文化符号在生产领域是一种文化消费的形态,具有很强的潜力。文化学家威廉斯曾经这样写道:“新的技术具有经济关系,其实际作用因而带有极端复杂的社会性。技术的改变必然使资本的总额与集中程度大为增加,从报纸和电视的经营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种增加的曲线至今仍然在上升。”[8]威廉斯一语道出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生产模式,为了大众的消费而去进行大众的生产,甚至将经典意义削弱,这种经典意义削弱实际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电视剧的观看行为长久以来被认为带有强烈的消费化特点。在这样的日常活动中,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逐渐养成,并去重塑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取向,经典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质变,成为日常生活审美。经典的美学变革也暗示了美学所包含的人生态度的一场转换,依靠消费对日常人生状态的呼唤而成为人类日常存在的一种新式坐标。曾经一度有知识分子幻想能把所有的精英文化对普通大众进行开放和启发,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大众文化的喧嚣形成了一定的反差,知识分子原先主张的一种贵族式的理想已经变得非常荒诞,因为审美日常化已经成为当今美学的重要主题,类似张爱玲的文本只有经过当代重塑才能实现受众消费,众多经典的美学定义和理论范畴都做出相应的变化,经典的张爱玲文本也就失去了原先的价值,而改编进入到每个人自身的存在领域当中,以此希望提高当代人对美学的日常应用与经典意义的提升。毋庸置疑的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美学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当代美学革命的一场重要前戏,经典美学改变了曾经从某种自然美或艺术美出发去确认美本质的抽象思辨,转而以自我的认同来关注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随意。改编的美学变革也暗示了美学所包含的人生态度的一场转换,依靠大众对日常人生状态的呼唤而成为经典存在的一种新式坐标。
第二,在对张爱玲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中,大众的梦已经成为文化经典削弱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支点,呈现出大众消费的审美快感。费斯克曾经反复强调大众在自身的文化消费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快感,他认为:“快感、切身相关性与赋予权力的行为为其共同的母体,就在大众文化的核心。”[9]8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世俗性极强,大众消费时能获得一种快感。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文化学者把大众文化看得一文不值,但是对张爱玲作品的电视剧改编而获取的蓬勃收视率毕竟是不争的事实。艺术家在面对职业化时必须依靠买办与艺术中介力量来进入市场领域,使大众获得收视快感。对张爱玲经典文学的电视剧改编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经典文本发生动摇之际,正是观看生理欲望与功利思想追逐的顶峰之时。传统文学中所具备的个性独特、意味悠长、意境高深变成了欲望的无尽释放和快感的无尽追逐,崇高庄严的大悲剧式模式被消解,油滑的喜剧被捧上高高的艺术台阶,传统的典雅艺术是少数美学家的象牙塔专利,形而下的经典文化改编和身体感官享受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必然选择。“把快感在文化中的作用加以理论化,此类尝试可谓屡见不鲜。这些尝试虽然相去甚远,但其共享的期望,是将快感分成两个宽泛的范畴,一个他们弹冠相庆,另一个他们痛加谴责。”[9]60费斯克所理解的快感和庸俗式的享乐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着一定暧昧关系,崇高快感的存在有时是为了映衬低俗的享乐。“我也愿意承认快感的多义性,并能够采取相互抵触的形式;但我更愿意集中探讨那些抵抗着霸权式快感的大众式的快感,并就此来凸显在这二分法中通常被视为声名狼藉的那一项。”[9]60费斯克所认定的快感可以分成两组:有时这种快感是围绕身体而造成了一种冒犯;有时这种快感表达了一种社会认同度,实际则是对于传统经典霸权的符号化抵制,这就构成了一种反权威的力量,是一种合理的快感。而这种观点恰好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的大众文化只是低俗浅薄的观点相左。
对张爱玲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本身即是世俗与审美的结合,当受众观赏后,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是建立在自身快感体验基础上的,表现出自身情感与世俗审美的强烈统一,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下,消费文化借助受众日常情感的潜移默化,实现了经典审美的日常价值。
[1] 〔法〕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76.
[2] 范智红.世变缘常 四十年代小说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8.
[3] 金民卿.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18.
[4]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5.
[5] 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69.
[6] 〔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114.
[7]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 〔英〕雷蒙得·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89.
[9] 〔美〕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钰,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张爱玲认为的真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