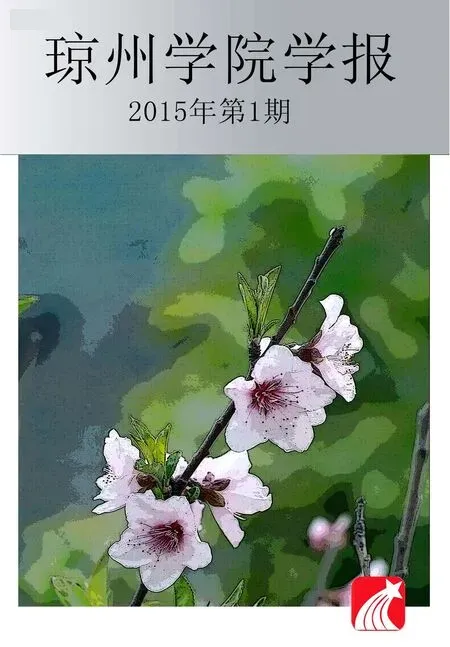叶适《论语》记言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51000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书,列专章对叶适进行批判,视其为“隔绝论”“冥惑论”“皇极一元论”。其中,第六、七两节对叶适的“孔子观”批评尤甚,“其于孔子之仁教全无所知甚显”[1]210,“自己于孔子之仁教全无所知,而反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责曾子,岂不谬哉?岂不狂悖矣哉?”[1]238直欲将叶适排除于儒家学者之列。本文以《习学记言序目·论语》为主,对其中的“仁”学思想和“非曾”现象进行分析,以求教方家。
一、仁礼合一,践礼以知仁
牟宗三认为“仁是全德,是真实生命,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它超越乎礼乐(典章制度、全部人文世界)而又内在于礼乐;在仁之通润中,一一皆实”,“是孔子真精神之所在”,[1]211而叶适对此全无所知。冯友兰曾将“仁”分为“理想之仁”和“现实之仁”①详情可参见冯友兰早年所著《中国哲学史》第四章第五节《直、仁、忠、恕》。,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论语》一卷,提及“仁”字的共十条,关键者有三,大抵侧重于现实之仁,旨在指示成仁之路。
叶适将“仁”分为“仁之具体”“仁之操术”“术之降杀者”三个层次:
今若体孔子之言,要须有用力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孰可以言知矣。[2]178
以上所引三段话皆为孔子答弟子问“仁”,是他指示的成仁之路,原文并无高下之意,叶适对此加以区分。其中,“仁之具体”系答颜渊所问,叶适认为这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包含了仁的全部内容,“‘克己复礼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2]192,此为上(见下文详述)。“仁之操术”是答仲弓所问,原文作“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阮元说:“《周礼》凡言大宾客,皆诸侯朝觐之礼。《尔雅》曰:‘禘,大祭也。’可见非朝觐禘夹不得称大宾大祭。”[3]东晋范宁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也。仁者举动使民事如此也。”[4]952由此,叶适所说“仁之操术”当就遵守朝觐和国祭的礼节而言,着眼点在“复礼”。能复礼则“在家无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无怨,仁及乎一国矣。天下归仁,仁及乎天下矣”[4]952,叶适以此次之。“术之降杀者”是答子贡所问,黄怀信认为“能近取譬,‘近’即所谓己,自身也”[5]554,正与朱熹引吕氏说“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6]92同义。孔子这里强调的是从自身做起,推己及人。故叶适此言的落脚点当为“克己”,并认为克己不如复礼。对照《论语·宪问》篇孔子答子路问君子,孔子所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并非朱熹理解“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6]92,而是说“修己以安百姓”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在这一点上纵然尧舜贵为帝王也不易做到。这里也可看出,在孔子的观念中,“修己以安百姓”的外在功业高于“修己以敬”的主体自觉,这和该篇孔子以管仲为“仁”的落脚点一致。毛奇龄《四书改错》“夫子许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为怀,以国家天下为己任”[4]144,正是此意。叶适上述观点也是在这种思想下提出的,是契合孔子原意的。此外,子张、樊迟、司马牛等弟子问仁,叶适均未提及,要之,或因其均非“孔门十哲”,尚不足以“稽合乎孔氏之本统”。
“仁之操术”与“术之降杀者”,皆为孔子所说“仁之方也”,通过对它们的践行可以成“仁”,但它们并非“仁之具体”。叶适认为它们是孔子因材施教,对不同资质的弟子所作的不同回答,其中颜渊资质最高,孔子以“仁之全体”告之:
“克己复礼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固未尝以全体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颜子曷为能受之?得全体而能问其目故也。全体因目而后明,凡孔子之言仁,凡弟子之问仁,未有的切明白广大周遍如此者。[2]192
“克己复礼”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叶适评程颐《视听言动箴》:“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矣,言己之重也,己不能自克,非礼害之也。”[2]731这是说,克己的目的在于成己、立己,不能克己成仁是因为“非礼”之故。换言之,叶适承认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并且赞同“为仁由己”“克己为重”,所谓“人之所以为仁者,心也”,此为内。[2]182同时,他认为“仁”并不仅仅是“一己之德”,克己是成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仁”不能离开礼而单独存在,它还需要合乎礼的具体实践(“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常由此用力”才能“一息一食无不在仁”,此为外。再看《论语?八佾》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何晏引包咸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乐”[5]201,刘宝楠说“礼乐所以饰仁,故惟仁者能行礼乐”[7],是孔子认为仁是实行礼乐的必要条件,没有仁就没有真的礼乐。在此基础上,叶适进一步认为礼也是克己成仁的必要条件,所谓“己不能自克,非礼害之也”。综上,无论是单纯的“克己成仁”还是“复礼济人”,叶适都认为有所欠缺。体为仁,目为礼,“全体因目而后明”,他的仁学思想是“克己”与“复礼”的统一,是内外合一、仁礼合一。
以上为孔子答弟子问仁,叶适称之为“仁之体状”,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仁之指归”: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自见此仁,如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叩之即应,运之即从,其言捷疾,无所疑贰,自颜渊以下皆未明也。学者能以孔子之告诸子者识仁之体状,拟议深熟,然后以孔子之自言者知仁之指归,造诣径直;则颠沛造次可以弗违,不但日月之至而已。[2]187
“仁之体状”是就外在表现而言,“出门如宾,使民如祭”等是其手段,“克己复礼”是其全体,克己复礼从而行仁于天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此处“仁之指归”当指在己之仁,“孔子自见此仁,如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叶适主张行仁于天下而后将其内化于己,这样才能“颠沛造次可以弗违”。这不同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仁”解释为“心之德,非在外也”[6]100,从而一味反求于自身,甚至陷入佛家顿悟说。叶适主张的成仁途径是由外而内的,是“践礼以知仁”,这与他“自身始而推之天下,推之天下而反其身”[14]的为学主张相一致。
由上可知,叶适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不离礼,仁礼合一,这与“专讲一己之成德”[8]的理学家不同,与牟宗三所谓“超越乎礼乐而又内在于礼乐”则无本质区别。他不仅明白“仁”是“孔子真精神之所在”,还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仁之具体”、“仁之操术”,并指出了“践礼以知仁”的成仁之路。
二、“非曾”依据述评
两宋道学家多认为曾参受孔子之道,传之于子思,再传至孟子。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便明确提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二程”的道统观。①详情可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统的论述。叶适对此表示不满,他说“曾子没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2]188总结叶适此说依据,有以下数端。
第一,曾子未能正确领会孔子的“一贯之道”(所受之道有误)。叶适认为“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已,无所问质”,“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2]178,不合孔子一贯之指。叶适论“颜渊问仁”一章,在提出孔子举“仁”之全体以告颜渊之后,又说“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2]193,是认为一贯之道即上述“仁”之道。曾子所谓“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2]178按“忠恕”即上文所述“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只是实现仁的手段,而不是仁之本身,叶适是以非之。他接着说:“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2]179叶适这里认为,一贯之道不止在学,不止在“忠恕”,而且指向“性命”与“天道”,子贡虽然不能做到,但是明白孔子一贯之指所在,而曾子则于此一无所知,是以所受之道有误。
第二,曾子告孟敬子之言与“一贯之道”不合(所传之道有误)。叶适认为此言与一贯之道“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关于“粗细之异”,他说一贯之道“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尽物可也”,而曾子所谓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可与未克,归与未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叶适认为曾子仅仅重视修身和“一己之德”,只是在“克己”上下功夫,“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10]1746此处所谓“大道”当即第一点“性命”与“天道”。“贵贱之别”是针对曾子所说“笾豆之事”而发,叶适将“笾豆之事”看作“礼”的内容,认为孔子及其徒“未尝不习礼”,而曾子将礼的内容排出儒者视野,是“尊贵忽贱”“得末失本”。曾子“尊其所贵,忽其所贱”的做法“盖谨于外而完其内”[9],与孔子的一贯之道不合,是以所传之道有误。
第三,曾子非“孔门十哲”,且孔子说“参也鲁”。《先进》篇将孔门弟子十人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即为著名的“孔门十哲”。但其中并无曾子,而且孔子说过“参也鲁”(《论语·先进》)的话。如果说曾子是在孔子晚年或死后“德加尊,行加修”,从而“独任孔子之道”[10]1746,则没有明确依据。
第四,圣人之道以书传,曾子无言以立。叶适认为尧舜之道之所以能够一脉相传至孔子,并不只是言传身教,“道者,自古以为微妙难见”,必须赖“书”“言”以传,所谓“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2]188而曾子并无“书”“言”可考,所以不能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后人。
此外,叶适还对子思作《中庸》的说法有所质疑,认为此书不是子思一人所作。即便子思参与其中,该书“高者极高,深者极深”,也并非上世所传之道,试图从另一方面说明曾子不能传孔子之道。
以上所列“非曾”依据,第一、二两条是批判曾子独得孔氏之道。第三、四两条是根据常理推测,最后一条则是侧正。按叶适并没有完全否定曾子的传道之功,也并未说曾子之道不是源自孔子,他只是对曾子“独传”孔子之道表示质疑。他说“礼一日不行即一日坏,惟义数之在书册者尚可传,义理之在人心者犹不泯,故颜、曾欲反求之于心,子贡、游、夏之徒欲求之于书”[2]102,又说“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2]652,是认为他们皆有偏失之处,继承的都只是部分的孔子之道,真正的孔子之道应该是“内外交相成”,仁礼合一。牟宗三对叶适“非曾”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师生相乘只是外部之薰习,若夫深造自得,则端赖自己”,“有引申,有发展,有偏注,有集中,然而不碍其通契,此之谓传”。[1]221继而逐条论证曾子之言行“是根据孔子之仁教而来者”,“若谓曾子之规模不及孔子之万一可也,若必谓其不传孔子之道则大不可也”。[1]225关于“独传”问题已如上分析,牟宗三此说实则是没有弄清叶适批判曾子的重点所在。
其次,他将孔子的“一贯之道”归结为四点①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将“一贯之旨”归结为“一贯之直接意义”、“一贯之实”、“内圣之一贯”、“内圣外王之一贯”四点,详情可参照该书第五章第七节《曾子与“孔子之传统”兼论忠恕一贯》。,从而认为叶适并未真正理解孔子的之道,而“徒自外面看圣人之德业文章或王者之制度功业以为道耳”[1]238。这是牟宗三视叶适为“皇极一元论”的落脚点。如上所述,叶适虽然以“礼”为重,侧重于从器物制度方面理解儒家精神,但并未忽视内在之“仁”,而是主张仁礼合一,“践礼以知仁”,牟宗三未能认识到这点。
最后,他再次声明曾子之道并非“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进而认为叶适每每提到孔子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对孔子之道“实皆轻忽而一无所知”,是“并孔子而亦抹之也”[1]238。这是牟宗三批评叶适的又一大关键,即所谓“吾非反其言经制事功,乃反其反孔子传统也”[1]238。
其实,叶适对孔子的尊崇是显而易见的,“自有文字以来,凡不经孔氏者,皆息灭矣”[2]163,他并不是简单的把孔子视为“档案家”,而是主张“要把孔丘放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看待其学说,不能割断历史,把一切都归功于孔丘,而抹煞在他之前的‘古圣贤者’的贡献,制造一切都开始于孔丘的神话”[11]。
牟宗三又说叶适:
惜乎自己既非英雄,亦非豪杰,更非帝王,亦仍不过一书虫之知识分子耳……美其名曰朴、曰实、曰经济事功、曰三王之道,而终于一无所有,一无事功,并未知历史盛衰大运之所由,政治治乱大关之所在,亦未研究出一个经济事功之方向与夫合理政治之原则,只落得以词章考据终其身。[1]237-238
此话未免太过,是完全忽视了《水心文集》《别集》中的论治救世之术和叶适在开禧北伐中的征战建设之功,若如此,则当世学者于“一书虫之知识分子”更为不如。按牟宗三的批判是从一己观念出发对《总述讲学大旨》所作的“衡定”,他没有对叶适思想做整体性的考察,没有又或是忽略了叶适所处的政治学术环境和思想成因,更没有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不能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
不过,叶适对《论语》的分析也有粗略之嫌。如他并没有说明“克己复礼”为什么是“仁”,也没有将“在己之仁”的“性命”与“天道”所包含的内容具体展开,这些是引发牟宗三批评的重要原因。
结 论
《习学记言序目》一书是叶适晚年对自己思想和学术的总结,作为南宋最后一位著名学者,他“《温州新修学记》以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陈君举四人为永嘉相承之儒宗”,是欲集永嘉学术之大成;“混然于四者(笔者注:朱晦翁、陆象山、陈同甫、陈傅良)之间,总言统绪”,是欲“集诸儒之大成”。[12]近观龚鹏程《永嘉学派的真面目》一文搜集各种材料欲证明永嘉学派非事功学派,认为“养心工夫,即叶适经世之术的根本”[13],其实未免牵强。但同时,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叶适并非仅关注外在事功,他同样注重“养心工夫”,主张内圣外王合一,这才是永嘉学派的“真面目”。正是在这种思想体系下,叶适将孔子的“一贯之道”理解为仁礼合一,认为正确的成仁之路应是“践礼以知仁”。从而通过曾子这个节点对朱熹等理学家的“道统论”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旨在“上接孔氏之本统”,从学理上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思想提供依据,并反映出永嘉学派与道学主“天”、心学主“心”不同的主“事”特色,对南宋思想界甚至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叶适还就《论语》中的其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分析孔子为何以管仲为圣人,辨析《季氏》诸篇并无错简等,不乏真知灼见,应在“论语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清]阮元.揅经室集[M].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185.
[4]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5]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8.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8:81.
[8]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87.
[9]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04.
[10][清]黄宗羲.宋元学案:第三册[M].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张义德.叶适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59.
[12]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855.
[13]吴光,洪振宁.叶适与永嘉学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18.
[14][宋]叶适.叶适集[M].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