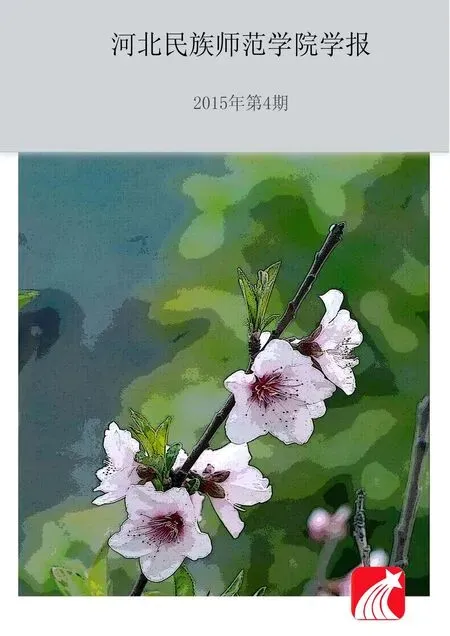“思想”与“哲学”之间
——读和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的一视角
津田雅夫
(岐阜大学,日本501-1193)
“思想”与“哲学”之间
津田雅夫
(岐阜大学,日本501-1193)
在日语的学术词汇中,“哲学”(philosophy)一词仅被用在近现代哲学中。近代以来的日本哲学是通过“西方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前现代,常被使用的则是“思想”(thought)一词。在这两个词之间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的代表作《日本伦理思想史》一书就是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说明日本思想的连续性。不过,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达成。和没有理解这两个词之间许多相互关联的谐恰性,“间(あいだ)”的问题具有暧昧和关联的特征。
哲学;思想;和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
一
然而,这与本书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点并不矛盾。①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学界都没有考虑到和哲郎的整体的构思,而只是从赞成或反对的层面来讨论他的思想。此书自1952年刊行以来至今已近70年,现在终于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本文试图对和哲郎的“伦理思想史”的构想中所蕴含着的根本性矛盾进行阐明。
在这个研究阐明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从哪里着手进行的问题。尽管每一个问题点终究会贯通,但在现在必须要思考的是能够使和哲郎的构想最为核心的问题凸显出来的基本视角。这也会成为《日本伦理思想史》研究今后发展的基石。
二
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我们不能以印度哲学或中国哲学同样的意义上来谈论“日本哲学”(包括伦理学)。为什么时至今日依然不能这样做呢?恰恰是和哲郎的《日本伦理思想史》为我们将其中原委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说明。
《锁国》(1950年)一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从思想上进行了总括,而《日本伦理思想史》一书的写作正是在《锁国》一书所进行的历史反省的基础上进行的。书中的内容多数是在战争之前既已写就,或者可以说此书是对之前的各论考进行修正之后的一部集成之作。但是该书开头的“绪论”部分是新完成的,非常坦率地表达了在集文成册时和哲郎的见解。
“伦理”作为“存在的法则”,对其所包含的问题将在文章的最后进行论述。“伦理思想史”的构想中的核心是“伦理思想史”与“伦理学史”之间的关系,其判定的标准正是在于和哲郎对“伦理学”的独特的理解。在所谓的“伦理学”、“哲学”中,和哲郎围绕着如何理解其中的“学”的概念这一问题,对于“学”的成立要件提出了严肃的思考。
这里所说是不能追溯江户儒学中“伦理学本身内容”的历史性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由。但是,江户儒学当然已经在儒学者们的议论中实现了其学问的展开。和哲郎并没有着眼于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为什么对此和哲郎不做评价呢?其背景是值得一问的。
为什么“学问的历史”无法追溯呢?目前能够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在日本历史大多数时代里,尚未出现从严密意义上可以称作伦理学的东西”。但是所谓的“从严密意义上的伦理学”究竟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只能将原产自西洋的“哲学”、“伦理学”的模型作为范型来理解吗?
例如,中江兆民在其《一年有半》(1901年)中断言“我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时,对于江户时代的儒学,兆民认为“仁斋徂徕之徒就经说创出新意者,唯经学者也”[2],这样简单明快地否定了“儒教伦理学”。而且,为了给明治的文明开化找寻真正的根基,兆民认为必须需要“康德或迪卡尔”这样的真正的“哲学”。
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仔细思索,提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围绕着“严密意义”上的伦理学与“大体”上的伦理学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大体”上的伦理学称为“广义伦理学”的话,也可以将严密意义上的伦理学称为“狭义伦理学”。
这样,“伦理学史”便作为广义的伦理学的历史而成立存在。于是,和所面对的课题就是日本的伦理学史。然而,在此他做出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在日本并不存在“广义的伦理学”。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处理方式。即使最初的契机是起源于引进的学问,但是作为一种对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教义的怀疑”,当然会形成“广义的伦理学”。
诚然,在这幅奇妙的构图中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日本的“学”作为“进口学问”所具有的特点。然而在另一方面,进口的学问却也无法维持其血统的纯正。在被志贺重昂所谓的智慧的“胃管”之中,进口的学问被咀嚼、被吸收——“只在输入泰西之开化(之际),以日本国粹之胃咀嚼之消化之,欲(将之)同化为日本之身体者也。”(日本人第2号所载《“日本人”所怀抱之旨义之告白》《志贺重昂全集》第一卷、5页》)[3]。在这过程中起到作用的是选择性接受,未被消化的残渣只有被排泄、被消灭。
三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围绕着“自宋朝引入”这一点,很明显问题被偷换了。应该明确的是,必须要理清伦理思想的“令人瞩目的发展”与输入的儒学(宋学)的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宋学是被输入的,但确实通过被“咀嚼”从而实现了江户儒学独自的理论发展。当然,阐明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一个课题。江户时代的伦理思想与伦理学(儒学)的发展之间是在毫无关联的情况下实现各自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应该是不合理的。
的确,一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敏锐的方法论上的自觉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到和优秀的感觉,把握到了“思想”与“哲学”(伦理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而言,作为结果,(和)确立了“伦理思想史”这样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广泛的、一般的角度来思考“学问的历史”的话,这个不同点就是次要的。当我们思考“科学”这一词语时,在我们讨论何谓“科学的精神”之前,首先就会很自然地遇到“科学史”。
例如,只有将“医学”的著作作为材料,才会有“医学史”的成立。(作为日本医学史的经典著作,富士川游的《日本医学史》的发行是在业已久远的1904年。从那时起才有了“有史以前的医学”(这一说法)。)无论怎样,我们都不需要将“医学思想史”这一领域特别对待。考虑到“思想”一词所具有的总括性的、含义暧昧的用法,就更加没有这样的必要。(“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美学史”与“美学思想史”等等)
四
但是,仅仅通过锁国来对普遍性的“学”的不成熟所进行的历史性的说明并不充分。那只是对于近代世界中日本的“学”问的落后所进行的一般性说明。这里其实和想要强调的是锁国所带来的“外来性意识”的新的成立。无论佛教也好,儒教也好,都已经化为日本文化的血与肉。锁国所隐含着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让人们将这些已化为日本文化血肉的部分重新意识到其作为“外来文化”这一点。
日本文化之花是盛开在这些先进文化的土地之上的。因此那些先进文化对于日本文化而言已经成为其血肉。如果将它们抹杀,那么日本人创造性工作的大部分也会变得无所依凭。而且,那些血肉并未失去其外来性的性格,即它们自身也同时感觉到自己作为他者而存在。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个世界罕见的锁国状态所造成的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1]
是锁国促使了“外来性意识”的形成。并且那恰恰形成了日本文化的“珍贵性”。和这样的说明非常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来说,如果“外来性意识”一直持续,那么普遍性的“学”就无法形成。引进的学问将始终是引进的学问。和对于“江户初期以后儒学者的废佛运动”以及“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国学者的排外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1]。
这个成立于对记纪神话的进行的解释的基础之上的、最初的“国民全体的自觉”作为以“对祭祀统一者的权威的归属”为核心的“伦理思想”,被命名为“清明心的道德”。其内容是以“清明之心”为基轴,宣扬对“慈爱”与“社会正义”的尊重(“绪论”第3章)。重要的是,在这个最初的“国民全体的自觉”之中所蕴含着的多个要因在之后的各个时代的“伦理思想”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与展开。这正是“伦理思想的传统”的形成。
五
上面我们通过“外来性意识”对于(日本文化)作为“无从依凭的内容”的“珍贵性”的来龙去脉。其“珍贵性”通过“锁国”而表现得特别显著,但最终这一现象又作为各时代共通的特点而被一般化。结果是珍贵性作为积极地为“伦理思想”所付以特征的传统,被重新给予了肯定性的理解。
但是,这个“传统”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保持与继承呢?其中是否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呢?正如和自己所担忧的那样,“仿佛只有尊皇思想才是日本的伦理思想这样的误解”是否被消除了呢[1]。最终,问题在于现代的评价,存在于第6个阶段。如果说“锁国”使得“珍贵性”的存在浮现出来,那么相对而立“开国”就成为对这个“传统”的新的挑战。
明治政府在其帝国宪法中产生了一些例如“天皇作为大元帅,赋与其统帅权及特别的地位”这样的“(概念的)混淆与时代错误”。这是那些要“将天皇视同为将军”的“封建性的武士的君臣意识”所使用的手段,总之就是“明治政府中身居要位的封建武士的技俩”[1]。而将这个“灾祸”扩展开来是就是“通过官宪之手而在教育者中间推行开来的国民道德论。”[6]
作为“伦理思想”的第6阶段,尽管人们期待着“东洋道德与西洋道德的统一”,但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逆转,只是一味强调“我国特有的国民道德”的“国民道德论”成为了“日本巨大的癌症”[6]。和是这样表达他的悲愤与感慨的:对于某个国民来说,历史性地创造出来的特有的道德可以原封不动地在现实的实践中作为标准发挥作用,这是极大的谎言。……正如将封建式的忠君的内容偷换成为对天皇的忠诚,其中之罪重矣。……至于与忠并列的孝德,成为家庭道德,而不是国民道德,这一点变得越发显著。而且这个忠孝是“我国特有的国民道德”,如此将这个国民道德表述成为站在国民立场上的道德。这里存在有两重的混淆,原理问题的混淆与历史问题的混淆。……国民道德论作为这样的混淆的产物在明治末期变得兴盛,这对于明治时代来说是极不光彩的事情。[6]
然而仅靠这样的悲愤与感慨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教育敕语中忠孝被定为是“国体的精华”的理由。同时,“如果能够以教育敕语来作为明治时代的伦理思想的代表的话,其特征在于它主张的是可以在古今东西都妥当的道理,而不是在于它是力主宣扬尊崇天皇和忠孝的思想。如果我们冷静地探讨敕语的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1]”。然而和以上的解说也并非只要“冷静地探讨”就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解释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愿望。
结语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作为“无从依凭的内容”的“珍贵性”之上,来做一总结。这一论题在根本上支配着和对于“思想”与“哲学(伦理学)”二者的关联所进行的议论。
诚然,观察一种文化是有视角的。特别是对于被认为是先进文化的异文化来说,这样的意识就会非常敏锐。可以说对先进国家的这种关心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这样的关心会产生对自我文化的相对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成立。但是这样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可能依靠自己来维持。对于异文化的过剩的关心会不断转化。其关心的对象会从外部转向内部。
文化相对主义向自文化中心主义的转变是很容易分辨的。异文化的意义转变为只是为了丰富自文化的手段。这样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必然会导致成为对吸收异文化的本文化的优越性的说明。从和所提出的“外来性意识”来看,其起到的作用就是这种性格的。
反而我们应该从中发现积极的意义。当我们积极地来理解断绝所具有的意义时,就会产生“间”的观念。这对于自己的思考来说是一种新的意识或态度的成立。在日常的日语世界里,“哲学”被用作表明每个人的人生哲学或处世道理的词汇;另一方面,“思想”则被大家茫然地理解为用来表示社会(或是其一部分)通用的想法、观点,或是表示意识形态的一个词语。从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思想问题”。反言之,不会产生“哲学问题”。“哲学”在每个人的层面上被处理,对此进行相互讨论便成为情趣上的(美学上的)问题,被作为疏于世事的事情而被忌避。
思考“间”,就是作为新的思索空间的“哲学”的可能性。在这个看起来极为个人性事务的“哲学”中,可以看到思索的新的样式。自己的判断便存在其中。怀疑的自己就成立了。这是“哲学”成立的必不可缺的要件。在“思想”之中业已发挥作用的选择性接受,介由怀疑的自己,再次成为“哲学”。
诚然在“哲学”的引进之中,西洋近代哲学被看作是哲学的典型、模范。但是今天存在着多样的“近代”,存在着多样的“哲学”,这也正在成为被认可的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且在这些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哲学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也会得到推进。
不是从外向内的反转,这里面没有“间”。也不是从异文化向自文化的反转,也不是中心与边缘的角逐。不过,在观察“多文化”的遥远的视角中,才会有哲学这样的文化活动的形成。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活动现在才刚刚开始。
注释:
①岩波文库版的解说者木村二氏已经就其中的几个基本性问题有所指出。
[2][日]中江兆民.一年有半[M].日本:岩波文库,1901.31.
[3“]日本人”所怀抱之旨义之告白[A].志贺重昂全集,第一卷[C].出版年月:5.
Tsuta Masaō
(Gifu University,501-1193,Japan)
In academic terms of Japanese language,‘philosophy’is used only in modern philosophy.Modern Japanese philosophy was established by‘Westernization’.In case of Pre-modern,‘thought’usually has been used.There aremany complicated problems between two words.Watsuji'smain work History of Japanese Ethical Thought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to explain the consistency in Japanese thought.But his ambition was broken.Watsuji could not understand many co-related mediations between two words.Between-ness’has ambiguous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
philosophy;thought;Watsuji;History of Japanese Ethical Thought
I206
A
2095-3763(2015)04-0044-06
2015-05-04
津田雅夫(ツダマサオ)(1948-),日本大阪人,1972年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卒業、同大学院博士课程单位修得退学后、同文学部助手を経て現在、岐阜大学地域科学部教授,专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