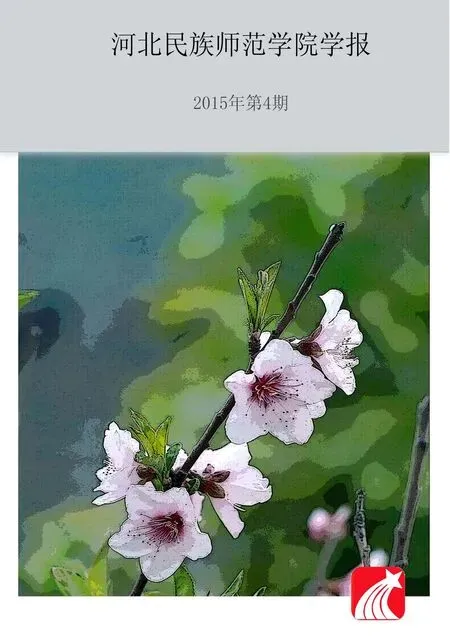北方壁画墓乐舞百戏图像与汉晋之际“焦点式身体”的生成
李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北方壁画墓乐舞百戏图像与汉晋之际“焦点式身体”的生成
李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研究将以汉晋之际为例,以墓葬壁画中的乐舞百戏图像为具体对象,通过三方面来阐释图像在观念史上的有效性:身体要素在图像中的不同组合情况,表征着特定时期的人们对个体身体的不同理解;个体身体和整体场景之间的互动,使图像中的身体开始具有时空的特征;图像为身体规定了存在的场域,并赋予其焦点性的地位。
墓葬壁画;乐舞百戏;汉代;魏晋
一、引论
本研究拟以墓葬壁画中的乐舞百戏图像为例,说明古典中国的绘制者和其他绘画参与者对待个体身体的基本态度,并以此为起点,对汉晋之际的身体观念作出简要回答。通过探讨图像中个体身体要素的不同呈现方式,西汉末期到十六国时代的三种身体模式将被揭示;它们从属于一个渐进的过程,共同指向时代观念中新的身体范式——“焦点式身体”的生成。
为了保证论据的有效性,图像例证的选取将依据三方面原则:(1)乐舞、百戏图像应从属于宴饮背景,以保证作为其“底色”的情境具有一致性;(2)表演者身体应得到尽可能完整的呈现;(3)表演者动作目的应当明确,即方向、态势能够被清楚辨别。
二、回顾:汉魏晋壁画墓中的乐舞百戏图像

图1 宴饮图及局部
中国到西汉晚期,已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的统一状态,重要政治势力集中于都城洛阳(202 B.C.-200 B.C.)、长安(200 B.C-9 A.D.)为中心的中原和关中地区,并辐射至整个北方。因此,大多数规格较高、壁画图像保留较好的墓葬集中于北方,除两都而外,也包括东部地区、河西地区、东北辽阳地区和内蒙陕北一带。[1]由于在西汉时期,乐舞百戏图像在墓葬壁画中尚未具备典型性价值,故而所能选取的实例数量也十分有限。现存较完好、且人物符合选取标准的图像,来自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
壁画位于M1墓室西壁,是四组壁画中自南向北第一组。画面中,“女主人和宾客并排跽坐于围屏前的木榻上,观赏面前的乐舞,前方两侧各有一组人物,均为女性,席地而坐,欣赏乐舞,面前有圆案,案上有樽、耳杯等。中间舞者身姿婀娜,双手执红飘带,翩翩起舞。”[2](如图1)舞女体量较女主人和诸位女宾略小,梳高髻,着杏黄色深衣,体态纤细,面东而舞。双臂平举,两手各持飘带平行甩出,腰部半折,上体前倾,两膝踞地。其上肢完全伸展、开放,下肢则完全隐于衣内,造型相对封闭。尽管上肢已尽力向“动”的方面靠拢,下肢动作却表现出仿佛有意而为的含蓄与节制:跪坐的姿态本身,连同微屈的腰身线条,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服从意味的表演者形象。
这一特征在之后的二百年里,被东汉时代的画师和工匠打破了。宴饮乐舞在这一时期逐渐摆脱原先“偶发”的情况,成为中国北方墓室壁画重要的主题之一。《乐舞百戏图》(图2)来自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画面右侧为乐队,上下共有九人……皆戴红帻,着红衣、红领和袖……左上角六人,中间观赏者似为主人,戴黑帻,着红衣。”[3]位于画面上部的一对男女十分引人注目。两人几乎与左侧观赏者同等大小,左侧男子上身近于赤膊,臂上系红带,两臂抬起至胸前,下着白色阔腿,一脚着地,一脚抬起,似为舞步。躯干挺直,面部侧向朝右侧舞伴,表情诙谐。右侧女子着短襦、阔腿,梳椎髻,背对画面外观者,双臂上扬,袖口飞舞,下肢则凌空跃起,重心前倾。这里,图像呈现的并非两具简单的表演者身体,而是两个负载着运动机能的、不同功能部分的复合体:两臂负责高举过头颅、舞弄袖摆,双腿负责跳跃、奔跑,腰身负责保证挺拔的体形,仰起的头颅则负责将人的姿态向上提升。由于各个功能部分都在呈示一种放射状态,身体占据空间显然得到了扩张。但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舞蹈百戏图像,都运用某些道具作为演员姿态的陪衬,这些道具的作用类似舞伴,使表演者目光集中于画面内的某个定点,避免了和画面外的观众直接相望。

图2 乐舞百戏图及局部

图3 燕居行乐图及局部
在魏晋南北朝的图像中,之前被回避的方面得到了显示。甘肃酒泉宁家闸墓群中的5号壁画墓常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基础材料之一。燕居行乐图(如图3)位于前室后壁。画面左上部为四名乐工,跽坐一列。偏右侧为舞蹈部分,其中扇舞女伎尤其引人注目。女舞者上身穿广袖襦,下着长裙,双手各执一把九华扇,右手举至头部,左手伸直、将扇甩向外侧。右腿直立,支撑重心,左腿向外伸直,左脚略略点地,似乎正处于原地旋转中。梳环髻,颈部外露,面部略向画面右侧,双眼有神,斜视下方。躯干挺拔,由于重心原因略微向画面左侧倾斜,总体正对观者。很明显,与东汉时代的表演者相比,这名女子似乎更加自信:完全向观者开放的姿态,将之前被有意忽略或隐藏的颈部、胸部展示于众;面孔的细致刻画,眼神的流转,为观众开辟了一条通向这位女性内心世界的道路。
于是,又一种新的身体类型,即“铺展式”的身体出现了。相对于放射式的身体,它不仅更直接地向观看者呈现出身体基本要素(四肢、躯干、头颅)的形态,也以清晰描绘的五官和神情,揭示着人物更细腻、更内在的方面:人物心理状态开始被关注,它借由略微夸张的眼部和自然张翕的肢体表露于外。这样,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领域,身体都在图像中得到了日渐精密的规划,由简单的概念化形象逐渐演变为真实的生命体再现。
三、乐舞主题与身体的时空性
每一时代的艺术都有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别的要求,这些要求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就是在艺术作品形式方面实现某些“强调”与“忽略”:“当特定的艺术意志在考虑要满足某些特别明确的要求,以一种不合比例的手法加大与另一部分相联系的某些部分的时候,人们就会立即接受这样一种背离比例的作法。然而这种不合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美”的本质。”[4]如果某一对象所占据的空间(与画面中的其他部分相比)明显有扩张的趋势,则这个对象很可能是作者和他所属的时代所意图强调的。本文的研究对象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实了来自古典文本的结论,即汉晋之际的身体开始逐步具有时空的特征。
重新回到前文中的西汉末期宴饮图像,可以发现,人物大小的分布因循着十分有趣的序列。在场的十七位主要女性中,位于画面中央的表演者体量最小,其次是图像右侧五位女性,体量最突出的则是左侧四位妇女。女舞者占据图像中心位置,作为观众的贵族妇女则围绕舞者,被置于画面左右和偏上位置。长条状的几案使十六位妇女观众共同组成一个接近等腰的梯形,中央表演者位于其对称轴偏右,被三面观众所环绕。舞者仅仅由于舞蹈表演本身的原因被置于画面中心,其体量和近于“卑下”的姿态,都表明她并非图像的主角。图像作者通过人物占据空间的不同情况告诉我们,较之乐舞的直接提供者,他更希望强调的是拥有财富、地位的贵族观众。
而到了东汉时代,相当一部分出自文本的证据表明,百戏、乐舞表演者的活动具有属于它自身的价值,作为环境的有机成分而存在。傅毅(武仲,约90 A.D.)认为,“舞”是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它承载着特殊的视觉形象:“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凤》《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①蔡邕(伯喈,133-192 A.D.)则告诉读者,“舞”不依赖观众鉴赏而存在,它有一套独特的、形式上的规范和要求:“乐容曰舞,有俯仰张翕,行缀长短之制。”②因此,在看待这一时期的宴饮图像时,应当注意到表演者在画面中地位的变化,以及被这种变化所强调的、表演者身体与整个宴饮空间的关系。在展示了“放射状身体”的和林格尔东汉壁画中,可以看到画面内不同人物间的“配称”:一面建鼓占据了靠近中央的位置,它同时也是图像中体量最大的单个事物,远超出观看者(包括主人)、表演者和其他道具。演员们被绘制为几乎同等大小,穿着相似的红色服饰。位于画面上部左右两侧的观众(包括主人)并不比舞伎更加夺目:尽管主人身穿红衣,显著区别于黑衣宾客,体量也略微偏大,却并未获得如西汉壁画中那样的优势地位,而服从于与演员们共处的同一时空。演员个体身体占据的空间相对膨胀了;他们开始取代贵族观众,成为这一时期的图像强调的重心。表演本身是一件大事,观赏则降为次要。
于是,身体与时空之间的关联逐渐在图像中展开,以至于到了魏晋南北朝,观看者从图像中阅读到的,不再是每一个孤立的个体形体,而是被组织在一个具体瞬间场景之中的、群体化了的身体;它们也同时建构着这一时空的连续性,从而印证着整个宴饮乐舞主题的真实发生。宁家闸壁画中,除却位置因素导致的相互遮挡,六位几乎是横向排列的主要表演者,在体量上基本没有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早先的时代未被强调的、表演者的目光变化,此时得到了充分的提示。双眼的轮廓被绘制得大而清晰,黑白分明,因此更能表现人物的心理动势。执扇而舞的女伎拥有更复杂的态度。通过线描图可以看到,女伎的目光并未追随左手扬出的舞蹈道具———扇,而是延伸至画面外的某处,指示着尚未出现在图像中的事物,引导观者走向未知的场景。“身体”由是成为可能发生的新情节的预告者,整个“乐舞故事”的推动力:它滋生着故事发展的环境。
故而,汉晋身体观念的这方面特色,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与其说赋予其一种“人—事件”的相关性逻辑,毋如说是将之进一步导向“身体—时空”的互构性逻辑:当身体存在于特定时空时,时空构成了它的存在场域;时空依托这一特定的身体形象获得其实在性,个体也建构了时空。
四、“焦点式身体”的双重作用
相对于以往的时代,汉晋之际的身体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焦点特性。一个来自《人物志》的例子呈现了观人行为中“察视—显现”的双重结构:“然则平阪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悸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5]表征为一个整体的身体成为一条引导他者领悟个体生存境况的通道,同时也成为一个以真实的声色将某种特别的人格显豁于外、因而能够予他者以新的发现的场所。关于这两种不同质的功用,究竟何以在同一原点上达到平衡的问题,比较可能的一种回答,是作为焦点的身体自身的包容性,即对周遭经验要素的吸纳和辉彰。
在河南新密打虎亭东汉壁画墓中,我们看到了同时兼具这两种功能的身体形象。百戏图(如图4)位于墓室北壁,所绘表演者位置分布零散,却仍然给图像观看者某种统一的视觉印象:不同个体的“在场”以同一的舞台为背景,舞者因其活动的需要,统一身穿红黑相间的短衣,区别于长袍、戴冠的宾客;尽管不同表演者神态各异,其动作的张弛因循着特定而一致的节奏,因而表现出相似的态势。表演者的身体并不独属于他自己,而是服从于情境赋予它的功能,即表演。情境成为身体展开其形态的全部背景,并通过布满空间的音乐和舞蹈,被表演者所内化,渗入个体身体要素当中,使个体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场景中的角色,接受着情境的安排,或动或止。

图4 百戏图及局部
于是,汉晋之际的身体便显示出它的复杂性:它往往不是单纯的身体实体,而是存在于某一背景中、因而与广大的“经验场”相互作用的身体。为解释“实体”的存在而在的“经验场”,从其展开过程上看,并不是某种单一的质素;它从身体外部的广大世界介入其中,为身体提供了自我扩展的可能性。经验通过一系列现象被人接受,从而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与原生身体的各个要素形成一种构成性的关系。当身体成为一个集聚经验场域的焦点时,它具有最为广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见彼有失,则正色而谏之;告我以过,则速改而惮。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纳,不以巧辩饰其非,不以华辞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若情而口合,不面从而背憎,不疾人之胜己,护其短而引其长,隐其失而宣其得,外无计数之诤,内遗心竞之累。[6]
葛洪(稚川,284-363 A.D.)的论述呈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变化着的“色”、“言”、“情”等身体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它们共同汇聚为整体性的“交狎”行为,并借之与其他个体产生联系。于是,作为连续体的身体内部和外部活动,不仅持续推进着自身的运作,也以一系列行为推动着经验事实向前发展;一旦把活动看作一个由不同表征所组成的不可分割的反应链,则不仅它自身的结构性更加明晰,它作为环境组成部分的作用也将由于反应链不断向前推进而得到彰显。
这样,焦点式身体的第二重意义便显现出来:将已被内化的经验要素“发作于外”。在图像中,这种经验要素和事件表现为人物活动的整个场合,以及伴随可视场景出现的、合乎逻辑的不可见元素,如乐曲伴奏、舞步和衣裾摆动等不同声响。由于舞蹈活动的发生,这些成分在开始的阶段便成为表演者自身机体的一部分,支持着整个舞蹈行为的进行;而一旦这一行为发展到高潮,原初的环境要素将以全新的面貌涌现于外,使源自人物的、特别的气氛充斥全部空间。百戏图下部抛丸者为两名青年男子,着红色短衣,袒领,体格健壮。由于合作的需要,两人目光集中于抛丸,并未面对画面上部的观众,反而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情节空间。但这一空间不是封闭的。抛丸者持续进行的移动、跳跃,不仅使两人组成的小空间具有了跃动的气息,也将这气氛扩散到更广大的宴饮空间,使之获得了特殊的动感和活力。作为焦点的身体将舞乐场景内化为自身行动的依据,又将之整合、外化为场景本身难以造就的热烈景象,引领周遭的经验要素围绕个体身体进行着“集聚—整合—外扩”的运动。于是,身体对于环境的统摄并不只是合聚,而且是使之“和”,使其中无限多的事物彼此协调,而形成一种有序的关联,静待着某个足以使它“发作于外”的特殊情境的到来:
五常既备,包以淡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5]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7]
精气、威仪、“神思”与“才气”盈满某个形体,并从中喷薄而出的过程,在作者的语境下,流露着对于超个体力量的深沉向往;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古早期典型的身体形象,既由于直接地与日常世界打交道,能够从其周遭环境各种实际的关联中获得极为丰富的内容,也因为自体固有的能动性,为这些被内化的经验要素提供合作的模式,从而使之凝聚、外发、显示为某种灵性。
五、结论
至此,我们已经汉晋之际墓葬壁画中的乐舞百戏图像做出了来自身体观念的解读:“半放射式”、“放射式”和“铺展式”是三种代表性的身体要素组合方式,而个体身体与宴饮时空的关联性,则直接促使身体成为整个环境的焦点与中心。事实上,这些特质的生成与开显,植根于中古早期的中国人对“绘画”这一实践活动特别的感情:他们乐于将思想成果贯穿其中,而不仅仅依赖文本的书写。
并且,“墓葬”这一载体的特殊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图像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由于直接与特定时代的生死观关联,“身体”成为图像不得不面对的主题之一;它不仅仅被形象化地贮存于图像中,也自发地生成着更深刻的论题,从而构成着时代信念中与个体生命相关的部分。
注释:
①傅毅:《舞赋》
②蔡邕:《月令章句》
[1]汪小洋.中国墓室绘画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5):7-45.
[3]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J].文物,1974,(1):8-20.
[4](奥)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M].陈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刘劭著.李崇智撰.人物志(卷上)[M].成都:巴蜀书社,2001.
[6]葛洪著.庞月光注.抱朴子外篇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7]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On Acrobatis M urals in Tombs of Han and Jin Dynasty
LIX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is study is mainl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murals in tombs of Han and Jin dynasty.Three pointswill be demonstrated and explained:different combining patterns of body parts exhibiting different comprehensions of human body in varies era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bodies and frontier environments entitling the body in imageswith features of space-time;images stipulating the body's existential circumstancesmaking it the focus of its environment.
tombsmurals;acrobatis in dancing;Han Dynasty;Weiand Jin Dynasty
J211
A
2095-3763(2015)04-0034-05
2015-06-30
李想(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