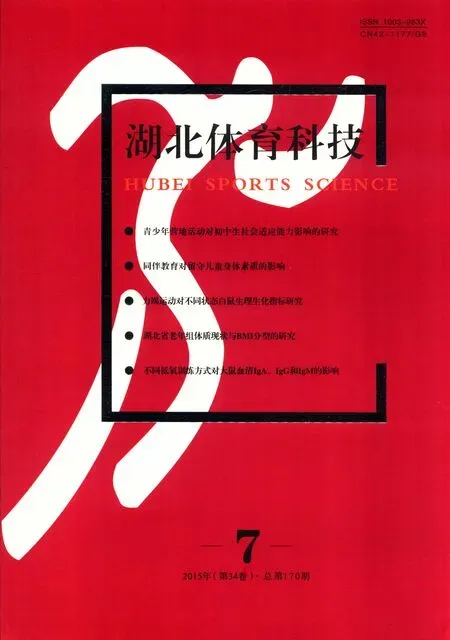运动员认同的研究进展
宋湘勤
运动员认同(Athletic Identity,简称AI)在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是一个较新的议题,它是指“个人对自己身为运动员角色的认同程度”,即是个人觉察自己是一位运动员,是在其所拥有的自我概念当中有关自我认同的部分 (Brewer,Van Raalte, & Linder,1993)[1]。 运动员认同与运动员的健康、自尊、自信、社会关系、运动参与、运动满意度及其职业生涯的发展等有密切关系。目前,国外关于运动员认同的研究较丰富,国内此领域的研究才刚起步。
国外运动员认同研究主要从自我与运动员认同、运动员认同量表的研究发展、运动员认同与伤病、运动员认同与认同预先终止、运动员认同与其它变量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1 自我和运动员认同
自我认同是在生活不同方面中表现出的与自我相关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的组合。认同是自我系统的一部分,它构成了人们在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中具有的多重角色的意义。大多数研究认为由认同构成的自我概念是多维度的。个体在不同时期会激活自我认同的不同维度,加速与自我相关的信息的加工过程。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和改变。Brewer,Van Raalte和Linder将AI定义为个体对运动员角色认同的程度[1]。在多维自我概念框架中,学者们认为AI既是一种认知结构,也是一种社会角色。作为一种认知结构,AI提供了解释信息、采取应对策略及影响与运动员角色相一致的行为的框架[2]。从广义来看,AI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会受到重要他人知觉的影响。这个概念与早期的 “镜我”(looking glass self)理论很相近。“镜我”理论认为重要他人就像一面社会的镜子,人们从他们这里获得对自我的反馈,然后据此对自我进行建构和修正。
2 运动员认同量表的研究发展
Brewer,Van Raalte和 Linder研发了运动员认同量表(AIMS),它能够测量出运动员角色认同的程度和唯一性[1]。此后,研究者们致力于考察AIMS的效度,改进AIMS量表和结构构成[3,4]。AIMS 最初由 10 个题项组成,包括了社会、认知、情感等因素。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93)和重测信度(r=.89)较好[1]。
虽然Brewer,Van Raalte和 Linder最初构想和研发AIMS的时候没有划分维度,但随后的因素分析研究显示AIMS是具有维度的。 Brewer,Boin,Petitpas,Van Raalte 和 Mahar研究发现如剔出10个题项中的1个,AIMS可称为一个3因素的模型。这 3 个因素分别是:1)社会认同;2)唯一性;3)负性情绪[1]。Martin et al.以残疾运动员(包括脑病、截肢及脊柱伤等)为样本检验了AIMS,他们用9个题项确定了一个4因素模型。在原有3因素的基础上,Martin et al.提出了自我认同的因素[5]。Cieslak研究确定了22个题项的AIMS,他命名为AIMS-Plus。AIMS-Plus量表中增加了一个因素,即第5个因素——积极情绪,它包括4个新题项。AIMS-Plus量表中五个分量表的效度和信度高低排列依次为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唯一性、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6]。
Brewer,Cornelius和Hale等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通过与以前模型的对比,重新考察AIMS的因素结构。Hale发现3因素模型比未分维度的模型与4因素模型[4]。Brewer和Cornelius历时10年进行了一项大样本研究(N=2,856),旨在评估最佳AIMS模型和建立男性、女性、运动员与非运动员的常模。他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了先前的4种模型,包括未分维度的 模 型 (Brewer,Van Raalte, & Linder,1993)、3 因 素 模 型(Brewer,Boin et al.,1993)、 修订的 3 因素模型 (Hale et al.,1999)、4 因素模型(Martin et al.,1994)。 结果支持构建一个更高层的新模型。这个模型包括7个题项,由3个二阶因素构成(社会认同、唯一性和负性情绪),这3个因素没有任何交叉影响。与其它模型不同的是,这3个二阶因素直接和一阶因素运动员认同相关[3]。 最近,Alfermann,Stambulova 和 Zemaityte 进行的比较运动员对退役的不同反应的一项研究中,采用了5个题项的AIMS,并将它翻译为德语、立陶宛语和俄语[7]。研究者把研究中发现的三组之间的AI的显著差异归咎为文化影响。这项研究拓展了AIMS翻译版本的研究,但它也反映了还没有目前还没有一个AIMS模型适用于任何研究背景。AIMS的跨文化效度研究需要继续进行。
3 运动员认同和伤病
大多数研究都显示运动员认同高的人群受伤的几率也高[7-9]。Brewer进行了4个系列性研究,探讨大学生运动员对于受伤的反应。第一项研究(N=109)结果显示抑郁的情绪(采用POMS测量)与想象组的AI呈正相关(r=.49),但与控制组的AI呈负相关(r=-.42)。第二项研究(N=131)结果与第一项研究也很相似,但是只达到了一个接近显著水平。实验组抑郁情绪分数与AI正相关(r=.12),控制组抑郁情绪分数与AI负相关(r=-.21)。第三项研究(N=121)发现AI水平高的运动员不管是用 POMS(r=.21)还是用贝克抑郁量表(BDI;r=.23)测量,结果都表明他们更容易体验到负性的情绪。在最后一个研究中,Brewer发现BDI和POMS的结果有差异。仅有BDI的研究显示受伤运动员的抑郁情绪和AI呈正相关(r=.35),未受伤的运动员呈负相关(r=-.19)。POMS的结果没有显示有任何显著联系。Brewer对此的解释是研究的被试都是年轻人,他们更愿意回答BDI关于躯体症状的题项,而不是POMS[1]。
Brewer提出了“认知评价过程”和“自我聚焦注意”两种潜在的机制解释研究结果。认知评价过程认为抑郁的心境是由运动员对他们伤病的评估引起的,如果运动员认同越强则抑郁心境就越重[1]。自我聚焦注意机制认为特定目标(例如运动员成绩)和当前的状态(例如受伤与不能参加比赛)可能会增强自我意识,结果就产生了负性情感。
Green和Weinberg以受伤业余运动员为被试进行了一项研究(N=30),考察AI、应对技巧、社会支持和心境障碍之间的关系[10]。研究结果显示受伤运动员的社会支持和情绪障碍呈负相关(r=-.37),AI和身体状况呈正相关(r=.40)。 Sparkes和Smith研究了4个受伤橄榄球男运动员的生活经验,考察AI和男性气质的相互作用[11]。这些被试都具有较高的AI,当他们受伤后立即体会到巨大的丧失感和修复自我的强烈愿望。研究者们认为男性的AI比女性强,男性认同强的个体AI高于男性认同低的个体,但没有一致的统计结果显示AI具有性别差异或性别角色差异[8,12,13]。 Tasiemski和他的同事研究了脊柱受伤残疾人运动参与时间和AI的关系(N=985)。研究结果显示参与时间对AI具有主效应,每组的AI都显著地不同于其它组,并且呈升序排列(也即,运动参与时间多的个体具有较高的AI)。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花费1-3h进行运动的参加者和那些少于1h的参加者差异相对而言较小。其它组间的差异达到中等程度或较大[14]。
4 运动员认同与退役
Grove,Lavallee和 Gordon 研究了退役运动员(N=48)在转折时期的心理适应和应对策略以及AI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忽略运动员退役的原因,AI和情感适应(r=.67)、社会适应(r=.70)、情感适应时间(r=.36)、社会适应时间(r=.49)之间存在正相关。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在采用应对策略方面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与低AI组相比,高AI组更多的采用情感宣泄 (F=28.52,d=1.89)、有效的社会支持(F=7.41,d=1.63)、心理解脱(F=12.84,d=1.26)和行为解脱(F=10.31,d=1.13)策略[15]。
Webb,Nasco,Riley 和 Headrick 研究了 AI、对退役的心理调适、人格特征和退役的原因之间的关系(N=93)。研究者采用4个题项评估运动员认同的强度,这些题项可分为两个因素:1)公众运动员认同,它是指其他人认为个体是运动员的程度;2)个体运动员认同,它是指个体内部运动员认同的程度。整体样本分析显示,只有个体运动员认同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显著相关(r=.25),公众运动员认同则不显著(r=.07,p>.05)。 尤其对于因伤退役的运动员,整体运动员认同(即公众运动员认同和个体运动员认同分量表的总和)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r=.63)和退役所遇到的困难(r=.79)之间显著相关。研究者认为受伤的不可预期性使运动员没有为退役做好准备。受伤后运动员生涯并不会立即终止,AI在康复期间可能会得到加深[16]。
Alfermann等测量了德国、立陶宛和俄罗斯3个国家的运动员对运动员生涯终止的反应 (N=256)[7]。 研究发现前苏联(立陶宛和俄罗斯)的退役运动员与德国运动员相比,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较低。应对策略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国家的运动员的应对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俄罗斯运动员与德国和立陶宛运动员相比,更倾向于采用分散策略,例如讲笑话、做一些其它的事等。德国运动员与其它国家运动员相比,较少采用“倾诉”的策略。
Alfermann等让参与者对6个运动生涯终止的原因进行排序。结果显示,前苏联的运动员退役主要是因为一些与运动相关的不可预期的原因。研究同时发现立陶宛和俄罗斯运动员在退役后AI的水平高于德国运动员。研究者认为在这两个国家中,优秀运动员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因此运动员退役后仍倾向于延续他们所从事的运动或所具有的身份和作为优秀运动员的认同。退役后仍保持较高的AI是维护自尊的防御机制[7]。
Grove,Fish和 Eklund采用纵向研究(N=47)探讨了在运动员挑选过程中的自我保护与自我促进的关系。他们发现,全明星队落选的运动员在队员挑选当天的AI与挑选一周之前的AI相比较低(d=.47);但入选者的AI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研究者认为自我保护机制发生了作用[17]。
5 运动员认同与认同预先终止
认同预先终止是指个体过早认同某种角色,从而停止对其它角色的认同。Good等探索了AI、运动参与和认同预先终止之间的关系(N=502)[18]。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学业成绩和运动参与水平之间存在双向作用(F(2,490)=3.67,p﹤.05)。学业优秀的大学生认同预先终止的分数随着运动参与的增加而上升,学业差的学生则没有这种情况。AI存在三维(性别、学业分组、运动参与水平)交互作用(F(2,490)=3.32,p﹤.05)。Good等发现在两组中AI都随着运动参与的增加而增高。Good等强调全样本的AI和认同预先终止水平显著相关,但相关值较小(r=.21)。
Murphy和他的同事也进行了相似的研究,探讨认同预先终止、AI和生涯成熟度之间的关系(N=124)[12]。 研究结果显示生涯成熟度与AI(r=-.31)和认同预先终止(r=-.36)都呈负相关,但AI和认同预先终止没有呈显著相关(r=.11,p﹥.05)。这个研究结果和Good等的研究结果相反。Murphy和他的同事解释说,AI和认同预先终止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生涯决定的做出和其它角色的探索起抑制作用。方差分析显示,大学生运动员与非大学生运动员相比,具有较高的认同预先终止,较低的AI和生涯成熟度。参加有收入的运动的运动员与无收入的运动员相比,具有较高的认同预先终止和较低的生涯成熟度。这些差异的效果量具有中等程度和大之间。
Miller和Kerr通过对8个加拿大大学生运动员的深度访谈发现尽管大学生运动员认同感很强,但在学业结束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遇到认同预先终止或职业生涯不成熟等问题[9]。研究者发现对角色的过度认同通常发生在大学的低年级,这段时期一般很短暂。在大学的高年级,研究的参与者会把关注点从运动员角色转移到学生角色。Miller和Kerr的研究关注了AI和认同预先终止的发展过程。尽管他们的研究只反映了加拿大的运动文化,但他们认为研究者不应该过度关注AI高的影响和它与认同预先终止之间的关系。
6 AI与其它变量的关系
排除潜在的负性影响,AI高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运动表现满意度、较佳的体适能、运动参与的较高认同、高的自尊水平、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和对经验的高度开放性[19-21]。Brewer,Selby,Linder和Petitpas进行了两项研究(Ns=90 & 105)探讨 AI和运动员运动表现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两项研究结果都显示赛季后的AI显著地与总体赛季满意度(r=.35)及个体赛季满意度(r=.28)相关。赛季运动表现不佳的运动员与表现好的运动员相比,AI较低[19]。
国内目前仅检索到2篇有关运动员认同的研究[22,23],研究包括残疾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同一性与运动定向的关系和运动特质认同度的量表评价与相关研究,此领域的研究较少。
7 评价与展望
7.1 国内该领域研究需进一步开展与深化
从以上综述可看出,国外关于运动员认同的量化研究迄今为止有至少13年的研究历史,研究范围不仅包括AIMS量表的反复修订、多维最佳模型的探讨,而且包括运动认同与伤病、认同预先终止、退役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研究呈现横向、纵深发展趋势。这些研究为运动管理者、教练员等提供了运动员成绩提高、运动员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有益参考。中国国内运动员认同的研究甚少,目前仅检索到两篇文章,此领域的研究有待开展与深化。
7.2 运动员认同研究工具有待进一步开发与完善
虽然自1993年Brewer等研发出运动员认同量表至今,运动员认同量表已经过多次修订,但却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研究者们编制的运动员认同量表分别包含10个、9个、5个、7个等题项。并且研究者也未就运动员认同的因素结构达成一致研究意见,有的研究认为运动员认同不分维度,有的研究发现运动员认同包含3个因素,有的研究则发现运动员认同包含4个因素。同时,研究者也发现运动员认同量表存在着文化差异,量表的跨文化研究需要继续进行。以上这些都说明运动员认同的研究工具有待进一步开发与完善。
7.3 运动员认同的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
国外有关运动员认同的研究相当广泛和深入,但审视其研究对象,不难发现其大多数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大学生运动员或业余运动员,关于职业运动员与青少年运动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研究对象选择的便利性有关。运动员认同是受多因素影响,并且随年龄发展变化的自我概念。职业运动员与青少年运动员关于运动员认同的测量、与伤病、运动满意度等变量的关系是否呈现出与大学生运动员相同的趋势,是否有不同的特点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7.4 运动员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有待开展
国外学者对运动员认同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多是围绕运动员认同量表的编制与结构,或运动员认同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仍然缺乏对运动员认同在人口统计学上、训练和运动项目上特点的研究,缺乏对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运动员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是运动员认同的基础研究,只有在探讨清楚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把握运动员认同。
[1]Brewer,B.W.,Van Raalte,J.K., & Linder,D.E..Athletic identity:Hercules’ muscles or Achilles’ he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1993,(24).
[2]Horton,R., & Mack,D..Athletic identity in marathon runner:Functional focus or dysfunctional commitment[J].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2000,23:101-119.
[3]Brewer B W,Cornelius A E..Norms and factorial invariance of the Athletic Identity Measurement Scale (AIMS) [J].Academic Athletic Journal,2001(16).
[4]Hale,B.,James,B., & Stambulova,N..Determin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athletic identity:A Herculean cross-cultural undertaking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1999(30).
[5]Martin J.,Eklund R C,Mushett C A..Factor structure of the Athletic Identity Measurement Scale with athletes with disabilities [J].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 Quarterly,1997(14).
[6]Cieslak T J..Describing and measuring the athletic identity construct: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Ohio State University,Columbus,2005.
[7]Alfermann D,Stambulova N,Zemaityte A..Reactions to sport career termination: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German,Lithuanian,andRussianathletes[J].Psychologyof Sport and Exercise,2004(5).
[8]Brewer,B.W.,Van Raalte,J.L. & Petitpas,A.J.In D.Lavallee and P.Wylleman (Eds.),Career transitions in sport: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WV:Fitnes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2000.
[9]Miller,P.S., & Kerr,G.A..The role experimentation of intercollegiate student athletes[J].The Sport Psychologist,2003(17).
[10]Green,S.L. & Weinberg..Relationships among athletic identity,coping skills,social support,and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injury in recreational participants [J].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2001(13).
[11]Sparkes,A.C., & Smith,B..Sport,spinal cord injury,embodied masculinities,and the dilemmas of narrative identity [J].Men and Masculinities,2002(4).
[12]Murphy,G.M.,Petitpas,A.J., & Brewer,B.W..Identity foreclosure,athletic identity,and career maturity in intercollegiate athletes[J].The Sport Psychologist,1996(10).
[13]Wiechman,S., & Williams,J..Relation of athletic identity to injury andmooddisturbance [J].JournalofSportBehavior,1997,20:199-210.
[14]Tasiemski,T.,Kennedy,P.,Gardner,B.P., & Blaikley,R.A..Athletic identity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people with spinal cord injury[J].AdaptedPhysicalActivityQuarterly,2004(21):364-378.
[15]Grove,J.R.,Lavallee,D., & Gordon,S..Coping with retirement from sport:The influence of athletic identity [J].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1997(9).
[16]Webb,W.M.,Nasco,S.A.,Riley,S., & Headrick,B..Athletic identityandreactionstoretirementfromsports[J].JournalofSportBehavior,1998(21).
[17]Grove,J.,Fish,M., & Eklund,R..Changes in athletic identity following team selection:Self-protection versus self-enhancement [J].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Special Issue:Self-Presentation in Exercise and Sport,2004(16).
[18]Good,A.J.,Brewer,B.W.,Petitpas,A.J.,Van Raalte,J.L., & Mahar,M.T..Athletic identity,identity foreclosure,and college sport participation [J].Academic Athletic Journal,1993(8).
[19]Brewer B W,Selby C L,Linder D E,et al.Distancing oneself from a poor season:Divestment of athletic identity [J].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1999(4).
[20]Dollinger,S.J..Autophotographic identities of young adul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lcohol,athletics,achievement,religion,and work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96(67).
[21]Perna,F.M.,Zaichkowsky,L., & Bocknek,G..The association of mentoring with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mong male athletes at termination of college career [J].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1996(8).
[22]张 晓,赵春英,孙延林,等,残疾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同一性与运动定向的关系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5).
[23]谭先明,黄晓华,陈小敏.运动特质认同度:量表评价与相关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