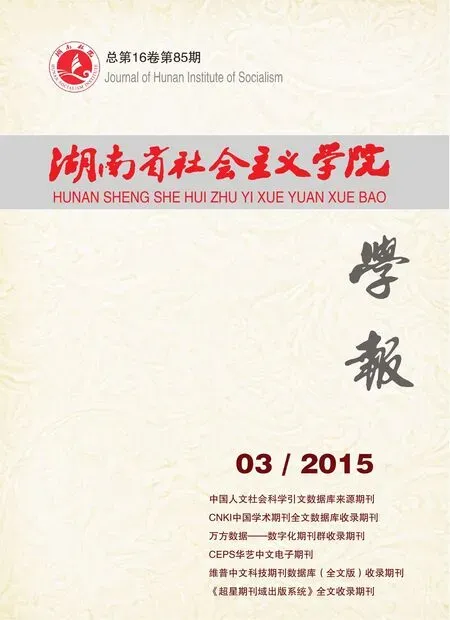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洞庭湖水神信仰的思考
康琼
(湖南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洞庭湖水神信仰的思考
康琼
(湖南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洞庭湖区的人们在长期与水打交道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水神信仰,并以文化血液的形式世代相传。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水神信仰发展到巅峰状态,参与民众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呈现出功利色彩浓郁、地理影响明显、政治色彩显著等基本特点。洞庭湖水神信仰折射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体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文化写照。
人与自然;洞庭湖区;水神信仰
洞庭湖水神与当地人们的关系,就是千百年来洞庭湖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缩影,是洞庭湖与当地居民不可分割血肉关系的精神显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华美篇章。
一、洞庭湖水神信仰中的人格神
洞庭湖水神信仰中,人格化水神的数量众多。这些水神往往是当地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特别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并能激发他们一种地域性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湘妃神。唐代君山上即修有湘妃庙,宋代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李邕为岳州知府,他与参军茅无竟等人重建君山湘妃庙。明代,湘君庙破损,弘治五年与嘉靖初年先后对其进行了重修。据清道光《洞庭湖志》载:“明弘治五年(1492年)初通判李士修重修拓其制中为大殿,后为懿范宫,前为门周围缭以撰”,“明嘉靖初(1522年)郡守韩士英重修。”[1]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重修湘妃祠,并写了洋洋洒洒四百字的祠联,为天下第一长联。除君山外,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长沙、岳阳等地均有一些以湘妃为祭祀对象的祠庙。
柳毅(洞庭湖神)。柳毅的故事源于唐传奇《柳毅传》,是洞庭湖区影响最大和受官方最为重视水神。据《洞庭湖志》载:“洞庭君像,一手遮额,覆目而视;一手指湖旁。从神亦然。舟往来者,必致祭。舟中人不敢一字妄语,尤不可手指物及盖额;不意犯之,则有风涛之险。”[2]清明时期,中央政府多次对其进行封祀,清一代就达五次之多。此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还多次兴建、重修洞庭湖神的祠庙,并规定地方官员定期致祀。
杨泗将军。杨泗又称杨幺,南宋时期领导了席卷洞庭湖流域七个州十九个县的农民起义,深受当地百姓的敬仰,并尊为水神立庙奉祀。洞庭湖各县,并上溯至湘江流域的地方,都修有杨泗庙。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中,杨泗将军的信仰传入四川,成为当地的水神。
屈原。屈原自沉汨罗江死后,洞庭湖区的人们就认为其变成了水神,并立祠祭祀。明万历四十三年(1616),中央政府曾遣司礼李恩封大帝水府庙为屈平大夫,要求各处祀之。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尤其是在湘江下游至入湖河段,以屈原为祭祀对象的水府庙较为多见。
龙母。龙母原为湘江流域水神,据道光《永州府志》载,唐代便已经建有龙母庙了。当时,久旱不雨,当地民众旦夕诵经求雨,一老妪愿遭天罚而代民求雨。雨后,人们立庙塑像祭祀,称其为龙母。明朝后,龙母信仰由湘江流域发展到洞庭湖区域。
刘公。刘公刘锜是南宋的抗金名将,曾带领百姓治理蝗灾有功被后人尊为虫神。清道光《洞庭湖志》载曰:“刘公庙,在巴陵县北十五里城陵矶,明建,祀宋刘琦(錡),奉为水神。……其为水神颠末未详,然岳属多祀之。[3]说明,当时刘公已成为洞庭湖区广祭的水神了。
天妃。天妃也称天后,福建、广东、台湾一带呼之为妈祖,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的职司。随着福建等地的客商来湘居住,天妃信仰迁移到洞庭湖流域,成为专司水神的人格神。据清嘉庆《常德府志》载:“天妃庙一名万福宫,在上十字街,福建客民所建。”[4]
关帝。关羽(关帝原为三国人物,其死后逐渐被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主要对象之一。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各州县都建有关帝庙,如遇天旱,则接神求雨,抬像游乡。这说明,关帝在洞庭湖区已兼司水神一职。
陶公。位于长沙县朗梨镇的陶公庙为祭祀两晋陶淡、陶恒叔侄所建,据说香火十分灵验,当地民众曾多次求雨于此。康熙二十六年夏大旱,湖南巡抚赵申乔曾迎请陶公肉身进城求雨。
太上老君、水母娘娘、观音、吕洞宾、孟姜女等仙人,或在洞庭湖留下修仙足迹,或是曾显圣于此,都被当地百姓顶礼膜拜,其中广降甘霖或者庇佑洞庭风平浪静是其一项主要的神职。
二、洞庭湖水神信仰的祭祀参与
明清洞庭湖水神的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各个阶层、各种社会群体的广泛崇奉与祭祀,主要包括祠庙的修建与祭祀活动的举行。
首先,参与水神祠庙修建的社会群体相当广泛,有官员、土绅、民众等。如澧州龙王庙“州牧魏式曾重修”[5];城隍庙“道光元年五月州牧安佩莲倡捐。同治六年,前署州牧吴嗣仲,州牧魏式曾重修”[6]。安乡龙神庙“道光二十六年(1846),邑监生胡作保倡捐升基建修正殿、戏楼及周围城垣”[7];水府庙“康熙六年(1667),邑令王之佐建”[8];城隍庙“明邑令宋粥创建。慈利龙王庙“百姓募修”;关帝庙“康熙时副将韩永杰、守备杨杰建祠,营中先后建”[9];城隍庙“康熙时副将杨璜等建,乾隆间游击阮玉堂等修。同治二年(1863),吉隆阿率绅重修”。[10]常德府的天妃庙则由“福建客民所建”[11]。
其次,参与水神祭祀的民众相当广泛。明清时期洞庭水神祭祀是一项全民性的参与活动,涉及官吏、士人、普通民众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如洞庭湖神、风雨雷电坛坛、龙神庙、圣帝武庙的祭祀根据国家《祀典》的规定的时间、祭仪,由中央政府遣抚臣致祭,或由地方官吏致祭;而日常的祭祀活动,如求雨活动中,求石、求洞等,多是民间的自求,官吏很少参与,但遇到严重的旱灾,士绅或是地方官吏就会带领百姓祷求于神。据《湖南通志》载,仅嘉庆年间,湖南就有7位知县在遇到岁旱的情况下,虔诚祈雨,以求甘霖。明嘉靖二年(1523)、三年(1524)桃源连续大旱,县令张瑶率众祷雨并在祷雨的过程中殉职身亡。
虽然,洞庭湖水神信仰参与群体广泛,但每一种水神信仰的参与群体又略有不同。如洞庭湖神、湘妃、龙神等信仰分布于各类群体之中;而“水母娘娘”信仰主要在洞庭湖船民中流行,“天妃”信仰则主要流传于福建等自沿海而来的外来客民当中。明清时期洞庭湖信仰参与的群体广泛而又多元,官方的水神信仰活动隆重而肃穆,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祭祀礼制,体现出封建等级制度的威严;而民间的水神信仰活动形式活泼多样,而又不失虔诚,反映出俗民观念中水神的人格化倾向与世俗化特点。
三、明清洞庭湖区水神信仰的基本特点
明清时期洞庭湖水神信仰空前活跃,各路神灵皆加入了水神的队伍,使得这一时期的水神信仰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呈现出功利色彩浓郁、地理影响明显、政治色彩显著等特点。
(一)功利色彩浓郁
洞庭湖区的居民普遍敬水神、拜水神,但这种虔诚的信仰并非无条件的奉献,或是不计回报的付出,而是通过这种形式取得神的庇佑。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信仰水神大多是出于生计考虑的,是无可奈何的虔诚;对于地方官来说,信仰水神可能是诚心实意的“为民请命”,也可能是与民“共度灾难”的政治作秀,还可能是为一己私利的“沽名钓誉”。总之,为了功利的目的,不惜祈求一切神灵,自然神可求,专职水神可求,甚至刘錡这种类型的,本为虫神,到了洞庭湖流域为满足当地功利之目的,则改头换面成为了全职的水神。天妃由海神转化为水神就更是名正言顺了。
即使如此,明清时期的洞庭湖居民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膜拜水神。对于“风雨雷电坛”、“龙神庙”这样直接关系到当地生活、生产的大水神,多为春秋两祭,说到底为是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律来安排祭祀活动,让神为人服务。而日常的水神祭祀活动,则更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行船洞庭时会祭湖神;干旱时会祭龙神;水灾则求助于河神……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情况人们很少会想到神,水神最终是为人的利益而服务。
(二)地理影响明显
明清时期洞庭湖水神众多,祠庙林立,但其地位的消长与香火的兴盛很大程度就受当时地理环境的影响。唐代以前,湘妃神(湘君与湘妃)的地位是独一无二,他们既是湘水之神,又是洞庭湖最大的水神,各地方志中都留下了“官民祷而有应”灵验实例。关于柳毅(洞庭湖神)的记录则始现唐昭宗天佑二年(905),洞庭湖神被敕封为“利涉侯”,与当时湘妃神“懿节侯”的地位大致相当,但到了明清时期,洞庭湖神的地位则明显超过湘水神。这种水神地位升落很大程度上与洞庭湖水域的变迁密切相关。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湖泊;魏晋南朝隋唐时期,洞庭湖水域面积快速扩大;唐宋时期洞庭湖和青草湖水面积不相上下,故当时政府对洞庭湖神和青草湖神是分别进行封祀的。明清时期,洞庭、青草、赤沙湖已连成一片,洞庭湖成为了三湖的总称。在此地理变迁之下,洞庭湖水神地位也随之不断崛起,而随着洞庭湖的水域的扩大,湘江在地区性防洪中地位的下降,故此湘水神(同时兼洞庭湖神)的二妃则逐渐遭受冷落,不但在各地方志中排名居洞庭湖神之后,其祠庙也颓损破败。
即使是洞庭湖神这样最受重视的大水神,由于其祠庙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其香火的旺盛程度亦差别很大。明清时期,君山洞庭中庙和岳阳街河口南侧的洞庭龙神庙规模最大,最为民众重视。前者是因与柳毅传说相联系,后者则因为其处于洞庭湖要冲之地。也就说,洞庭湖众多水神地位的消长,同一水神祠庙的兴盛程度,很大程度是由当时的地理环境、或者是其祠庙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貌似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背后却有着地理因素的深深影响。
(三)政治因素突出
唐代以后,中央政府多次对洞庭湖水神进行封祀,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央政府更是加大了封祀的力度,并多次兴建、重建洞庭湖水神的祠庙,规定地方官官员定期致祀。
清初,吴三桂集中精锐近二十万人与清军鏖战洞庭湖区,结果清军取得最后胜利。大多数统治者认为这是洞庭湖神显圣的结果。康熙十八年(1679年),皇帝遣礼部主事五级鲍复业致祭洞庭湖之神,并在《敕封洞庭神文》中言及:“地当师旅之屯,众赖精英之佑,阅时八月,波浪无惊。俾我六师,舳臚共济,坚城立拔,余孽宵奔。眷言挞伐之奇勋,实属神功之丕显,特申昭告,式考彝章,封洞庭之神,载诸祀典。神其永膺嘉号,配岳渎而皆尊;益著贞符,格馨香而勿替。专官告祭,惟神鉴知。”[12]。这里,康熙用溢美之词讲述洞庭湖神的功绩,且派遣专官告祭。
洞庭湖神本是一域之水神,在官方的政治生活中并无地位,但一旦与镇压农民起义与和平定“三藩”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相联系,其地位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祭祀礼仪也纳入了国家礼仪体制的范畴。而中央政府对洞庭湖水神的肯定与封祀,一方面是对其显圣权的感激,但更多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肯定现有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获得民间和社会底层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清末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最重要的现代转型,洞庭湖区的水神信仰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乡村内生秩序的复兴,洞庭湖区水神信仰也随之兴盛。毋庸讳言,水神信仰的内容、形式却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但洞庭湖区水神信仰始终是一个开放、变动的系统,可以在与现代化文化的碰撞中成长并得以奉持,最终建构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多层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互动与和谐。
[1][2][3][12]陶澍,万年淳修撰.清洞庭湖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24、106、125、20.
[4][11]涂春堂、应国斌编.清嘉庆常德府志校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1.
[5][6][7][8][9][10]陈国华、应国斌.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3、1043、1048、1055、1055.
(责任编辑:谢建美)
G122
A
1009 -2293(2015)03 -0076 -03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洞庭湖水神信仰研究”(课题编号:11XBA176)阶段性成果。
康琼,湖南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DOI】10.3969/j.issn.1009 -2293.2015.0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