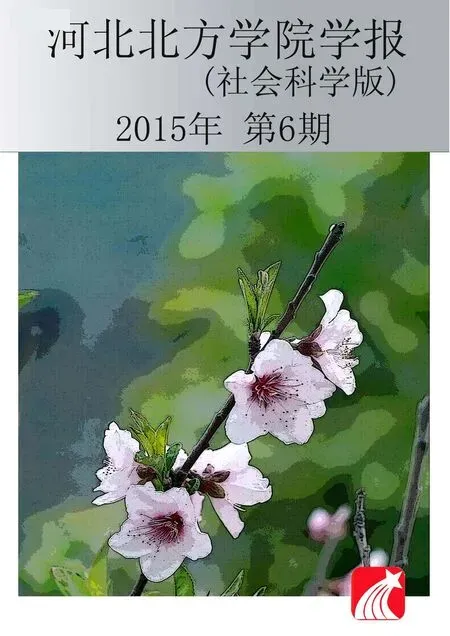《搜神记序》“八略”考释
王 婧 璇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搜神记序》“八略”考释
王 婧 璇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搜神记序》中有“今粗取以演八略之旨”一句,其中“八略”一词的意义至今仍未有明确的定论。目前已知的相关释义有梁启超“小说略说”、李剑国“佛道略说”和小南一郎“篇目总称说”3种。笔者对以上3种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并支持小南一郎“篇目总称说”的观点。
关键词:《搜神记序》;八略;小说;目录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130.1121.00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30 11:21
干宝《搜神记序》:“……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无尤焉。”[1]19以往涉及《搜神记序》的研究多将“八略”作为已知概念进行阐述。例如,张庆民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一书中声言:“‘发明神道之不诬’,‘演八略之旨’无疑是干宝编撰《搜神记》之目的。”[2]92-93但是纵观全文,作者只对“发明神道之不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对“八略”与其提出的“创作目的”有何关涉,并没有进行更为具体的说明。
“八略”的意义与如何理解前后文出现的“明神道之不诬”及“游心寓目”无疑有密切的关系。国内两位学者的论断正是分别从以上两端出发。梁启超认为“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3]172-173,持相似观点的有韩洪举《中国小说理论的发端:干宝的〈搜神记序〉》;李剑国则认为:“而‘演八略之旨’就是发挥佛典道书的大旨,也正是张皇神鬼仙佛。”[4]369持此观点的有马银琴《中华经典藏书系列·搜神记·前言》[5]2。然而,两位学者都只是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并没有对“八略”的意义进行深入考释。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则推断“八略”是指《搜神记》篇目总称,即认为《搜神记》原本分为8篇且各有篇首议论性文字[6],支持这种观点的有胡雅君《20世纪以来干宝〈搜神记序〉论辩研究》[7]。
总体来看,“八略”一词单见于《搜神记序》,学界历来将它作为已知概念进行阐述,但一经深究就发现其意义并不明确,现今所知的3种解释也只停留在观点阐述的阶段。尽管与“八略”直接相关的材料较少,但依旧有可拓展的空间。该文就以上3种观点进行比较辨析,参照序文与干宝其他作品对“八略”的意义进行考释,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分析。
一、目录增类说一:小说略
梁启超主张“八略”是就“七略”而言的目录增益,而增益的类别则是小说。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首次将“政治小说”的概念引入中国,并在宣扬“小说为国民之魂”的论述中,着重说明了小说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今中国识字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虽未明言《搜神记》,然“八略”之意尽显。韩洪举在《中国小说理论的发端:干宝的〈搜神记·序〉》中表示:“到了晋代,小说创作蔚然成风……干宝认为小说业已日渐成熟,理应成为独立的文体,《搜神记》等小说当为一略。”与“小说略”密切相关的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是干宝创作《搜神记》所处的时代概况。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仍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8]37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据胡氏而提出了著名论断,即入唐以后“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从“有意设幻”区分小说与历史,鲁迅则从唐代小说“有意叙述”来区分六朝“粗陈梗概”。生存于东晋的干宝是否有以上两种创作观念,从而具有明确的“发扬小说旨趣”的自觉呢?“八略”之前有“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一句,说明干宝并不看重《搜神记》的虚构性,他更期望《搜神记》中的“变异之谈”可以佐证现实,这正符合其史学家的立场,却也使他与“有意设幻”拉开了距离。现存《搜神记序》开篇有“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佚于当时”一句,这种收集资料并进行整理的方式与史书编撰有相似之处。《搜神记》具有东晋志怪著述的普遍特点,且有集体创作的痕迹,虽然干宝在行文上多有润色,但更多是以“粗陈梗概”为主。无论是东晋的时代条件还是干宝本人的观念,都没有“有意为小说”的可能性。在《搜神记序》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干宝在修史与“游心寓目”之间的矛盾,这更证明了其处于小说创作的“不自觉”时期。因此,将小说观念强加于干宝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是小说在东晋是否有单列为一略的可能。《汉书·艺文志》依据《七略》将书籍分为6类,其中《诸子略》下有小说15家,《六艺略》下将史书内容归入春秋。从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小说在《七略》中已有安置;其二,史书与小说都没有单列为一略。《晋书·干宝传》载其仕历:“……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欶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籍’。”[9]2 150作为史学家的干宝,在史书没有独立为一略的情况下,却将小说升为一略,这显然与其经历及思想不相符。史书在《隋书·经籍志》始列为一部,究其原因,主要是史书有“定世系,辨昭穆”的重要作用。相较之下,历来被称为“小道”的小说,无论从著作规模还是地位上都远逊于史书。所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干宝弃史而列小说为一略显然不符合客观情况。
第三,是梁启超提出“小说略”的时代背景与目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这一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梁启超因参与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宗旨的戊戌变法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清议报》的创刊号上,而《清议报》是梁启超等改良派逃往日本后首先创办的刊物,在同刊的《横滨清议报叙例》一文中介绍了《清议报》刊录了6门主要内容,且这6门①均与政治论述相关。在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后的第四年(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提升小说地位背后的政治目的。
二、目录增类说二:佛道略
李剑国的“佛道说”则认为“八略”是突破《汉书·艺文志》的新型目录分类。他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声言:“所谓‘八略’是就‘七略’而言……所指应当是汉魏以来不断出现的佛教和道教的著作,而‘演八略之旨’就是发挥佛典道书的大旨。”
“佛道略”是否成立需要考察3方面因素:第一,佛道典籍在东晋的情况如何;第二,佛道思想对干宝有何影响;第三,佛道内容是否在《搜神记》中占有绝对比重。
道教在魏晋时期开始分化,并逐渐形成了对上层社会和下层民众皆有影响的神仙道教。干宝《晋纪总论》:“二祖逼禅代之期……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黔六经,谈者以虚薄为变而贱名检。”这说明干宝所处的时代道家思想处于强势地位,从中可以窥见道家的强势影响。魏晋之间,大批具有神仙方术背景的名士活跃在社会上,如葛洪、寇谦、陆修静和陶弘景等,其中陆修静搜罗1 228卷道经并撰写《洞经书目录》,其书虽在干宝之后,亦可证南朝前道教典籍的积累情况;葛洪著有汇集神仙方术的《抱朴子》和志怪作品《西京杂记》,而且在《抱朴子·遐滞篇》中介绍了魏晋时期道教书籍的增长情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葛洪和郭璞与干宝的交游可证神仙道教对其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以东汉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为起点,佛教典籍开始了逐代积累的过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与干宝同时代的著名僧人也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佛图澄和道安等。
在具体篇章中,佛道内容也相对集中出现。道教色彩明显的篇目有《淮南八公》“淮南王安好道术”、《刘根》“入嵩山学道”及《介琰》“从其师白羊公受玄一无为之道”等,而以道士为主角的篇目也颇多,如于吉、葛玄与营陵道士等。佛教内容就现阶段的统计来看,则较少于道教内容。具有佛教色彩的篇目有《天竺胡人》《汉阴生》与《苏易》等。
在目录学发展方面,佛道内容可并列作为一略的实证是南朝齐王俭的《七志》:“佛、道附见合九条。”虽然王俭在干宝之后,《七志》也常为后人诟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距离《搜神记》编撰完成较接近的目录学著作确实将佛道内容单独列为一类。
李剑国的观点有无可待商榷之处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不但重视佛道思想与内容对魏晋志怪小说的影响,也注意到了原始宗教的渐染影响:“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来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10]45张庆民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也以古代宗教、道教及佛教3种宗教作为切入点来论述志怪小说的发展历史。《晋书·干宝传》介绍干宝时有“性好阴阳之术”及“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这样的文字,“阴阳”即战国邹衍建立起的阴阳五行学派;“京房”乃是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创始人,其学派好谈灾异;“夏侯胜”则是西汉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创始人,其学派亦言阴阳灾祸与政治得失。《初学记》存《干宝撰搜神记请纸表》中,干宝将自己正在撰写的内容归纳为“古今怪异非常之事”[11]517。虽然道教融合多家思想,且脱胎于原始宗教,佛教和道教在魏晋时期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两者也与道家及儒家甚至玄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用佛道两家来概括《搜神记》的主题宗旨,亦或是容纳干宝崇尚的阴阳学、易学和尚书学,亦或代表“古今怪异非常之事”,都稍显不相称。尤其应看到的是,魏晋时期将佛道内容并举,同时将之列为单独一类并没有其他实证,如果“佛道略”成立,那么就现阶段的材料来看,这种认识也只是干宝的个人自觉。
三、分篇总称说
小南一郎在《〈搜神记〉的结构》一文中提出:“这里所说的‘八略’,大致可以推断原本《搜神记》的30卷是8类篇章所构成,这8类篇章又在其开头部分,安排了说明该篇内容的议论文字。”由此可以看出,小南一郎的观念是否成立,要考虑的因素有30卷本《搜神记》是否分为8类,是否有8篇议论文字;“八略”一词指代篇章数是否合适。
前代学者通过考据已确认《搜神记》有4篇:一为神话篇,源于《水经注·汝水》;二为感应篇,源于《水经注·泸江水》;三为妖怪篇,源自《法苑珠林·妖怪篇·述异部》,该篇同时透露了《搜神记》分篇有序论性文字,原文为:“妖怪者,干宝《记》云……”;四为变化篇,《荆楚岁时记》和《法苑珠林》同时提及《搜神记》有变化篇且有序论。以上结论在小南一郎的《〈搜神记〉的结构》中有较详细介绍。李剑国也将以上4种篇名引入其辑校的《新辑搜神记》之中。由以上可考的4篇可以推论出30卷本《搜神记》确有依据主旨分篇,且可知妖怪篇与变化篇的确均有序论;从行文规律进行推论,其他两篇也应有序论。
《说文解字》:“略,经略土地也。”由张双棣和陈涛主编,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汉语字典》对“略”的释义中有“大概、概要”一项。自刘歆将目录称“略”,后世普遍认可“略”是“目录”名称中的一种,如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依据现有发现,五代杜光庭撰写的《录异记》即采用了以小说内容分类的方式,其有仙、异人、感应及鬼神等8卷。
小南一郎的“八略”,如果是就《搜神记》本书的目录分类进行讨论,将《搜神记》以内涵分类且发表分论性质的文字,并将分篇类别与序言称之为“略”,那么在称谓上确有一定的可行性。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运用了前代书籍中暂未发现的“八略”一词,由于可参考的资料有限,通过对前代3种释义进行讨论,暂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小说略”说当误。就时代背景而言,梁氏的“小说略”说有明显的政治诉求。原文除了“增七略而为八”,还有“蔚四部而为五”等语,说明梁启超在这里是有意“古为今用”,以突显政治小说的地位,而并非着意于讨论“八略”与“五部”。梁启超在“八略”的问题应上是以政治改革家的身份发言,而并非以学者身份进行考证。后代学者更不能将“增七为八”作为干宝《搜神记序》中“八略”一词的释义来看待。
第二,李剑国“佛道略”有可信取之处,但所关涉的宗教范围还可商榷。就时代背景而言,“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就内容而言,《搜神记》中的佛道内容确实占一定比重。但将干宝撰写《搜神记》的宗旨定义为单纯宣扬佛道两教,并不能将全书内容包含其中。
第三,小南一郎“分篇总称说”有可以成立的证据,已知的4种篇目有可靠旁证,但更多的分类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考究。另外,现有4类篇目的佐证称序论性文字为“论”或“篇”而非“略”,这也是应当注意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从内容和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可行性出发,并以目录学的发展作为参照,笔者较为认同小南一郎对“八略”的释义。由于现有材料的限制,对“八略”意义的考释还有待进一步发现与讨论。
注释:
①分别为: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及政治小说。
参考文献:
[1](晋)干宝.新辑搜神记[M].李剑国,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晋)干宝.中华经典藏书系列·搜神记[M].马银琴,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日〕小南一郎.《搜神记》的结构[A].四川大学历史系.冰蚕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C].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515-523.
[7]胡雅君.20世纪以来干宝《搜神记序》论辩研究[J].赤子,2014(9),220-221.
[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9](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唐)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张盛男)
The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of “Balue”
in the Preface toStoriesofSearchingforGods
WANG Jing-x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00,China)
Abstract:In the Preface to Stories of Searching for Gods,there is a sentence“Currently,it is roughly chosen to interpret the key points of Balue”,in which the meaning of“Balue”has not been clear yet.Nowadays three explanations are popular and they are Liang Qi-chao’s“Brief Explanation of Novels”,Li Jian-guo’s“Brief Explanation of Buddhism”and Kominamiitirou’s“General Names of Chapters”.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viewpoints in detail and supports Kominamiitirou’s“General Names of Chapters”.
Key words:Preface to Stories of Searching for Gods;Balue;novel;catalogue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6-0001-04
作者简介:王婧璇(1990-),女,河北承德人,云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文学。
收稿日期:2015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