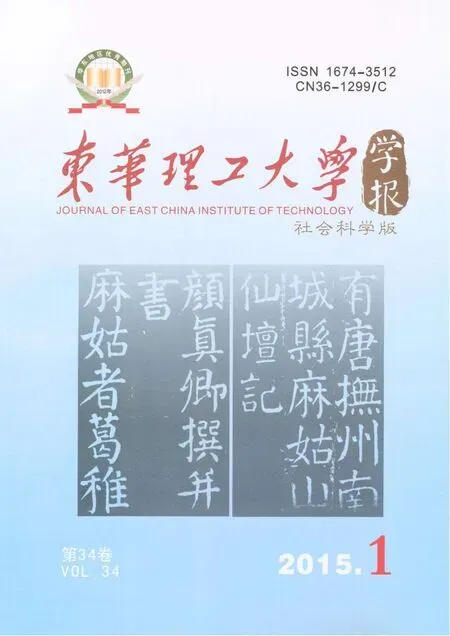论斯坦贝克生态观及其写作
潘晓燕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学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
论斯坦贝克生态观及其写作
潘晓燕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学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
摘要:斯坦贝克是上世纪一名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突破了狭隘的“人类中心论”的朴素生态观,多次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对于自然的“魅”的力量的敬畏,以及生命循环论的观点。他在作品中提出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人性堕落、战争、物质崇拜等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割裂的问题,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恶果、提出解决办法。从朴素的田园思想到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思考,斯坦贝克的生态意识写作从传统的“生态意义写作”向“生态写作”过渡,其作品对于现代社会具有警示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观;人与自然
潘晓燕.论斯坦贝克生态观及其写作[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1):38-43.
Pan Xiao-yan.On Steinbeck’s ecological view and his writing[J].Journal of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34(1):38-43.
1974年,约瑟夫·米克提出的“文学生态学”[1]概念把文学纳入了生态批评的对象行列中。文学与生态学的有机结合,推动了一部分文学作品的兴起。“生态写作”这一概念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多种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题材探讨人与动物、人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作品不断涌现。这种作家有意识地进入生态环境的创作,关注环境污染,对人类自身行为进行反思的文学形式,也就是我们当前所称的“生态写作”。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一类作品的创作焦点。
然而,并不是所有与自然相关的作品都能被称为生态写作。在中西文学史上,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也许涉及自然,关注自然,但并不具备生态写作所必备的“生态忧患意识“。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田园诗歌,西方文学史上的“超验主义文学”等,虽以自然为主要的创作对象,但它们主要体现了“作家对自然的亲近,从自然中体味情趣,并无意于生态忧患意识”[2],这一类只能称之为“生态意义的写作”。
但是,我们仍然有第三类作品,这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生态环保意识,但不以生态忧患意识为根本出发点,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也不是作家创作的根本目的。这类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带有生态意识的写作”。这也是 “生态意义写作” 向“生态写作”的过渡阶段。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名著作品也是数不胜数。老子的“自然无为”,孟子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的“天命论”等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也作为无价的知识瑰宝流传到海外,成为了东方哲学的典型代表。而在西方文学史上,如卢梭的“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爱默生的“令人快乐的力量不在于自然的魔力,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探讨的经典警句也比比皆是。
在第三类作品中,由于环保问题没有严重到无法忽视的程度,因此,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只是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业文明导致自然环境严重恶化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生态写作。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或许体现了一定的生态意识,但环境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创作核心。这些作家已经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朴素生态观” 这一狭隘概念。而约翰·斯坦贝克则属于这一类作家的行列。
1从“祛魅”到“返魅”
斯坦贝克的创作过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逐渐发生了从传统型生态观到发展型生态观的演变。而三十年代则是体现他在写作过程中生态意识得到加强的重要时期。以《愤怒的葡萄》和《致一个无名的神》(也称《大地的象征》)为例。
《愤怒的葡萄》严格地说并不是一部以生态环境问题为焦点的作品,但作品里面所描述的农民、土地以及以银行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出斯坦贝克对于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的怀疑与否定。在小说中,由于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的极度恶化,以及来自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上百万农民不得不放弃祖辈赖以生存的家园,背井离乡,奔向西部寻求生存空间。土地与人类的密切联系已经无法用“人类中心观”来解释。小说背景里的以俄亥俄州为代表的中部地区的严重沙尘暴以及土地沙化等环境恶化问题正是“人类中心论”里的“按照人学原则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一切”的恶果[3]。因此,人类只有改变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对立模式,把自己纳入到地球生态圈的范围中,承认自己与其他自然成员的平等地位,与自然协调发展,才能够避免人类的生存危机。在小说里,乔德一家人对于加利福尼亚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葡萄园的向往,对于重建美好家园的期待,显然和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栖居”以及“家园意识”这种非现代社会人们无法实现的特有的感受是吻合的。《愤怒的葡萄》向读者们传递了一点,那就是:人类中心已不符合世界的有序发展。
人类中心论的失败,必然要求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祛魅”过渡到“返魅”。那么,何所谓“祛魅”和“返魅”呢?根据普遍定义,所谓“魅”,乃是远古时期由于科技不发达所形成的自然自身的神秘感以及人类对它的敬畏与恐惧。祛魅随着科学的兴起和宗教影响的削弱而产生,通俗来讲就是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和魅惑力的消解。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祛魅”的弊病。美国的格里芬认为,“由于现代范式对当今世界的日益牢固的统治,世界被推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改变。而这就要求实现‘世界的返魅……’[4]”而《大地的象征》这一作品则是斯坦贝克试图重新建立“返魅”的精神体系,或者说重新建立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感而做出的努力。
弗拉基米尔·沃纳德斯基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圈的科学。由生命存在以及空气、陆地、岩石圈和水所形成的生物圈概念早在1920年就获得了生态意义。虽然绝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如斯坦贝克等在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大地的象征》里有三个代表意象:主人公约瑟夫、大橡树以及长满青苔的岩石。约瑟夫代表着一切雄心勃勃的美国创业者。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通过对土地的开发来积累财富。因此,约瑟夫象征着向自然索取的人类。约瑟夫在大橡树下收到了兄弟的来信,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约瑟夫凝视着大橡树苍老的枝干,虽然悲伤,但是却莫名地相信“父亲那样强大而又简单地存在……已经附在了这个树上。”[5]他亲吻着大橡树,把它当成了父亲。如此这般,人的灵魂与自然中的生命体结合了起来,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长满青苔的岩石在小说中充满了神秘感,如同图腾一般地存在。约瑟夫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怀孕期间就受到了这块大岩石的神秘吸引,而约瑟夫在靠近它时也认为“这里有魔鬼”[5]。大自然的神秘以其令人恐惧的一面向约瑟夫夫妇拉开了面纱。因此,在小说的末尾,极度的干旱中,约瑟夫不顾亲人的劝阻,独自奔向那块大岩石,并在上面以自己的鲜血献祭,模仿古代以牺牲祈雨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敬畏,并在生命即将消逝之际迎来了久违的甘霖。大橡树和大岩石就是“魅”的具体表现,并且这一元素始终贯穿着小说的情节发展。当科学已经无法解决人类所碰到的难题时,“返魅”是非常自然的趋势。主人公约瑟夫对大橡树的精神依赖以及对青苔巨石的崇拜,一方面是出自于在干旱灾难来到时产生的畏惧以及迷茫心理,体现了人类在摧毁的家园前对天威的恐惧,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神秘力量的崇拜以及自我牺牲的行为也表达了人类希望能够与自然和解,得到救赎的心态。
斯坦贝克始终保持着对“自然以及自然现象的固有的神圣信念”[6],往往用干旱与洪水等元素来表达当代世界中自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威力。生命循环论的观点也在多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与好友海洋生物学家里基茨合作的传记《科尔特海斯海日志》中,他很明确地表达出了该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明显物种只是句子里面的逗号……同时任何一种物种都是某一点,也是金字塔的基石。所有的生命都和这一点息息相关……物种与物种之间融合形成新的物种,群体与群体之间融合成新的生态群体直到我们意识到他们已经进入了非生命的圈子:甲壳衍生了岩石,岩石衍生出土地,土地衍生出树木,树木又衍生出空气和水。”[7]生命的循环是无止境的,任何生命和非生命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已经完全脱离了以往的“人类中心论”的人与自然割裂的论断,并且斯坦贝克常常用预言等形式在他的作品中将生命循环生生不息的观点表达出来。而这种预言的出现往往是借带有印第安血统或者说号称带有印第安血统的角色之口来表达出来,因为“这些印第安人把我们和土壤、水以及和我们有关的非人类生命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把我们和生物群联结起来的生态纽带——该生物群指的是我们力图拒绝否定并摧毁的有机环境……这洪潮充满了骚动与混乱…..理性、秩序和仁慈可以洞悉这一切但却无法控制住这真正的蛮荒的环境”[8]。例如《致一个无名的神》里主人公约瑟夫的自认为有印第安血统的朋友胡安尼托与他梦魇里的干旱以及从地底下冒出的拉住他的骸骨,预示几十年前的大干旱将再次降临,梦里的情景将会再次出现。约瑟夫所疯狂追求的“富饶”也将化为乌有。这是一种从生到死的转化,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小说结尾中约瑟夫用鲜血献祭带来的雨又预示着另一种新生的开始。雨水——干旱——雨水、富饶——贫瘠——富饶以及新生——死亡——新生等关系象征着生命循环存在的合理性。
斯坦贝克追逐着人与自然(无名的神)的奥秘。在他的作品里,似乎人与自然是可以沟通的。《致一个无名的神》里约瑟夫的自我献祭之死与《金杯》里的亨利·摩根的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死亡具有相似的意义。在《金杯》里摩根认为“我是一切的中心,已经无法移动了。我就像宇宙一样重。也许我就是宇宙”[9],而在《大地的象征》里,约瑟夫认为“我就是大地,我就是雨水”[5]。虽然约瑟夫终于迎来了雨水,但是雨水是否真的是他的献祭所带来的呢?斯坦贝克并没有做出说明。也许雨水是上帝对于公正以及不公正的审判,也许雨水是上帝对于约瑟夫献祭的接纳,也许雨水仅仅是自然的气象活动。但是,在读者看来,斯坦贝克赋予了这一自然现象极度的浓厚的神秘色彩。自然科学和宗教仪式联系在了一起,两者相互融合又互相冲突,人与自然也是互相融合又互相冲突。这也是斯坦贝克前期作品的特色所在。这也就是斯坦贝克所认为的“人和所有的一切都相关,也不可避免地和一切现实相关,无论是你所明白的还是不明白的……这种深刻的情感造就出了一个耶稣、一个圣·奥古斯丁、一个罗吉尔·培根、一个查尔斯·达尔文,还有一个爱因斯坦。他们惊奇地发现……一物就是万物,万物就是一物。”[7]这种观点又与东方哲学里的道家学说里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与里基茨的交往过程中,虽然很多人认为斯坦贝克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的朋友那道家学说、生命主义以及其他教义互相融合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但是从他的航海日志里可以隐约看到斯坦贝克所受到的影响。
2从赞美到批判
如果说从斯坦贝克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作品里我们还能见到充满诗意和谐的田园生活,那么进入四五十年代后,人类社会的“诗意的栖居”开始逐渐从他的作品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社会由欲望与斗争所代表的黑暗面对“诗意的栖居”生活的破坏,“田园诗结构”[10]也不再是他小说的主体形式。谨以《珍珠》以及《月亮下去了》为例。
《珍珠》是被称为带有寓言意义的短篇小说作品。墨西哥印第安人吉诺发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他和妻子胡安娜梦想着用这颗珍珠去换取财富,脱离贫穷的生活,挽救自己患病的孩子。然而,珍珠引来了各方人士的觊觎。在不断的保护珍珠的过程中,吉诺的孩子不幸丧命。最后,吉诺和妻子意识到珍珠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于是把珍珠扔回了大海。这是一篇描述从获得财富到失去财富、从失去纯真到重拾纯真的作品。
琳达·瓦格纳·马丁认为斯坦贝克采用“珍珠”这一题目,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回想起圣经里的“无价的珍珠”。在那个寓言里,商人用自己的一切交换来的珍珠象征着天堂的生活。一个人的世俗存在和生活在上帝的乐土里相比,都是无可足道的[11]。然而,吉诺所捡到的珍珠正是使他从平静安详的生活陷入到充满黑暗、袭击的陷阱里的罪魁祸首。在小说开篇,作者用短短的一段话描绘出一幅安宁、和谐的乡村自然景象:“星星还在闪耀,东方低矮的天空微露熹光。鸡已打鸣,猪开始不停地翻腾着树枝和烂木找吃的。在屋子外面,一群鸟儿在鸣唱飞翔。”[11]这些景象把人类生活和自然景观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使人心情平静。清晨吉诺的妻子胡安娜照看着儿子科犹迪托,吉诺唱着家族之歌,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然而,在吉诺发现了那颗“像月亮一样完美、大如鸽卵”[11]的珍珠之后,吉诺开始打算用珍珠去买酒、买性,去购买他们所知道的物质生活。但是,珍珠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在名为“和平之村”的拉帕兹集市上,珍珠的现身给吉诺和他的朋友带来了多次袭击。最后,原本完美的珍珠在吉诺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丑陋的灰色,并且充满恶意。在极度的憎恨下,吉诺和妻子把珍珠扔回了大海。虽然他们将继续过着衣食不济的贫苦生活,但是心灵却回复了平静。唯一的代价是这个家庭永远失去了儿子。在大海里,珍珠恢复了昔日的美丽光芒,吉诺和妻子也重回了昔日的纯真时光。人性与“动物性”[12]也重新达到了平衡点。珍珠本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给人的恩赐。然而,在斯坦贝克看来,任何一种自然产物在经过人类充满物质欲望之手之后,都会丧失掉本来的美丽色彩,转为邪恶之物,破坏人与自然本来的和谐生活。因此,对于斯坦贝克来说,安贫乐道似乎才是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的最佳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斯坦贝克在科特斯海考察中,印第安土著居民的一渔舟、一鱼叉、连电灯都没有的原始生活会给他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满了自然性,与物欲横流的现代世界所带来的各种精神危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此外,由人类的丑陋欲望而主导产生的衍生物“战争”也成为斯坦贝克极力批判的对象。斯坦贝克在《曾经有场战争》里尖锐地提出自己对战争的破坏性的抗议:“内战被称为是‘最后的绅士之战’,所谓的二战无疑是最后的全球之战。下一场战争,如果我们愚蠢到让它发生的话,将会是所有的终结之战。世上将不会留下任何人记得任何事情。如果我们真的那么蠢的话,那么我们,从生物角度来说,没有生存的资格。许多物种因为突变的审判中的各种错误而从地球上消失。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人类可以免疫于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13]在斯坦贝克看来,战争是人类愚蠢的产物。它不仅会摧毁地球上的其他非人类物种,同样也会毁掉人类本身。因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也无法摆脱自然法则的惩罚。过度的军备,过度的装饰以及过度的融合,在作者眼里,都是即将灭亡的征兆。战争在破坏自然性的同时,自然法则也将施加惩罚给人类。这种辩证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月亮下去了》是一部描写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毁掉了一个平静小镇生活,从而引起小镇人民各种反抗的作品。侵略者在入侵小镇最初遭到的反抗寥寥无几,战役结束,仅仅留下了六具尸体。然而,披着“文明”与“法治”外衣的上校兰瑟的“自由”假象在其残酷的统治中被小镇的人们给揭穿了。原本“简单、和平”的小镇人陷入了茫然之中。随着兰瑟独裁统治的恶化,小镇人默默地进行反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小镇原本和平安宁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原本可以在林木里徜徉的人们不得不钻进林子里去排除炸弹,连孩子也被卷入了战争之中,他们“在玩雪的时候发现了炸药,到了这个时候,即便是孩子也接到了命令。他们把包装纸打开,把巧克力吃掉,然后把炸药埋在雪地里,最后告诉父母埋藏地点。”[14]孩子的纯真和幸福的童年已经在战争中消逝。冰雪这个原本最吸引孩子的自然现象也成为了战争的罪恶场所。在小说里,人与自然已经完全割裂开来。人们无法去感受自然所带来的美感,给自然带去的也都是破坏。通过这些描写,战争的丑陋面貌完全暴露了出来。战争也被列入了破坏人类“诗意的栖居”的罪魁祸首的榜单。
从早期的作品直到五六十年代的《伊甸之东》和斯坦贝克最后一部小说《我们烦恼的冬天》,人性在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方面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归根结底,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索求和破坏,都是人性的丑恶一面所造成的后果,包括战争。因此,在《伊甸之东》中,斯坦贝克通过描写一部跨越美国南北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汉密尔顿家族以及特来斯克家族的历史,借助圣经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从上帝的视角来揭露人性中善与恶的选择问题。伊甸园本是人与自然最为和谐时期的象征。但斯坦贝克用“伊甸之东”来作为小说的标题,用“timshel” (可能,可以) 来解释人类在善与恶之间的选择性问题时,人类选择问题就已经与重建伊甸园式的“诗意的栖居”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而《我们烦恼的冬天》里,20世纪美国社会的畸形现象通过主人公伊坦·郝雷背叛亲朋好友的痛苦、精神出行到救赎的艰难历程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美国的市场拜物主义、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心理疾病蔓延等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人的具有善良本性的第一潜能转化为具有破坏性的第二潜能”[15]。生态批评学家眼里的“诗意的栖居”已经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及。
斯坦贝克相信美好的生活是由质量决定而不是由数量决定的。因此,在他发现美国的消费主义和自私自利主义越来越严重,使得维系美国道德完整体系的价值观逐渐沦丧之后,1960年,他决定携爱犬查理横越美国,重新认识美国以及美国人。他们从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的最北角旅行到西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半岛,驾驶着与唐吉可德的坐骑同名的特质露营车“南西罗帖”,穿梭在州际公路和乡间小路之间,与卡车司机和老朋友一起用餐。他们穿越森林,走过尘土飞扬的小径和公路,游览各大都市与壮丽的原野,自由自在地与路上的陌生人闲聊。斯坦贝克以幽默但偶尔带点疑惑的眼光观察着美国以及美国人。他看到的是一个孤寂、物产丰富、但充满单一看法的个人国度。因此,印第安人的虽然物质并不丰富,但是和平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对该生活充满了向往之情。《和查理一起旅行》成为斯坦贝克最为满意的一本游记。
3结语
从20世纪的20年代至60年代,斯坦贝克一生留下了几十部作品,在生态意识方面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一方面,与艾德·里基茨的数十年的交往,里基茨的海洋生物学家的身份促使斯坦贝克形成了科学探索的态度。两人对于科特兹海的生物探索旅行增加了斯坦贝克对于生命与世界的了解。里基茨曾做过一个关于小水塘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调查研究。这份研究也对好友斯坦贝克的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在他的小说里,斯坦贝克已经早早地意识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并很早就发出了不遵守自然规则必将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警示。另一方面,对于生态系统科学知识的了解并没有让斯坦贝克抛却作为人而对自然产生的尊重与敬畏。科学并不代表一切。美国先代文豪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的思想精髓也在他的身上得到体现。人与自然的沟通形式,按照爱默生的观点,是可以通过超灵实现的。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玄学思想,在斯坦贝克的作品里,具体表现为斯坦贝克对于自然的“魅”的承认和尊重。总而言之,坚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坚持基于科学观点基础上的对于自然的敬畏一起构成了斯坦贝克的整体生态观。
然而,斯坦贝克对于生态的认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从人类视角出发的对自然认识必将受到观察者本身的束缚。作为一名作家而不是科学家,斯坦贝克的观察与研究重心仍然是人与人类社会。自然在其作品里扮演的终究是被人类感知的角色。即使不以人类中心为目的,但他笔下的自然无论是服务于人类或惩罚于人类,仍然是次要角色,主人公仍然是人。此外,自1948年里基茨去世之后,他的非目的论思想在斯坦贝克作品里的影响逐渐消退。认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目的论思想在其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里的比重慢慢超过了“世界是什么样”的非目的论。如在《伊甸之东》里他所提出的对于圣经里希伯来文的“timshel”的再定义表明了他强调人类选择的态度[16]。这种以个人经验出发的对于世界的认识区别于非目的论的发散性、开放性写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读者的认知,并且在人、自然与世界的生态系统认知方面不够深入。但是,作为一名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能够用现实手法来区别于纯粹“田园派”的浪漫主义创作,本身就具有进步意义,并且在物欲横流、精神危机严重的现代世界,其作品具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丽丽.文学生态学的建构——生态批评的思考 [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5.
[2] 蔡登秋.“环保主义”、“自然艺术”和“商业化”——谈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几种意识倾向[M]// 余达忠.生态文化与生态批评: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77.
[3] 朱荣英.“人类中心论”、“反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试析当代生态观研究范式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关联[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2):4.
[4]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1-222.
[5] Steinbeck, John. To a God Unknown (Electronic Version) [M].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1995:35, 189,404.
[6] Chester Eisinger, “Jeffersonian Agrarianism in The Grapes of Wrath,”[J] 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Review. XIV, 1947:149.
[7] John Steinbeck. The Log from the Sea of Cortez [M]. New york:Viking Press,1951:216.
[8] Charles R. Metzger, “Steinbeck’s Mexican-Americans ”[C].Steinbeck: The Man and His Work. Ri chard Astro & Tetsumaro Hayashi eds..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42-143.
[9] Steinbeck, John. Cup of Gold [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7:265-267.
[10] 田俊武,陈梅.人,诗意的栖居——简论斯坦贝克喜剧小说的主题和结构模式[J]. 西安外国语学报,2004(2):48.
[11] Steinbeck, John. The pearl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7,23,39.
[12] 徐向英.斯坦贝克作品“动物化倾向再认识”—— 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人与动物[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12.
[13] Steinbeck, John. Once there was a war [M]. New York:Bantam Books, 1960: 5.
[14] Steinbeck, John. The moon Is Down [M]. New York:penguin classics, 1995: 195.
[15] 郑莉.善恶之网的挣扎:斯坦贝克《烦恼的冬天》的美德伦理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 2014(3) :120-131.
[16] 潘晓燕,石立林.由伊甸之东看矛盾的斯坦贝克[J].衡水学院学报,2009(5) :60.
On Steinbeck’s Ecological View and His Writing
PAN Xiao-yan
(FacultyoftheForeignLanguages,EastChinaInstituteofTechnolog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John Steinbeck was a writer with strong ecological sense in 20th century. His works broke through the narrow and simple “human-centered”ecological view, and for several times he expressed his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is reverence toward the enchantment of the nature, and the life circle theory. In his works, he pointed out thos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gradation of human soul, war and materialism and so on which brought out the seper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lso, through his own observation he tried to lead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problems and how to sovle them. From the simple pastoral thoughts to meditation about modern human society, Steinbeck’s ecological writing transi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to “ecological writing”, which was greatly significant in warning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Steinbeck; ecological view; human and nature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12(2015)01-0038-06
作者简介:潘晓燕 (1983—),女,江西婺源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 (WGW1314)。
收稿日期:201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