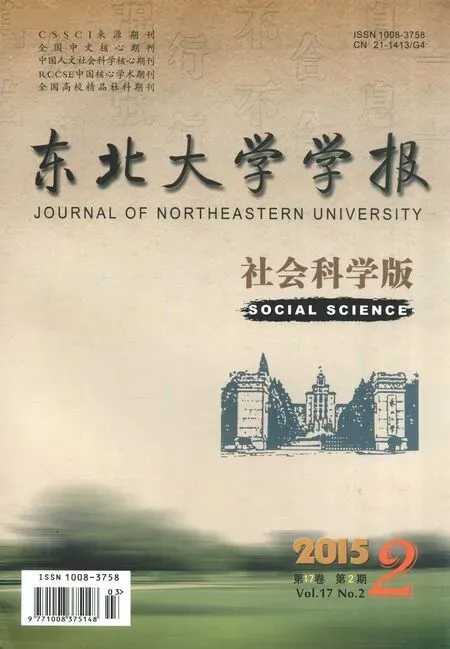从马克思到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兼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从马克思到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兼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刘顺,胡涵锦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
摘要:“现代性”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理论领域,其中马克思和吉登斯的观点具有重要代表性。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概念,但却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根本方向,因为现代性悖论产生的内在动因正是被马克思持续批判的资本逻辑;尽管生态批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和其所处时代的主要任务,但他却在对资本、工具理性和异化劳动的现代性批判中,经意不经意间展露出深刻的生态思想。发展到20世纪,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亦是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的,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他的现代性批判中的生态思想对马克思有着微妙的“继承”。对于二者深刻的生态批判思想,有必要结合实际实现“中国解读”,进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有所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 吉登斯; 现代性; 资本逻辑; 生态维度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2.015
收稿日期:2014-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2CZX007)。
作者简介:刘顺(1988-),男,河南鹿邑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胡涵锦(1953-),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2-0198-07
Abstract:Although modernity is a theoretical field in which all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the views of Marx and Giddens are amo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lthough Marx did not explicitly raise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he always represented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of critique of modernity in that the intrinsic factor of modernity’s paradox is what Marx continuously criticized—capital logic. It is true that ecological critique couldn’t be a main task for Marx in his time, but he unintentionally revealed his own profound ecological thoughts in his critique of capita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alienated labo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iddens’s thoughts of modernity also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ism, so they couldn’t do without Marx; i.e., he subtly “inherited” Marx. It is of great benefit to interpret the two thinkers’ profound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ritiqu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which may carry implications to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Marx to Giddens: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Critique of Modernity
——Discussion on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IUShun,HUHan-j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Key words:Karl Marx;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capital logic; ecological dimension
吉登斯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1]69,而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时写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所以在此种意义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现代性,正是资本逻辑不断展开、不断社会化的产物,并持续地围绕着资本逻辑运转”[3]。现代性肇始于启蒙时代,凭借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并且使工具理性逐步占据统治地位,无疑资本、科学和理性成为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素,其所生成的文明成果对历史有着毋庸置疑的巨大推动。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碾进,现代性悖论也凸显出来: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压倒道德和生态逻辑,经济理性取代生态理性,实质上折射出现代性的生态悖论。笔者择取现代性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和吉登斯,试图对他们现代性理论中的生态批判思想进行探究,最后以期实现对二者该深邃思想的“中国解读”。
一、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资本、工具理性和异化劳动
现代性在本质上折射出人的“实然”与“应然”存在方式之间存在冲突,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持续运转。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概念,但却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根本方向,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4],而马克思对现代性诠释的逻辑中轴正是资本逻辑[5]。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洞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 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肇始于资本的扩张本性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不但诊断出资本霸权宰制下经济危机的内在症因,而且间接揭示了生态危机的逻辑源头。资本透射出的是一种扩张性和膨胀性的社会关系。“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6]714资本要安身立命,就逃不脱这一“绝对规律”。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资本家“绞尽脑汁”扩增生产规模和穷尽手段来提高生产率,以期生成更丰厚的剩余价值。又加上自由市场机制的刺激,资本家狂热盲目地为了纯粹的利润而生产,就势必强化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有哪一个资本家会去考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呢?因为利润才是他们的首选,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私有法权下,保护生态环境就直接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精明的资本家只会“自扫门前雪”,“公地悲剧”无可避免。
就目前言之,自然界(地球)是全体人类共同栖息的唯一家园,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却归属于资本家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私人财产。这样,资本主义尽管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却把公共的生态环境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6]269从常态意义上说,资本家骨子里镶嵌着唯利是图,自己的利益永远是首位,别人的得失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摧残都是其次,甚至根本排除在视野之外。“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6]311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每天都在加强,各种自然界原生态不存在的人造物横空出世,但它们都不能回到自然界以待分解和能量转化。当前生态危机愈来愈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因为其成为了关系着社会成员及其子孙生存死亡的“显性”问题,也同时成了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对此,资本主义或者通过发展绿色技术或者通过生态帝国主义跨国转移生态灾难,但都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并非从根本上堵住危机的源头。因此正如恩格斯当年所言,需要变革当前的生产方式及整个社会制度[7]。唯有通过变革社会关系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
2. 对资本与科学工具理性共谋的生态批判
马克思认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含在资本中的东西”[8]41,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科学这样的“一般精神产品”也异化成资本的内在要素;“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9],为了追逐最大化的利润,科学则成为协助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资本家无论经由何种渠道来扩大资本积累和增加财富,最终都要落实到对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上,因为不管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10]158。资本逻辑的“在场”不可能允许以生态友好的姿态去开发自然界,只能是单向度的掠夺性开发。科学工具理性嬗变成资本家为实现最大利润而不惜破坏自然生态的“帮凶”。
18世纪初启蒙运动开启的理性化进程,也是对自然“脱魅”的过程,因为在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面前,原本图腾式的大自然逐步被层层“解密”,仿佛并不存在让人类畏惧的“自然之力”。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迅速增加,把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魔幻般地生产出来。在现实利益面前,具有天然增殖倾向的资本很容易与自然科学不谋而合,结成利益联盟。随着人们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推崇,再加上资本和资本家从中“怂恿”,启蒙理性在有意无意中走失在工具化滥用的迷途中,尤其在资本霸权的怂恿下,除人自身之外的一切“他者”降格为创生财富的“被动”手段。本来“有机生命的自然”沦落退化为脱魅的“物体世界”,工具理性的尊贵地位拔地而起,正是现代性悖论的一个十足体现。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11]90-91工具理性笼罩下的科技,对待这种“脱魅”自然界的认识,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式“狡猾”利用。在资本现代性的语境中,自然只不过是因人而存在的工具性“待开发物”,脱离人的需要就一文不值,也就没有其存在的“自我价值”。如果不利于资本增殖,即使某项研究存在科学价值,资本家也不愿意投资支持该项活动的开展;反过来,如果该项研究有利于资本增殖和扩张,即使科学意义和公共价值微乎其微甚至生态公害很大,资本家也会极力撺掇自然科学去研究。因为利润,只有利润才是资本追求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是没有理性,在资本增殖的驱动下,“自觉”蜕化为工具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利益,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1]91资本在其内在效用原则的驱使下,再加上工具理性这个强大的“帮凶”,二者“利益共谋”把“纯粹自然”日益变成为“人化自然”。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超越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观念,要把自然升格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展现和确证。
3. 对资本统治下的异化劳动的生态批判
“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方面失去生活资料:……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10]158。在现实实践场域中,人与自然之间融合统一的中介无疑是劳动,但在资本逻辑取得支配地位后,劳动却被变质为异化劳动。资本家愈是设想经由异化劳动来成为外部自然界的主人,那他愈是难以梦想成真,反而失去的越多,就好比“某只手本想一把抓住河里游泳的鱼儿,但越着急、越用力,越是抓不住,稍有不慎,自身也会落水、小命不保”。资本统治下的异化劳动终究会让人类付出代价,终究会使人类“找不到回家的归途”,那时再想改变,恐怕晚矣。“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10]164最终资本逻辑下的人,流变成只追求一己私利的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
在异化劳动的运行机制下,人类将会再一次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因为愈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自然界奴役人类的“法宝”。“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0]158照此循环,劳动者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将会日益加重。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使自然与人的关系“异己化”,逐步将人类的生存家园陷入万劫不复的危机之中。这即马克思关于资本统治下的异化劳动思想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批判维度。
二、 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现代性的“生态负面”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12]“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首先表现为弥漫全球的生态危机,吉登斯主要从以下两方面阐说。
1. 对风险社会的生态批判
生态危机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修补被破坏的环境与其被理解为环境本身的终结,不如被理解为重新解决贫困”[13]177。这是吉登斯对当今生态危机与如火如荼的现代性之间“沟壑交织”关系作出的深刻论断,也道出了现代性的“生态自反性”。
随着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延展,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正如吉登斯指出,随着全球生产力在数量上的飞跃式进步,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和技巧相比启蒙运动前已明显的今非昔比,但“表面上似乎促使我们摆脱作为自然的生物统一性的破坏者的力量,实际上把我们向破坏者推近了。后果严重的风险是飞速发展的人类相互依赖关系的消极一面”[13]170-171。这里的“风险”主要指“人造风险”,因为“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两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1]192-193,“外部风险”主要是指大自然与身俱来的、不在人类操控范围内的天然风险(如地震、海啸、台风、雪崩和瘟疫等),但在一定地质时期内,“外部风险”爆发的概率非常小,当前很可能把人类置于危险境地的却是“人造风险”。“人造风险”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能把人类限于困境的非天然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14],它是现代性悖论的主要动因,主要体现为愈来愈难以预测的生态灾难。
这正好对应吉登斯所言的“自然界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自然界的终结”,言外之意是“人化自然的泛滥”,也即是说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和理性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步被奉为圭臬,这本是好事情,帮助人类战胜了蒙昧、提升生存能力,但是到近来特别是资本逻辑的登堂入室,科技和理性的作用被单向度夸大了,异化成了科技主义和理性主义,最终流变成控制、掠夺自然的主要“帮凶”,已经背离了启蒙运动时的美好初衷。在此背景下,自然界完全成了“单独有用物”,即资本家财富的纯粹对象性存在。自然界已完全沦陷、没有了应然的存在地位,面临着“终结”。与此对应,“传统的终结”则是指传统观念和非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解构和消亡,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按照吉登斯的解释,就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听天由命了,相反,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却要大规模地掠夺和奴役自然”。在以往的社会中,人类吃的用的穿的几乎来自原生态的自然界,可谓“循规蹈矩地生活着”,但现时代随着合成技术和人造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又有多少直接来源自然界且能分解返回到自然界以待完成新陈代谢。这就是“传统化终结”的一种典型表现。吉登斯认为当下社会中的自然和传统正在消亡,截然相异于先前工业社会的情形[15]。许多曾经来源于自然界的“原生物”,现在很可能直接就是人类的制造物,就连过往被视做极限区域的生命体之细胞器官照样也能“人造”,以后更可能直接3D打印。当下自然界内生的“外部风险”并不在人们的主要担忧范围,而是相反,人们开始纠结施加给自然的人为后果,“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16]。
因此,当代的自然生态环境正日益成为人类自己行动的产物,相应地,各种由“人造风险”导致的生态灾难接踵而至,现代性的“生态负面”凸现出来。吉登斯指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与自然的消解一起出现的伦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对存在问题的压制。现在这类问题又不可避免地被重新提及,我们必须在由人为不确定性组成的世界中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13]169
2. 对科学主义的生态批判
吉登斯指出:“在现代工业的背景下,对于解决生态问题来说,与管理环境同样重要的是管理科学和技术。”[13]165自启蒙理性时代以来,科学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人们逐渐产生了“对人类理性的一种夸大了的信仰,或者说这样一种信念”[17]。然而,由于“出发了太久,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科学异化成了帮助人类掠夺自然的工具性知识体系,并不是当初设想的认识大自然的独立性知识存在。在吉登斯看来,科学愈来愈披上“资本意识形态”的神秘面纱,成为当前生态危机的“科学”根源。对此,他进行了坚决的生态批判。
科学本是中性的,一方面是人类智商和欲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物质性结果,另一方面是人类欲望得以满足的物质载体。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受到质疑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和技术涉足到现代性的控制倾向之中”[13]167。这是吉登斯对科学主义的生态批判思想中的核心关切。
吉登斯认为:“如果‘自然’保持相对静止,科学在技术上的利用所遇到的风险是外部的而非人为的,那么这种运转就可以良好地运转。一旦这种关系转变了,科学的‘内部’争论开始反思性地进入非科学的话语和行动领域中,这样的情况就无法再维持了。”[13]167资本逻辑导控下的传统科技走的是一种“压挤式”发展路径,以利润最优化为首要的目标导向,几乎遵循着“自然资源——市场产品——废料废弃物”的路径运行。长此以往,其结果可想而知,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灭迹于地球,同时地球上堆积着愈来愈多难以消化吸收的各种废弃物。更加严峻的生态困境也不会太远,除非自然资源能供无限开发并且自然生态系统永远完好无恙,人类才有可能持续地生存下去。然而,这两个“除非”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并非真实存在,因为在资本逐利和人性贪婪的背景下,传统的科学理性已变成纯粹的工具理性,对自然造成严重的破坏,凸显出反生态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的生态悖论。“在今天的新情况下,科学进步参与了,然而也揭示了现代性的限度”[13]168,此乃是现代性的“生态负面”。
当然,批判归批判,吉登斯也开出了可能的药方:“数世纪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部分成就已经被人类与自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的生态恶化抵消了。……我们必须培养起‘对待生物圈的新的敏感度’,并且‘恢复人类与土壤、动植物生活、太阳以及风等的交流’”[13]154。
三、 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比较: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继承”
在吉登斯看来,在对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逻辑的分析层面,马克思是举世无双的。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也包括结构化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的,自然离不开马克思,稍微翻阅吉登斯的几本知名著作,就会时不时看到他在自觉不自觉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为自己所用,或褒扬或批判,足见他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视,换言之,这位思想家是借助于马克思来“激扬文字”。在现代性思想生态批判维度方面,吉登斯也对马克思有着很微妙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看待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尽管吉登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曾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首席顾问,但却对资本“并无好感”。他认为现代性的积极方面是因资本的强大“物化作用”而起,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也给人类制造出生态诘难,实现全球生态管理绝非易事,不但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遭遇的压力在加大,而且还因为生态风险和技术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充斥着争议[18]160。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又是由资本和自由市场的利益媾合造成的,他进一步说道,“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18]155。换言之,资本逻辑下的市场经济唯利是从,顾不上保护大自然甚至连开发式保护也很难做到,因为资本更多地关注短期收益而投资自然界的收益周期又很长,因此自然生态空间开发的“公地悲剧”就是必然。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确继承了资本批判的鼻祖——马克思关于资本反生态性的思想,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19]前言3,开启了对资本统治和资本逻辑生态批判的理论视域。
同时,尽管马克思早已清楚地意识到资本的反生态本性,但同时也看到了资本的历史性和文明化趋势。在这方面,吉登斯仍然传承了马克思,并没有大的“理论跳跃”。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发展不是始于创世之初,不是开天辟地就有”,资本是随着大工业一起得到充分发展的[8]120。也就是说,资本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逻辑演进的产物,其产生和消亡都不能由人为意志所决定,有着“安身立命”的客观规律,因此必须正确对待资本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尽管站在历史的高度观之,资本内含着逐利和反生态本性,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正“阶段性”凸显,对激活生产要素和提升生产力水平发挥着难以替代的“正效应”,诚如马克思所讲:“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0]。这就是马克思对待资本的态度:“总体性扬弃”。吉登斯继承了马克思“总体性扬弃”的态度,在其看来,马克思是举世无双的,他的著作对理解现代世界之塑造的资本主义至关重要[21]。
第二,如何看待现代性进程中科学的反生态倾向?前文已述,科学本是中性的,但吉登斯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加深并在没有过渡到后现代性之前,科学在资本逻辑下越来越“外生出”反生态倾向。“科学和控制的倾向无法完成合法化这个工作,……自然‘禁区’已经随着反思的发展和人为风险的出现被突破了。”[13]168因此,随着人类在科学主义的协助下,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没有一个人怀疑,在短短数十年中人类行动已经对自然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而且环境主义从一种边缘性关切已经受到几乎所有的考察者的严肃对待”[13]157。以此论及,在现代性进程中科学的反生态倾向问题上,吉登斯也进行了深刻思考,但吉登斯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和逻辑洞见,而是加以继承式发挥。因为在吉登斯之前,马克思早已“指出了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复杂相关的实践现实,洞见了‘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本质,预见了社会理性、人文理性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趋势”[22]。
第三,在现代性批判的生态意蕴上,吉登斯对马克思能否称得上超越?尽管在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方面,吉登斯对马克思有着很微妙地“继承”甚至创新发挥,但吉登斯作为英国布莱尔政府的顾问和智囊,他的任务主要是“改良”资本主义[23],而非“革掉资本主义的命”。因此,他倡导的生态批判及解决问题的理路,整体上仍在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内,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站在时代哲学的高度和使用现实批判的力度去挖掘生态问题的“深层病灶”。从此意义上讲,吉登斯算不上“革命”,只能说是“改良”,这就是他自己最根本的局限,尽管他曾高调宣称“在新的千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个‘幽灵在世界游荡’,——这个幽灵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生态激进主义”[13]155。以此论及,吉登斯是站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巨人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超越巨人,正如吉安富兰科·波吉指出:“吉登斯在各个方面都受惠于古典思想家”[24]。尽管吉登斯堪称享誉世界的思想巨擘,但站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他并没有超越马克思,而是仍在资本逻辑统治的制度框架内“打转”。
四、 基于二者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解读”
当前我们在生产力尚不算发达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肩负着生产力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使命”。虽然马克思和吉登斯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的现代性展开了生态批判,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生态问题也同样可能在中国“异地重生”,这一点决不容忽视。
其一,正确看待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力避现代性的生态悖论。在马克思和吉登斯看来,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制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推手;并且吉登斯进一步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和释放,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无处不存在着威胁”,尤其是生态威胁,在难以估计的生态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在当前阶段,现代性的悖论突出表现为生态悖论。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现代化仍是我们的时代使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物质内核,但经济增长不应是单求数量的“疯长”,而应建立在生态友好和环境良好的根基之上,正如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把“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也应创造一切可能的途径维护好公平正义,努力避免贫富差距悬殊,防止私人财富过度膨胀“挤伤”公共财富,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最大公共财富,关系着当代人和未来子孙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正确对待资本的“历史性”和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生态导向”作用。马克思和吉登斯均认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就在于以资本积累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他们又在具体思想上存在差别。尽管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不会出现他们批判视域中的生态危机,但绝不能说生态问题离我们很遥远,实际情况是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生态压力;尽管我们的国民积累在性质上也不同于吉登斯视域中的资本积累,但却同样面临着如何“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的难题。从正面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98,在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仍离不开资本的强大“物化力量”,其对调节生产要素和释放生产力潜能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从反面来讲,我们也应高度警醒,看到资本的逐利和反生态本性,积极管控资本的“深层不道德”。更为关键的是,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生态导向”作用,为其他形式的各式资本参与“生态投资”作出引导和表率。
其三,努力规避异化劳动与对自然资源进行确权,以期提高公众对自然生态空间开发的监督话语权。马克思深刻透视异化劳动的逆生态性,异化劳动造成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循环的断裂。资本主义国家维系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是对自然生态空间实施“私人占有”,在私有法权的护航下,为了最大规模地创生利润,资本家就自然而然地无情压榨工人,利用他们的“异化劳动”过度掠夺自然界,以期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哪里还顾得上生态后果和生态灾难。“前车覆,后车鉴。”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必须明确生态责任主体,防止无责属的“公地悲剧”,既要对自然资源进行确权,又要利用国家公权充分动员民众的力量对自然资源开发实行社会化监督。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健全自然资源的资产产权制度,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而且要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理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制度[25]。在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确权时,应优先考虑资本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股份制企业,便于公众拥有最初知情权和“过程监督”话语权。
其四,注重平衡科技的“复合作用”。马克思和吉登斯均批判科技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反生态倾向,因为原本客观中立的科技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很容易异变化成“科技主义”。然而,不管怎样讲,科技仍是第一生产力,当前国家间的竞争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水平,其在我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甚至决定着它们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因此,面对生态危机,“我们无法摆脱科学技术文明,不论它会触发什么样的‘绿色怀旧’”[13]165,但一定要注意规避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科技主义之反生态倾向,在“利用科技的正能量”和“限制科技的负效应”之间寻到平衡,驾驭好这头强大的“猛兽”为我所用。
一言以蔽之,“现代性的‘缺陷’向我们表明,它们是消极的乌托邦”[13]173,我们应该努力避免它们尤其要规避现代性的“生态负面”。诚然,包括生态困境在内的现代性问题毕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领域,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复杂情况,因为当代中国“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而且更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26]。
参考文献:
[1] 吉登斯.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 尹宏毅,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2] 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89.
[3] 郗戈. 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J]. 社会科学辑刊, 2010(1):30.
[4] 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47.
[5] 杨炯. 简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多元视阈[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0,12(6):118.
[6] 马克思.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 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61.
[8] 马克思.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9] 马克思. 相对剩余价值[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572.
[1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1] 马克思. 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2]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6.
[13] 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 李惠斌,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4] 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22.
[15]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52-53.
[16] 郎友兴.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143.
[17] 迈克尔·曼. 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M]. 袁亚愚,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556.
[18]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M]. 郑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9] 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0]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927-928.
[21] 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8:1.
[22] 徐岿然. 复杂实践情景中理性的多维渗透与自反[J]. 哲学动态, 2009(6):67.
[23] 陈学明. 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2):81.
[24] 郭忠华. “人类创造历史”——吉登斯的诠释与评价[J]. 浙江学刊, 2006(6):54.
[2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52.
[26] 罗骞.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6.
(责任编辑:付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