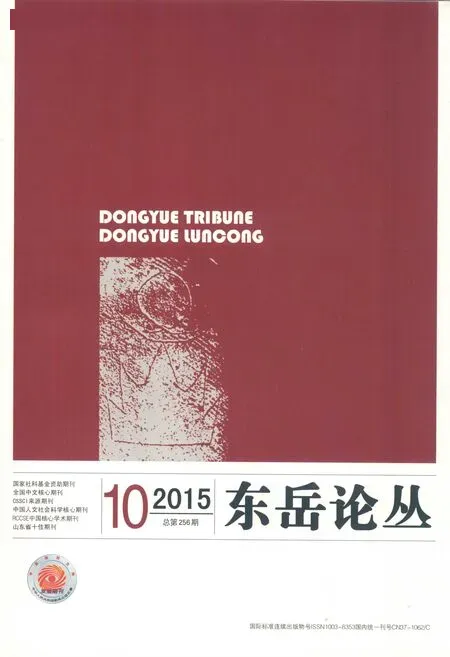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在明代的传播途径
杨 倩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文学研究
论《文心雕龙》在明代的传播途径
杨 倩1,2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是明代《文心雕龙》传播的主要途径。人际传播以藏书为基础,并延伸到书籍的借阅、馈赠和抄写,藏书家对诸多版本的整理、校对、纠正讹文的过程使书籍的传播具有了学术交流的性质。受商业资本的带动和政府废除书税等政策的影响,以私刻和坊刻为主体的商业传播成为明代图书传播的重要途径,但商业传播在促进《文心雕龙》传播的同时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出版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和文人市民化的审美转变在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中也有直观的反映。
明代;《文心雕龙》;传播;广告
作为一部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六朝文论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的历史影响除了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外,有利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渠道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明代是《文心雕龙》传播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文心雕龙》的存世版本仅有敦煌莫高窟的唐人草书残卷和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刊本。魏晋时期的文论多已亡佚,但《文心雕龙》却得以流传且发扬光大,直至成为当今显学,这与它在明代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大致分为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两种。人际传播主要是指书籍在人际之间的收藏、借阅和传抄,此以私人交游为主,多在范围较小的文人间展开,参与者不仅多具有藏书家的身份,而且其中一部分也是从事《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学者;商业传播以私刻和坊刻为主体,它扩大了《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商业本身的逐利性也给《文心雕龙》的接受带来些许负面影响。
一、《文心雕龙》的人际传播
在传播学中,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相对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个体间或个体与群体间发生的传播关系。书籍的人际传播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书籍传播途径之一,《文心雕龙》的传播方式以藏书、借阅、抄书、馈赠等方式为主,其中藏书为借阅和传抄提供了资源,借阅和传抄扩大了书籍的流通范围。
藏书是古代书籍、文献保存和传播的基础,也是书籍借阅和传抄活动的基础。先秦时期官书垄断,秦代“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至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的颁布,民间藏书才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行为。明清两代是中国藏书活动鼎盛时期,《文心雕龙》的部分研究者本身就是藏书大家。明代藏书分官方藏书、私人藏书、藩王藏书、书院藏书、寺庙藏书等众多门类,《文心雕龙》的藏书以前三种为主。明代私家藏书涵盖了贵族、士大夫、布衣、隐士等社会阶层,尤其是“嘉隆间,天下承平,学者出其绪余,以藏书相夸尚”①。在明代私家藏书的带动下,书目编制也空前繁盛,收录有《文心雕龙》的如:《文渊阁书目》,这是明代第一部国家藏书书目,仅录书名、册数,不录作者和卷数,《文心雕龙》在日字号第一厨;《行人司书目》,分经、史、子、文、杂6类,仅录书名及数,不录卷数、著者、版本,在“古文”类录有《文心雕龙》;《秘阁书目》,所录书只有册数而无卷数,《文心雕龙》在“文集”类;《万卷堂书目》,分为经、史、子、集,编为四部,仅录书名卷数和所撰人名氏,《文心雕龙》在“杂文”类。同时,明代最为著名的几大私家藏书书目,如叶盛的《菉竹堂书目》、陈第的《世善堂书目》、晁瑮的《宝文堂书目》、高儒的《百川书志》、徐惟起的《红雨楼书目》、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俱录《文心雕龙》。一方面,藏书家对待所藏图书的态度不一,清代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五类。他们中的一部分奉行书籍“秘不示人”、“鬻及借人为不孝”的祖训,不愿将自己所藏公开。有“秘书”称谓的《文心雕龙》是藏书家的心仪对象,值得庆幸的是,《文心雕龙》的收藏者多具学养,鲜有“掠贩家”式的藏家,其藏书或是为满足嗜好书籍的兴趣,或是为了学术研究,更多时候是两者兼有。因此,他们更希望将此书广泛流传,诚如佘诲云:“苦印传之不广,博古者致憾于斯,予偶搜罗诸壁间,如见良玉。又恶夫己而不人者也,遂梓布焉”②;当时的藏书界还有这样的情况:“今之人略有一得,则视为奇秘,不肯公诸人;偶有藏书,便秘为帐中之宝。”(《红雨楼序跋·文心雕龙》)又因《文心雕龙》“时罕印本,好古者思欲致之,恒病购求之难”,一些学者便希望以己之力使其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明代《文心雕龙》的收藏者多兼具研究者的身份,诚如吴晗所言:“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公家藏书则复寥落无闻,惟士夫藏书风气,则数千年来,愈接愈盛,智识之源泉虽被独持于士夫阶级,而其精雠密勘,著意丹黄,秘册借抄,奇书互赏,往往能保存旧籍,是正舛讹,发潜德,表幽光,其有功于社会文化者亦至巨”③。吴氏在这里明确说明了中国古代文人藏书对于书籍留存以及学术研究的价值。以曹学佺为例,他“尝谓二氏有《藏》,吾儒无《藏》,欲修《儒藏》与之鼎立。将撷四库之书,十有余年,而未能卒业也”④。福建的藏书大家陈第、谢肇淛、徐惟起也是明代著名的《文心雕龙》研究者。
借阅、馈赠和抄书是藏书活动的延伸。藏书者或因经济拮据,或由于书籍的版本是世所罕有的珍贵秘本等原因,使图书在彼此之间相互交换,辗转传抄,构成了书籍在人际间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梅鼎祚)尝与焦弱侯、冯开之暨虞山赵元度订约搜访,期三年一会于金陵,各书其所得异书遗典,互相雠写”⑤,钱谦益与徐惟起和曹学佺有“互搜所藏书,讨求放失”之约;陈第自述“自少至老,足迹遍天下,遇书辄买,若唯恐失,故不择善本,亦不争价值。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见书,抄而读之,积三四十余年,遂至万有余卷。”(《世善堂书目题词》)这些书籍中就包括了《文心雕龙》。此外,明人尤重手钞本,手抄活动多在学术修养层次相当的小范围文人团体间展开,藏书家多手自缮录,还通过一些途径共同校勘,《文心雕龙》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上述现象。梅庆生在其《文心雕龙音注本》卷首开列了30余人的《文心雕龙》校勘者名单,这些学者虽声望不一,所处地域南北不同,主要有福建、江西、江苏等地的藏书家中展开,但在研究中却能有无相通、取长补短,使得这一版本在当时就成了既是集大成又是奠基性的著作⑥。
使《文心雕龙》的版本更加完善,如徐惟起曾自言他与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皆有书嗜之好,且各有所长,“偶得升庵校本,初谓极精。辛丑之冬,携入樵川,友人谢伯元借去校,多有悬解,越七年,始复还……又校出脱误若干,合升庵、伯元之校,尤为严密。”⑦他们私交融洽,互相借阅、抄录《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谢兆坤的跋文可视为一篇《文心雕龙》收藏者的交游小录。
明代《文心雕龙》的藏书活动对《文心雕龙》的保存、流传以及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它在传抄中也经历了整理、校对、完善讹文脱字的过程,如《隐秀》篇,“谢耳伯借之钱牧斋时,牧斋虽以钱本与之,而秘《隐秀》一篇”⑧,冯舒言:“予从牧斋借得此书,因乞友人谢行甫录之……其《隐秀》一篇,恐遂多传于世,聊以自录之”⑨。可见,书籍的收藏、借阅、传抄不仅是书籍的传播和接受,更是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二、《文心雕龙》的商业传播
经济作为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础对于文学有直接影响。“经济力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同精神力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不是外在的、外加的,而是内在的、自生的……文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精神的属性,同时又具有经济的属性”⑩,文学的经济属性亦贯穿于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各个环节。在明代商业资本的带动下,明代书坊的商业化特征显著。明代洪武元年废除书籍税以及笔、墨税,确保了出版业的高利润,官刻、家刻和坊刻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商品流通领域。出版商对利润的追逐是一种理性的欲望,图书刊刻更广泛地融入到书籍的商业化流通中,极大地促进了《文心雕龙》在明代及其后世的传播和接受。
明代的图书刊刻机构包括官刻、家刻和坊刻,后两者构成了《文心雕龙》较重要的传播的途径。官刻是由中央、地方政府和藩府出资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明代官刻所刻书刊数量庞大,居历代之首。中央刻书多是学术价值比较高的经、史“监本”,或皇帝批准刊刻的书籍;明代南京和北京13个省下的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无不刻书。以徽州为例,单徽州府就有府署、具署、新安郡斋、紫阳书院、县学等刊刻机构,据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中统计,万历之前的官方出版物就逾三十种,《文心雕龙》亦在其中;明代藩府刻书多以藩王的兴趣为主导,出版图书校勘严谨,装订精良,多为精品。明代《文心雕龙》藩府刻本以隆庆三年(1569)鲁藩翻刻的冯本和万历三十七年(1609)宁藩的南昌刻本为代表;家刻是指私家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刻书,刻主多是文人、官员,他们希冀以一己之力传播书籍,弘扬学术。私刻本大都细致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坊刻是指由书商开办、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书坊的刊刻。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家刻和坊刻的主要区别标准,然而两者在商业性上也存有交叉,有的私刻也从事生产和销售,如毛晋的汲古阁。
明政府在图书出版方面的各项政策直接、有效地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废除书税极大地鼓励了刊刻业发展,《明史·本纪第二》载“洪武元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这与蒙古统治者有关书籍出版的“三十税一”、“二十税一”政策有宽严的差别。政府宽松的出版政策为书籍的刊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元代刻书管理严格苛刻,出版管理机构涵盖了中书省、秘书监、广成局、太史院和司农台等各级机构,官方图书的出版要经中书省审批,颁发相应的牒文后才允许刊刻,地方私人刊刻要先经过地方主审官员审阅,通过路这一行政机关逐级上呈审批才可出版,一些书籍也因为繁琐、严格的审批程序失去了出版和流传后世的机会。与元政府的出版政策相比,明代出版政策尺度宽泛许多,尤其是对于学术类的刊刻不做干涉。明初的民间刊刻业尚未成规模,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云:“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⑪。正统年间,私刻和坊刻逐渐兴盛,于嘉、万年间走向高峰,书铺如林,《文心雕龙》的版本多集中于这一时段,以嘉、万年间为最,如:嘉靖十九年(1540)汪一元私淑轩刻本,嘉靖二十二年(1543)佘诲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乐应奎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载尔本,万历七年(1579)张之象本,万历十年(1582)胡维新、原一魁序《两京遗编》本,万历十九年(1591)伍让本,万历二十年(1592)汉魏丛书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梅庆生音注本(初校本),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万历四十年(1612)凌云五色套印本等。其中,张之象本、王惟俭本、梅庆生音注本、凌云套印本、《两京遗编》本、《汉魏丛书》本、五家言本皆刻于万历年间。从地域范围上看,明代刊刻中心集中于南京、苏州、徽州、湖州等地,嘉靖、万历时期,刻本以金陵、吴兴、新安三地最精,书籍市场以苏州与金陵流通最广,对此,胡应麟曾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文心雕龙》的出版也集中于南方,这在程宽序中可见一斑:“岁弘治甲子,冯公允中以锓于吴,汪子一元再锓于歙。兹嘉靖辛丑,建阳张子安明将重锓于闽,以广其传,乃拜余属以序”⑫。
从市场的角度,明代商业资本发展迅速,国内整合经济体系形成,书籍的商业运作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文化现象和经济趋势。商人对利润最大化的诉求、文人市民化的审美转变和思想倾向,在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中都有直观的反映。明代中后期图书刊刻机构的市场性在进一步加强,为了牟利,“广告”或广告性宣传作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被出版商运用到了书籍刊刻、销售中的各个环节。不同类别的图书所对应的广告策略不尽相同。与现代广告相比,明代图书广告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如它的信息传递尚不具备连续性的特点,其广告也没有专门的代言人和固定的宣传费用,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性的商业宣传和广告意识,以达到介绍、宣传作品,及扩大影响、推动传播的目的。版本激增是明代《文心雕龙》刊刻的一大特点,本文以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5)冯允中刊刻于吴中之《文心雕龙》本为例进行说明:
天地间物,莫奇于书;奇则秘,秘则不行,此好古者之所同惜也。有能于其晦伏之余,广而通之,使不终至于泯没,非吾党其谁与归?梁通事舍人刘勰撰文心雕龙四十九篇。论文章法备矣。观其本道原圣,暨于百世,推崇其始,备陈其诀,自诗骚赋颂而下,凡为体二十七家,一披卷而摛辞之道具;学者如不欲为文则已,如欲为文,舍是莫之能焉。盖作者之指南,艺林之关键,大可以施庙堂资制作,小亦可以抒情写物,信乎其为书之奇也。
经史子传、诗歌文集大多前有序引,后有跋文。序位于作品之首,其作用在于“明作书之旨”,阐明著作的内容、创作动机、成书过程,版本流变的功能;跋列于作品之末,其内容“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以序跋文为载体对书籍进行宣传的题跋式广告在宋代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形式的图书广告。明代《文心雕龙》的序跋也体现出了广告性特点,刻主将书籍的信息有目的、有计划性地传递给消费者,这种带有说服性的信息传递不仅对广告主有利,也可使消费者对图书有更全面、直观的了解。
由冯允中序文可知,一、强调《文心雕龙》的“实用性”,即它在指导写作方面的价值。明人视《文心雕龙》为“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指导范围涉及诗歌、散文以及公文在内的所有的文体,因此“大可以施庙堂资制作,小亦可以舒情写物,信乎其为书之奇也”,这从何良俊的论述中就有所发现,“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谷《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冯允中亦在序中强调《文心雕龙》“论文章法备矣”、“学者如不欲为文则以,如欲为文,舍是莫之能焉”的。同时,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核心思想的《文心雕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应用上都与明代科举相契合,对于科举文章的写作有指导作用。明代科举应试类书籍是最畅销的图书类别之一,而这也是对《文心雕龙》卖点的宣传。二、突出名家名流对《文心雕龙》的评点,并对此加强宣传。信息来源的说服力和信息本身的说服力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序跋作者正承担了这种传达信息的角色。《文心雕龙》的序跋作者大都学养深厚、声名显赫,他们既是作品的阅读者,也是阐释者。他们的评论对消费者了解、接受作品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如载尔在序中言:“予尝闭关却扫,驰骋艺圃之场,文章自秦汉而上……圆融密致之体,峻结遒劲之格,足以启多识蓄德之助,擅登高作赋之奇者,惟梁通事舍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⑬,序者介绍了自己的学养,还结合阅读感受,认为《文心雕龙》乃“文苑之至宝,艺圃之琼葩”,其言辞与今天的广告颇为相似。更重要的是,经过名家评点的版本更容易得到大众认可,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元素,也是商家的主要卖点之一,以杨慎为例,杨慎一门地位显赫,且都为科举出身,杨氏本人更是贵为状元,他“批点《文心雕龙》,颇谓得刘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误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说破又宋人矣”⑭。他的评注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其在近百年的时间印刷近十版。三、凸显版本和印刷的优势。版本因底本、校勘、刻工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高下之别。因此,对版本的宣传也成为书业广告的重要内容之一。序跋文的作者会在文中有意识地强调书籍的版本特色,如“方今海内文教盛隆,操觚之士,争崇古雅,独是书时罕印本,好古者思欲致之,恒病购求之难……呜呼,此刻既行,世有休文,宁无同赏音者。”⑮虽说有很多所谓的古本、秘本是书商为牟利而随意增删而成的劣本,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版本对书籍销售的重要性。印刷工艺对图书的价格和销量也有直接的影响。明代木活字印刷成为一大特色,有书名可考的约有一百多种。吴兴闵、凌两家是明代套版印书的代表,其中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分朱、青、黄、古、黑五色印制,明代套色无出其右者。对此傅增湘云:“其格式则阑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萃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己”。(《涉园陶氏藏明季闵凌二家朱墨本书书后》)四、用对比、并举等能引起消费者关注和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的方式宣传。程宽在序中言:“文之义大矣哉,魏文《典论》,隘而未扬;士衡《文赋》,华而未精。若气扬矣,而法能玄传;义精矣,而词能烨烨:兼斯二者,其刘子之《文心雕龙》乎”⑯,将《文心雕龙》与其他书目并举,指出《文心雕龙》兼具诸书之长而避诸书之短,以此来刺激阅读者的购买心理。五、宣扬“奇书效应”。明代对“奇书”、“秘书”有特殊的偏好,各类文学体裁都显露出“奇”的特点,在小说中最为显著,如曾蓕在《剪灯余话》序中说“迩日必得奇书也”。《文心雕龙》序跋作者或有意为之或受时风影响,在序中也特别强调此书的“奇”和“秘”。如冯允中序云:“天地间物,莫奇于书,奇则秘,秘则不行,此好古者之所同惜也”⑰。张之象则说:“自非博极群书,妙达玄理,顿悟精诣,天解神授,其孰能兴于此耶?”将《文心雕龙》的“奇”直接解释为“天解神授”。可见,在明代《文心雕龙》序跋文中已经反映出了出版商“广告”意图和宣传目的,从某种层面上讲,这对《文心雕龙》的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图书的商业化也为《文心雕龙》的传播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明代刊刻业免税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吸引了众多商家投身其中。出版商与收藏家关注学术不同,他们以获利为直接目标,有的书坊为了利润而疏于校对和刊刻的精良,刊刻过《文心雕龙》的凌氏刻坊亦被指责:“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⑱;有的书坊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惜牺牲书本的质量,如郎瑛曾讲:“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获半部之价,人争购之”⑲;有的书坊甚至对版书、内容妄加改动,诚如清代黄廷鉴云:“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⑳。而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中也有上述问题存在。
[注释]
①李希泌,张椒华主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5页。
②⑦⑧⑨⑫⑬⑭⑮⑯⑰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8页,第748页,第751页,第751页,第729页,第731页,第745页,第731页,第727页,第725页。
③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④[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⑤[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页。
⑥以上观点参见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91页。
⑩许建平:《文学生成发展的经济动因》,《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⑪[明]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⑱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⑲[明]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
⑳[清]黄廷鉴:《第六絃溪文钞》,北京:中华书局,1985版,第1537页。
[责任编辑:曹振华]
I207
A
1003-8353(2015)10-0097-05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立项课题“明人对魏晋文论的接受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代表”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3DWXJ04)。
杨倩(1979-),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