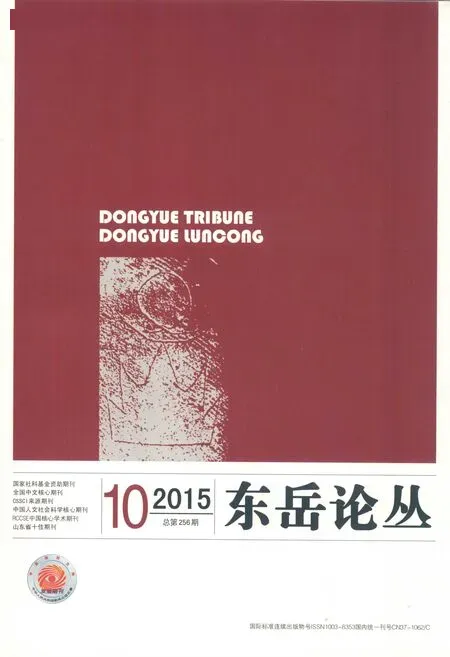文学视野中的“地方意识”
——以池莉的“汉味小说”为例
陈红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文学研究
文学视野中的“地方意识”
——以池莉的“汉味小说”为例
陈红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作为现代环境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概念,地方意识要求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生态和文化,并且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从而自觉地形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池莉的“汉味小说”不但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意识,还展现出作者对于地方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及其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地方意识;池莉;汉味小说
作家池莉以其表现市井生活的“汉味小说”独步中国文坛,其对地方文化的关注一直以来都是学界评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称其为具有地方意识的作家。然而“地方意识”一词在本文里的含义远比我们的一般性理解要复杂得多。它是现代环境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概念,它要求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生态和文化,并且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从而自觉地形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应该说池莉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意识;不仅如此,她还将其视为应对现代化的有力手段。事实上,池莉对武汉这座城市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地方性与全球化之争,而作家自己也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到当今国际学界围绕地方意识所进行的辩论当中。本文将利用“地方意识”这一概念所提供的理论视角对池莉的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汉味小说”进行分析,展示作家对城市环境以及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传统的关注,进而展现作家对于地方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及其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一
“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这一概念与西方环境运动几乎是相伴而生。环境运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兴起于北美和西欧。从其诞生到发展至今的几十年里,一些世界性的矛盾始终伴随着它的成长,厄休拉·海斯将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立场总结为:“对于全球关联性的拥抱和抗拒”以及“对全球视野的全情投入和对地方的乌托邦式再投资”①。海斯所说的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地方与全球之争,它们绝不仅限于环境运动内部或仅限于西方,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就“全球关联性”(global connectedness)而言,它实际指现代社会跨国跨区域的一体化趋势,比如跨国大企业所形成的全球性经济垄断乃至政治、文化强权,而由此引发的担忧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频现,并从七十年代开始涉及有关环境问题的讨论以及体现在环境文学作品中②。环境运动置身于如此重重矛盾当中,势必要在其中寻找一个更加具体的关注点,那就是生态环境。当美国的阿波罗八号和十七号载人飞船分别在1968年和1972年捕捉到“蓝色星球”的影像并将之公布于世时,它所催生的是一个关于地球的整体主义观点。但在一些人看来,以生态环境的平衡性和相互依赖性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观点似乎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来自核毁灭和生态灾难的现实威胁让他们意识到,“蓝色星球”固然美丽,却也正因其自成一体而更显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整体主义观点不得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则来自于人们重返地方的呼声。
“地方意识”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它与前现代社会的联系使得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对抗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的重任。或许是由于人们对于“地方”问题的研究具有多学科的特点,目前学界对于“地方意识”这个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人比较倾向于人类学者塞萨·洛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们赋予一块特定的土地以文化共享的情感意义并与之形成象征性的关系,而此关系亦成为个体及群体理解环境并与之相处的基础”。他认为地方意识“不仅是一种情感和认知的经历,还包括把人们与土地连接起来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实践”③。在本人看来,这个定义很好地把握了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紧密关系,更明确了地方意识所包含的地方传统的因素。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试图去定义,他们通过“地方意识”或类似表达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个体或群体都有必要“与其所在之地重建联系”④。美国小说家、诗人及环境活动家温德尔·贝里对回归地方的意义做如下解释:
如果(我们)缺乏对于地方的复杂知识,缺乏这种知识所倚赖的对于地方的忠诚,那么这个地方将不可避免地被滥用,直至被毁灭。更何况,一个国家的文化一旦缺少了这种知识和忠诚,便只是表面装饰。⑤
贝里无疑看到了地方意识所具有的生态和文化意义;而对于阿伦·奈斯等众多环境主义思想家来说,他们对地方意识的强调更有着与社会现代性相对抗的精神价值,因为它出自“一种不愿被某个硕大而非伟大的东西——正如我们的现代社会一样的东西——所吞噬的‘本能’反应”⑥。换用海斯的话讲,地方意识可以让人们“克服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疏离”⑦。
地方意识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似乎不容置疑,但其实它在学界引起的争论颇多,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否所有居住在某地的居民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获得关于该地的知识?二、他们作为本地居民的身份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三、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人们的身份是始终依附于某地还是体现为对于分散在多地的群体和文化的忠诚?四、在一切都飞速变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或有可能坚守那些特色鲜明的地方传统?五、是否小型的地方群体就一定会自觉地采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六、是否有可能在保有地方意识的同时拥有全球视野?池莉的部分武汉小说间接或直接地涉及以上这些问题,更在第四和第六点上与学界相关意见形成明确的对话关系。
二
池莉的地方意识在其作品中可以具体表现为故事中角色对诸如气候等自然环境的敏感,对于环境所决定的地方传统或习俗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对于环境和文化共同构成的地方所怀有的深厚情感等等。
池莉在多部小说中对武汉的天气施以浓彩重墨,极力渲染其极端气候带给人们的不适感。小说《致无尽岁月》里的叙述者暨女主人公如是描述: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下油凌的日子,但是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都是那么轻薄。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烈的寒潮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导致武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以致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⑧
主人公对于季节的感受是深切的;她不单有长期的切身的感官体验,更有对于影响气候的地理现象如西伯利亚寒潮和副热带高压的理性认知。在另一篇小说《汉口永远的浪漫》里,作家又借男主人公的视角把本该美好的春天大肆抱怨一通:“眼下武汉市的春天就很令人厌恶。突然地暴冷暴热。空气潮湿沉闷。法国梧桐的刺毛毛、柳絮和各种花粉面目肮脏,性欲张扬,弥漫在漫天的灰尘里,玷污和骚扰着城市居民”⑨。寥寥几句里,主人公对于天气的不满显而易见,而隐藏其后的则是作家对于温度和湿度这类天气现象与城市景观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不当结果的了解。
当然,仅仅只有对于环境的体验和了解还远远不足以形成我们在此所说的地方意识或生态区域主义所强调的“基于土地的敏感”⑩。这种敏感性要求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生态及文化,了解其中的好与不好,并投入全部的感情。池莉对于武汉这座城市无疑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以致于它那恶劣的气候在她的眼里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样还是《致无尽岁月》里那个不堪忍受武汉气候的女主人公,却道出了气候中蕴藏的自然奥秘:
我吃过了东西南北的蔬菜之后,才发现没有什么地方的蔬菜比得上武汉。是不是正因为寒冷,土地才有机会浓缩和积攒自己的哺育能力?是不是正因为湿润和火热,植物才能够进入最佳的生命状态?武昌洪山宝通寺附近的紫菜苔,在初春的时节,用切得薄亮如蜡纸的蜡肉片,急火下锅,扒拉翻炒两下。那香啊,那就叫香!真正的人间美味是无可言表的,惟有你自己来亲口尝一尝。⑪
小说中这段文字所展示出的情感只属于那些长期贴近土地、熟悉土地的人们。他们感激自然赐予的一切,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美味蔬果。
在柯克帕特里克·塞尔看来,这份对于土地的情感以及敏感只属于“土地上的居民”,这些人不仅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其优劣势了如指掌,并且懂得欣赏当地的文化,欣赏“因地貌特征而形成的且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的社会和经济形态”⑫。池莉作品中的武汉天气是构成城市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催生出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池莉以可谓细碎的笔触,再现了上世纪70、80年代武汉人夏夜当街大摆竹床阵的情形。小说中竹床的第一次现身是这样的:
太阳这时正在一点一点沉进大街西头的楼房后边,余晖依然红亮地灼人眼睛。洒水车响着洒水音乐过来过去,马路上腾起一片白雾,紧接着干了。黄昏还没来呢,白天的风就息了。这个死武汉的夏天!
燕华拎了两桶水,一遍又一遍洒在自家门口的马路上,终于将马路洒出了湿湿的黑颜色。待她直起腰的时候,许多人家已经搬出了竹床。⑬
两段简洁的文字把武汉夏天的闷热之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道出了竹床阵的来由。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活动基本都是围绕着竹床阵展开的:一家子围着竹床吃饭、看电视,街坊们聚在竹床上聊天、打麻将,孩子们在竹床间游戏。原本应该在室内的私密性极强的睡眠活动,因高温所迫,成为家家户户参与的集体户外活动。在池莉的笔下,酷热难耐的天气为街坊邻里提供了难得的社交机会,反而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乐趣。人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起后来利用空调等现代技术干预天气的影响,显示出更大的智慧。小说的最后,年轻的公汽女司机燕华“驾驶着两节车厢的公共汽车,轻轻在竹床的走廊里穿行,她尽量不踩油门,让车像人一样悄悄走路”⑭。角色在此表现出的体贴实际是对竹床阵这种自然形成的生活形态的极大尊重,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于竹床阵所代表的地方习俗的极大尊重。用生态区域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彼得·伯格和雷蒙德·达什门的话来分析,池莉作品中的武汉人认识到,“人类生命和其他生命都受到发生在当地的地球活动规律如季节、天气、水循环的影响”,因而想方设法,以“确保(对此地的)长期占用”;而作家对于他们的关注也表明,她充分理解“在地生活”的可贵⑮。
三
武汉的竹床阵在全国独一无二,其原因自然不是单单一个天气因素可以解释。池莉虽然没有深究其中的人文因素,却显然比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人物更加明白它的文化独特性,因此才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口吻描述本地人和外地人对此现象的迥异反应,末了感叹一句:“武汉市这风景啊!”⑯如今,那些曾经遍布武汉大街小巷的壮观的竹床阵早已淡出人们视线,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武汉市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早已被现代化的洪流席卷而去。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传统性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日新月异和全球一体化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前者也似乎不容置疑地成为这场遭遇战的失败一方。池莉的多部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地方文化与现代化之争,其中隐含的态度发人深省。
池莉在小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通过女主人公徐红梅,表达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忧患之情。徐红梅在武汉汉口的闹市区生活了四十多年,眼见着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汉口人爱逛的老字号专营店一个个倒闭关张,取而代之的是“把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和胭脂香水绫罗绸缎混在一个店子里卖”的百货商场,而随同这些老店铺一起消失的还有老汉口人悠闲自在的生活⑰。新兴商业模式抹杀了附着在不同商品及其产地乃至出售地之上的文化差异,正如米克·史密斯所指出,“现代性的‘全球化’现象意味着在一个以一致为原则的工具性经济体制内,消化掉所有的差别,所有的‘地方’。”⑱
池莉在她的“汉味小说”中常常以小吃和家常菜等武汉地方食品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一方面透过食品带给角色的由衷满足,表达角色的地方依附感乃至强烈的地方身份感,另一方面则借角色的怀旧之举或其与现实的冲突,表现地方文化在一体化经济模式的冲击下所面临的窘境。《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街坊们最喜欢聚在一起谈论武汉的早点小吃,王老太一口气可以数出上十种;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过早”这件事情上,无论上海北京广州还是国外的很多地方,“哪个城市比得上武汉?”而让老武汉人念念不忘的不单是早点的品种之多,还有那些遍布街头的老字号小吃店,因为它们可以满足小说中的老街坊们“满街瞎吃”的喜好⑲。池莉自然不能在她的这部背景设于1990年的短篇小说中讲述那些始自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与该作品的创作大致同期发生的事实:老字号纷纷倒闭,被连锁式早餐店取代;原本纯手工制作的传统小吃被迫进入从流水线到连锁超市货架的标准化程序。但作为读者,我们依然能够从小说中这段情节所散发出的浓烈的怀旧情绪中清晰地感受到传统饮食文化的衰落之势。其实武汉小吃所经历的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再熟悉不过的故事。史密斯在他的书中讲到,从前欧洲的公路旅行者可以充分体验道路两旁的风景和民情,而现代公路设计在追求“狭义的功能性”的同时,剥夺了司机们体验生活的机会⑳。同样,原本颇有讲究且带有一定社交性质的武汉人的“过早”活动被现代商业模式极大地功能化,成了一项简单的饱腹之举。
池莉小说中出现的武汉小吃或家常菜基本都采用当地当季的食品原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要吃就吃当季食品”的养生之道,也与生态区域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不谋而合㉑,因此可称得上既有利于健康又有益于环境。地方食品成为角色们世俗生活的一个重要点缀,乃至重要组成部分;但真正成为作品的核心,只有在《生活秀》这部小说中。该作品聚焦环境污染问题所引发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地方文化与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池莉将《生活秀》的故事置于一个真实的场景——著名的武汉夜市大排档吉庆街,并通过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环境、社会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小说的主人公来双扬是个地道的武汉女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吉庆街。在她十六岁因故被工厂开除后,就开始在街上摆摊卖油炸臭干子为生,后来改卖鸭脖子。故事开始时,来双扬的做新闻记者的妹妹来双瑗正计划着在节目中曝光吉庆街的扰民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问题。而故事中对于吉庆街的描述以及对其历史的交待,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来双扬。作为一个依靠吉庆街夜市大排档谋生的人,她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她一方面承认大排档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同情那些深受其扰的居民,另一方面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力。与之相比,妹妹双瑗显得不够客观,被指责为不懂现实,或是“只有主观意识,没有客观意识。”㉒来双瑗主张通过取缔大排档来达到彻底治污的目的,却受到了来双扬和故事叙述者的嘲笑,说明作家本人对于吉庆街的环境污染问题抱有一个复杂的心态㉓。
其实我们在《生活秀》中观察到的矛盾冲突绝不仅限于双扬和双瑗姐妹之间,甚至也不限于她们所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从一个更大的意义上讲,它是文化传统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吉庆街的夜市自存在以来,历经多次整顿取缔,却仍旧“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两者间的矛盾极其复杂。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有关一次取缔行动的描述,深入挖掘矛盾的根源。作家在这部分故事中以戏剧性的画面,展现政府与吉庆街之间的冲突场景。在政府一方,有“政府官员,戴红袖标的联防队员,穿迷彩服的防暴武装警察和消防队的高压水龙头”;在街道一方,有“卖唱的艺人、擦皮鞋的大嫂、各种身份的小姐……没有执照的厨师”等等,大家“纷纷抱头鼠窜。”在一片混乱之中,似乎只有来双扬保持着淡定:“来双扬从来不与取缔行动直接对抗。她呆在自己家里,坐在将近一百年的阳台上,抓一把葵花子嗑着,从二楼往下瞧着热热闹闹的取缔过程”㉔。面对政府来势凶凶的行动,来双扬这个女人以她的镇定自若,无声地表示着她的藐视,也更加符合作家努力为她打造的传奇式人物的特征㉕。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我们明白,来双扬对吉庆街形势的把握来源于实践经验,正如叙述者在文中所说:“吉庆街大排档就是这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又一次,取缔多少次就再生多少次。取缔本身就是广告”㉖。叙述者在这里表达的态度和来双扬的态度无疑是一致的。一次原本严肃的整治行动就这样在作家的导演下演变成一场闹剧。作家借此嘲讽政府采取行动时的简单粗暴,同时肯定以来双扬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实际需求;只需简短的一句话,“这就是人们的吉庆街”,作家的立场便显露无遗㉗。
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句话中的“人们”指的是谁?难道我们能否认,在吉庆街这样一个人员混杂、矛盾重重的小社会里,不同的人群势必有着不同的需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文本。在这句话的上文中,叙述者给我们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吉庆街,它有着自由随意的气氛,“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让所有来到此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心情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吉庆街所代表的是武汉当地老百姓所崇尚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媒体在分析政府的取缔行动屡遭失败的原因时所说,“很多市民潜意识认为,越是在马路上,越能体会到那种平凡味道;越是在马路中央,越能显示大众化”㉙。可见,小说中的“人们”一词实际是文化传统这个抽象概念的具体表达;因为文化传统,尤其《生活秀》这部小说展现出的武汉的市民文化传统,恰恰反映在无数像来双扬一样的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来双扬在吉庆街享有“偶像的待遇”,其传奇般的形象是作家赋予的,反映出作家对她以及像她一样为生存而努力打拼的“人们”所怀有的敬意,也反映出作家对文化传统的重视㉚。
在《生活秀》中,我们看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鸭脖子一类的地方小吃和大排档主营的家常小炒等地方特色食物,以及当地人极具文化特色的饮食习惯,竟然成为吉庆街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具有高度的文化和生态敏感性的作家池莉,在吉庆街这个事件里,似乎更多地倾向于文化传统保护,而非环境保护。对此现象,我们该做何解释?在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池莉的“新写实主义”立场上来,必须看到作家从此立场出发,对世俗生活所给予的关注乃至提升;正如戴锦华指出,“在池莉的现实景观中,烦恼而琐屑的日常生活几乎具有了某种圣洁的意味。”㉛换言之,作家承认日常生活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的一部分,并投之以最深的敬意。这份以世俗生活为乐的态度正是武汉市民文化的特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池莉在《生活秀》中会选择支持来双扬和吉庆街所代表的市民文化传统。而且作家在吉庆街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与其生态敏感性并不矛盾。她选择的前提在于她充分理解目前吉庆街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的根源之所在,因此希望政府能拿出更合理的办法,在解决吉庆街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当地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
《生活秀》所展示的武汉地方文化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作家池莉的眼里,它原本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它之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与人们针对这一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商业化运作大有关系。像吉庆街一样的夜市大排档在武汉市还有很多,其前身就是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出现的竹床阵。最先是一家人围着自家竹床吃,后来一部分下岗工人开始制作一些卤菜小炒之类的家常菜卖给路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以此为谋生手段,发展出一个又一个的颇具规模的夜市。到了小说里的吉庆街的这个阶段,又引进了街头艺人等,进一步招徕生意。其实书中描写的吉庆街还只是其商业化的初期,还有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商业扩张行为尾随其后。事实上,吉庆街在池莉的这部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的联合推动下,早已从武汉市的众多夜市大排档中脱颖而出,俨然成为武汉地方文化的一个地标。来双扬每晚只卖十五斤的鸭脖子,如今在遍布全国各地的专卖店和超市中出售,销量难以计数。这其中因机械化规模生产、食品包装和长途运输等造成的生态压力不容小觑,因为此类跨地区的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影响范围上,都远远大于为满足本地居民所需而进行的规模有限的同类活动㉜。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为了彻底整治吉庆街的脏乱差,已从2009年开始,着手把整条街集体搬迁至一个现代化超大型购物中心内,该项工程已于2011年底完成。面对这些变化,我们有理由担忧,吉庆街会因其商业化的发展而丧失宝贵的地方文化传统,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危害。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当现代化及全球化以势不可挡之势向我们奔袭而来,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是否必受其害?我们能否在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寻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作家池莉所拥有的地方意识能否让她在珍视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坦然面对新时代带来的挑战?
四
经济全球化对吉庆街所代表的地方饮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无论是地方食品本身,还是与之相伴的饮食习惯,都十分依赖于具体的地理-物理环境或“地方”。但在我们为此指责经济全球化之前,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文化传统”中的“传统”一词。我们在论及某地的地方文化时,常常会用到“传统”这个词,这是否意味着该文化与该地之间有着超越时间的、永久性的联系?答案自然是“不”。因为无论这个文化多么独特,也无论这个地方多么与世隔绝,其传统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不难想象,像武汉这样一座有着悠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的大都市,从其诞生至今必定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从夏夜里的竹床阵到夜市大排档,这个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那曾经的夏夜景致,当那一排排首尾相连的竹床阵悄然消失的时候,人们或许会感叹于一个特色鲜明的地方传统的消失。但事实是,这个旧的传统只是被一个新的传统所取代,热热闹闹的夜市大排档能提供武汉人最爱的家常小炒和最难以割舍的世俗生活氛围,同样具有浓浓的地方味道。可见,地方传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丰富和更新着自己。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地方传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高速推进的今天已越来越难以生存。人们习惯用“小市民”一词来形容武汉人,池莉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这些小市民,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不思进取,容易满足于现状,和现代性“对未来的痴迷”背道而驰㉝。那么以小市民生活为中心的武汉地方文化传统是否有可能和现代化相结合?池莉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故事中的成功商人康伟业和漂亮女孩时雨篷坐在一家国际连锁大酒店的餐厅包间里,吃着他们从吉庆街叫来的“无比新鲜无比火爆的家常菜”,感觉到久违的轻松和痛快㉞。此情此景中,当角色们从洁净时尚的环境和地道美食之中分别获得自己的所需时,地方食品与国际性的潮流文化之间在尝试一种相互间的妥协。
多琳·梅西率先在其著作《空间、地方和性别》一书中提出她对所谓“地方依附”的看法,之后劳伦斯·布依尔又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加以重申:
对某一地方的依附……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使得我们既可以想象(个人)与某个特定的、有界限的地点紧密相连,也可以想象一个都市内区域如何被全球人口流动以及资本流动所塑造和再塑造,同时仍然保持着可塑却鲜明的地方意识。㉟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布依尔的观点:一个有着深厚的地方意识的人不仅忠实于该地及其传统,而且还能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认识到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就吉庆街夜市而言,它在整体搬迁之后保留了原有的地方文艺表演和一部分室外就餐区,显然也试图在地方传统和现代商业以及舶来文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至于移植后的传统是否能满足市民的文化心理需求,区域内的环境整治是否掩盖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危害,这些问题另当别论,但无疑都值得我们深思。
吉庆街的改造为梅西和布依尔对地方依附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虽然不一定成功,但其设想与加里·斯奈德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即“在国际多元化和强烈的地方意识之间寻找平衡点”㊱。池莉虽然没有在她的小说中为吉庆街的未来指示路径,但她显然也在思考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做才能不被彻底地淹没在全球化的汹涌波涛之中?池莉在小说《化蛹为蝶》中,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她的答案。故事中的主人公小丁自小在孤儿院长大,多年以后,已是企业家和慈善家的他投资承包了往日寸草不生的孤儿院,将它迁移到城郊一处“乡野味很地道”的荒地,与孩子们一起载树垦荒,养鱼种菜,享受鸡鸣狗吠的田园生活㊲。孤儿院从此变成了他和孩子们的天堂,而他们生产的绿色无污染的鸡蛋和蔬菜也成为附近的一家外国公司高价收购的抢手货。故事的结尾写道:“(小丁)看书听音乐种菜钓鱼在院子里同孤儿们叫喊着跑来跑去。……他……觉得自己人生的状态好得无与伦比。”㊳小丁由衷的满足来自他听从心声的选择,也来自内心选择与现实之间的幸运对接。与小丁有着类似感受的人物还有此前提到的《致无尽岁月》里的女主人公。故事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身为医生的她已步入中年,事业有成,带着她学生时代的好友来到她的家,一栋位于郊外的别墅。面对朋友的艳羡,她只说这其实就是个农舍,因为里面的一切都是“最简单和最普通的”,但在她的感觉中,唯有这个远离城市喧嚣、贴近土地的地方才能让她感受到“生命的挣扎”,即最真实的生命体验㊴。这部小说是池莉少有的半自传性质的作品,故事中的女医生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的代言人,表达了作家身处20世纪之交的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所感受到的压力,因此她渴望回到孩童时熟悉的简单质朴的生活,仿佛唯有此才能做回自己,也才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向前。更为重要的是,她已将自己深深扎根于武汉这座她所熟悉并出于本能紧紧依附的城市。故事中,女医生的朋友试图劝说她离开“可恶”的武汉,与他一起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女医生在心里对她的朋友讲:
从何光亮的解读来看,“互相帮助、互相补强”将是未来瓮福集团和开磷集团协同发展的一条基本准则,两家公司也将进入“融合发展”时期。但双方仍有可能保持各自最大的独立性,与此同时给予对方最大的帮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协同一致应对市场上的变化。但不管怎样,双方的关系已经由“掰手腕”走向“一家亲”。
我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经常被雄辩者说得频频点头。但是我坚信我的本能。我本能需要什么我就离不开什么,这不是道理可以说得清楚的。也不是恶劣的气候和恶劣的人文环境可以与之匹敌的。个体生命的需要在关键时刻可以战胜一切!我坚信。㊵
这段话表达了叙述者与作者共有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我们在《化蛹为蝶》中的小丁身上感受到的一种态度;它建立在一种强烈的地方意识之上,其蕴含的生态意义和精神价值值得关注。塞尔认为生态区域主义对于我们每个个体的要求就是解放自我,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摆脱“外界对个人自由及选择的限制”,同时贴近土地、集体、集体价值等一切能够“促进个体发展”的事物㊶。塞尔既强调个体和个人自由,又重视集体和集体价值,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或者至少重点不明确,但如果我们把他的观点放置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他所说的“个人自由和选择”实为个体出自本能的需求,“集体和集体价值”则是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相对并日渐受其侵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而这两者都与土地相关,都来自人们对生养之地的依附和敏感。因此,当池莉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以及对土地的热爱与感激之情时,她其实是在告诫人们:无论我们周遭的世界怎样变换,我们都必须在心里为地方的和传统的东西保留一块圣地。值得注意的是,池莉眼中的地方及其传统并非仅有抽象的精神意义。当小丁和女医生在不同程度上回归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时,他们实际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减少日常消费环节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如果就此认为池莉是彻底反对现代化的,并不正确。事实上,池莉在小说外的一些文字媒介,比如散文《武汉话题(二十七则)》中,曾清楚地表示自己期待武汉重拾旧日雄风,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迎来一个现代化的未来。为此她说:“武汉市肯定是在变了,我对这一点充满了信心。”㊷评论家於可训认为,池莉从其早期创作开始即表现出明显的崇尚自然的倾向,之后这种倾向逐步“发展成一种‘知足’、‘能忍’、‘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以“调解日益膨胀的人欲”瑒瑣。从上段提到的《化蛹为蝶》和《致无尽岁月》这两部作品来看,於可训的观点显然成立,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对于池莉而言,“顺乎自然”意味着不仅要遵循自然法则,还要尊重现实;而她眼里的现实既包括武汉的世俗文化传统,也包括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客观地讲,池莉的武汉小说在地方意识和全球意识之间更多地表现出前者,但她的现实主义态度、她对现代化必将带来的改变所持有的较为开放的姿态,使她最终有可能跨越地界和国界,拥有真正的全球视野。
池莉以她的武汉故事激发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与生养我们的土地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与它的环境和文化以及它的过去和未来有着怎样一种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在其中至少有一个会是:在我们身处地球村并随着它一起改变和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可忘记孕育我们的土地和滋养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只有在它们的陪伴下我们才能捍卫自己的个体自由,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带给地球的负担。
[注释]
①④⑦Heise,Ursula K.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p.21,p.28,p.28-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②海斯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一些表达反全球性垄断观点的文学作品,它们包括西里尔·科恩布鲁斯、弗雷德里克·波尔的小说《太空商人》(1953)、艾伦·金斯伯格、维廉姆·伯勒斯以及托马斯·平琼等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而真正在此观点中注入环境主义思想,还要从爱德华·阿比的《故意破坏帮》(1975)开始。
③Low,Setha M.“Symbolic Ties that Bind:Place Attachment in the Plaza”,Place Attachment,eds.Irwin Altman and Setha Low,p.165,New York:Plenum Press,1992.洛在他的定义中使用的是“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一词,而不是“地方意识”,但两个词通常可以互换。
⑤Berry,Wendell.“The Regional Motive”,A Continuous Harmony:Essays 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p.68-69,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⑥Naess,Arne.Ecology,Community and Lifestyle,trans.David Rothenberg,p.14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⑧⑪㊴㊵池莉:《致无尽岁月》,《池莉小说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24—528页,第543页,第552—553页,第542—543页。
⑨池莉:《汉口永远的浪漫》,《武汉故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⑩学界有关地方意识的讨论常涉及多个概念,“生态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是其一,此外还有“居所”(dwelling)、“再栖息”(reinhabitation)以及“土地伦理”(a land ethic)等。虽然武汉市是一个行政区域,但出现在池莉作品中的武汉有着鲜明的地理特点,尤其是自然地理特点,可以被视为一个生态区域。因此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还会用到一些生态区域主义的观点。句中引文的原文是place-based sensibility,出自生态区域主义的倡导者米切尔·托马肖,见Thomashow,Mitchell.“Towards A Cosmopolitan Bioregionalism”,Bioregionalism,ed.Michael Vincent McGinnis,p.121,London:Routledge,1999.
⑫㊶Sale,Kirkpatrick.Dwellers in the Land:The Bioregional Vision,p.42,p.47,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85.
⑬⑭⑯⑲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武汉故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第16页,第9页,第13页。
⑮Berg,Peter&Raymond F.Dasmann.“Reinhabiting California”,Home!A Bioregional Reader,eds.Van Andruss et al.Philadelphia,p.35,P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0.
⑰池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武汉故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⑱⑳㉝Smith,Mick.An Ethics of Place:Radical Ecology,Postmodernity,and Social Theory,p.209,p.161,p.154,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㉑该观念提倡谨慎地使用当地自然资源,供当地人所需,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长途运输食品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
㉒㉔㉖㉗㉘㉚池莉:《生活秀》,《池莉近作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第245页,第246—247页,第247页,第247页,第244页。
㉓作家在该小说中经常采用“自由间接思想”的叙事手法,将叙述者和来双扬的观点合二为一。以下是上句引文所在的完整段落,是运用自由间接思想的典型例子:“来双扬怎么回答(她)妹妹的一系列质问呢?来双瑗所有的质问只有主观意识,没有客观意识,(她)脑子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想透,却还有强烈的教导他人的欲望,这下可真是把来双扬累着了。”
㉕评论界普遍认为,池莉自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以来,进入了创作的新时期,即“新写实主义”时期。但就《生活秀》这部作品而言,尽管它发表于2000年,理应属于“新写实主义小说”,来双扬这个角色却有着明显的传奇色彩。
㉙《吉庆街:“丑小鸭”变“白天鹅”》,荆楚网,2002年9月14日。
㉛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㉜大量研究已表明,跨地区的经济活动会产生诸如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等问题。章锦河在他的文章《商品包装的经济生态效益研究》中,以商品包装为例,说明用于非本地市场的包装比本地市场所需的包装成本更大,造成的污染也更大。见章锦河:《商品包装的经济生态效益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㉞池莉:《来来往往》,《池莉小说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㉟Buell,Lawrenc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p.77,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该段引文为作者自译,同时借鉴了刘蓓的译文,见《环境批评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㊱Snyder,Gary.“Bioregional Perspectives”,Home!A Bioregional Reader,eds.Van Andruss et al,p.20,Philadelphia,P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0.
㊲㊳池莉:《化蛹为蝶》,《武汉故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第39页。
㊷池莉:《武汉话题(二十七则)》,《池莉文集4:真实的日子》,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版,第165页。
瑒瑣转引自贾万钟,聂一:《地域文化与文学发展:於可训教授访谈录》,《湖北日报》,2001年4月19号。
[责任编辑:王 源]
I207.42
A
1003-8353(2015)10-0070-08
陈红(1967-),女,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