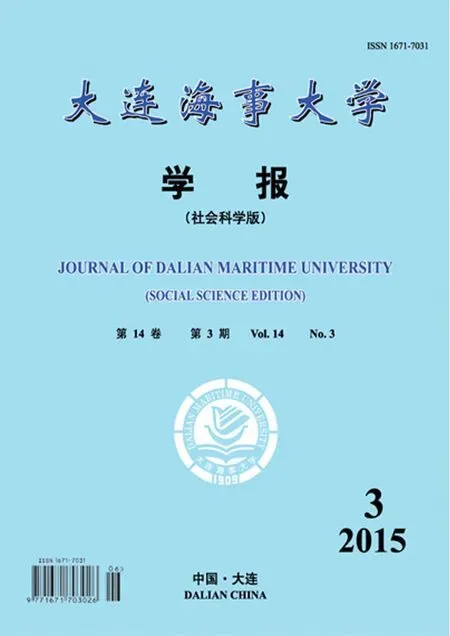毛姆与张爱玲的性别意识对比
郑素华
(福州大学 应用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福州 350002)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创作了20 多部长篇小说、32 部戏剧、120多篇短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游记、随笔和回忆录,都广受读者喜爱和好评。但是他的作品在评论界和文学史上却不受重视,甚至备受冷遇,这就是毛姆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毛姆问题”。
国外评论界对毛姆及其作品的研究著作数量非常少,大多数仅局限于对毛姆的生平介绍。在我国,毛姆的研究在1978年以后才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我国学者对毛姆作品的研究大致是从存在主义角度、精神分析角度、对毛姆本人的解读、形象学角度、创作手法角度和女性主义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的,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把毛姆及其作品同莫泊桑、庄子、张爱玲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其中又以与张爱玲及其作品的比较研究为重点和热点。
张爱玲,民国时期临水照花的传奇女子,她的作品受到无数读者和评论家的追捧。学者从文本解读、传奇人生、美食服饰和书信译著等方面对张爱玲进行了研究。而毛姆和张爱玲的比较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多,如论文《试论毛姆与张爱玲创作的异同》《论毛姆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与毛姆小说主题比较》[1-3]等,研究点普遍集中在两者相似的人生经历、对“人性趋恶”的共识、作品中呈现的畸形的婚恋观、不可抗拒的原欲对人性的控制,以及反高潮的叙事结构上。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于毛姆的研究并未有新的突破,笔者认为在毛姆和张爱玲的对比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毛姆和张爱玲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对异性的贬义性书写,出于对异性的偏见,毛姆和张爱玲都试图在作品中尝试构建一个同性主宰的世界。然而毛姆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始终无法摆脱“情欲”的困扰,这里的“情欲”也就是女性的象征。而张爱玲作品里的女性,在成为“男权世界”的主宰者之后,幸福快乐并没有来临,余下的只有精神的疯狂和情欲的折磨。那么毛姆和张爱玲为何对于异性有着如此的偏见和抵触呢?本文将从二者的出身背景、成长经历、情感生活以及两位作家分别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探讨毛姆和张爱玲性别偏见的根源所在。
一、毛姆笔下的性别书写
毛姆笔下的异性书写大都是负面的,他作品中的女性常以荡妇或伪善者的形象出现,她们为了世俗的名誉、财富或情欲来纠缠男人。例如《刀锋》中一心追求物质生活的伊莎贝尔,“我年轻,我要生活得有意思。凡是人家干的事情,我都要干。我要参加宴会,我要参加舞会,我要打高尔夫球,我要有马骑。我要穿上等衣服”[4]。还有在丈夫和儿子车祸身亡后,过度追求自由、放纵自己堕落的索菲。《情场失意一例》里的凯斯特兰子爵夫人与外交界最有才华的年轻人杰克·阿尔蒙的风流韵事暴露后,为了不失去财富、社会地位和安定的生活,选择了继续维持和丈夫的婚姻。
另外在毛姆的笔下还描写了许多“女结婚员”的形象,她们走进婚姻的目的,就是获取一张长期的饭票。《彩色的面纱》里的凯蒂,为了不被母亲数落,为了赶在妹妹多丽丝结婚前出嫁,匆匆答应了细菌学家瓦尔特的求婚,虽然瓦尔特保守冷漠而不善交际。《赴宴之前》里的女主人公米莉森特,嫁给了年近四十、有不错职位的哈罗德,原因就是到了二十七岁,没有其他人愿意娶她了。这两个女主人公走入婚姻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是她们依旧不满足。凯蒂在婚后不久,就和道貌岸然的查理私通。而米莉森特无法忍受哈罗德的酗酒,将其谋杀,并编造谎言说哈罗德是酗酒后出现幻觉而自杀。
既然女性都是如此的贪婪、虚伪而且耽于情欲,于是毛姆便试图在他的作品中构建男性主宰的世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为了追求虚幻的理想,他抛妻弃子,只身来到巴黎学画。对真心帮助他的恩人——施特略夫,思特里克兰德却恩将仇报,与他的妻子勃朗什私通,并霸占了恩人的私人画室,对勃朗什始乱终弃,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勃朗什·施特略夫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5]231在思特里克兰德看来,凡是对他有任何需求,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要求的女性,都是可怕的,都是他想要逃离的。“要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你,除非连你的灵魂也叫她占有了,她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女人是软弱的,所以她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统治欲,不把你完全控制在手就不甘心……你还记得我的妻子吗?我发觉勃朗什一点一点地施展起我妻子的那些小把戏来。她以无限的耐心准备把我网罗住,困住我的手脚。”[5]229-230“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谈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女性。但是一旦我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我就准备做别的事了。……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对她们提出什么事业的助手、生活的陪伴这些要求非常讨厌。”[5]228-229可以说,思特里克兰德说出了许多男人,当然更是毛姆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最后,思特里克兰德定居远离文明社会的塔希提岛上,遇到了一个给予他一切却从不向他索取任何回报的土著女人——爱塔,创造出一幅又一副的惊世之作。因为在他的作品里“人的最原始的天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眼前,你看到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恐惧,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5]334。爱塔是一个化身为“奴”的女人,是男权世界所期待的完美女人,也是毛姆追寻了一生而没有寻获的完美女性。在思特里克兰德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他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是在他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令人向往的伊甸园,其实就是男人与女人有着和谐关系的乐园。这幅伊甸园作品的消失,也正说明了毛姆认同了构建绝对男权世界的失败。
二、张爱玲笔下的性别书写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对男性大多进行了去势化的书写,她笔下鲜有内外兼备、强健伟岸的中国传统男性形象。《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怨女》中的姚二爷“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人缩成一团”。《花凋》中“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的郑先生,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留情》中的米先生,“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地像个婴孩”。
除了这些肢体残疾的男性形象,张爱玲作品中还刻画了众多幼稚贪婪,在情感上虚伪狡诈、无真情可言的有精神缺陷的男性。《花凋》中的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乔琪乔“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不成材了”,最后干脆靠妻子卖淫来养活他。《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在妻子和情人间徘徊。还有终日游手好闲、荒淫无度、五毒俱全的姜季泽,长期冷落正室、包养姨太太、强奸丫鬟的席五爷,《多少恨》里自私虚伪、卖女求荣的虞老头。
这些丑陋的男性形象的刻画彻底颠覆了传统对于男性神话的书写,把父权制文化的丑陋揭露无遗。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无疑给女性带来了无限的悲剧。那么如果让女性获得话语权,独立建构世界,会怎么样呢?林语堂先生曾说过,“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残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不过后来媳妇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达到这个经久盼望的高龄,那实在是荣誉而有权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来的”[6]。当中国女性掌握了家庭中的权力,往往也以类似的放纵和残酷来对待他人。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未出嫁时自由自在,嫁入姜家后备受压抑和屈辱。她既没有中国传统女性“三从四德”的美德,也没有办法用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为自己争取自由与幸福。在长期的性压抑和强烈的金钱欲望下,她一步步走向了人性恶的深渊。当她由媳妇熬成婆时,却比她周遭的男人更恶毒,她诱使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吸食鸦片,探听儿子和儿媳的私房事,并到处宣扬,使两个儿媳含羞而死,儿子终生不再敢娶媳妇。女儿长安恋爱时,她也竭力破坏,到处污蔑女儿的清白,最终断送了长安的幸福。是什么导致了曹七巧性格的扭曲变态呢?无疑是对黄金的欲求,是封建等级制度和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长期压抑。曹七巧是可恨的,但也是可怜的,曹七巧的恶也正是女性反抗男权中心主义意识的觉醒。但是与19世纪欧洲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中国女性的这种反抗也依旧是软弱无力的,最后曹七巧在自己主宰的小天地里,仍然是走向了毁灭。
三、性别意识的成因
1.不幸的童年
毛姆与张爱玲有着非常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出身于名门世家。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名臣,曾外祖父是李鸿章。在晚清时期,与张爱玲血脉相近的亲属,个个非富即贵。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张家很快就没落了。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靠变卖祖产过活的贵族家庭。而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几年,张家就迅速陷入了窘迫。但是记忆中贵族的优越生活已经在张爱玲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贵族的血液也永远流淌在张爱玲的身体里。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的,“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7]57。
可以说,张爱玲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出身,并对家族的没落耿耿于怀的。随后,新派的母亲由于不满旧式父亲抽大烟、逛窑子,终于与父亲离了婚。随着继母的来临,张爱玲的童年生活可谓是没有半点温情可言。不堪忍受父亲和继母虐待的张爱玲,终于逃到了母亲家里。可是思想西化、手头拮据的母亲也没有给他无私而深厚的母爱。
同样的,毛姆的出身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毛姆的祖父是英国律师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至今他的大量法学著作还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毛姆的父亲是个牙医,母亲虽是个孤女,却有着高贵的出身,是巴黎社交界的名人。毛姆小时候,母亲经常在家里举办各种政要名流云集的晚宴。毛姆因此继承了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绅士文化。然而毛姆八岁时,母亲就早逝了。十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三个哥哥又都在异地求学,毛姆只好被寄养在谨小慎微、经济拮据的叔父家。由于毛姆有口吃的毛病,童年又失去了母亲的庇护,这份痛一直隐藏在毛姆的心中。毛姆晚年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她的逝世对我是一个创伤,五十年过去了,它还没有完全愈合”[8]452。
童年的创伤性经历,对毛姆和张爱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海明威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形象,都含有她父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是张廷重的化身或投影。”[9]懦弱而冷漠的父亲,深深地刻在张爱玲的心中,自然她作品里便很难塑造出温暖而正直的男性形象。而母爱的缺失,使毛姆没有感受到女性最伟大无私的母性光辉,对于女性自然是很难爱起来,偏见也在所难免了。
2.不幸的情感生活
毛姆的爱情婚姻之路是十分坎坷的。他曾经与著名剧作家亨利·亚瑟·琼斯的女儿苏·琼斯(1883—1948)维持了八年的恋情,他明知琼斯同时和多个其他男人保持着性关系,他还是决定向她求婚,可是却遭到了琼斯的拒绝。求婚的受挫严重打击了敏感的毛姆,他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实际上,毛姆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是政府要严惩的有伤风化的行为。为了隐瞒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毛姆在1916年和辛瑞叶结了婚。这段弥漫着争吵、威胁和恐惧的婚姻终于在1927年以离婚收场。垂暮之年的毛姆还对辛瑞叶心存怨恨,口出怨言,“我当时是那样的虚荣和愚蠢,竟然相信了她……而她却毁了我的一生,她使我陷入了绝境”[10]。婚姻和恋爱生活的不顺利,以及异于常人的性取向,使毛姆产生了强烈的厌女情绪,并把有女性参与的婚姻当成了人生的枷锁。
而张爱玲在情爱之路上也是遇人不淑,所托非人。张爱玲受母亲和姑姑影响,有“女权思想”。张爱玲曾谈到祖母让姑姑穿男装,称“毛少爷”。李家的小辈也叫我姑姑“表叔”,不叫“表姑”。“我现在想起来,女扮男装似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7]56然而不能脱俗的是,张爱玲的内心却追求世俗的爱情。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在1943年年底,张爱玲说:“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还是欢喜的,从尘埃中开出花。”1944年8月他们写下婚书,1944年11月胡兰成前往武汉,移情别恋周训德,对张爱玲的爱开始降温,后来的两年半基本是分分合合的状态。直到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才彻底了断了这份感情。有着女权意识的张爱玲,没有见到完美的婚姻,也没有遇见完美的爱情。看透男女情爱世界的张爱玲,发出了“人生就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的感叹。“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11]对于这样的婚姻,张爱玲是不屑的,对于这种婚姻里的男性,张爱玲是不耻的。可是张爱玲就是和这样的男人纠缠了许久,她所渴望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生活就如镜中花、水中月。在现实生活中,明知不可为,却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张爱玲是悲凉的。然而,她的文字终归是毫不留情地展示了这种悲凉和无奈,以及对男性深深的失望。
3.思想史语境里的阐释
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如何通过人们的思想,作用于或反作用于“文学”?文学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背后没有思想;文学现象不仅是现象,背后还有思想。[12]毛姆与张爱玲性别观的形成除了与他们童年的经历、婚恋生活有关,也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的思潮。
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客厅里的知识女性发起了女权运动。虽然她们在妇女的受教育权、监护权、离婚权、财产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仍然是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进行的,其艰难可想而知。19世纪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报复的也就是真正囚禁她、在现实世界又无法战胜的西方男权社会。而传统的女性主义,早期主要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出了以男性标准作为女性解放的目标,试图通过清除男女性别的差异来达到男女平等,但其结果却是抹杀了男女两性的差异,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传统女性主义将男女平等与男女性别差异二元对立起来。
对于这种思潮里的新女性,毛姆的看法是什么呢?毛姆曾在1929年回复一位女研究生关于女性形象问题时谈到,“这个时代的妇女一般地……既无她母亲的优点,也无她女儿的优点。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可是不了解自由的条件。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她不再是家庭妇女,但还未成为一个(好)伴侣……”[8]376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女性,与毛姆心目中绅士文化里的英国传统女性是不同的,与毛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不一致的。毛姆的绅士情结,注定了他对这个时代女性的偏见和厌恶,也反映了19世纪西方男权社会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抵制和不屑。
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男性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三从四德”一直是社会伦理体系的主导思想。在“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思想的渗透下,中国传统女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社会中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成为男权社会统治的奴仆。
明清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启蒙,但是由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深厚根基,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的束缚和压迫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的启发,又开始了中国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但是与19世纪西方社会一样的是,中国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也是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下,女性在经济上一直处于从属地位,遗留在女性主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对金钱的膜拜和骨子里的奴性才是造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的根源。而聪慧的张爱玲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已不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而是进一步指向女性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自由。“无论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中挣扎。”[13]而张爱玲发现,她所怀念的贵族文化里的积极上进、光明磊落的传统男性,她想“低低”地爱着的“能给她现世安稳”的男子,都是她自己心造的,在现实生活中都是薄情寡义、自私虚伪、软弱无能的。
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告诉人们“娜拉出走之后”的结局,而张爱玲以女性的立场,在作品里描述了女性生活的艰难真相,重提对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质疑,以及女性获取“话语权”、替代男性行使“父权”的不可能性。
四、结 语
相似的童年创伤经历、不顺利的婚恋生活,还有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思想深处对贵族文化和绅士文化的向往和认同,决定了毛姆和张爱玲的性别观——对异性的偏见。但是同性独立建构世界的失败,又说明了男性和女性性别的二元对立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毛姆与张爱玲的性别意识的对比研究为当代的两性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些借鉴和思考。什么样的两性关系才可以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呢?
或许可以从道家学说获取一点启示,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阴阳和合”就是指男女两性和谐共生,构成有机的统一体。“故有阳无阴,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无阳,亦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故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14]而在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也反思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症结所在,在性别问题上采取了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平等和谐的模式。这种伙伴关系模式,是指一种消除冲突、对抗和权利等男性统治话语,推进爱、温情、友谊等新的文化政治话语模式。[15]无论是道学的“阴阳和合”还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伙伴关系模式,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男女关系模式。
毛姆与张爱玲的性别意识对比研究,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两性的二元对立是不可取的。只有消除男女两性之间的隔阂,达成男女之间的主动合作和平等合作,才能建构现代意义上和谐美好的婚姻爱情伦理关系。
[1]李春燕.试论毛姆与张爱玲创作的异同[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4-96.
[2]赵智. 论毛姆对张爱玲的影响[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86-90.
[3]韩蕊.张爱玲与毛姆小说主题比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4):62-65.
[4]毛姆. 刀锋[M]. 周煦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2.
[5]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林语堂.吾国吾民[M].黄嘉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127.
[7]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5)——对照记·1952年以后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8]摩根. 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M]. 梅影,舒云,晓静,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9]林幸谦.反父权体制的祭典[M]//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334.
[10]毛姆. 盛誉下的孤独者——毛姆传[M]. 李作君,王瑞霞,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161.
[11]张爱玲.谈女人[M]//曾湘文.都市的人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23.
[12]葛桂录.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42.
[13]于青.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J].安徽大学学报,1989(4):21.
[14]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44.
[15]张广利,陈仕中.后现代女权主义对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继承与超越[J].人文杂志,2003(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