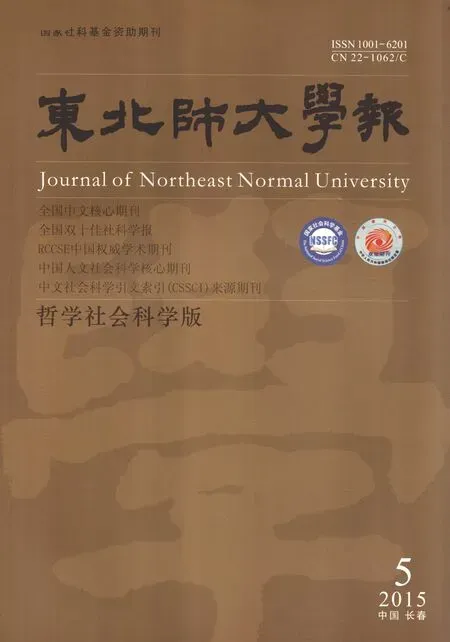解开妙曼文字背后的谜团——徐志摩散文《曼殊斐尔》中的人事、学理与正能量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写的《曼殊斐尔》一文,情真意切、文采飞扬,是现代散文名篇,与他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等齐名。这篇散文初刊于1923年5月《小说月报》14卷5号,深情回忆了1922年夏天在伦敦拜访新西兰籍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今译曼斯菲尔德,1888—1923)的经过及所见所感。经由这篇散文的描写,曼斯菲尔德“仙姿灵态”、温柔婉约、冰清玉洁的形象深入国人之心。方平先生在《笔端蕴秀,如见其人——谈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艺术》一文中,提到曼斯菲尔德令他“常会想起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的形象”[1],就是对曼斯菲尔德如此想象的延伸。其实这篇散文还涉及诸多人事话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只是徐志摩的笔墨重在抒情,对相关人事的交代常模糊不清,甚至有误;他还喜欢使用缺乏完整信息的英文和译文,致使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通过考释,试图使读者在欣赏《曼殊斐尔》的文情之美外,也能够发现其中包含的人事、学理和正能量。此外,我想进一步指出,《曼殊斐尔》中英杂糅的文体形式其实在现代中国也十分普遍,称其为“《曼殊斐尔》现象”亦不为过。因此,笔者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唤起人们对现代文学文本“中英杂揉”文体的重视和研究,探索一条增加现代文学文本学术附加值的路径。
一、会见的时间、地点、人物
徐志摩面见曼斯菲尔德的时间是在1922年夏天,当时他已经结束了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访学,即将启程回国①徐志摩在剑桥大学访学的时间等细节,可参阅刘洪涛著《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一书所述。。临行前去拜访想见的名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写明自己是在“七月中有一天晚上”拜访的曼斯菲尔德,但这时间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徐志摩写这篇文章时,距访问曼斯菲尔德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有可能把时间记错。徐志摩1922年8月7日给英国批评家罗杰·弗莱写过一封信,发信的地址是剑桥,这表明徐志摩8月7日之前还没有离开剑桥。8月29日徐志摩在给哲学家罗素写信时,他已经离开伦敦赴柏林。此后到巴黎,经里昂乘船回国。这些证据表明,徐志摩拜访曼斯菲尔德的时间不可能在7月,而是在8月7日至8月29日之间的某一天。
能否把二人见面的时间考证得更精确一些呢?回答是肯定的。徐志摩在上述给弗莱的信中说,自己会在8月17日以后去伦敦他的住所(7 Dalmeny Avenue,London,N.7)拜访他。再查曼斯菲尔德的书信集和年表可知,肺结核已至晚期的她8月17日前还在瑞士接受治疗,其后才从瑞士返回伦敦。据此我们可以把徐志摩见曼斯菲尔德的时间限定到8月17日至29日之间。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还提到见面的时间是星期四。我相信这个记忆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徐志摩在此文中提到他星期三曾去拜访过英国小说家威尔斯,第二天与他的夫人一同回到伦敦,前后时间的关联度比较高。经查万年历,17—29日这个时间段中,星期四有两个日子,分别是8月17日和24日。到底是哪一天呢?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在见曼斯菲尔德“早几天”,徐志摩与她的丈夫默里在伦敦市中心的Charing Cross街的一家A.B.C.咖啡馆里见过面。由此可以断定,徐志摩访问曼斯菲尔德的时间不可能是17日,而是8月24日。
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提到曼斯菲尔德在伦敦的住所时,用了一个地名:海姆司堆特(Hampstead),一个门牌号,是彭德街10 号。前者附有英文,一查可知,是伦敦北部的一个坡谷地带,通译汉普斯特,历史上是有名的温泉疗养区,空气清新。许多肺结核患者都喜欢到此疗养,英国诗人济慈就曾在那里居住过。曼斯菲尔德患有肺结核,回到潮湿肮脏的伦敦,找到这样一个郊区住所,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徐志摩说曼斯菲尔德住在彭德街10号。因为他没有附英文,很难根据这一点确定其具体所指。再查曼斯菲尔德的书信和年表,得知她此间住在伦敦汉普斯特地区邦德街6 号(6 Pond Street,Hampstead)。“彭德”与“Pond”的读音相似,指的应该是这个词。但为什么曼斯菲尔德住在邦德街6号,徐志摩却说是10号呢?
让我们把话题稍稍绕开一点。邦德街6号并不是曼斯菲尔德的房产,而是她的临时栖身地。这处房产的主人另有其人。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提到屋主人时,含糊地说“不知是密司B—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提到她是个画家。查曼斯菲尔德的书信和年表,这个“密司B”才露出真容,原来是画家多萝西·布雷特(Dorothy Brett,1883—1977)。多萝西小姐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就读于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她17岁时,听力出现了严重问题,她的父母为她在汉普斯特买了这栋房子,并资助她独立生活。单身的多萝西把自己的住所办成了一个沙龙,接待文学艺术界的朋友。曼斯菲尔德是多萝西的朋友,她在这里停留到当年10月2日,随后离开英国去了法国,1923年1月9日夜病逝于枫丹白露。多萝西在1925年追随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去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陶斯,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劳伦斯死后,她又陪伴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度过后半生。她的画风因为接触到美国西部印第安文化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徐志摩所说的邦德街10号其实是默里的暂居之所。曼斯菲尔德与默里这一对作家夫妇的关系此时已经亮起了红灯。默里陪伴曼斯菲尔德从瑞士回到伦敦,却选择在近邻栖身,这可能是他们分居的信号;再者,多萝西一直钟情于默里,默里在伦敦不住她的房子,可能也有避嫌的考虑。徐志摩与默里的关系并不深厚,所以无从知道这一点,还在《曼殊斐尔》中,极力渲染二人的恩爱情意。现在要去邦德街6号,可以选择在伦敦地铁汉普斯特·希思站(Hampstead Heath Station)下车,沿South End Road向南行不远,就到了与此路交叉的邦德街了,它在地图上的位置是NW3。
1923年1月,曼斯菲尔德在法国病逝,距徐志摩对她的拜访仅过去4个多月。
二、几个重要话题的来龙去脉
《曼殊斐尔》一文涉及三个重要话题,试一一索解。
话题一:曼斯菲尔德与契诃夫。该话题的起因是徐志摩“早几天”与默里在咖啡馆见面时,谈到中国新文学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最深。这句话拨动了默里的心弦,激动得几乎跳起来。徐志摩知道默里和曼斯菲尔德夫妇喜爱俄国文学,默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专门研究,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一书,曼斯菲尔德则“私淑”契诃夫。徐志摩引出相关话题,显然是投其所好,也难怪默里会激动。徐志摩趁默里激动之际,提出了拜访曼斯菲尔德的请求,自然得到了应允。在见面时,曼斯菲尔德果然向徐志摩谈起契诃夫,询问中国读者最喜契诃夫的哪些作品,这些作品译得怎么样。徐志摩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些问话,但没有提到自己是如何回答的。此时的徐志摩对契诃夫肯定了解得不多,或许只是为了与曼斯菲尔德见面时多一些谈资,才临时抱的佛脚;而在中国,五四运动初期契诃夫的小说只有周作人、鲁迅、胡适等翻译的寥寥数篇,因此这个重要话题没有展开。曼斯菲尔德去世之后,徐志摩才开始认真探索曼斯菲尔德小说与契诃夫的关系。1926年,徐志摩在他写的《再说一说曼殊斐儿》一文中,认定曼斯菲尔德是“心理的写实家”,“短篇小说到了她的手里,像在柴霍甫(她唯一的老师)的手里,才是纯粹的美术(不止是艺术)。”而此时,徐志摩已经翻译过曼斯菲尔德的8个短篇小说,还翻译了《契诃夫论新闻记者的两封信》(1925)、《高尔基记契诃甫》(1926)、《柴霍甫的零简——给高尔基》(1926),写了《一点点子契诃甫》和《契诃甫的零星》(1926)两篇短文,对曼斯菲尔德师法契诃夫的心理现实主义和短篇小说艺术,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他的这番话说起来底气十足,也是十分到位的。
话题二:关于“背女性”。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对曼斯菲尔德毫无保留的赞美,是建立在对“背女性”的讽刺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曼斯菲尔德的对立面是“背女性”。在徐志摩笔下,属于“背女性”的是一群“有怪癖”的“近代女子文学家”,她们的装扮、习气、喜好都违反常态,惊世骇俗:
头发是剪了的,又不好好收拾,一团糟的散在肩上;袜子永远是粗纱的;鞋上不是沾有泥就是带灰,并且大都是最难看的样式;裙子不是异样的短就是过分的长,眉目间也许有一两圈‘天才的黄晕’,或是带着最可厌的美国式龟壳大眼镜,但她们的脸上却从不见脂粉的痕迹,手上装饰亦是永远没有的,至多无非是多烧了香烟的焦痕;哗笑的声音,十次有九次半盖过同座的男子;走起路来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后身;开起口来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话:当然最喜欢讨论是Freudian Complex,Birth Control,或是George Moore与James Joyce私人印 行 的 新 书,例 如“A Story-teller's Holiday”与“Ulysses”。总之她们的全人格只是妇女解放的讽刺画[2]226。
徐志摩这里所描绘的“背女性”,其实是在英国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在20世纪头二十多年,英国女权运动的声势达到了顶点,新女性在社会中也大行其道。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封闭、恋家、无性”女性风尚的反抗者,新女性要求变革传统家庭关系,积极参与公共社会生活,追求思想独立,经济独立,更主动地与男性交往,有的还追求性解放。徐志摩的描述虽嫌夸张浮浅,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些最前卫的新女性的特征。从徐志摩行文的语气和用词来看,他对这些新女性是反感的,推崇的是曼斯菲尔德这样的古典美人形象。
在《曼殊斐尔》中,徐志摩提到了一些新女性的名字,其中能翻译考证出来的有麦考利、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的姐姐凡妮莎·贝尔。这些人在当时还没有很大名气,但行事作风已经在圈子中享有“盛誉”,这些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核心人物引领了当时的反潮流时尚。徐志摩当时与剑桥—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一些男性成员交往密切,如罗素、弗莱等,对他们的许多观念从善如流,但他对这批女性作家、艺术家却持反感的态度。
《曼殊斐尔》一文写于1923年。徐志摩回国之后,经过几年的历练,对“背女性”伍尔夫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去英国时,曾请弗莱引见自己拜访伍尔夫,他称道伍尔夫1927年刚出版的小说《到灯塔去》“真是精彩之至的作品”,称伍尔夫“美艳明敏”,想“找机会在她宝座前焚香顶礼。”[3]1929年10月发表于《新月》2卷8期的《关于女子——苏州女中讲稿》(原为1928年12月17日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讲演)一文中,徐志摩有三次提到伍尔夫。第一次说:“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房子,这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4]273这个“名小说家”就是伍尔夫。第二次是匿名引用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奥斯汀的议论。徐志摩说:“再说近一点,一百年前英国出了一位女小说家,她的地位,有一位批评家说,是离着莎士比亚不远的Jane Austen——她的环境也不见到比你们强。实际上她更不如我们现代的女子,也没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从不出门,也见不到什么有学问的人;她是一位在家里养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几本书,每天就在一间永远不得清净的公共起居间里装作写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4]274徐志摩对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有关奥斯汀写作状况描述的引用,是十分恰当的。第三次是在表彰了一批英美女作家后,又格外说“近时如曼殊斐儿、薇金娜·伍尔夫(通译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等都是卓然成家为文学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4]278这个时候,他已经将伍尔夫与曼斯菲尔德相提并论了。这说明徐志摩对伍尔夫及其与曼斯菲尔德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与他诗歌、小说创作的成熟发展是一致的。此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把曼斯菲尔德与新女性对立起来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来自当时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能够在伦敦文坛崭露头角,是得益于20世纪初叶英国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开创的自由、开放氛围的。曼斯菲尔德自己,无论是生活作风,还是思想观念,都属于新女性的一员。
话题三:曼殊斐尔与东方。徐志摩是中国人,宾主双方的话题自然谈到中国和东方。徐志摩与默里谈到东方的观音,埃及和波斯的女神,认为与天主教圣母及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狄安娜有着共同的特征。徐志摩拜访曼斯菲尔德时,拿了几卷中国字画,分别是赵之谦的“草书法画梅”,王觉斯的草书,梁山舟的行书。默里询问时,徐志摩打开给他和多萝西看,并讲些书法大意,引起了多萝西的兴趣。在与曼斯菲尔德相见的那“不死的二十分钟”里,徐志摩注意到她的发式:“直而不卷,整整齐齐的一圈,前面像我们十余年前的‘刘海’,梳得光滑异常。”徐志摩说这种发式自己在欧美从来没有见过,倒“疑心她是有心效仿中国式”[2]230。两人交谈的话题也涉及中国。曼斯菲尔德告诉徐志摩,在瑞士时她与罗素夫妇比邻而居,常听罗素谈起东方的好处。曼斯菲尔德原就敬仰中国,受了罗素的影响,对中国“更一进而为爱慕的热忱”。他们还谈到中国诗的翻译。曼斯菲尔德推崇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译诗,称它们是一个奇迹;对美国诗人阿梅·洛威尔的译诗则感到失望。韦利翻译的《中国诗一百七十首》的确是汉诗英译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在伦敦文学界就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洛威尔翻译的《松花笺》虽然没有获得同样的赞誉,但对意象诗和美国新诗运动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曼斯菲尔德还再三鼓励徐志摩翻译中国诗歌,只是徐志摩对此似乎没有兴趣。曼斯菲尔德在去世前几年,对东方神秘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参加了其团体组织的体验活动;她甚至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东方的智慧能够使病入膏肓的自己肉体痊愈,灵魂重生。这是曼斯菲尔德与徐志摩谈论中国话题的重要背景。
三、《曼殊斐尔》对徐志摩学术、翻译与创作的激励和影响
徐志摩在写《曼殊斐尔》一文之前,还写过一首诗《哀曼殊斐儿》,刊于1923年3月18日《努力周报》第44期,对曼斯菲尔德去世,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我昨夜梦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我昨夜梦登高峰,/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竟已朝雾似的永别人间?”在《曼殊斐尔》一文之后,徐志摩还写过《再说一说曼殊斐儿》(1925)和《“这是风刮的”》(1926)两篇短文。在这些诗文中,徐志摩始终把曼斯菲尔德奉若神明,对她怀着热爱、崇敬和仰慕之心。这种情感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推动着徐志摩在学术道路上前进,推动他持续不断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作品;而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也自觉接受了曼斯菲尔德的影响。
就文学学术而言,徐志摩并非科班出身。他在美国读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到剑桥大学访学时,才转向文学。回国后又经过不断自修,终于结出了“善果”,逐渐成为英国文学研究专家。1927年9月,徐志摩开始在光华大学任教,讲授英文小说流派课程,同时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英文教授。1929年,在中央大学任教,开设西洋诗歌和西洋名著等课程。1931年初,他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这是他在学术上获得认可的重要标志。而从前述对曼斯菲尔德理解的变化,可以看出徐志摩在学术上日益精进。写《曼殊斐尔》时,他只知道人云亦云地说曼斯菲尔德“私淑”契诃夫,自己并不明就里。到写《再说一说曼殊斐儿》时,他提出的“心理写实”和“短篇小说艺术”这两点,可以说抓住了曼斯菲尔德“私淑”契诃夫的关键。到《“这是风刮的”》中,他提到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大半是追忆早年在故乡新西兰的经验,并且总有她弟弟的身影闪现其间;还提到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文笔“轻妙”。这些片言只语,透着真知灼见;思路上,从追踪曼斯菲尔德对契诃夫的师法,到探寻她创作的内在动因和个性。此外,在开始时,他把曼斯菲尔德与伍尔夫对立,褒此贬彼;后来,他把二人并称,这说明他对英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及其背景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趣味上,从传统转向现代。
徐志摩在与曼斯菲尔德见面时,向她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翻译她的小说,得到了应允。徐志摩没有爽约,他从1923年到1930年,持续七、八年的时间,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10 篇短篇小说,按翻译时间的先后依次是:《金丝雀》(1923年6月)、《一个理想的家庭》(1923年8月)、《巴克妈妈的行状》(1923年10月)、《园会》(1923年10月)、《夜深时》(1925年3月)、《幸福》(1925年5月)、《刮风》(1926年4月)、《一杯茶》(1926年9月)、《毒 药》(1927年4月)、《苍 蝇》(1930年9月)。此外,徐志摩还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三首诗:《会面》、《深渊》、《在一起睡》,刊于1930年8月15日《长风》半月刊第一期。
徐志摩并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加上性格没有“常性”,不肯精雕细琢,很多翻译遭人诟病。他在翻译曼斯菲尔德小说时,尽管已经十分用心,但各种错译、漏译、增译、硬译,以及文字诘屈聱牙处仍然比比皆是。他译的曼斯菲尔德小说在1927年结集为《曼殊斐尔小说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学者张友松著文《我的浪费——关于徐诗哲对于曼殊斐尔的小说之修改》(《春潮》2期,1928年12月15日),就指出其中的几十处错译。虽然胡适为徐志摩辩护,说那些所谓瑕疵,其实“几乎完全是张先生自己的错误,不是志摩的错误。”[4]即便如此,属于徐志摩自己的错译,而张友松没有指出的,甚至更多!此外还有大量硬译的例子,如“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这句话来自《园会》(今译《花园茶会》)中的“What nice eyes he had”一句,徐志摩的译文照搬了原文的语序,在中文中却完全不通。再如《刮风》中有一句“her knees crossed,her chin on her hands.”画线部分本意是“她用手托着下巴”,徐志摩却直译成“她的下巴在她的手上”,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总体而言,徐志摩翻译的曼斯菲尔德小说已经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美感与可靠性,只能作为供批判用的历史文本。但与徐志摩其他翻译相比较,他对曼斯菲尔德作品翻译用力最勤,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专注的;在现代文坛,正是靠着徐志摩的大力译介,陈西滢、茅盾、赵景深的跟进,曼斯菲尔德才进入中国,对徐志摩、凌淑华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徐志摩虽以诗人著名,但也创作过15部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艺术技巧等方面考察,徐志摩创作小说与他翻译的曼斯菲尔德小说存在着明显的可比性。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对女性和儿童的生活与心理有独到的表现,关注和同情底层民众的苦难与不幸。这方面的题材,也都出现在徐志摩的小说中,如《两姊妹》、《船上》、《轮盘》、《珰女士》以女性为主人公,《吹胰子泡》、《童话一则》、《香水》写儿童,《家德》和《老李》写下层民众。
但徐志摩师法曼斯菲尔德更多的,还是她的心理表现技巧。徐志摩把曼斯菲尔德称作“心理的写实家”,说她小说的心理描写能够瞬间捕捉住“人的心灵变化的真实”,“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能“到人的脑筋里捉住成形不露面的思想的影子”[6]。徐志摩自己在《一个清清的早上》、《轮盘》、《船上》三篇小说中,就充分吸收曼斯菲尔德小说《金丝雀》、《夜深时》、《幸福》中的心理描写技巧。
曼斯菲尔德小说《金丝雀》写一个与金丝雀相依为命的单身女子,在她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金丝雀的欢唱,以及喂养金丝雀,与金丝雀逗趣,给她带来了快乐和安慰。小说通篇是女主人公的絮语和倾诉,她似乎面对着一个听者,但这个听者始终没有在小说中出现。在过去,她是对着金丝雀倾诉内心郁结的,而如今,这只金丝雀死了,她的孤独再也无处诉说。曼斯菲尔德小说这种得自契诃夫真传的“苦恼无处诉说”模式,传递给了徐志摩的小说《轮盘》。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倪三小姐嗜赌成瘾,结果一败涂地。她半夜三点从赌场回到家里,瞅着镜子里自己惨不忍睹的憔悴模样,意识浑浑噩噩、恍恍惚惚,疲倦、孤独、空虚到了极点。在徐志摩的《轮盘》中,也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是女主人公的友伴,倾诉的对象。在她倍感痛苦的时候,这只鸟儿开始欢唱,带给她快乐。但这快乐是短暂的,不久,不堪回首的记忆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这两篇小说的主旨都是表现女主人公的内心孤独,都把絮语和倾诉作为叙事的主要方式,都有金丝雀作为主人公情感寄托物出现。
曼斯菲尔德的《夜深时》写一个叫弗吉尼亚的女子在深夜时分的独白。她渴望男人,渴望爱情,渴望被人爱,渴望把自己嫁出去。但在现实中,她给意中人织袜子示爱被拒,还被意中人写信羞辱。她后悔没有控制住自己向意中人主动示爱,奇怪为什么自己每每向男子主动表白时,他们总是害怕似地逃掉。今晚她总想哭,忧心自己红颜将逝。最后,她的心绪又回到那封意中人的来信,想烧掉它,但炉火已经熄灭,还是睡觉吧!可一想到睡觉就又忍不住要哭……徐志摩《一个清清的早上》写主人公咢先生清早躺在床上的白日梦,思绪的中心是女人。他恨自己没有出息,做不到不去想女人!但哪个男人能不想女人?咢先生的思绪最后集中在他追求的那一个“她”身上。他是喜欢她的,如果能够娶了她,她的美艳风雅会给自己挣足了面子,准保叫几个朋友气死。想到美处,他甚至把枕头都挤扁了。但自己为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并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领情,女人的冷酷是通性,没有办法讨得她们的欢心。想也无益,只好结束自己的白日春梦,起床了。这篇小说缺乏积极意义,但主人公对女性、爱情的幻想和渴望,他的意识流,与《夜深时》颇为相似。只不过《夜深时》写女性意识流,徐志摩写的是男性意识流。
《幸福》是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写了一个幸福感很强,处于激情之中的中产阶级女子培达在家宴上发现自己的丈夫与他的情人眉眼传情,如梦初醒,她望着窗外一树雪白梨花,大脑一片茫然,原有的幸福感当然也被浇了个透心凉。徐志摩《船上》中的腴玉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随母亲乘船到乡下看坟地。从未到过乡下的腴玉兴奋极了,她在青草地上打滚,拿鼻子使劲嗅青草的味道,活像一只快乐的小狗。晚上,腴玉躺在船上,看着船的模样,船家摇橹的动作,渔家的孩子,也觉得稀奇快乐。但当夜色渐深,腴玉望着窗外的月光,听着隐隐的水声、狗叫、风声,心窝一阵子发冷,她的忧愁和烦恼猛不丁全都浮现上心头。小说并没有交代腴玉的烦恼是什么,但她开始时情绪的亢奋快乐与《幸福》中的培达相似,情绪的转折也与《幸福》相似,也与培达一样,因发现了人生的不如意而陷入沮丧和痛苦之中。
[1] 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31.
[2]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1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6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33.
[4]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3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5] 胡适.论翻译——寄梁实秋,评张友松先生评徐志摩的曼殊斐尔小说集[J].新月,1929-01-10.
[6]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2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6.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