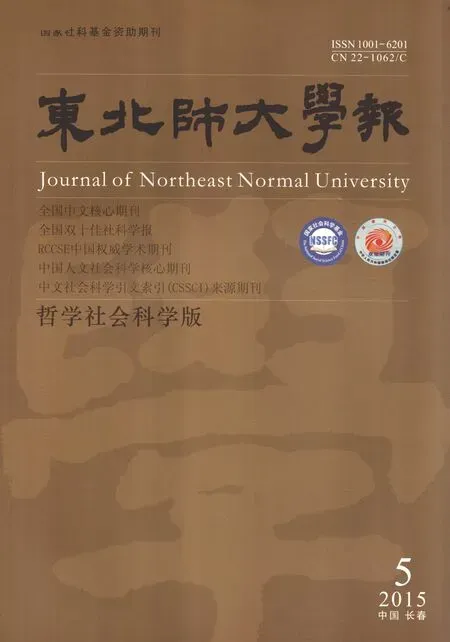论20世纪初美国“满洲开发计划”的余波——以司戴德全美对外贸易委员会成立演说为研究视角
梁大伟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116023)
20世纪初,美国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迫切需要抢占海外市场,倾销剩余产品。西奥·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执政后期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执政期间,美国通过各种政治和外交手段对清政府施压,妄图借“门户开放”之由,强行使美国资本渗入中国东北,参与远东角逐,打破当时基于大国间角力形成的“易碎均势”,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然而事与愿违,因列强远东利益之争无法调和、日本与俄国的联手阻挠、华尔街金融危机与美国政权的频繁更迭及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等多重因素影响,“金元外交”以1913年美国退出六国银团而宣告破产。作为“金元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对中国东北的资本渗透,其机缘、肇始、挫折、转机及失败的过程中,威廉·迪克曼·司戴德(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的身影始终活跃于台前幕后,他从190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首途来华直至1918年病逝,先后供职于中国海关,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及后来成立的美国远东司,期间也曾改任路透社记者、美国驻汉城及古巴领事馆副领事及美国财团驻华代表等职。他极力促成美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和贸易借款,实质上是为20世纪初美国“满洲开发计划”①“满洲开发计划”是美国“金元外交”战略的跗骨之蛆。在20世纪初美国远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极具代表性,彼此之间既有重合的部分,又有各自独立的地方。“满洲开发计划”先于美国“金元外交”政策而筹谋,执行中依附于“金元外交”而存在,但“金元外交”时代终结后却因司戴德的坚持和努力而余波未息。司戴德主要是由从1901年来到中国至1918年去世的一段时间里所力主实施的希望借助于美国政府支持,使美国资本染指中国东北,参与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打压日本与俄国的侵略势力,对中国实行“银行和铁路征服”为主的所谓“和平经济渗入”,以提高美国国际地位及其远东影响力,实现美国对中国东北经济掠夺,监管中国财政乃至最终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以最终确立美国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的庞大计划。该计划以美国“门户开放”外交政策为理论依据,以垄断中国东北的铁路、煤矿、电报、邮政等主要国有设施为实施原则,以发展美国的国际贸易,完成其垄断资本的远东渗透,强化其世界霸主地位为终极目标。虽因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列强远东的纵横捭阖及中国政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交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而最终宣告失败,但为美国谋求对外经济利益扩张提供了现实参考,对20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干预下从州际贸易到全球贸易的经济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目前我们研究美国远东政策、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海外投资方略等方面的问题均有借鉴意义。尽心竭力。遗憾的是伍德罗· 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上台后迅速终结了塔夫脱政权的“金元外交”战略,这无疑使“满洲开发计划”遭受重创,但司戴德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而是继续奔走于美国民间商业团体、文化教育机构及一些特殊职能部门,为“满洲开发计划”做最后的努力。
1913年2月7日,司戴德给著名银行家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写信介绍美国外交情况,希望获得沃伯格及刚刚宣告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支持;1914年秋,司戴德协助赫伯特· 克罗利(Herbert Croly)出版《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并亲自担任编辑。该杂志发行之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针对19世纪末的工业化给美国带来的巨变,支持社会民主经济政策并专注亚洲,同时宣扬美国新自由主义和世界强国论,在今日的美国依然具有极强的影响力;1916年3月17日,司戴德写信给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详述了爱德华·H·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的“环球铁路计划”①环球铁路计划:环球铁路计划又称哈里曼计划,是当时著名的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生前最后一个没能实现的愿望。1905年8月31日,哈里曼一行到达横滨(Yokohama),希望与日本协商,用1亿美元购买中国的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并派出美国驻日公使劳埃德·格里斯康(Lloyd Griscom)出面斡旋,当时哈里曼掌握着美国2/3的铁路股权资金,计划修筑一条横跨大西洋到波罗的海(Baltic)的环球铁路,在波罗的海与纽约之间建立航线,沿西伯利亚铁路与中国东北境内铁路相连,而后从大连起,将太平洋航线与美国铁路实现最终贯通。由于甲午战后,日本财政濒临崩溃,首相桂太郎(Katsura Tarō)曾一度与哈里曼签署了备忘录,但后来因为小村寿太郎(Marquis Komura Jutarō)外相的反对没能最终达成协议,后来因1907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和1909年哈里曼去世等原因,环球铁路计划胎死腹中。,并大肆渲染投资远东的灿烂前景。最为重要的是1914年5月27日至28日,司戴德以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主席身份出席了詹姆斯·奥古斯汀·法雷尔(James Augustine Farrell)组织的全美对外贸易委员(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成立仪式,并发表了题为《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Loans)的重要演说,这一演说逻辑严谨、步步为营,首先论述了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分类和当时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借款的方式及成果,用以开拓美国银行家的视野,转变其投资观念;接下来论述了美国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的机遇及资本渗透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用以坚定美国银行家的信心,鼓舞其投资热情;最后论述了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获得成功的可靠保证及投资的最佳对象,用以打消美国银行家的疑虑,指引其投资方向。
司戴德全美对外贸易委员会成立演说目的是鼓动美国银行家参与远东角逐,投资中国东北,成就美国的“满洲开发计划”。在当时的美国政界和商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满洲开发计划”的真实存在和余波未息。笔者在研习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司戴德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借助美国外交档案资料、罗斯福档案、塔夫脱档案资料及日俄同期档案资料佐证,辅之以国内美国“金元外交”问题研究的前期成果,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以初步分析。
一
全美对外贸易委员会是美国最早主张开放式国际贸易的金融组织之一,奉行以财团联合而非武力打压的方式控制他国经济命脉和进行制裁。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税收政策、人力资源及单边经济制裁战略等方面服务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整合和传播关键议题信息和专家意见,借助国家政策支持推进全球贸易。该组织自1914年成立至今,对20世纪初美国从州内贸易到州际贸易再到全球贸易的社会发展转型及美国全球化经济战略影响深远,5月27日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人员皆为当时知名银行家、政客及进步主义政论家。司戴德作为其中重要代表,在演说中详细论述了当时美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现状、对外投资方式与获利渠道及政府支持对银行家投资成败的重要作用等问题。
首先,他提出美国正处于经历国内战争和美西战争之后的第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和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的绝佳时期。众所周知,南北战争之后的30年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工业产值在1880年已赶上英国,1890年更是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1%,1897年至1914年间,对外贸易发展突飞猛进,1900年出口额不足14亿美元,1914年则激增至近25 亿美元,输出产品也由原来的农产品过渡为工业产品,对外已完成从农业出口国到工业出口国的转变,对内则已开始从州经济体的联合逐步转型为全国性经济体模式,在司戴德看来,“美国资本海外拓殖时代已经来临,对外倾销剩余产品是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淘汰落后产能,引领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赚取国外流动资金,提升综合国力的良策。”[1]1他列举英、法、德等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成功范例,并强调指出:“那些疾速发展的国家,缺乏资本管控能力,需要通过购买国际债券以使资金保值,而充分认识到贸易发展的潜力是抢占先机,在新一轮国际贸易竞争中制胜的关键”。[1]4
其次,司戴德将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划分为政府债券和外国借款两大类,并提醒美国银行家们区分其投资目的和形式。“作为投资而独立购买的政府债券获益立竿见影,且利润回报丰盈;而淡化投资价值的外国借款看似风险极大,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的获益远非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1]5这里,司戴德的导向性明显倾向于后者,并向银行家们传递了两种极为重要的信息:其一,经济与政治必须相互扶持,密切配合,否则注定失败。当时的美国铁路债券、股票与俄国、西班牙乃至其他国家的欧洲借款虽同属于独立购买的政府债券,但后者因经济与政治剥离,致使发展所需超出自我供给预期而前景黯淡;其二,美国资本进军远东和抢占中国商品市场是当务之急。司戴德进一步分析,所谓淡化投资价值的外国借款又包括三种方式:一是借款担保依赖于债权国监管下的税收。如对希腊、土耳其、埃及、中国、尼加拉瓜等国家的投资;二是借款支出收益由债权国监管。如对土耳其、中国和埃及等国家的投资;三是借款收益被用来购买债权国商品。如对俄国、西班牙、埃及和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司戴德在此三种方式中都重点提及中国,显然,他是希望将美国银行家的目光引向中国。
最后,司戴德还分析了对外贸易特点及优势。他坦言,“美国及美国商界正处于发展国际贸易并于中攫利的黄金时代。塔夫脱总统执政期间曾公开表明,美国的资本,正在向中国属望。因此,我们特别急于要做的,就是促进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2]毋庸置疑,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除了具有丰厚的回报以外,还可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并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当时的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等主要国家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拥有大量海外投资借款并早已认识到政府投资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外交领域可以全方位的保护本国贸易,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也注定会因此而迅速提升。当然,国际借款无论在昔日还是在今时,都具有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它可以使普通的商业行为变成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使债权国家及其金融集团获得真实而稳定的收益,以至于最终成为控制债务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工具。
二
司戴德接下来论述了美国参与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当时,埃及、土耳其的外债借款均是以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澳大利亚、印度的银行家为监护代表,包括后来于1908年重新建立的希腊借款,都完全没有像外债委员会等类似相关管理机构,中国与别国的借款模式也与之相同。司戴德强调,“获取巨额商业利润的诀窍在于发现其潜在价值。国家的发展壮大依赖其政治和金融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其政府公信力和领导民众拓展商业贸易的能力。”[1]6他鼓动美国银行家们抓住当前机遇,以前瞻的眼光和果决的行动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间的商业竞争,尤其是对远东,确切来说是中国东北的投资。号召其充分认识美国作为即将步入发达国家的强大经济体所具备的实力和已经具备的对外投资条件,通过政府主导下的金融重组,利用积弱国家资源,为自身打造金融和政治影响力,并最终将其成功转换为商业优势,建构政府、银行家、商人和商业集团“四位一体”的投资贸易模式,形成政府为贸易开路,贸易为国家服务,彼此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状态。为证明其个人论点的正确性和无可辩驳,他列举了当时“先进”国家对海外借款的重视程度和取得的“成功”经验:首先,当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强国法国是重视国际贸易并将国家机器与对外投资完美结合的样板,国家对投资者在维护法国外交声望和拓展法国国际贸易方面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自身的陆军和海军。事实上,在当时的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没有任何一项借款是不经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批准的;其次,德国虽然在贸易协定签署之前,表面上并没有所谓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但是银行家们与外交部通力合作,汉堡和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无一不听命于柏林及德国政府;再次,英国外交部也大力鼓励和支持对外借款,即便国内屡有政敌提出反对意见,但只要政府觉得有利可图,股票交易所从来不避讳将参与外国借款的实体公之于众。
司戴德认为,经历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之后,美国已经步入世界强国之列,对外贸易事业“方兴未艾”,其潜力和增值空间更是前所未有。美国政府也渴望利用国际贸易助推国家发展、维持国际秩序和加速扩大在全球的贸易规模。所以,他在演讲中适时抛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执政期间签署的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来证明历届美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重视。对于美国,这一法案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其作为陆军拨款法案补充条款和古美关系的修正案,后来作为附录写入了古巴宪法,致使古巴政府因名义上与美国政府存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而实际处于美国的保护国地位。按照法案规定,未经美国允许,古巴政府不得擅自提高债务的额度,不得通过税收创造额外收入和损害国际金融稳定。这一被司戴德称之为“捍卫了古巴政府的声望”[1]8的法案,实质上是在国际公约体系之下,通过国际借款实现了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控制,既避免了其他国家染指古巴,又一定程度上窃取了古巴的国家主权。至于圣多明哥、埃及、土耳其乃至中国,司戴德认为均可如法炮制。
司戴德在演说中也扼要提及了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的风险性和解决之法。他提醒美国银行家,为避免加勒比海沿岸的连锁反应,必须要对需要借款国家的偿还能力予以评估。考虑到责任分担,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投资。同时,必须建立自身稳定的金融防护体系,保持持久和充足的货币流入,而实现这一愿景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效仿美国对圣多明哥和尼加拉瓜的借款模式,即垄断关税。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睿智”之举,看似轻描淡写,实为必杀之技,因为关税是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部分,而财政税收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并使其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一个失去关税主权的国家,国家主权难以保证,国民经济难以发展,国家收入难以为继,除了依附于强权国家之外将无路可走。司戴德当时是公认的美国最年轻有为的远东问题专家[3]1-1-11,有着 中国任职和参与湖广铁 路借款、锦瑷铁路借款、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四国银团”及币值实业借款等多项美国对华投资经历,在此他虽未明确说明中国东北是美国“新的海外边疆”,但实则目的不言而喻,同时,也意在为接下来来分析美国投资中国东北的合理性做铺垫。
三
司戴德论述了美国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下一步需要做的自然是怂恿美国银行家义无反顾地投资中国东北,实现重拾“满洲开发计划”的终极目标。而这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想当然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阐明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以打消银行家们的最后疑虑;其二是阐明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的最佳对象,为银行家们指明投资方向。为此,他着重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中国作为美国海外市场的现实条件。他将“金元外交”政策说成塔夫脱政府希望继续推行“门户开放”,使美国资本家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获益的英明之举,将美国银团在中古东北所获得的进展归功于政府与银行家的精诚合作,而将其失败归咎于别国的干涉与破坏。他指出,“欧洲国家野心勃勃,亚洲国家枕戈待旦,世界战争引弦待发,但若没有极端事件发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已雏形初具,通过战争占有领地远不如控制经济命脉更能够给国家带来恒久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后发优势,所以,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金融系统并保持它的稳定,创造一个公平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商机是各国时下所需,也是美国未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1]5中国借款银团组织一经建立,对华投资规模一旦形成,美国国际地位必将大幅提升,银行家们弹冠相庆之日自然可翘足而待。还将美国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冠以维护远东多国势力平衡的光环,宣称世界上除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足以对当时中国的“独裁”统治模式产生影响,与欧洲银行家合伙开发中国的举措,对于美国银行家们有百益而无一害,更是对中国施以爱心援手。
司戴德继续分析威尔逊政权给美国银行家带来的契机。“我国政权稳定,商业繁荣,信誉良好,负担国内所需绰绰有余,且可以获取大量欧市流动资金,商务部受命于国会特殊指令并极力鼓励对外投资,驻外使馆和外交官群体对海外贸易拓展同样充满热情”[1]10。他赤裸裸的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直陈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商业必须依赖银行,而投资、贷款又必须得到外交的支持和保护。”[3]10-2-75提醒美国银行家“自由放任政策”及其思想体系已经过时,要想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对传统政策进行修正。德国在巴黎和伦敦疯狂攫取商业利益和捞取政治资本,其政治影响力之所以可以在欧洲高歌猛进,恰是因为德国政府提早意识到政治和经济本为孪生姐妹,“经济是国家血脉,政治是国家大脑,任何试图将其分离的做法其最终结果则必然是走向灾难”,[1]11而国际金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国际贸易竞争是全球商品市场的竞争,成败系于银行家、商人、商业集团与政府之间。政府不但可以在关键时刻运用武力确保银行家的资本回收,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公法对那些无力偿还外债的国家进行制裁并最终收缴其领土。在此,司戴德规避了国家主权问题。所以,他一直所鼓吹的所谓对外贸易和对外借款无非是一种经济侵略方式,借款国家即便出现短暂商业繁荣也不过昙花一现,最终结局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经济上依附于债权国家,在政治上处处受人掣肘,一旦崩盘,债权国最终依旧要诉诸武力,这与前面提到的保护弱国主权和领土完成的论调是明显背道而驰。
司戴德在论述经济和政治关系时也显示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救世主”情结,他呼吁银行家们要认识到美国已经告别“拐杖”时代,跻身于世界强国中之列,美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按照其价值观重塑世界,它的未来“处于它领导的世界之内,但不属于这个世界”[4]。美国人民尤其是银行家们肩负着拯救全人类的“总资本家”的责任,而用政治手段去获取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无疑是美国的“时代特征”。他还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债权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债务国都已经认识到金融稳定是确保全球贸易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稳定意味着世界和平和经济的良性运转,而不是意味着以强凌弱。美国银行家必须汲取海外借款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合理运用和充分发挥国家这一“社会平衡器”的巨大作用,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接受考验并捍卫国家荣誉。
四
20世纪初是美国“进步主义”①进步主义: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始于北美的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此意识形态虽然属于中间偏左,但并非所有中间偏左派皆为进步主义的支持者。进步主义者支持在混合经济架构下劳动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持续进步,他们是福利国家和反托拉斯法的最早拥护者之一。进步主义者一度主宰美国1890年—1920年的政治中间派。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者们在努力改革美国的政治程序,他们导入总统初选制和无党派选举制,成功降低政治角头的势力,他们披露腐败并建立公共管理制度管理对公共资源的垄断事业,他们还是儿童劳工法、公共教育和妇女投票权制度改革和制定的驱动力量,在1913年美国第17宪法修正案(参议员直选制)和1920年美国第19宪法修正案(妇女联邦选举投票权)的撰写和批准方面有突出贡献。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进步主义的功利主义特征,自由主义建基于自然权利之上,其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尊重民权的社会,而进步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是否尽善尽美,而是看社会的运行能否让人民感到快乐和满足,他们根本没有所谓完美社会的概念,他们的愿景是持续不断的进步和没有特定的终点。时代,是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时,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推进对原有经济、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政府为应对剧变,逐步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试图“调整资本主义精神,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5],通过有限的政府干预来化解美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难题。美国外交也随之走出美洲,走向世界,其所谓非殖民原则更是不断向亚洲拓展[6]。“满洲开发计划”的酝酿和实施时期正好与此重合,司戴德全美对外贸易委员会成立演说大而言之是“金元外交”政策的续曲,小而言之是“满洲开发计划”的余波,所述内容是当时美国银行家最为关注和极度迷茫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借款问题,他深知问题的症结在于解决银行家们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现状,所以整篇演说极具煽动性。从解释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的概念、分类和方式,到论述美国参与对外借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再到总结其获得成功的可靠保证及投资最佳对象等,既有理论,又有实例,既具前瞻性,又具操作性,正如“门罗主义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发展的结果”[7]一样,司戴德的这次重要演说的长期效应可能远非如此,它根本上是为美国银行家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贸易的思路,即借政府之手融资,重塑金融体系与高关税壁垒,为国际性工商企业提供金融和市场条件,促动美国资本的世界性流动,为美国国内工商企业的顺起、经济的腾飞、工业社会的来临创设制度性前提。美国在长期的“孤立主义”传统中形成了依托国内市场推动自身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式,随着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美国政府及国内银行家们的眼光开始转向全球市场,司戴德的这次演说为美国谋求对外经济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本质上说,司戴德所鼓吹的对外贸易与对外借款是为美国霸权与美国财团利益服务的。当时的中国政府试图借助美国资本来制衡日俄在华经济与政治扩张,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扩张,激化了其与日、俄等国的矛盾,客观上起到了加固英日同盟和促使日俄联手的效果。虽然1917年,美日签订“兰辛—石井协定”,实现了双方的暂时妥协,但随后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绞尽脑汁地拆散英日同盟之后,马上宣布废除“兰辛—石井协定”,使“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重新成为对华关系的国际准则,并服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远东政策。后来,在华盛顿体系下,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被迫单独应付美国的挑战,这种严峻的形势转而又刺激日本再次选择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从这一系列结果来看,近代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包括“金元外交”和“满洲开发计划”,总体上是差强人意的。当然,司戴德的主张和做法深刻影响了东北亚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他的全球化贸易思想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果剔除其为美国经济霸权主义服务的私念,在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上推进全球化贸易,实则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从全球经济交往中受益提供了启示。
[1] Willard Straight:ForeignTradeandForeignLoans,For the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nvention Washington,D,C,New York,1914.
[2] Anderson D F:TheLifeofTaf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245.
[3]WillardDickermanStraightpapers,#1260.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4] [美]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M].吴万伟,译.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3.
[5]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311.
[6] 毕元辉.从“非殖民”到“国际托管”:罗斯福政府殖民地政策论析(1941—1945)[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69-70.
[7] [英]C·W·克劳利,等.新编剑桥史: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