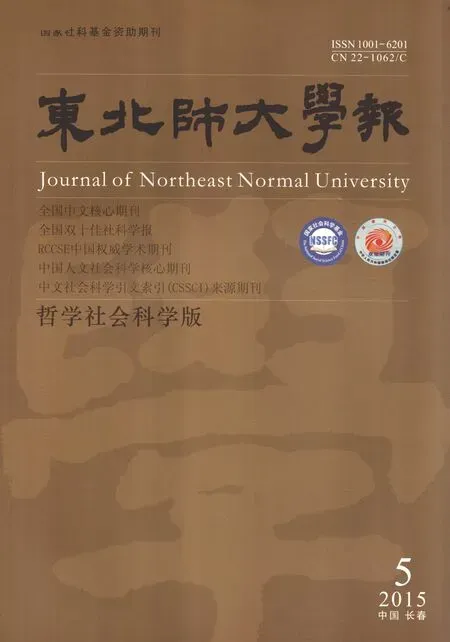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封建剥削”抑或“民族压迫”:近代民族地区农家致贫因素再讨论——以苗疆为例
李飞龙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史研究所,贵州 贵阳550004)
追寻历史发展的演变逻辑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始,迄今已有80 多年,围绕乡村经济的变化趋势是发展还是衰落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复兴农村”和革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全盘否定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意见代表,如陈翰笙就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农民的生活程度和经济地位还不如在纯封建下[1]。梁漱溟也指出,民国以后,农村日趋破坏,农民的日子大不如前[2]。可以说,当时的学院派、乡村建设改革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都强调中国乡村经济逐渐走向崩溃。但是,也有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卜凯就认为,在1910到1933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者居多,农民衣食改善,瓦屋代替草屋[3]566-567。实际上,不论其发展趋势是发展还是衰落,农民生活处于结构性的绝对贫困状态之结论基本为学者所认同[4]。
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乡村经济的衰败和农民的绝对贫困呢?不少学者也给予了分析和讨论,农村技术派的代表卜凯将其总结为,农场面积零细、生产力薄弱、人口繁密、劳力过剩、农民积蓄缺乏、水利不修、交通不便、森林太少、缺乏信用组织等方面[5]。不过,分配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不大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中国的封建压迫才是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6]。尽管上述的讨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农村技术派和分配派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致贫因素又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就是民族压迫、外国资本主义等外来势力等,内因就是封建经济的土地分配、雇工关系、租佃剥削等。依此角度而言,中国乡村经济衰败和农民绝对贫困的原因则有新论。尤其在民族地区,阶级分化、民族关系使得内外因的划分更具典型性。有鉴于此,本文选择解放前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形态的苗疆作为讨论对象,拟从内外因的角度,通过苗疆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困现状的梳理,分析苗疆乡村经济衰败和农民绝对贫困的内外因,试图展示苗疆农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寻找苗农贫困产生的根源。
一、苗疆经济的曲折演变与农家贫困的日常化
(一)苗疆经济的曲折演变
清代以来,由于苗疆驿道的开通、大道的延展、航道的整治,打破了以往相对封闭的局面;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清廷设立以屯堡为中心的初级市场,改变了苗疆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使得生活在清水江、都柳江沿岸的苗农逐渐与“腹地”发生联系。苗疆经济在此背景下也日渐发展,比如农业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提升,湘西和黔东南的苗农已能制造铁质工具,而且种类繁多。商业也走向繁荣,黔东南和湘西一带的定期集市十分普遍,表明苗农有了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可供市场进行交换[7]9。
苗疆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苗农利用远离战乱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农家经济,尤其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成品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一时期,纺织业逐渐与农业脱离,涌现了大量买卖织布的商人,如湘西古丈县龙鼻嘴地区,织布出卖的苗族农户在抗战之前只有十几户,抗战中期则增加到了300多户,其中50%以上从事纺织的妇女脱离了农业生产。乾城县苗族聚居区还出现了将丢梭织布机改装成拉梭织布机的技术,生产出来的布匹产量高,质量好,销路广。贵州松桃县巴坳乡的生门、小河等苗族村寨,织布出卖的农户,由战前的二三十户,增加到抗战结束时的130多户,从事纺织的妇女基本脱离农业生产,此时农业生产已降到家庭经济的次要地位。此外,紫云县苗族种麻的也很多,大部分都是为出卖而生产,商品化程度很高[7]258。实际上,苗疆的很多地区工商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日趋增加。据统计,1939年在湘西凤凰、永绥、保靖三县43 147户苗族中,有独立工商业7 029户,占总户数的16.3%[7]260。
不过,也不能夸大苗疆工商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就湘西的独立工商业而言,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小手艺者和小作坊主,而且多数集中在场镇附近和交通要道上。大部分农村,独立工商业户大致只占1%到2%,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贵州西部及云南,苗族独立工商业户更少,有的县连一户都没有[7]260。整个苗疆呈现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商品化程度不发达的特点。由于苗疆经济的整体水平不高,一旦受到外力的限制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极易出现大幅度的滑坡,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内战爆发以后,由于受捐税增多、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苗疆很多地区工商业开始走向衰落。贵州炉山县洋排寨的100多户打铁户,欠债户由1944年的50%上升到1948年的70%,到解放前夕,营业的只有十多户。炉山县湾水乡的纺织业,也由300多户下降到只有20多户。同时期,农村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甚至衰退。黔东南有些地区水稻亩产量从500斤左右下降为二三百斤,棉花亩产量从二三十斤降为十余斤。湘西十个县的水稻总产量,由1937年的800万担减到1949年的450万担,下降了43.75%;油桐林由310万亩减到120万亩,下降了61.42%;油茶林由224万亩减到79万亩,下降了64.26%[7]261。
此前未能发展起来的乡村手工业也丧失了其发展的空间。广西大苗山融水镇是大苗山最大的集镇,也是土特产的集散地,不过手工业比较落后。全镇计有1 497户,6 788人,其中手工业户188户,占全镇户数的12.5%,手工业人口347人,占全镇人口的5.1%。不仅是手工业人口所占比例不高,而且手工业种类也相对单一,主要有铁器、竹器、木器、纺织、成衣、首饰、弹棉、皮革、白铁修理、印刷、牙刷、雨伞、神香、雕刻等[8]。反排苗族每家都有纺织工具,纺车为手摇式、单锭,制作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不过,每家实际织布数量都很少,如棉花条每次只买二三两,有的要数年才能织一机布。有的贫苦农民无力织布,穿衣问题主要是以购买破旧衣服来解决。根据对17户的调查,1948年织布共10匹,买土布1匹,磅布3丈5尺,新衣3件,旧衣23件,共折合新旧衣服55件[9]132。
(二)农家贫困的日常化
就苗族农家而言,苗疆农家经济的贫困已经日常化。农家收支水平与生活质量是农民生活质量最为直接的体现,同时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10]。不过,苗疆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苗农生活相当贫困。根据对贵州省大方、织金两县5户典型家庭的调查统计:1948年,苗农租田收入和支出相抵后,5户分别亏损45元、53.58元、54元、78元、101元。为了维持生计,他们需要将背煤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所耗劳动力十分惊人,5户苗农每年需要背煤100天到200天不等,即便如此,这5 户家庭仍旧入不敷出,少的负债15元,多则达到30元以上。在家庭支出方面,5户苗农的生产资料支出极少,只占总支出的2%左右,并多为购买种子和添补小农具等日常补充[11]。贵州省台江县反排苗寨的农家收支调查也是如此,在1948年的15户家庭收支中,只有一户(地主)收支相抵后,还剩盈余,其余包括富农、中农、贫农在内的其他苗农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虽然反排苗寨是台江县的主要产粮区,但是贫苦农民却是连年缺粮,甚至口粮都严重不足。1948年,苗农平均每户粮食收入为2 254斤谷子,其中杂税和地租支出968斤,剩余1 286斤,如以5口之家进行计算,平均每人仅有257斤谷子,即便全部用作口粮,也不够维持人所需的最低热量。为此,苗农只能出卖劳动力谋生,有的进行采集野菜,有的以米糠充饥,甚至讨饭生活。全寨每年都会有数十个劳动力出外帮短工或长 工,4—5 人 讨 饭[9]157。实 际 上,近 代 苗族生产生活的贫困状态已经日常化。
二、封建经济下农家致贫的内在因素
在致贫的因素中,土地占有集中、地租剥削深、雇佣程度高都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因素。在苗疆社会,这三者又具体如何呢?
(一)地权分配与贫困
土地是农民繁衍生息的前提要素,是乡村政权结构、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苗疆的土地也是如此,在土地的分配关系上,解放前苗族聚集区的土地占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离汉族地区较近的地区,土地分配接近于汉人的情况,这类地区是占有总人口10%以内的地主,占有土地总量的50%左右;二是平坝地区,该地区阶级分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但土地集中情况不明显,这些地区占有总人口10%的地主,占有总土地的25%左右,并且中农居多,约有50%(占有土地达40%);三是偏远山区,这类地区地主人口只占0.4%,土地占有也仅有2.5%左右,绝大多数是贫农和中农[11]17。数据说明,即使是一类地区地主占有土地都仅是50%左右,其他地区的土地占有更呈分散之势。费孝通的调查也得出相似的论证,“苗家男女普遍的劳动,就是有土地的,甚至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也不脱离劳动,因之,除了个别的地主外,至多是地主式富农。比如黄平的谷陇区4 100户,占人口95%的苗族,没有地主,仅有半地主式富农10户和富农50户,中农占大多数并占土地的大部分。”[12]6
除去土地占有相对分散外,土地占有的数量也并不多。由于苗族农民主要生活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等地的山区,土地资源有限,人多地少成为常态。据调查1948年贵州省台江县反排苗族的137户539人中,劳动力有264人,占总人口的49%。以劳动力264 人计,全寨有稻田5 210挑(1 挑约为0.29亩),平均每个全劳动力仅耕种稻田20挑,折合3.3亩[9]118。如果是人均占有土地,则只有1.6亩。贵州省雷山县大塘区桥港乡掌披苗族拥有140 户677 人,拥有土地522 911.6斤[13]209,每人平均占有土地772.3斤,即人均占有土地不超过2亩。从阶层户均、人均占有土地计算,掌披苗族地主13户63人占有土地131 568斤(约329亩)、富农10户59人占有土地76 363.1斤(约191亩)、中农68户324人占有土地251 151.2斤(约628亩)[13]302,那么地主户均占有土地25.3亩、人均占有5.2亩,富农户均占有土地19.1亩、人均占有3.2亩,中农户均占有土地9.2亩、人均占有1.9亩。可以看出,苗疆的土地占有状况并不是某一阶层(如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数量多,而是全苗族的普遍问题。换句话说,并不是封建剥削导致的苗农贫困。
(二)租佃关系与贫困
从租佃关系看,大部分苗族地区的租佃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出租田土的数量不多。根据加勉苗族土改时的统计,全寨130户共有田产面积344.412斤,全寨出租田数45 300斤,占全寨总面积13.1%。出租田者共18户,占130户的15.6%。其中贫农4户,中农4户,富农3户,地主3户,小地主出租者4 户。租入田的共38户,共佃种田18 840斤(其中一部分是外寨的),其中贫农21户,雇农6户,中农10户,小手工业者1户[13]38。必下苗族的地主,出租田也极少,而且租出的都是远田或坏田。以1940年为例,该寨共有49户,其中相当于地主的有13户,全寨共有田2 533挑,地主共占有1 210挑,占出租总田面积的47.6%,其中的出租田只有85挑,占地主总田数的7%[13]170。贵州省雷山县掌披出租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15.9%。
地租形态一般是实物地租,“苗族内部平常都是活租制,只有很少是定租制,一般没有押金。租额一般是平分,较少数有在分租前抽10%上粮。除了帮地主小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12]9活租率是每当秋收时,佃户请地主亲自到田间去监督收割谷子,所收稻谷挑回家后,按地主和佃户各半分配。稻田除种稻谷外,不种别的作物,所有交付的实物地租全为稻谷,田赋由地主负担。有的贫困农民由于无地可种,也向地主富农租种一块山坡来种小米,收成时也要交纳一些小米作为土地的报酬,但数量无统一规定,必下苗族一二亩山坡大致要交5斤至15 斤的小米穗[13]170。除地租外,佃户还要承当一些额外负担,如帮工或送礼。佃户每年必须给地主帮工,这是一种只供饭吃、无报酬的无偿劳动,帮工的多少,没有一个统一规定。必下苗族租地主10 挑田,佃户每年要帮工半个月[13]170。送礼在部分苗族地区也普遍存在,必下苗族佃户佃耕的田中,若养有鱼,须送给地主一两条(1斤以下),并由地主亲自挑选。佃耕的田中如没有养鱼,本寨地主可以不送,外寨地主还是要照例送[13]170。从上述租佃关系中看出,苗疆基本上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相比较汉族地区比较成熟的封建经济形态,苗疆的地主数量比较少,地主对佃农的剥削程度并不高。
(三)雇佣关系与贫困
从雇佣关系看,苗族地区的雇工种类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在农业生产范围内的雇佣关系,一种是搬运的挑夫。在农业生产范围中的雇工分长工和短工(零工)两种。贵州省从江县加勉苗寨自1938年到解放前当过长工共31人次,其中外出作工者28人次,在本寨者3人次。有的是给别人种田,有的是给人家放羊,后一种情况多数是未成年的儿童,前一种占67.7%,后一种占32.3%[13]35。在待遇上,长工成员有男女之别、大小之分。成年男长工,每年的工资一般为12元(大洋,吃饭除外),如果是好年成,可多达20—22元,在不好的年成里,每年工资只有6—7元,遇到灾荒之年,苗农为了活命,只吃饭不拿工资的长工也不少见。此外,还有女长工和小孩长工,他们的工资,一般每年只有二三元,尤其是小孩长工,甚至一点工钱也没有。长工工资,在一年内分别作四、五次付清[13]170。除工资外,雇主每年还给长工一二套旧衣服,但当长工离开雇主家时则要归还。在社会地位上,一般很少出现打骂雇工的现象,雇主的态度亦比较和缓。在逢本民族或本寨节日的时候,雇工也休息。但仍然要挑柴、挑水。吃饭时,雇主与雇工在一起吃,吃同样的饭食[13]35。
比较而言,苗族地区零工更具有优势,因而短工占的比重很大,很多苗族地区短工只管饭吃,不给工资。从剥削率计算,短工的剥削率更高,长工的剥削率一般为43—45%左右;雇零工的剥削率为76.9%(按中央规定120个零工等于一个长工计)[13]34-35。因此,出卖短工的极为普遍,必下苗寨甚至连中农都出卖短工,几乎占总户数的50%。短工工资在解放前20年里,一般男工每天给谷子10斤,女工5斤,灾荒年一般都只管饭吃,不给工资[3]175。根据1952年土改时的统计,加勉苗寨每户地主除极个别时间雇佣长工外,雇佣零工数量相对于2.6个长工,每户雇农被雇佣零工平均数相当于1.5个长工[13]35。有些苗族地区还存在月工,在必下苗寨,较好的年份月工的工资可达3元,一般为2元,做月工是按天支付报酬[13]174。此外,挑夫完全是外出工作,出乡、出县、出省,主要工作是挑木炭或搬运货物,工资按重量及道路远近计算[13]35。从多种雇佣的关系看,苗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而是比较和谐的相处。
三、农家致贫根源的外在因素
在考察土地占有、地租剥削、雇佣程度等封建剥削的三个重要纬度时,我们发现:苗疆的土地占有关系并不集中,相反呈现出一种分散的态势;地租的剥削并不严重,大部分苗疆的租佃关系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出租田土的数量不多,即便在存在的租佃关系,地租所交比例也不高;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地主与长工、短工同吃同住的现象十分普遍,两者关系比较和谐。因此,近代苗族地区基本上属于封建经济,处于水平落后,市场化水平不高,土地交易率低的初级发展阶段[14]。可以看出,上述分析与传统的革命范式差异较大,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尖锐,中国主佃关系可以概括为“有剥削而无尖锐斗争”[15]。那么苗家贫困的根源是什么?我想可能是多方面的,基本上受到资源禀赋(自然环境、人口压力)、要素流动(农家负债数额、公有土地比例)及社会分工(商业化程度、国家赋税征收)等因素的影响[16]。不过,民族地区的地权关系,还涉及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是异族压迫。苗族自古就是一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由于战争的关系,苗族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的远距离大迁徙,唐宋以后,苗族的大部分已在西南定居。不过,除极少的一部分苗族聚居外,大部分与各民族交错杂居。也正因为迁徙和杂居的原因,苗民大部分为外族所压迫。在压迫苗族的外族中,以彝族和汉族为甚,杂居的苗民极少占有土地,无地的佃农约在80%以上[10]263。费孝通曾言,“汉族封建势力罩住了苗族,汉人地主有着政治权力压迫着苗族,使苗族本身不易生长出地主阶级。”[10]9四川省古兰县麻城乡的寨和东园两村,共有苗族6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26%,其中佃耕中农10户,佃耕贫农53 户,他们完全佃耕汉族地主的土地[17],因而苗疆也就出现了“老鸦无树桩,苗族无地方”的谚语。二是政府盘剥。近代中国,政府对苗民的盘剥尤为严重,征收苛捐杂税和抓兵拉夫是基层政府最为常用的剥削手段。在贵州省炉山的凯棠乡,从1938年开始农民被迫种植鸦片烟,地区经济走向畸形发展,基层权力掌握者疯狂抓兵、派款,从而使得大量中农普遍下降为佃农贫农[10]263。
如此,苗疆农民生活贫困的外在因素可能更为直接和严重,而非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正因为异族压迫和政府盘剥,才有了苗民与异族和政府的尖锐矛盾,正如费孝通所论证:“当苗家农民经济势力上升到一定程度,”“也就发生了武装起义。”“经过一度战争后,苗族又被屠杀,土地又被霸占。”而西南地区流行着一句话,“苗族30年一次小反,60年一次大反。”也正印证了苗家经济贫困的原因所在。
[1] 陈翰笙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9.
[2]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4)[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592.
[3]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出版,1941.
[4] 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J].近代史研究,2010(4).
[5]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561-565.
[6] 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0:9-13,122-127.
[7]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8]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大苗山苗族自治县融水镇调查报告[R].内部资料,1964:3.
[9]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
[10] 张等文,陈佳.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7-51.
[11]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苗族简志:第二次讨论稿[M].内部资料,1959:20.
[12] 费孝通,等.贵州苗族调查资料[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13]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
[14] 李飞龙.近代苗疆土地所有权转移问题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5).
[15] 李金铮.2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新探索[J].历史研究,2003(4).
[16] 张一平.近代租佃制度的产权结构与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地权构造的再认识[J].学术月刊,2011(10).
[17]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