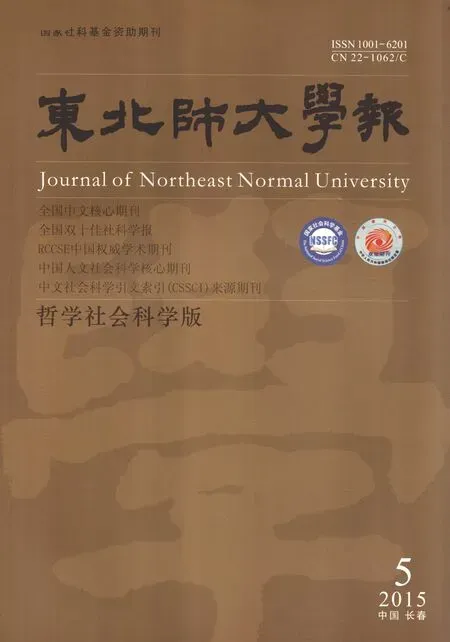穿越物化的“幻相”——卢卡奇辩证法的真实意蕴
雪 婷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1]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言,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著作。众所周知,卢卡奇的辩证法经常被人们冠以“历史辩证法”、“总体辩证法”、“历史实践辩证法”、“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辩证法”等名号,这些名号仅仅是为了突出卢卡奇辩证法的某个局部,还是对同一个内容的不同“称谓”?如果是前者,这就遮蔽了卢卡奇辩证法的真实意蕴,重又陷入我们所批判的“细枝末节”中;如果是后者,这些不同的“称谓”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理解卢卡奇辩证法的症结所在。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称谓”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突破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契合的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穿越物化“幻相”重建被物化消灭的人。
一、物化意识结构:物化“幻相”产生的内在逻辑
面对实证主义“抹杀”辩证法的“挑战”和庸俗马克思主义“歪曲”辩证法的“危险”,马克思辩证法面临空前的危机。为什么马克思的辩证法面临如此大的“灾难”?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一种非常迎合自然科学方法的物化意识结构。正是这种物化意识结构,使人们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把握,从而把持续生成的现实割裂为孤立僵硬的事实,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不仅切断了劳动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幻相”。卢卡奇的辩证法就是针对这种物化“幻相”提出的。那么,这种物化“幻相”产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描述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入手的,他把商品拜物教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问题。首先,卢卡奇从主客观方面考察这种“物化”现象:“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2]152-153这种“物化”,不仅客观上切断人与劳动对象的自然关联使物与物的现成世界与人相对立,而且主观上使主体与自身相分离从而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系都变成可计算的偶然联系。由于这种“物化”根源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后者在主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因而物化对应着“抽象的暴力”[3]292。
其次,受韦伯合理化思想的影响,卢卡奇不仅从主客观方面阐述“物化”现象,而且深入剖析合理化原则对人灵魂的“侵蚀”——物化意识。在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人们的劳动过程逐渐被分解为一些抽象的局部操作,工人由此变成机器的零部件,“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2]154。当这种合理性原则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时,处于机器链条上的工人就会失去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总体性把握只能对其采取一种直观态度,这种态度侵入工人的心理结构并使其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枷锁”,“这种物化意识的出现将消解人的主体性,使人全方位地接受物的统治”[4]。
再次,合理化、规律化使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永久化为根深蒂固的物化意识结构。随着劳动过程的日益合理化,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丧失作为劳动主人的身份,因而对生产只能采取直观态度,这种态度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即“时间空间化”。这样,时间就凝固成一个精确的、可量化的“物”的连续统一体即空间,同时处于这种“物性”时间下的劳动主体也被分割为僵化的孤立原子,“在物化的意识看来,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性质——作为物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2]161这种由可计算性形式不断加强地物化意识结构不自觉地浸入人的意识,并使得人的肉体和心灵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
最后,这种物化意识结构在哲学上的体现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两难困境”。由于近代理性主义愈来愈发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联系,当理性主义要求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方法时,非理性问题就会起到瓦解整个“理性大厦”的作用,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这一非理性界限的典型。因此,对康德“自在之物”的克服就构成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旋律”。康德从主体实践出发试图克服理论理性的内在局限,但普遍必然性的知识须以先验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这必然导致自然的必然性与个体的自由性之间相矛盾。费希特试图把康德的“认识主体”转化为“行为主体”并通过“正、反、合”的主体设定活动为康德的先验辩证法注入活力,但最终陷入自我的“怪圈”。为解决这一问题,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把思维的主客对立纳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既把一成不变的概念溶入理性的自我运动中,又把所有的逻辑问题都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上,这使得辩证法成为一种有内容的总体辩证法。但由于黑格尔的行为主体是先验的世界精神,所以这种总体注定是抽象的。由此可见,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已经把握到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并试图通过向内发展的道路加以克服,但由于它只是在思想上把这一矛盾推向极点,因而最终只能陷入“两难困境”,“古典哲学本来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思维重又落入主体和客体的直观二元论的窠臼之中。”[2]235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德国古典哲学在试图克服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时陷入“两难困境”,但它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为我们穿越物化“幻相”奠定了坚实的辩证法基础。
二、辩证的总体:如何从事实上升到现实?
卢卡奇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贵遗产”,从辩证的总体出发试图把孤立的事实不断提升为持续生成的现实。但是,“如何从事实上升到现实”直接关涉到卢卡奇辩证法的本质问题。实质上,卢卡奇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总体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性的统一以及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相统一的“内在一致”,这是从“事实”上升到“现实”的根本路径。
(一)历史根基: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
卢卡奇把历史作为整个哲学的理论基石。在他看来,面对形式与内容的分裂,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反而回避问题本身,其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这些孤立事实的历史性质。因此,我们要突破资产阶级物化结构,就必须把辩证法奠定在坚实的历史根基之上,“几乎在每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后面,都隐藏着通向历史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就是通向解决问题的道路”[2]228,黑格尔哲学在这一点上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他发现了形式和内容统一的辩证中介即绝对精神的历史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内容与形式等所有僵硬的对立都溶解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了。
卢卡奇把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倾向发挥到极致,既把社会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历史问题,又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与此同时他也识破黑格尔绝对精神表面上创造历史的“概念神话”。在卢卡奇看来,真正的辩证法就是要剥离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把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置于总体性的现实历史之中,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因此,卢卡奇的“历史”是从孤立的“事实”上升为持续生成的“现实”的一把“金钥匙”。
但是,卢卡奇的“历史”,既不是黑格尔抽象的“理性运动”,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辩证法的历史,“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2]62这种“历史”是人一连串的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关涉形式与内容等二元对立的问题都将得以解决。同时,卢卡奇的辩证法既不是脱离历史的自然辩证法,也不是超越历史的“绝对精神”运动,而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2]27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辩证法与历史看作同一个过程。因此,卢卡奇辩证法的历史根基是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
(二)具体的总体性:总体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性的统一
在卢卡奇看来,以历史为根基的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性”。实证主义者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把整个社会看作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这使得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物化状态从而遮蔽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卢卡奇辩证的总体则是在思维中把握活生生现实的唯一手段,因为“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2]55虽然我们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但是我们并不停留于这些孤立事实,而是把它们置于一个历史的总体中并使其成为现实的一个环节,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从孤立的“事实”不断上升为持续生成的“现实”。
黑格尔虽然最早运用具体的总体,但由于他的“总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5],因而它的内容仍带有“永恒价值”的传奇性残余。与黑格尔超验的总体不同,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是对活生生的历史统一性的理解,是“历史地(因而在现实中)带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6],因而是历史的总体性。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当资产阶级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矛盾弃之不顾时,卢卡奇的辩证法却以此为出发点并将其扬弃于历史的总体性中以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2]86这是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性最具革命性的一面。
卢卡奇辩证法的本质不仅是历史的总体性,而且是总体性的历史,因为“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2]80。与资产阶级把社会发展的各环节都变成同等数量的“事实群”不同,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性”,既不把历史发展的各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社会同一性,也不是这些历史环节的外在“堆砌”,而是把这些环节置于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从而使各个环节的具体可能性不断上升为社会发展的现实性。由此可见,卢卡奇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性的内在统一。
(三)改变现实: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的统一
卢卡奇以历史为载体、以“具体的总体性”为内容的辩证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实践突破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结构,因为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2]94。与恩格斯规避各种干扰因素的工业实践不同,卢卡奇的辩证法不仅使无产阶级从总体上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而且使其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和自身存在的非人性,这促使无产阶级摒弃直观态度转而采取一种革命实践态度,“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2]51。
卢卡奇的实践不仅是历史的实践,而且是实践的历史。与德国古典哲学家极力推崇的伦理实践不同,卢卡奇“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不仅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而且将其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实践与辩证法的历史息息相关。因为这种实践,既不是超历史的理想环境中的“抽象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伦理实践,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实践活动;这种历史,既不是个别历史事实的叠加,也不是脱离实践的精神运动,而是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因此,卢卡奇“改变现实”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的内在统一。
由此可见,卢卡奇以历史为根基,以具体的总体为本质、以改变现实为己任的辩证的总体,真正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这是一个比任何物化的经验世界更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个超验的过程,而是现实世界中“我们”创造的结果,“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即看作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2]231这个创世的“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由于卢卡奇的辩证法始终围绕无产阶级的现实命运而展开,而工人只有经历无产阶级意识这一环节才能成为历史的主客体,因此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卢卡奇辩证法的必由之路。
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辩证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同一种物化现实,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独具革命性?这是由两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作为物化的客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表面的主体而存在,这种双重存在使他们对生产只能采取一种纯直观的态度,这种从量上把握对象的方式只能形成一种虚幻意识。相反,无产阶级自它产生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一种“物化意识”,这既加速了工人与其个性的分离使其沦为一种商品,又迫使其成为被量化的纯粹客体。由于它的“灵魂”并没有变为商品,这表明无产阶级身上还存在尚未被资本主义克服的力量,这构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生成的起点。数量化是蒙在客体上的物化外衣,而作为历史主客体的无产阶级自身蕴含着一种质的变迁,这是无产阶级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存在的根源。卢卡奇的辩证法就是要使无产阶级自觉地意识到:只有消除这种直接存在的虚假形式,才能作为真正的阶级而存在。
直接性和中介作为辩证过程的两个因素是内在统一的。存在的每一个既定客体都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接性,而超越这种直接性就意味着创造。中介范畴是从直接现实性通达客观现实性的“桥梁”,每一种中介必然产生一种立场。资产阶级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把现实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事实并将其置于抽象的规律之下,这必然导致历史与起源相分离。相反,无产阶级却能超越这种直接性,因为它通过中介范畴不仅能从总体上把握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而且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性,这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至关重要,“对无产阶级来说,自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乃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2]256
只有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发展而来时,无产阶级意识才能成为过程本身的意识,无产阶级改造现实的实践才能发挥它的威力。但无产阶级即使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也不可能一下子从实践上消除所有的物化形式。因为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主体”过程的真理本身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2]96因此,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本质在于它不断生成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通过中介范畴超越物化意识从而把握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力量。由于卢卡奇正是发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革命性,所以才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自身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来对待,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自觉到革命实践。
四、思想“悖论”:卢卡奇辩证法的历史限度
毫无疑问,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辩证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本质,还是对于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都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当时,一场重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理论表述”[2]21。但是,由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自身存在“悖论”[3]360:它把劳动对于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看作物化的根源,但是却把“克服”这一根源的辩证法置于形式上的从属层面,这决定了卢卡奇的辩证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卢卡奇辩证法的黑格尔色彩过于浓重。虽然卢卡奇试图通过恢复黑格尔传统狠狠地打击机会主义者,但是在寻求突破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的历史主体时却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客体,这是一种“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具体而言,卢卡奇在阐述马克思辩证法的过程中虽然力图超越黑格尔的“概念神话”并试图与其划清界限,但在涉及阶级立场与无产阶级意识的关系问题时,却又不自觉地运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这是他无法摆脱黑格尔的根本原因。
二是卢卡奇对实践的理解过于抽象。卢卡奇对于辩证法的强调不是一种理论抽象,而是始终与工人实践密切相关,但是由于他的辩证法难以摆脱黑格尔的“阴霾”,这决定了他改变现实的历史实践注定是抽象的,因为这里的实践主体是“无产阶级及其意识”。这种把主体的阶级意识等同于主体自身的做法,不可能完成“冲破”现实的实践任务。
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与阶级意识之间缺乏现实中介。无产阶级立场的根本内涵是突破“被赋予的意识”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从物与物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这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为前提。如何弥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与阶级意识之间的鸿沟就成为卢卡奇辩证法的理论“难题”。尽管他在后期试图通过劳动及再生产弥合这一鸿沟,但由于缺乏一系列可操作的现实中介环节,因而只能不自觉地通过黑格尔的“反光镜”来理解马克思,从而使马克思的辩证法退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
由于这些理论局限,卢卡奇的辩证法遭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和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的广泛质疑,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卢卡奇无产阶级意识所可能导致的极权主义的批判,还是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对卢卡奇革命道路的推崇,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卢卡奇辩证法的魅力至今犹存。
[1] Maurice Merleau-Ponty.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M].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7.
[2]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衣俊卿,周凡.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越物化的狂欢)卢卡奇专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4] [德]弗洛姆.在幻想锁链世界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61.
[5]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 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4.
[6] [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M].杜章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14.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
——读《卢卡奇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