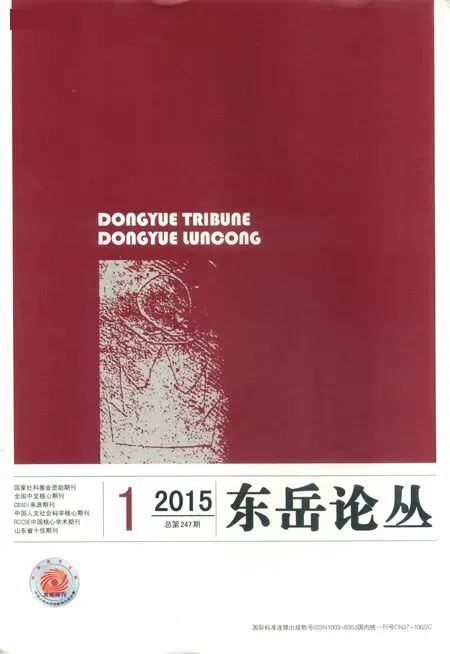生态城镇建设中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路径分析
刘伟红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生态城镇建设中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路径分析
刘伟红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城镇建设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日渐迫切。在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中,政府和社区是环境治理的两大支撑力量,但是,这种认知定位正在发生改变,市场这一“生态环境破坏的引发者”正逐步引发各界的重新审视。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合理地利用市场路径来解决部分环境问题是生态城镇建设的可行路径。
生态城镇;市场;环境治理;新型城镇化;公地悲剧;公共物品;生态经济
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到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亚氏的警示用在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也是非常恰当的。生态环境是人们最少照顾的事务,虽然每个人都享用它,却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存在之一。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无视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已经在冲击国人的生存底线,特别是近些年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雾霾天气,在各个层面上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全民性的环境觉醒时代正在来临,生态城镇建设的问题已提上实践日程并日渐迫切。
一、我国生态城镇建设面临的环境问题
我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6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我国派代表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受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官厅水库污染事件等的影响,我国政府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个具有法规性质的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②刘建伟:《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演进》,《理论导刊》,2011年第10期。,开启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先河。此后,在环境保护的法制、标准与组织建设领域,逐步走向系统化,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等都已出台。但是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生态城镇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城镇规划与发展中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明显
与乡村相比,城镇本是一种更加融合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它的聚集性节省了大量公共空间,使自然与人的相处更加具有生态效益。但是在我们建设城镇的过程中却人为地破坏了这种良性的秩序。人们忘记了建设城镇的目的,却以手段代替了目的。著名城市生态学家理查德·瑞吉斯特在其《生态城市:建设与自然平衡的人居环境》一书中谈到“在伯克利,35%的城市面积是街道、停车场和人行道,25%是建筑物,还有40%是开放的空间,主要是渗透性很好的草坪。这60%的硬化地面和40%的半硬化地面,使大部分雨水都流失掉了”③[美]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建设与自然平衡的人居环境》,王如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水资源作为城镇内在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一个立体的复合型城镇建设要求严禁破坏土壤的可渗透性,应尽量让街道和停车场的雨水就地入土。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我国全国城区面积为183618.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为43603.2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41860.6平方公里*②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2》。。这意味着在城市建成区,96%的区域是建设用地区域,同时,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9.2%,其中公园面积为285751公顷②,占建成区面积的6.6%,这说明大部分绿化面积是分散的小块绿地。
绿化面积的减少,混凝土阻隔使夏季大量的雨水流失,地下水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逐渐降低水位,城市里自然形成的河流、小溪因为没有地下水的补充而逐步断流,土壤因为缺少水分而不能滋长丰富的多元化的生物,城市土地的生命力日渐趋弱。
同时,城镇中大规模修建的地下轨道交通、轻轨、高架路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弱化城市的生态平衡系统,而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带来的汽车数量的急剧攀升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增趋势更使城市的生态环境遭受到日渐严重的侵蚀。
(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城镇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曾出现过比较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建国初期,我国也曾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环境问题表示过警醒,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城镇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重复西方走过的老路。虽然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我国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已经避免了某些污染问题的扩散,但时至今日,城镇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危险品污染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国各类城镇中。仅以水体污染为例,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4279159.1万吨,而污水实际处理量为4028972万吨,为生活污水排放量的94%,但是污水再生利用量仅为96262万吨,仅为处理量的2.3%,有97.7%的处理后污水实际上仍然是污水。而2011年主要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总计1218085万吨,其中直接排入环境的有861846万吨,占总量的70.8%,只有29.2%的工业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致使工业废水中污染物的排放量居高不下,如,镉8.275吨,总铬126.457吨,铅46.252吨,砷27.700吨,氰化物115.5吨,化学需氧量1489270.8吨,石油类10154.0吨,氨氮138056.7吨,挥发酚1374.0吨*④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数据整理。。现在城镇水体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突破城镇范围,沿着河流、洋流蔓延。其危害正处于扩散状态。
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大多没有直接渗透到城镇生活区土壤中,但是城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土壤污染源,那就是城市生活垃圾渗滤液。《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中2011年各地区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显示,渗滤液中污染物的排放量如下:汞排放量为164.803千克,镉792.959千克,总铬2687.263千克,铅4299.244千克,砷1404.626千克④。垃圾渗滤液正在侵蚀本已处于薄弱状态的城镇土壤生态。
(三)人们不良的生活、消费习惯加剧了城镇的环境负担
近年来,随着环境事件曝光率的增加,人们对于健康问题的重视空前高涨。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消费的生态性、卫生性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改观,但是在对环境的维护上,却缺乏整体环卫意识。虽然“限塑令”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塑料制品的使用,降低了环境负荷的程度,但是迄今为止,即便是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人们主动的实现垃圾袋装化的行为依然没有得到普及,更勿论垃圾分类。在许多城镇的公共场所,垃圾桶已经实现了简易分类(即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但是人们仍然很少有意识的对垃圾进行明确的区分,更少见居家垃圾整理中的分类处理。即便是现在经过堆埋的垃圾也存在较大的问题,更勿论那些露天的垃圾堆放场。大多数垃圾在自然界停留时间都很长:烟头羊毛织物1-5年,橘子皮2年;经油漆的木板13年;尼龙织物30-40年;皮革50年;易拉缸80-100年,塑料100-200年;玻璃1000年。在运输或露天堆放过程中,有机物分解产生恶臭,并向大气释放出大量的氨硫化物等污染物,其中含有有机挥发气体达100多种,这些释放物中有许多致癌致畸物。塑料膜、纸屑和粉尘则随风飞扬形成“白色污染”*“白色污染”现状及处理的研究,http://www.360doc.com/resaveArt.aspx?articleid=103803652&isreg=1。
为了“方便”的原因,我国城镇中大量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塑料袋等正在成为环境恶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那些传统的包装纸、布袋等日常用品却经常遭到各方的排斥。
二、 环境治理的一般路径及问题
环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优良的环境不会单独给某一个个体带来好处,它的好处是普遍性的;如果不是地理空间的局限,优良环境的影响不会因为某一个个体的享有而影响其他个体的享有。一般来说,我们将前一种情况称为环境的非排他性而把后者称为环境的非竞争性。
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看,环境具有的这些特性使市场介入环境治理具有较大的难度,因为优良环境的供给者无法对环境消费者收费,更不能排除人们对环境的消费。同时,历史的教训也在提醒各界一个事实:市场是环境破坏的元凶。所以市场就被排除在了环境维护与治理的范围之外。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使政府和社区成为理论与实践界认可的环境治理的两大支撑力量。
(一)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及其问题
政府作为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占据了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政府作为天然的公共产品生产主体,通过官僚制组织模式提供给社会。政府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经济重要的、主导性的主体,除了与公共产品的特性相关以外,还与政府的特征密切相关。从公共产品的特性来看,除了具有上述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外,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维护还具有如下特点:生产具有不可分性;规模效益大;初始投资特别大,而随后所需资本额却较小;生产具有自然垄断性;对消费者收费不易,或者收费成本较高;消费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公共产品的这些特征使得市场这种制度运行方式不能良好地供给公共物品,而政府则由于其强制性、税收的普遍性、公共性等特点而被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与维护的首选。
而政府对环境治理的介入则是其传统的公共经济定位的延续。由于环境本身的资源性特点,使得对环境的利用产生程度不同的收益。作为独立核算成本-收益比的个体,在自利本性驱动下的理性行为带来的往往是“公地悲剧”的发生。在“悲剧”发生的过程中,虽然个体行动者对于过度开发、利用环境的危害是心知肚明的,但自觉约束个体开发行为的结果却是损己利人的。要使个体牟利者退回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必须有更强大的、富有强制性的力量介入。而这个力量的首选就是政府。
政府介入环境治理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度,从一般意义上约束个体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或破坏性牟利,增强环境资源的自我修复能力;第二,加大对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开发的技术支持,利用政府强大的财力和政策优势,推动环境治理技术的发展;第三,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环境治理进行综合性监督;第四,运用政府的教育与宣传优势,塑造良好的环境维护的文化与认知环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政府维护环境的认知是充满信任味道的。政府被作为理性的、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环境治理者。但是自20世纪中后期公共选择理论诞生及发展繁荣以来,这个神话就成为了过去。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该理论指出,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目标认知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经济市场内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市场亦如此。因此,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的制定者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道德上他们并不会因为身份的转化而发生改变。
环境作为一种相对纯粹的公共物品,政府在维护环境的问题上并没有显见的激励机制。相反从环境中获益的各类利益团体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优势为政府中的官员行为提供激励。所以在环境治理上政府都不能成为理所当然的制度选择。迄今为止,即便是环境主义盛行的发达国家,其环境污染的境况也并不乐观,只是环境污染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而已,而政府则是最熟悉这一变化的组织。
(二)社区对环境的治理及其问题
社区对环境治理的涉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在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的认识,却是在政府发生了明显的失灵之后。政府失灵使市场与社区的价值得到空前的重视。但是,在一般的理论讨论中,环境治理问题的公共性却将市场这个环境问题的肇事者排除在了考虑的范围之外。于是社区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对社区的研究肇始于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滕尼斯在其盛名之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以共同意志与选择意志为分水岭,将工业社会之前的以共同文化导引下的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称为社区,由于社区具有良好的心理与文化约束,所以维护社区整体利益的行为会得到社区成员的一致维护,而破坏社区整体利益的行为则会时时处处受到社区规则的监督与约束。正是由于社区具有如此的集体利益导向,社区这种维护公益的存在就被作为环境维护的重要力量而被发掘。
从当前学界的基本共识来看,“社区是最容易达成相互合作的场所。即便我们将社区简化为最没有特色的一群陌生人的临时组合,他们也会由于人数规模有限、互动频繁而容易通过沟通实现合作。小规模与沟通性都被认为是一些最有利于合作的条件”*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而在一般的环境治理中最为缺乏的不是技术上的突破,却往往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群或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正是由于社区的这种优势,在环境维护与治理问题上,社区可以发挥如下作用:第一、通过利益的共享达成合作契约,规划社区内环境维护与治理的基本目标与实现路径;第二、通过社区内共享的契约精神或价值体系,监督社区内违反环境维护与治理的个体与集体行为,保障社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存在与发展;第三、通过社区“威望”这一特殊的机制,建构社区内富有权力的功能协调机制,协商裁定社区内生态维护上存在的争议。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社区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大环境之下,社区对环境治理介入的功能被放大。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公共经济学专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更是以其有限理性与道德行为的行为模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社区协作在小规模公共资源治理与利用上的巨大价值。她指出“当人们…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②[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5页,第275页。。
社区在解决环境维护与治理问题上有其优势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现代社区的形成大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社区,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冷漠、疏离,不信任、不沟通是常态。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的“当有着高贴现率、相互之间很少信任的人们,在缺乏沟通能力、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无法建立监督和实施机制的情况下各自独立行动时,是不太可能选择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策略的”②。其二,城镇以多元性、异质性、流动性等特点有别于乡村,即便是某些单一社区内部能达成行动的一致并遵从生态均衡的规律,但是城镇本身的特性却会弱化社区的环境治理能力。从而使社区在环境治理中的价值大大降低。其三,传统社区的道德与惯习的规则约束正在弱化并有被驱逐的态势,即便是单一农村社区发展而来的小城镇也在重蹈环境恶化的覆辙。
政府与社区在环境治理上有其特殊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劣势,这些劣势应该有一定的机制加以破解,而市场这一环境问题的肇事者近来也成为理论讨论的新动向。
三、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理论根据
环境恶化,在近代工业社会来临之前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近代工业社会的来临则是与城镇化时代的到来并步齐驱。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步又带动了工业化的深入。伴随这一过程的,还有城镇环境的恶化。市场本身的趋利性及人们追求利润与效益的无限贪欲使环境资源最终崩坏为环境问题。
市场重新介入环境治理问题的理论起点在于市场本身的特性以及学界对环境作为公共资源的特性的再认识,而其重点在于后者。
在传统的公共经济理论看来,按照公共产品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种特性而将公共产品分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公共资源(或公共池塘资源)和俱乐部产品。纯粹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由马斯格雷夫提出来的*Musgrave,R.A.〝Provision for Social Goods〞,in J.Margolis & M.Guitton,Public Economics,New York:St.Martinˊs Press,pp.124-145.,它指的是严格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而俱乐部产品的特点则是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却可以轻易的做到排他;公共池塘资源的特点在于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无法有效的排他,像区域性海洋资源、开放性绿地、开放性牧场等等都属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范畴。正是由于这类资源无法有效的排他,或者排他的成本较高,而无法通过市场来供给,只能由政府或社区供给。而完全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纯粹的公共物品更是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只能通过社区和政府解决。
这就意味着在公共物品供给与维护上,只有俱乐部产品是能够通过市场来供给的。因为俱乐部产品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可以防止那些没有付费的“搭便车者”的介入,同时,它又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能够保障那些购买了“门票”的消费者能够充分享有此类公共物品的全部价值。保障了“消费者”对此类公共物品的消费需求。
但是环境作为一类复杂性较高的公共物品,其外延部分涵盖的内容过于庞杂,它们在传统的意义上并不完全属于俱乐部类公共物品,还有许多属于学理意义上的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是公共池塘资源,比如空气、地下水、跨区域性地面径流等等。对于纯粹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来说,由于他们不能实现有效的排他,而使得每一个个体和组织都能无限地使用这种物品,而无法有效地抵制对这类物品的破坏性使用,致使此类公共物品的供给遭受打击。
在生态均衡的条件下,自然环境的维续本不是人类的创造物,相反,人是环境的创造物。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利用的价值逐步提升,使其生态资源的特点空前凸显,这类资源具有强烈的公共性。人类在利用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资源的再生性,那么此类资源的供给就很可能被中断。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看来,环境资源的大部分是属于纯粹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这些范畴的环境资源是无法通过市场来供给和维护的。
但是,最近理论界对市场的介入问题有了新的发现。正如梅森·加夫尼所说,“多一双眼睛观赏瀑布,并无损于瀑布的美丽。但是这双眼睛的拥有者需要有营地和道路空间,这些资源是有限的,是不得不受到限制的。”虽然瀑布的美丽不会因为增加了一个人的消费而减损,观赏瀑布的人也不会因为多了一个人而使自己观赏瀑布的边际收益受到损害。但是瀑布却不会是纯粹的公共物品,因为它毕竟坐落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零成本”观赏到的。这就意味着即便是那些具备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他们也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公共物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弗雷德·E.弗尔德瓦里才提出了即便是国防这种传统上被认为是纯粹的公共物品的典型也仅是一种区域性公共物品的观点*②[美]弗雷德·E.弗尔德瓦里:《公共物品与私人社会: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郑秉文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第32页。。继而,弗雷德·E.弗尔德瓦里指出,由于所有的公共物品的存续都要占用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土地所在的空间,而土地不是无限的,它的供给是需要成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公共环境资源都是有限而排他的。没有人能够在土地这片资源上成为“搭便车者”。当“物品被资本化,成为一个场地地租,这就推翻了市场失灵的观点,因为场地使用者不能逃避支付租金”②。
如此,所有类型的公共物品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类似的转化为俱乐部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类似地转化为俱乐部产品以后就可以顺利地实现治理的优化,还有一个更为细致的理论问题横亘于环境治理之前,那就是如何利用市场来解决实现俱乐部产品的供给问题。幸运的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基于所有权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就已经将自由市场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念有机的结合起来了。他们打破了以加尔布雷斯、米山、鲍莫尔等人开创并发展的环境干预主义的羁绊,发展出了市场环境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在产权明晰、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罗小芳,卢现祥:《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虽然市场环境主义所设定的理想状态并不能在现实中存在,很多情况下交易成本不但不为零,而且非常高昂。但是,这一理论为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向。
四、市场介入生态城镇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
市场介入生态城镇环境治理的基本切入点就是建构适当的方式以较低成本实现市场收费的合理化,具体来说就是在适当的范围内,将每一类生态问题尽量的区域化,在一定的区域内将生态问题转化为俱乐部类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具体路径如下:
第一,严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作用角色,在制度规划上保障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良性空间不受侵犯。
市场涉入生态城镇环境治理不是单纯的“交易”活动。说到底,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制度运行方式,这种制度运行方式需要得到一定范围的约束群体性行为的有效规则的保障。而这套规则往往是在政府这一拥有强制权的组织通过合法的方式确定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来看,市场的良性运行从来不能缺少了政府的作用,而政府对市场发挥作用的最有利空间就是为市场的发展规划框架和细则。虽然市场可以自发的产生,但是大范围的市场运行必定不能少了政府的协调。
在市场涉入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该积极的为市场的良性运行创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一、对市场涉入环境治理的具体资格、范围、淘汰规则进行设定,保障市场涉入环境治理的共赢结果;二、对市场涉入环境治理的过程进行随机抽查,并建立严格的“违规纠错机制”,建立良好的市场治理信用机制,保障市场涉入环境治理的社会效果;三、对市场治理环境的优异成果保持公益的立场,不随便介入环境治理的成果分享,最大限度地保障环境治理效果的公益性。
第二,在城镇规划与发展的各个区域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类型设定“俱乐部”范围,确立可进入市场交易的具体权力类属与交易方式。
按照丹尼尔·H.科尔对财产权制度的回顾,“有四种基本的财产权体制:私人财产权、共有财产权、国家财产权以及无财产权(或者称为自由获取的财产)”*[美]丹尼尔·H.科尔:《污染与财产权:环境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比较研究》,严厚福、王社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在传统的观念里,私人财产权是一种效率较高的存在。我国城镇土地的国有化形式看起来,似乎是对环境资源保护的一个理论难题。其实不然,在世界城镇环境保护的历史上,并没有明显的例证可以确凿无疑地说明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国家财产权的状态劣于私人财产权。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对“权力”的配置是如何实现的。
按照产权的内部构成来看,产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虽然在产权所有上,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在城镇中的大部分土地、河流、树木都是有一定使用或收益权归属的,只是具体的归属方有所差异。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对城镇里,那些可以确定的具有明确私人归属性质(包括群体性私人归属)的环境资源进行归属权确权并允许其按照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进入市场交易环节,但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要有适当的环境质量测评环节介入,以保障环境交易对环境维护的固化作用。同时,对那些已经确权的环境资源造成破坏的,权属单位按照市场价格要求赔偿,否则,权属单位应对国家进行赔偿。
第三,加大市场对城镇生活污染源的涉入力度,切实降低生活污染对环境的破坏度。
从比重上看,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环境污染正在超过工业污染。虽然生活污染看起来比较轻微,但是数量的积累却是非常巨大的。以生活垃圾为例,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接近于哈丁的“公地悲剧”,在这种情境下,环境处于类似的“无主物”状态,居民在垃圾处理上一次性付出成本以后,增加一份垃圾的边际成本为零,这种制度不能激励居民减少垃圾产生量,必须引入更加细致的市场机制方能解决。在发达国家,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资源利用率要远远超过我国,而生活垃圾的分类也是与市场结合起来的。以市场介入生活污染源的处理,看起来是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其实是在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可利用水平。在市场介入生活污染源处理上了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建立生活用水、用电、用气使用量与价格挂钩的制度,在综合考量家庭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的前提下,建立合理的用量与价格正比例增长的制度;第二,打破大锅饭式垃圾收集制度,建立精细的市场激励制度。在生活小区建立清洁费复合收费制度,综合考虑房屋面积、垃圾分类情况和垃圾产生量,以每户发放的垃圾收集箱(袋)为计量标准;第三,在垃圾实现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以国家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参与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与再加工、再循环,减少由于生活垃圾填埋等传统方式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五、结语
1962年,当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虽然在一些世界性大都市中,环境污染的问题已非常明显,但是从表面上看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所言,“《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阿尔·戈尔:《序言》载[美]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此起彼伏,今天环境主义的发展更成为世界范围内实践与理论认识的重要范式。
但是,环境问题尤其是城镇环境问题如此复杂,单一的环境治理制度根本无法解决此类问题,环境治理的切入必然是多元的,我们主张市场切入环境治理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城镇环境治理中市场都能够介入,也不意味着市场可以独霸环境治理的某一些领域。虽然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对政府与社区涉入环境治理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说明。但是市场在环境治理上依然需要政府与社区的协同*[英]蒂姆·佛西:《合作型环境治理:一种新模式》,谢蕾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成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社区公共治理体系重组——基于山东省的调查研究》,批准号(14YJCB840018)。
刘伟红(1977-),女,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F299.21
A
1003-8353(2015)01-01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