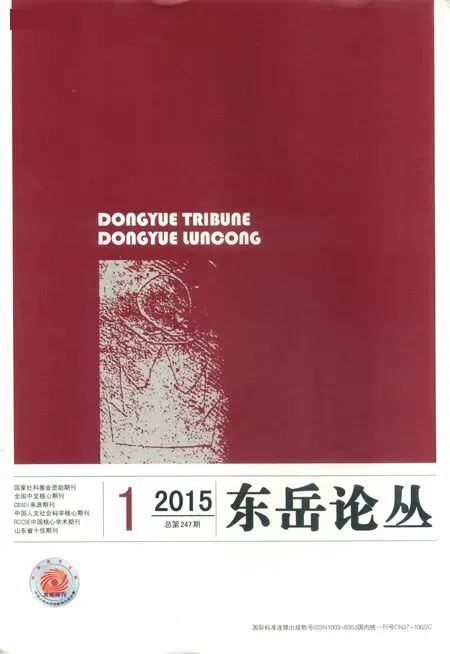后现代消费文化与日本角色消费模式的建构
韩若冰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科地域研究院)
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渗透到日本经济社会领域,日本消费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想色彩;于是,对现代消费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后现代性消费理论在日本动漫文化领域尤其是角色消费市场中得到了迅速地普及和发展。日本动漫角色消费模式的与时俱进和自然建构,使得人们的角色消费活动不仅成为社会个体规避外界压力、构筑个性生活的自然屏障,而且成为数字虚拟环境下人们平衡自身心理结构的手段和融入社会的桥梁。而这种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角色消费异化的消解以及角色消费模式从“物语消费”向“数据库消费”的过渡与转变。
一、后现代消费文化内涵及其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的碎片化和过度生产”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因此,后现代语境下消费文化不仅仅是指“成为商品的文化产品在生产和突出程度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还指大多数文化活动和表意实践都以消费为中介,消费也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符号和形象的消费。因此,消费文化标示着消费不再是一种效用或者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现,而是变成了符号和形象消费,其着重点在于有能力无穷无尽地重塑商品的文化或象征层面,使它更适合充当商品符号。因此,消费社会的文化被认为是碎片化的符号与形象飘浮不定的大杂烩,它带来没完没了的符号游戏,破坏了经年不衰的象征意义和文化秩序的基础”①[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而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则认为,后现代性既是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表示一种思想风格,既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又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与现代社会理论相区别的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将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依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与影像、媒体之间的共谋关系,看到了世界正在由媒介屏幕和各种文化形象符号——如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广告、电视、电影、波普音乐、电脑游戏等——所构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符号世界,其中,文化符号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独立力量;对这些符号的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并日益主宰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出于对现代社会理论关于理性、进步观念的斥拒,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求助于当代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了对各类消费符号的阐释,力图揭示消费和影像符号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社会区分意义,从而形成了从后现代视域出发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进路”①莫少群:《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这就是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当下消费文化中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会越来越被充斥于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消费符号、影像和媒体所操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日本理论界对现代消费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们开始关注后现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后现代艺术作品及后现代思想之于动漫角色创作与角色消费的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消费文化的社会表征系统开始发生变容。在日本最为时尚的东京街头、秋叶原等年轻人最为集中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身着奇装异服或扮成动漫角色形象的年轻潮人在到处游荡。在时尚商店内,许多凝结制造者现代智慧和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后现代商品则摆放在最为显眼的柜台上。仅从人们的穿戴和日常用品来看,人们的消费行为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消费品之“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和评价标准也愈来愈模糊,价值评价标准变得愈来愈多样化。时尚流行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而导致文化消费品“碎片化”的滥觞,并使得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明显。为此,日本理论界将此社会现象归结为后现代主义流行,即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的以“大故(叙)事解体”这一有名的论点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上的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在鲍德里亚、詹明信等人那里,符号与商品融为一体,时间被碎片化,人们沉浸于超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界限在人们眼中已消失殆尽,“无深度文化”成为当下文化的突出特征。而在动漫文化领域,浅薄的零碎式的“萌”片段以及拆分后的各种角色元素充斥社会各个角落而使得人们的感觉出现超负荷的状况。为此,日本学者间々田孝夫认为,这是社会文化的后现代性所致,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四点:(1)大故(叙)事解体,即整合社会的基本原则被削弱;(2)社会开始脱离既存的哲学、思想体系构筑,即既存的哲学、思想不再是普遍的事物;(3)统治社会的权利,由基于规律向信息管理转变;(4)信息环境的变化促发了类像制作的活跃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变容。以上,“(2)”属于哲学、思想范畴,“(3)”属社会学范畴,“(1)”和“(4)”与消费文化相关联②[日]间々田孝夫:《第三消费文化论》,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版,第10页。。间々田孝夫进而认为,“大故(叙)事解体”这个论点由于其表述新颖以及其自身内涵的魅力,人们在使用这一表述时逐渐脱离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论述而被广泛用于社会文化的各个研究领域。像美国艺术主流的迷失、各式各样的艺术层出不穷那样,日本人生活水平提高却丧失了共同的欲求以及对某些社会事务的共识等,都被阐释为“大故(叙)事解体”。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社会文化由精英主义走向大众主义的一个标志,也是动漫角色消费之所以能够进入消费社会主流文化的根源。
直到20世纪末期,人们才明显意识到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思想倾向已经在现代社会肌体中生根发芽,正如本雅明所强调的那样,“大众的乌托邦或积极的运动,生产出了大众消费品,同时也把创造性从艺术中解放出来,并允许这种创造性转移到多样化的大众日常物品的生产之中”③[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迈克·费瑟斯通进而指出,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一切“表明在当代西方城市中,文化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他们所感受和体验的,不仅仅是那些不断出现的日常消费中心,而且还有那些由文化工业(艺术、娱乐、旅游、传统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广泛的符号文化商品及其体验。在这些‘后现代城市’中,人们被迫从事纷繁的记号游戏,而这又正与城市建筑及其环境中大量繁衍记号发生强烈的共鸣。当代城市中的浪荡子或街头游荡者,玩味着、雀跃欢呼着神妙的小说杂集及各种奇异价值观所呈现的做作、随意和肤浅。这种现象,我们在城市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也能够发现。也可以说,这种情况代表的是一种通过高度强调情感与同情来超越个人主义的运动,是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大众以‘后现代部落’成员的形式暂时地聚集在一起”①[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从消费文化来看,在所有的消费领域中,正统的模式以及大家共同遵守的常识、规范的权威尽失,所有的消费行为(违法除外)都被同等视之。像时尚变为随着人们喜好而穿戴,性、暴力等题材则均被出版、电影、电视等媒体传播采用。而价值的相对化也促使了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的出现,这也促使具有多种爱好的消费者增多,从而促进文化的多样化。而这正是角色消费之所以存在和泛化的社会基础。
在间々田孝夫看来,后现代消费文化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非理性主义,即人们对近代社会特征的合理主义价值观反感,并在非效率、非合理的行为中找出意义。这是因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即现代状况的反抗,现代性的核心是合理主义。形成合理的社会,是近代化带给人类的巨大内涵,也是马克思·韦伯合理论以来的常识。但是,并不代表人们对待合理化总抱有好感。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包含了合理化对立面的文化反抗。而消费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亦产生了后现代式的反抗。像家务劳动的省力化、健康的吃穿住行、重视机能、必要性的消费,有利于工作的健康的休闲生活等内容都是消费领域合理化的表现,但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理的近代生活逐渐向其反面的后现代转变。后现代主义虽也把消费行为看作劳动再生产、身心再创造的手段,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成熟,也产生了超越限制、游戏式的消费行为”②[日]间々田孝夫:《第三消费文化论》,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版,第18-19页,第22-23页,第27-29 页。。二是解构,即近现代的文化整合迟缓,约束人们的价值观、规范不断变动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界限变得模糊。这主要是指“约束近代社会人们的各种构造,即文化模式、价值观、社会规范、礼仪等的作用相对迟缓,结果使人们更加自由奔放从而产生了混沌的文化。解构本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中,像近代艺术的不规律、思想上大故(叙)事解体没有批判构造解体反而对从大故(叙)事压抑中解放的个别价值予以肯定。而后现代性中,更是不断推进构造的解体,不仅大故(叙)事,小故(叙)事也予以解体,而这也多与消费文化相关联”③[日]间々田孝夫:《第三消费文化论》,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版,第18-19页,第22-23页,第27-29页。。因为,在这里,后现代主义在引发近代构造崩溃的同时并没有确定替代构造,而是认同各种价值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多元价值观并存这一现实。于是,以“混搭”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样式广泛流行于日常消费领域之中。三是类像的优越化,即相对于重视创造性、原创的近现代价值观,大量的模仿与复制化盛行,其文化意义也逐渐变得浑厚而深刻。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不仅仅是类像,有关模仿、复制、映像、图像、幻想等各种现象亦逐渐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虽说不是同类商品,但又处于‘像又不像’状态并被制造出来。这其中也有许多样式,首先是原本立体的事物,通过类像变为二次元④二次元,原意是指由点和线形成的平面世界,即二维的平面空间;也表示精密影像式测绘仪。现常用于指ACG领 域所在的平面世界,包括动画、漫画、游戏等一系列平面的视界产物。视觉现象。具体来说,即照片、电影、电视节目、电视游戏、漫画、动画、网络等映像,在过去看来,相对于现实中原本存在的立体实物,这些只不过是变化为二次元的映像而已并没有实感。但随着映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与现实相同或者更为逼真的二次元类像出现,改变了消费者的现实感。而游戏等还兼有现实以外的投入感等;所以,比起现实类像更吸引消费者并使消费者满意。而二次元之间可以实现复制,像电影的电视剧化、漫画的动画化、游戏的电影化等,产生各种类像。而三次元⑤“三次元”原意是指由空间坐标系x、y、z三条线组成的空间世界,也就是现实社会的正常生活圈。由于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动漫迷们就形象地比喻现实世界是“三次元”。之间亦可实现类像,像同一商品不同厂家的模仿制造等”⑥[日]间々田孝夫:《第三消费文化论》,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版,第18-19页,第22-23页,第27-29页。。不仅商品,商业设施、空间也可实现类像。
后现代消费文化不仅从本质上颠覆了现代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而且在表达形式上汲取当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成果而不断推陈出新。现代的生活消费模式逐渐被瓦解、改造、颠覆,甚至消弭。于是,在后现代语境中被置于“虚拟与现实”门槛上的人们,开始在纷繁的“类像”、片段式的记忆、碎片化的审美意识以及“似与非似”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并为漂浮不定的个体寻找心灵庇护之所。
二、角色消费异化的消解
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的碎片化和过度的生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美学”虚幻当中。这是因为“商品生产扩张的最终点是表意文化的胜利和社会的死亡:一个不服从于社会学分类与解释的‘后社会’形象,一个永无止境地复制与再生产导致意义爆炸的符号、影像与拟像的循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无拘无束、现实已在后现代的、分裂的、无深度的文化转换为符号的地域当中。保留人在这个层次上的只有大众,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如同‘黑洞’一般,吸纳着源自媒介的能量与信息的过度生产,并无可无不可地观赏着符号永不停歇、充满诱惑的表演”①[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26-27页,第106-107页。。而这些现象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体现。这种社会的“后现代性”表现,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反动”或者说是一种异化。所以,迈克·费瑟斯通进而指出:“在关于后现代的经验的描述中,通常都会提到这些特征:符号与影像漫无目的的混战、风格的折中、符号游戏、规则的混淆、缺乏深度、混杂、模仿、高度写实、即时性、虚幻与古怪价值的杂烩、强烈的情感承载、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边界的瓦解、形象凌驾于语言、戏谑地陶醉于无意识的过程而反对有意识的客观评价、历史现实感和传统现实感的丢失以及主体的去中心化等等”②[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第106-107页。。这就是消费文化典型的异化现象。
消费文化中的异化现象,在角色消费中同样存在,并且有着比较典型的异化形态,如,“美少女控”、“萝莉控”、“大叔控”、“伪娘控”、“二次元情结”③“二次元情结”,又称之为“二次元禁断症候群”。它是指一种特殊的精神病,患者只对漫画、录像带或电视游戏中 的虚构女性角色感兴趣,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则缺乏兴趣。、角色扮演症候群、虚拟恋人等等。这是因为,“消费主义文化为符号消费提供了必需的道德基础,它们本身就是‘消费异化’的表现,而信用卡、购物中心、网络购物街区等新消费工具则对‘消费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都在客观上推动着‘消费异化’向更广的范围扩展,向更深的程度发展”④郭晓敏:《“消费异化论”在当代的发展轨迹研究》,《湖州师范学院报》,2008年第6期。。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事实上是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限制地鼓励人们去进行消费,他们不断地通过现有的大众传播方式去煽动大众的消费激情,去挑起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求。这种超出人们正常生活需求的过度的消费行为同样也会反映在角色消费之中,其结果就是使得平静合理的角色消费在狂热情绪的支配下而走向极端或现实生活的反面。
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主义文化产生的现实基础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建立健全与推广。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杯水主义”、“快餐意识”、“一次性物品消费”等行为的普及和流行,决定消费者消费欲望和需求的经济因素退居到次要地位;而由资本主义文化和由此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则成为使消费者刻意模仿和追求流行时尚以及新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为此,斯克莱尔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力图使人们超越它们的感官需要去消费。以使带来私人利益的资本连绵不断地积累下去,换句话说,以保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永恒存在。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郑重地宣称,生活的意义存在于我们所拥有的商品之中。因此,消费就是生命的全部活力所在,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不停的消费。”⑤[英]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在动漫角色消费过程中,角色消费的制造者们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在角色消费市场中走的依然是这条路线。他们不断地制造出各种角色噱头,将人生的意义、精神慰籍以及文化活动与角色消费捆绑在一起,从而树立起不同的角色消费典型,进而制造出新的角色消费形态和角色消费模式。为此,许多人沉溺于角色消费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角色消费异化”现象。正如沃仑·萨斯曼所说,在消费主义滥觞的时代,人的个性特征在形成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关键就是从宣扬自己的美德转变为宣扬自己的个性人格。“即,个人被鼓励去采用一种对商品的非效用性态度,以精心选择、安排、改用和展示自己的物品(无论是装饰品、房子、汽车、衣服、身体,还是闲暇消遣),从而用独特的风格来显示出物品所有者的个性。为构筑一种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从云集在个人周围的商品和体验中获得满足,便会产生对生活方式信息的持续需求。一个抱有‘人生只此一回’生活观念的个人,对文化产品、体验和生活方式有着大量的、冗长的阐释,所有的解释都表明自身的能力及其生活方式的转变”①[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67页。。
在角色消费市场中,角色消费异化现象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从这样一个路线图就可以看出角色消费异化现象的实现途径。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标新立异以实现与他人的区别即是“时尚”,在社会学上称之为“示差”。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时尚”已成为他们角色消费的价值尺度。“时尚”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专事角色营销宣传的广告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以及现代网络传播技术手段,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将社会淹没在其所营造的“时尚”氛围之中。然而,其始作俑者却是角色制造商(包括角色创作者、角色版权所有人),而广告只不过是角色制造商把自己的销售意志通过一种看似合理合法的渠道转变成角色消费者的消费意识的一种手段而已。
事实上,是角色制造商和广告商以创造精神财富为名,共同为角色消费者描绘了一个温柔的“粉色愿景”。于是,在这种时尚流行与爆发的氛围中,营造出了无数的“超级角色粉丝”,他们以无限地拥有各种角色消费品而满足,以能够引领角色消费时尚而自豪。他们角色消费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角色的无限收集与收藏,真正享受的是角色收集占有这一过程,即通过角色粉丝之间的互动来展示自己在这一群体中的地位和价值。这对他们来说,“对许多物品,我们根本没有使用它们的要求。我们获得物品就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无实用价值的占有。因为怕摔坏贵重的餐具和水晶玻璃的花瓶,我们就从来不使用它们。人们买下一栋房子而占据着许多无用的房间,并且给房子配有多余的汽车和仆人,这栋房子就像小中产阶级街亭里摆设的老古董一样”②[美]弗罗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3页。。这种符号性消费,不仅表现在生活中的品牌消费之中,也同样表现在角色消费当中。在这种由广告效果所引发的符号性消费活动中,角色既是被消费对象,又是广告宣传的“帮凶”。这是因为,商品经销商们将各种具有诱惑力且文化意蕴丰富的角色形象与具体物品捆绑在一起,实体性的消费物品被角色形象所粉饰和美化;同时,“广告通过运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以及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使无意义的事物看起来令人着迷。它以符号的形式向人们展现着各式各样的消费品,通过赋予商品充满诱惑力的文化意义吸引人们,使其沉迷在消费中。在这里,真实消费与意象消费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表面的现实的消费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想象行为,人们从中获得的快乐和满足也是虚假的”③闫方洁:《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唯实》,2012年第8-9期。。于是,商品生产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角色广告控制了人们的消费意识,并打着关注人性、关注人生、关注生命的旗号,将他们制造出的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理念灌输给消费者,并控制和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进而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所以,阿道尔诺也认为,在文化工业中,与其它工业产品一样,文化产品也是通过标准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各种文化产品在制作和表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就像人们所熟悉的美国西部主题电影一样,情节和场景往往大同小异。但是,文化产品又具有个性化的含义,不同的文化产品似乎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而生产出来的,正是这种“个性化的气息”掩盖了文化工业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操纵④参见,Adorno,T.W.1991,The Culture Industry,London:Routledge.p86-87.。
角色消费是现代社会综合发展的产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角色消费的主客体,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角色消费关系是在经过了长期的主客体互动之后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折射到社会文化领域之后,又在社会关系领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角色符号表征系统。角色消费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固化了角色消费的表征作用,并使得角色消费向其它领域扩散。尤其是当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体成为左右角色消费的主要因素。传播媒体为了从角色制造商那里获得庞大的广告宣传费用,充分利用传媒技术制造出许多“虚假需求”,使得正常的角色消费走向异化,而这种异化在人们心理层面被愉快接受的同时,角色消费开始超越“合理需求”而成为一种非常生活方式,一种为了消费而消费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在媒体的诱导下自觉不自觉地蹈入到由现代传媒技术所营造的被动接受的“单向度”的大众商品文化之中。人们面对强势的传播媒体,不仅失去了自主意识和批判思想,而且还把自己与某一动漫角色融合,在传播媒体为人们搭建的虚幻空间游弋。于是,角色消费异化就成为由“自我”编剧,且由“自我”自导、自演的永无止境的具有“叠加”色彩的自娱娱人的生活演剧。
那么,如何消解角色消费中的“消费异化”现象呢?一般情况下,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文化的批判消解由“虚假需求”所带来的过度消费;二是通过批判的文化,树立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和建构科学合理的消费模式。在这里,文化的批判主要是指针对各种有悖于社会文明进步的陋俗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中所携带的具有消极落后、腐化堕落等现象所进行的甄别和批判活动。例如,角色消费中的炫耀性消费、铺张浪费、享乐主义以及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角色消费行为等。在现实中,适度的角色消费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而过度的角色消费则使得角色消费由手段变成了目的。角色消费一旦与人的基本需求相脱节,角色消费就成为一种为消费而消费的变态行为,而角色需求也就蜕变为一种“虚假需求”。批判的文化则是指在先进文化理念指导下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范式、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过程。角色消费批判的最终目的不是取消角色消费行为,更不是否定角色经济这一文化产业发展业态;更重要的是通过辩证分析,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恶扬善的基础上使人们确立起健康向上的角色消费意识,建构起科学合理,融娱乐休闲、精神慰籍、创新创意等相关积极性因素于一身的角色消费新模式,保障角色市场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日本当今社会所流行的角色消费浪潮,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角色这一媒介物去干自己想干但又无法实现的事情,即寄情于角色的一种个人私生活样式。角色消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欲求。
三、角色的“物语消费”向“数据库消费”的让渡
日本的动漫创作一直是以讲故事为主,即借助动漫这一人们喜闻乐见的媒介去表现故事情节从而构建一个庞大的虚拟愿景和“世界观”体系。谁的故事撰写得有趣味、有思想、有悬念、有期待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渗透力,谁就是市场的最大赢家。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众多的常年创作、连载、播放的史诗般的作品身上得以验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后现代文化意识的扩展,角色逐渐从动漫作品的整体中抽离出来,并成为当代动漫文化产业中的“主角”,由此,相对独立的角色消费市场得以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动漫角色市场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扩大了动漫创作者和经营者的收入来源,而且成为日本动漫产业的一个重要支柱。当前,日本角色经济以日本动漫产业为依托,呈现出更为细化的市场发展倾向。角色的创作者、制造者以及营销者作为“文化媒介人”,面对角色消费群体则以小众或大众、以分众或聚众传播的方式力图去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角色的抽离和塑成,角色的碎片分解和重组都变得与大众生活更加息息相关并互相交融,可以说这是动漫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日本的动漫角色消费出现了由“物语消费”向“数据库消费”①[日]大冢英志:『物語消滅論』——キャラクタ—化する「私」,イデオロギ—化する「物語」,东京:角川書店,2004年版。发展的态势。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化产业尤其是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已颇具规模。日本国内的文化资本以独特的方式大力攫取文化资源,即“借助或催生文化工业和传媒事业,利用符号变换或更新来迎合、引导或控制时尚,从而使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升值并进而转换为可量化的经济资本”②何林军:《消费文化视野下的后现代主义》,《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正如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当今世界的资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是知识转化为资本的潜在形式,而这种文化资本往往为现代的“文化媒介人”所拥有。“这些文化媒介人是知识分子的变体,是中产阶级的催生力量和辩护人,也就是说,文化媒介人垄断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控制符号生产与传播,使文化大众成为形式上的中产阶级,满足于生活同质化的共同嬉戏,并使艺术、美学与文化进入民间社会、日常生活”①何林军:《消费文化视野下的后现代主义》,《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正是在这一消费理念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大塚英志提出了“物语消费”这一动漫角色消费概念。所谓“物语消费”,是指源自当时日本市场中的“物语·市场”的市场营销理论。即,商品不再依靠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进行广告、商品开发,在思考怎样创造出符号的具体价值的过程中,将它们附着于“物语”的符号价值上,将商品看成一种故事媒介。与动漫作品中的故事设定、世界观附着于商品之上不同,“物语·市场”旨在商品、商店之上附加了物语并把物语看成媒介。所以,当人们在购买某一品牌商品时,当时的日本社会十分流行“不是买东西而是买故事”的说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品牌化战略”。品牌化战略本来是指企业针对成熟的品牌,为了保持其影响力或使其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通过不间断的推广来形成、维持品牌整体的大故事价值,例如,用历史、声望、地位、专有、手工、稀缺、不可再生、品质、传世等元素制造噱头,从而赋予其各种市场价值。对此,相原博之指出,品牌的历史、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各个主题的优势,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形成“大故事”整个品牌的价值,然后,再凭借品牌价值来刺激消费。耐克、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普拉达、路易威登这样的奢侈品牌,饮料、食品、家电各个领域,“品牌=大故事”的价值构造作为强有力的市场推广手段发挥着巨大作用。许多企业在广告宣传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消费者中提升知名度正是对“品牌=大故事”的一种认同体现。但是,如今年轻人已经体会不到“品牌=大故事”的重要价值观。人们已经开始脱离品牌的历史背景、整体理念、整体印象、主题思想,越来越多地根据其构成要素的差别以及对细节的偏爱而随意决定要购买何种牌子的商品。尤其是年轻人的消费已经从品牌的大故事消费中脱离出来,向“小故事消费=角色属性消费”的方向转化②[日]相原博之:《角色化日本》(講談社现代新书1910),东京:講談社,2007年版,第145页。。在日本,这种“物语消费”的形成与手冢治虫有着密切的关系。手冢治虫开日式动漫之先河,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设定和亦真亦幻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确立起了清新华丽且引人入胜的日式绘画风格并享誉全球。手冢治虫认为,旧漫画形式及其构图形式呆板、内容简单零散,缺少叙事逻辑和思想内涵。为了进一步拓宽构图的空间,加强物语(故事)性,以引起他人的共鸣,手冢治虫通过再创造使得日本动漫有了强烈的物语性。即,以作品的世界观构成整部作品的故事脉络,也可称其为“大物语”。手冢治虫的作品《铁臂阿童木》是日本第一部商业电视动画片,不仅获得了作品角色的商品化权,而且还成为日本动漫作品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驱者。在这个阶段,动漫消费者的消费对象主要为动画、漫画原作品及其相应衍生品,而消费主体主要为普通大众。
在现实商业活动中,杂志媒体、漫画及电影与它们的“物语·市场”有着质的区别。这是因为原本故事附加到没有形态的商品上是不可能的,“事物”不是媒介。所以,只有将印象样态的片断附加到“事物”身上。因此,将能唤起一定故事的信息附加到商品中,使受众自主组织片断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使每个消费者自发地进行故事创作,形成一定的动员消费方式。现实中几乎没有实现这一方式的商品,但就是如此的巧合,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出现了近似这一形式的“Bikkuriman巧克力”。还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下流行的故事广告。在电视剧中植入商品,将商品信息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潜在消费者的兴趣并使商品热卖,是当下十分流行的方式。但是,故事却有着特殊的地方,它必须将商品以15-30秒的广告形式在近一个小时的电视剧中展开。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将电视剧的某个场景作为广告,并且多次出现这一片断化的故事。结果使得观众开始怀疑故事的人物关系、发展趋势,并利用自己的“想象力”补全故事,从而创造故事的整体形象。对于故事的欲求,转化成“想象故事=创造”的欲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对商品的认知和亲和性,进而形成了故事广告的模式。
在大冢英志这里,“物语消费”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创作读者”这一消费形式。这也是对“物语.市场”的一种解释或说明。即在购买过程中或者消费欲求中,产生了想要知道故事的其它欲求。想知道的并不是单指读书,Bikkuriman就极具代表性。巧克力附带卡片的内侧有着片断的故事信息,只要大量购入卡片,就可以得到排列的片断故事信息,并在其中想象或创造。结果,从卡片上有限的信息,进而逐渐形成了名为Bikkuriman的庞大的疑似神话体系。而这时,受众对于故事全体的理解力与创造力是不相同的;这与通常单以文本表现的小说、电影的物语形式也不尽相同。在物语理论中,例如读小说这一行为,在读者进行“读”这一行为时,由于各自所处的角度不同,读者会产生各种想象,从而使“故事”独立展开。而“物语消费”更是将这一分离推入极端。在动漫角色营销中,商家只是向受众提供了片断的信息,但却没有展示故事整体,于是,由受众一方想象故事全体,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也形成了“物语消费”的动力。因此,大冢将能给予的信息进行一定组织,并使受众方进行创造的消费称之为“物语消费”。而作为“物语消费”的几个范例,除了前面提到Bikkuriman,还有一个是Comic MarKet(CMK),即“漫画同人即卖会”,也被称为“二次创作”。这是一种使用动画、漫画的世界观和角色,将自我化身为作者,进行漫画制作出版的同人志创作方式。但是,这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创作,应该说是角色经济中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其结果不仅促进了由CMK产生的角色及商品的消费欲求,而且大大促进了角色经济的发展。因为,在CMK中存在着大量具有强烈创作欲望的受众(读者),他们在互动与碰撞之中形成“二次创作”成果,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创作性消费模式。
大冢英志所说的另一个物语消费典型就是桌游游戏。这是由虚幻的故事构成的游戏,随着出牌,由游戏参与者进行相当于世界观、小说、电影等的信息和角色来历、特征的汇总。每个玩家在自己的角色创造中,任意组合选择种族、攻击能力、使用的魔法等。一方面兼顾到角色的背景故事,一方面由玩家的意志创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由自己创作而成的个性化角色。在虚拟世界中,以玩家为中心进行管理,共同作业从而展开故事的游戏,这样的模式已经在电脑游戏中实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类游戏更是一种“疑似创作行为”。而这种疑似创作行为的代表就是水野良的《罗得岛战记》,此书虽最终以小说形式刊行,但其原型是由作者玩桌游形成的故事记录。它如实记下了游戏中玩家的对话,当然并不是公式化的记录,而是将整个游戏过程以更为易懂接受的方式写成小说。这种题材也被称为再现(replay)小说,即将游戏的记录写成小说供人们阅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动漫创作者和动漫制作者来讲故事、表现故事的现实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年轻人开始摒弃之前的消费方式,即从“大故事”中脱离出来,只消费“角色萌元素”。在社会交际过程中,他们根据萌元素对圈子内的朋友进行角色定位;然后,在特定的朋友交际圈内形成“交流=消费”的角色萌元素消费特征。就像御宅族的动画消费无视动画的整体而一味地纠结在小故事或故事细节上一样,年轻人的交流也是无视朋友的人格以及整个圈子的“大故事”,只是互相笑说对方的“萌元素”的模式。所以,在大冢英志看来,漫画、小说、软件的“物语”已颠覆其原本形态,读者、作者亦产生了质的变化,所以用“消灭”一词来概括其意义上的“变容”。这就是大冢英志提出的并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物语消灭论”。对此,大冢英志进而采用对“物语”的因果规律进行考察的方式来加以探讨。即“物语”并不是指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大物语崩溃”,不是在意义上更为宽泛的“物语”;而是倾向于物语的文本解读,着重于故事脉络和内部构造。即,根据故事展开的因果规律探讨其社会构造的影响,或者这又导致了什么样的社会的形成。所以说,在后现代语境中可以用“物语”替代“意识形态”来建构或重塑现实社会。于是,在动漫角色消费领域就出现了由“物语消费”向“数据库消费”的让渡和转变。
“数据库消费”是日本角色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上形成的一种角色消费形式,是基于“大数据”背景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学者东浩纪先生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东浩纪认为,作为一种别样的消费行为,无关故事原作,只单独消费片断的插图及故事设定,并且面对这些片断,消费者会随便移植进自己的感情思想。也就是说,与先认同某种内容的世界观、主题、故事本身,继而引发消费行为的以往的消费倾向明显不同①[日]东浩纪:『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ンダ――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講談社現代新書,2001。。大数据时代,御宅族消费的主体,不再仅限于某个角色及其商品,而是涉及与角色有关的所有信息、片段的消费,即不仅是作品、商品,其关联的所有信息都会成为御宅所关注的事物,都会成为他的消费对象。在这里,从大背景的故事(大物语)中抽离出来的单个的角色不存在由上到下的阶梯性,而是数据库般的横向排列,消费者在消费时就如同在数据库中检索数据一样,挑选出自己喜欢的要素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组合后进行消费。而随着快捷便利的新媒体(手机、微博等)的发展以及信息传递虚拟空间平台的搭建,以角色为代表的信息片段(或碎片)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萌元素”信息,逐渐成为大众争相消费的对象。
日本当代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由“物语消费”向“数据库消费”发展的态势,与日本社会“同人志即卖会”的兴起和“御宅族”的成长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人志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已有的知名角色进行作品的二次创作,这也致使原作品与角色分离。关于角色化数据库消费,相原博之在其所著的《角色化日本》中举了三个例子。一是关于ipod的设计;二是关于运动电子产品Wii的设计;三是为年轻人服务的“时尚精品店”。此外,还有DJ音乐软件的设计等。这应该都是属于数据库消费的典型。
ipod是一款苹果公司设计和销售的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ipod自2001年问世以来,又相继推出了shuffle、nano等一系列产品,已经成为现今年轻人的“消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ipod与之前的随身听为代表的CD播放器之间决定性的不同在于,它是“音乐数据库”。其中,并没有以唱片为代表的创作者一方的世界观、主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大故事”的存在。在唱片中存在的统一感、世界观、总旋律等等,在听众的自由选择中被无限制地数据库化和重新编辑。年轻人从下载的无数曲子中选出自己喜欢的,重新编排,然后消费。这种ipod型的音乐视听、音乐消费模式,与之前的“萌消费”是极其相似的,是典型的数据库型消费模式。
任天堂的Wii制造出的真实和非真实的倒置景象,将“身体的角色化”象征性地展示给世人。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把遥控器作为球拍来玩网球的广告,而这就是革命性的游戏机Wii。最初,游戏就是使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物在游戏的空间里实现的模拟体验。Wii提供一种倒置的环境,特意让你在室内拿着遥控器面对画面就能玩需要真正握着球拍站在球场上才能玩的游戏。也就是说,把很容易进入现实的东西刻意在非现实的环境中使之成立的“游戏”。极端地说,对现代人来说,比起真实的网球,非真实倒置的Wii空间更加有趣。每次看到用遥控器来操纵球拍玩得正高兴的女孩子,都有她即将“角色化”的错觉。而真实的身体就那么毫无意义地挥舞着遥控器,很快就塑造了既不属于游戏空间也不属于真实空间的“角色化”的身体。
为年轻人所推崇的“时尚精品店”也是数据库型消费的典型形式之一。在当代年轻人中间,首先像过去那种用同一牌子的服饰进行整体搭配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而自由的对不同的主题、元素进行组合,搭配出颇具个性的自我已成自然。再进一步,故意破坏整体的统一感,着重突出像衬衫、鞋子、包包、帽子这样的单品的想法业已成为现在时尚的主流。这与在“身体的角色化”中提及的碎片化、服装化是相关联的意识。某个牌子由谁在什么样的想法下创造的,这自不必说会得到年轻人一定的认同与理解;而在搭配时反而故意舍掉这些特点,由自己来随意搭配,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意识。
在角色的数据库消费方面,Nico nico动画则更具典型性。Nico nico动画是日本国内有名的动画共享网站,它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能在动画中重叠表示即时评论的功能(国内称之谓“弹幕”)。用户可以在动画播放中的任何时间、任意地点发表评论,犹如与众人一起观赏动画一般。而对作者来说,可以随时把握观众对动画作品的反应和感知点。在Nico nico动画中,MAD动画十分受欢迎,它是由原创的动画作品中抽取动画音乐从而重新创作而成的作品,也可称之为混搭(Mashup)型作品。之后,MAD动画的作者们再根据Nico nico动画的特征,互相刺激、鼓励,并在Nico nico动画上传更多的作品。MAD动画的重点还在于其多从商业动画节目中抽取素材。2007年8月31日,虚拟动漫角色——“初音未来”面世,这是日本动漫角色表现的一个大胆而成功的构想,她融动漫萌元素、美少女角色、现代音乐于一体,塑造了一个给人以巨大冲击的典型的数字化视觉形象;而这些都基于日本现代网络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的发展。
“初音未来”的出现,也为MAD动画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初音未来的动画化并不是从商业动画等内容中抽取素材,而是由网络群体创作的作品中再创作新的动画。在借用其他动画的同时再加上新的内容,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由此还得到原作者的支持。许多作者欢迎自己的作品被他人引用,所以,许多动画都是合作创作的结晶。初音未来在这种合作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其横跨各界的创作活动,像数字音乐的作者、同人志和插画界的作者,以及数字动画作者等。虽大多数为业余粉丝,但也有许多专业人士参与其中,如,作曲、校准、作画、编辑等专业行家。初音未来这个角色动画创作,作为一种基于网络化状态下合作互动的创作活动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动画创作群体的多样性;二是创作活动作为数据的可视性。关于初音未来的创作涉及作词、作曲、声音合成、插画创作、动画制作、动画编辑等,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创作群体,他们以动画数据的再利用连接起来形成共同的创作群体。一般情况下,创造活动难以用数据表现,但Nico nico动画中的初音未来动画却使数据表示变得可能。初音未来的最大特点是她没有人物性格的预设。“性格设定”既是角色的重要构成,又是其魅力建构的最为重要的着力点。而初音未来只有简单的设定和声音,可谓是以“一张白纸”似的形式在用户的培育下成长为一个“如自己所望的偶像”。如此一来,公司更多的是在塑形,将注入内涵的初音未来以各种不同形式演绎,像现场演唱会等,从而又激发用户发现初音未来的潜在魅力。初音未来形成的正是“形的连锁”。其一方面外形似真正的偶像,另一方面又因其满足使用的期待而更具柔软性。在现实中,用户参与设定的角色,以及多种使用与初音未来的商品设定均由用户创作完成。由于Crypton公司及媒体的许可,以及多种商品开发,这些设定逐渐被大众误认为官方设定(公式设定)。严谨地说,这并不是官方设定,只可谓是“公式化二次创作的设定”。如此一来,初音未来的设定就如其芳名,“将来的可能性=未来”,其角色形象会逐渐丰富起来。
初音未来的成功之处,一是得益于现代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数据库环境的形成;二是其“草根性”特点的凸显。从一般意义上说,初音未来的出现使得“门外汉”也可作曲。使用初音未来软件,更多的是要具备电脑知识。如果能识音,软件操作更加简单。事实上,Nico nico动画中大受欢迎的创作者几乎都是专业出身,即使是业余粉丝也多从事与音乐有关的事业等。所以,不乏受初音未来的影响而购买软件,最后却因为音乐知识的缺乏而气馁的粉丝。这也促成了“汇集感叹为一身”的心情拟人化角色“弱音Haku”的诞生。当然,也有许多粉丝是出于对角色的热爱,把软件作为一种角色商品买入,这也是渗入萌元素作为销售战略的商业效应。初音未来作为音乐软件、视觉偶像、萌角色和交流工具,其“人格化”并不很完美,但这种“不完美感”可以看成初音未来的“萌”而更具人性。而这就是“初音未来”的生存模式。
四、角色消费的未来与建构
动漫角色本身所包含的符号性、社会性、经济性,使其具有了一般商品所应具有的属性,即使用性、交换性、表征性等属性。再加上角色的草根性、普适性、识别性等特点,角色消费经历了从小众到大众的发展过程,角色市场也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转换中建立起了自身发展的体制与机制,角色经济也由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在后现代语境下,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品牌消费”是一种“贵族式”高消费的话,那么,角色消费应该是一种“平民式”的草根消费。虽说这两种消费都具有符号消费的一切特征并具有“示差”和“趋同”的标识功能,但由于它们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其具体表征意义、评价标准和社会追求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品牌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取向是“示差”,而“角色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则是“趋同”。当然,在角色消费市场中,“示差”与“趋同”现象依然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一种角色消费行为可同时具有“示差”与“趋同”的功用,只是在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时其示差与趋同的表现有不同的侧重而已。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具有“两面性”,一个是现实社会人,一个是网络人;同时,人人都是“自媒介体”,即个体可以同时集受众、载体、信息源于一身。尤其是网络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和人们的生活剧场化倾向进一步推动了动漫角色进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可能。
“数字化角色”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在社会上演绎出一个真实的“虚拟社会现实”。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以及超常规的发展,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通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渐渐远离面对面的人际沟通,更加倾向于网络交流。在虚拟世界中每个人都给自己命名一个“代号”或者是动漫中的某一“角色”;于是,虚拟世界中的“角色”在网络上代替真实“自我”,在网络世界中纵横驰骋。与现实社会相比较,“角色化”了的人们用面具掩盖了自身的真实面孔,隐去了自身的现实身份,没有了社会化过程中承载的各种社会责任,从而也就失去了各种社会约束。这种脱胎换骨般的自由交际,使得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加真实①参见韩冰:《动漫·角色·符号:日本当代都市民俗的意义表达》,《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日本学者相原博之曾说,“这样的日本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比起肉体存在的现实世界,还是漫画、动画所形成的‘虚拟现实’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和共鸣,这也并不是什么骇人听闻了。我们已完全习惯于每天沉浸在网络和手机上的虚拟空间里。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甚至感到生活在虚拟空间里十分愉快。对那样的日本人来说,即使在不知不觉间感到‘肉体的现实世界’和生存在其中的‘肉体的我’之间有着不协调和排斥反应,也没有感到什么特别可吃惊的”②[日]相原博之:《角色化日本》(講談社现代新书1910),东京:講談社,2007年版,第8-9页。。这是因为,除去“肉体”,日本人十分注重保持“自己的可爱心理”。为此,日本人更是创造出了一些没有故事、没有世界观为依托的“子虚乌有”的动漫角色,假以真人配音,通过个人的自由创作而自娱娱人。
针对游弋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角色消费,已经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为中心进行分析,也不能用传统商品的消费观念来解释这种消费行为;事实上,在这种消费行为背后隐含着动机结构问题。因为,“这种动机结构通过商品来导致人们产生快乐、匮乏、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感觉”③[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第33-34页。。坎贝尔曾经指出:消费的扩张需要一种伦理存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是一种浪漫主义以及它所强调的想象、着迷、神秘、创造性与情感挖掘,而不是新教精神提供了动力。消费的核心行为并不是产品实际的选择、购买与消费,而是追求产品形象所赋予自身的想象的快乐,“真实”消费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精神”享乐主义的产物。“根据这个观点,衍生于小说、绘画、戏剧、纪录片、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时尚的快乐都不是广告人的操弄或者‘沉迷于社会地位’的结果,而是受白日梦刺激的虚幻的享受。这种愿意活在欲望、迷幻与白日梦的性情,以及投入大量时间对它们加以追逐的能力,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各有差异”④[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第33-34页。。“初音未来”的出现,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从被动观众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埋名网络虚拟空间之中,他们需要社会互动所带来的真实存在的感觉;同时,他们也不甘心沉溺于网络部落那种即聚即散的游牧生活,他们需要众人共聚互动所带来的那种无所顾忌的“草根式”狂欢。而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电视节目的录制,观众的参与度非常高,录制现场既是在场情景又是录制背景。制作人与观众、演员与观众的界限变得模糊,编剧的理念和创作思路被执着而又热情地的观众所左右,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与观众的喜怒哀乐高度契合,随着剧情的延展与跌宕,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众人迸发的热情所消解,结果被忽略而过程变得更为重要。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自我和角色已经融为一体,虚拟与现实已经融为一体,与其说是在欣赏一个演剧,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身临其境的有始有终的预定之中的草根式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