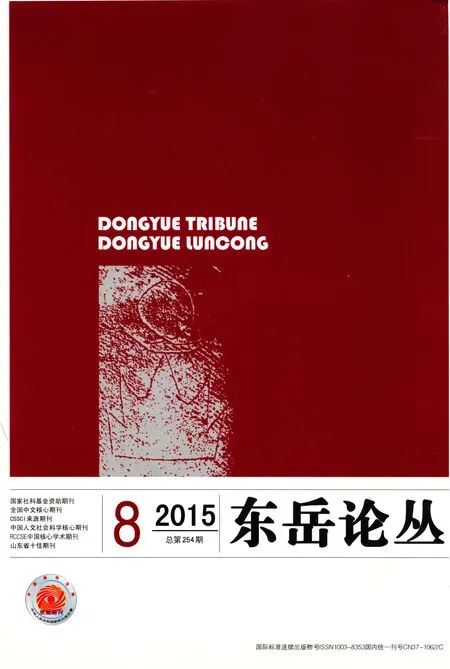论未遂犯的着手
黄 悦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一、概说
(一)处罚未遂犯的刑事政策要求
各国刑法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体现了法益保护的周延化和处罚前置的刑事政策要求。但是,如果刑法过于偏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要求,则必将损害国民的自由权利。处罚未遂犯的刑法规定在本质上就表现为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之间的矛盾和统一①。理论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概言之,有关未遂犯的全部学理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下述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阐明处罚未遂犯的实质根据;二是合理限制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亦即确定未遂犯的处罚条件。未遂犯处罚范围的限定又包括在犯罪阶段上区分预备犯与未遂犯,以及从处罚根据的角度(行为的危险)区分可罚的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
(二)着手的概念
从事实层面观察犯罪行为的结构,我们一般可以将犯罪分为决意、预备、着手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结束、发生犯罪的结果。当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之后,犯罪即宣告既遂,由此便构成了完全的法定刑威慑②。未遂犯的认定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在犯罪阶段上确定认定犯罪行为是否越过预备阶段并进入到未遂阶段,在刑法理论上即着手的判断。“着手”和“动手”一词在语义上有相近意思,一般是指“开始或准备做某事”。因此从语词的日常含义进行分析的话,犯罪的着手并非仅指未遂犯之“着手”,预备行为也属于“着手”语义的涵摄范围。但是,当前各国刑法无论其立法或是理论,都秉持着限制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之原则,且一般都将着手的时点视为未遂犯的成立时点。因此,在刑法解释层面,着手的判断就专指在“犯罪路途”(犯罪阶段)上如何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
(三)着手理论与不能犯理论的关系之厘清
限定未遂犯的处罚范围,除了在犯罪阶段上区分预备和未遂,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对未遂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进行实质性判断。即,根据未遂犯处罚根据理论,通过危险的判断来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关于不能犯的认定问题,尽管刑法理论上的争议非常激烈,但在论理形式上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未遂犯是指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不能犯因其行为不具有这种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不具有可罚性,不应作为未遂犯处罚Ⅰ出于主题限制以及文章篇幅的考虑,本文在此主要针对着手的认定展开探讨,不能犯的问题将另行撰文论述。。
着手的认定与不能犯的判断虽同属未遂犯领域的具体问题,两者在理论框架上有着明确的机能界限。日本刑法学者平野龙一教授就曾明确指出:“从阶段上看,未遂与预备的区别在于是否到达了‘实行的着手’。但即使从阶段上看到达了‘实行的着手’时,也存在不能以未遂犯处罚的情况。……‘实行的着手’是具有发生结果的迫切危险性的行为,因此,实质危险性也是‘实行的着手’的一个要素。缺乏这一要素时,就不存在‘实行的着手’,不成立未遂犯。这种情况称为不能犯”③。从平野教授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区分预备与未遂的理论学说,与不能犯的危险判断学说,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学说。尽管在平野教授的论述中,两者都属于“实行的着手”的范畴,但实际上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关联Ⅱ需要说明的是,平野教授之所以认为两者都属于“实行的着手”的理论范畴,很可能出于刑事立法规定的考虑。因为从日本刑法的未遂犯规定中,可以明确导出未遂犯的成立条件即实行的着手,因此不得不将区分预备与未遂,以及区分可罚的未遂犯和不可罚的不能犯全部统摄在着手理论的范围之内。即便是出于理论上的沿袭和约定俗成,同时赋予着手理论以区分预备和未遂、未遂犯和不能犯的机能,也应当在其内部对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界分。。国外的大多数学者在展开相关论述时,也基本上注意到了上述区别,并且也都对着手理论与不能犯理论的不同机能作附带说明。如西原春夫教授认为,“不能犯是指行为人自以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不可能发生结果而不能既遂的情况。对此不能作为未遂犯处罚,也称不能未遂”④。前田雅英教授亦指出,“形式上看虽有实行的着手,但该行为的危险性极端小、不值得作为未遂处罚的情况,就是不能犯(不能未遂),不具有可罚性”⑤。曾根野村稔教授、曾根威彦教授在论述不能犯理论是,也持类似观点⑥。着手理论和不能犯理论中都有所谓的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对立,但在对这些学说进行梳理和评析时,应当注意它们是针对不同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应混淆其各自的理论机能Ⅲ但是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缺乏学术敏感,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着手理论和不能犯理论的不同机能。参见劳东燕:《论实行的着手与不法成立的根据》,《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第1241-1250页。在该文中,作者以着手认定中犯罪人的主观要素被不断承认和采纳作为体现主观未遂论的论据,殊不知在着手的判断中考虑行为人设想的犯罪计划,只是作为判断行为是否跨越了预备阶段并对法益造成了一种紧迫性侵害危险的判断资料,这与危险本身的判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真正能够体现未遂犯处罚根据取向的是后者——危险的判断——这一实质性问题。在该文的论述过程中,作者对着手的认定与不能犯理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而是在论据列举上随意穿插跳跃,并且无视印象理论在德国已日薄西山、日本传统的具体危险说也正在被不断地质疑和修正的理论发展现状,最后认为各国未遂犯理论“最终都投向主观未遂论的怀抱”,其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二、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着手的关系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未遂犯处罚范围的具体限定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一般认为,主观未遂论和客观未遂论在着手的认定上,无论是论证思路还是具体结论都会有所差别Ⅳ一般认为,着手的具体判断标准与理论上采取何种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密切相关,但是如果彻底摒弃纯粹的主观未遂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认定着手的纯粹主观说,现在的着手理论已经不再像不能犯领域所展现的争议那样,必须以某种处罚根据为基础,而是逐渐显现出其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理论上的独立性在后文会再次论及,在此先不予展开。。因此,在对着手判断的具体标准展开讨论之前,还是有必要将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作为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关于未遂犯处罚根据的学说,日本刑法学者井田良教授明确指出,“现在的刑法学是以刑罚是针对‘所已作的事情’而科以作为其反动的制裁这种观点为基础,采取所谓客观主义的犯罪理论。未遂行为人也不是以‘将来也许会实施’为理由,而必须是针对‘现在所已作的事情’或者‘已引起的实际侵害’,接受作为其反动的刑罚。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未遂行为中何为‘已引起的实际侵害’”⑦。根据井田良教授的论述,我们可以认全部未遂犯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在何种程度上,一个不完全齐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仍然能够作为犯罪处罚,这种为刑罚处罚奠定根基的理由是什么。未遂犯的实质可罚性,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赋予根据。界定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历来就是是刑法教义学中被学者讨论最多、且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在处罚根据的问题上,客观未遂理论和主观未遂理论之间的交锋尤为激烈⑧。
(一)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之间的对立
客观未遂论源自费尔巴哈的“客观危险说”。客观未遂论主张应当从行为在客观上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险作为处罚未遂犯的实质根据。仅具有犯罪意思,但行为并没有引起既遂危险的,不应当纳入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未遂是以实现犯罪为目的的外部行为,具有客观危险性,只有当某一行为违反了或者威胁到了法律,它才是违法的,仅仅只具备违法企图,不可能给行为打上违法性的标记”⑨。客观的未遂论否定不能犯具有可罚性,由此限制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此外,由于未遂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产生既遂结果,因此客观未遂论主张对未遂犯应当减轻处罚。
客观未遂论虽然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前德国的通说观点,但这一时期德国的司法实务界确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主观倾向。例如当时德国帝国法院的判决中就有如下论述,“在未遂中,犯罪意志是刑事法律所禁止内容的征表,相反,在既遂中出现的是由犯罪意志所引发的违法结果。……如果说敌视法律的意志是可罚未遂的本质,那么行为人是否已经实施了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是不重要的,而只是出于法安全性的理由要求”⑩。主观未遂论认为处罚未遂犯的根本理由是犯罪行为所表现的行为人的危险性格,是行为所征表的犯罪意思。因此不能犯未遂同样具有可罚性,并且既遂犯与未遂犯在处罚上无需区别对待。
(二)“折衷”的印象理论
刑法处罚未遂犯,其正当化根据究竟是在于行为人通过行为所征表的犯罪意思,还是行为本身引起的侵害法益的危险。对此各国刑法实体法并没有表现出明确态度。我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刑法,对未遂犯的处罚上均采取了所谓的得减原则。因此,尽管学说上的主观未遂论与客观未遂论之间的争议仍在持续,但各国实定法至少没有对此表明立场,即“既未采取完全的主观主义也未采取完全的客观主义,而采取的是折中立场”⑪。
在未遂犯处罚根据的学说中,德国目前的通说印象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折衷理论。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倡借鉴印象理论,并试图通过其理论内核为我国的通说辩护⑫。印象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处罚根据上的折衷式理论,是因为该说主张在确定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时,行为的主观性要素和客观性要素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择一关系,而是应当以一种“叠加性方式”综合考量。并进而认为,在确定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时,应当以主观未遂理论为基本出发点,以行为人的行为“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秩序的信赖”作为限制处罚范围的辅助性原则⑬。通过“动摇对法秩序的信赖”这一客观性要素,印象理论在确定着手时点的认定以及赋予不能犯未遂的可罚性方面,既符合了德国刑法第22条关于着手认定的立法规定,也能够合理解释第23条第3款关于重大无知的不能犯未遂的处罚要求。得益于印象理论的主流学说地位,德国刑法学的理论与实务在未遂犯领域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即便如此,由于其理论上带有无法自我克服的缺陷,对印象理论的批判在德国也已经开始呈日益激烈的态势⑭。我国学者断不应盲目借鉴印象理论并试图以此维持不能犯未遂的传统学说,而应当看到全面审视德国目前的理论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并努力促成客观未遂论的理论共识。
(三)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对当前着手理论的影响
着手的认定与不能犯的判断都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具有密切关联。各种学说之间的争议背后体现的都是不同处罚根据论的角力。“例如,关于着手的认定,客观的未遂论主张以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达到紧迫程度时为着手;而主观的未遂论一般认为,客观行为征表出行为人具有特定的犯罪意思时就是着手。又如,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的区别,客观的未遂论坚持以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来区分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主观的未遂论基本上不区分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充其量将迷信犯排除在未遂犯之外”⑮。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有关未遂犯处罚根据的三种学说,其争议点更多聚焦在如何定义危险的概念这一问题上,而对危险概念的不同理解则直接体现为对不能犯是否应当处罚所持的不同立场。相反,在认定着手的时点时,即便在今天仍支持主观未遂论抑或其变种印象理论的学者,如果忽略已经完全失去市场的以主观未遂论为基础的纯粹主观说的话,其在着手认定上都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处罚范围的过于提前。现在的情况大体是,有关着手理论的探讨并未与不能犯领域产生的激烈争议形成呼应,换言之,着手指的是“行为对保护客体产生具体危险”的时点,其实质上是一个划分犯罪行为阶段的时间性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时空性概念)而非对危险概念本身的探讨,这种“时空性”特征决定了着手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处罚根据论的理论独立性。关于着手理论如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处罚根据论的限制,本文第四部分将展开具体论述。
三、着手的判断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并且出于法治国原则及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这种作为实质性处罚根据的“危险”应当辅以一种时空条件上的限制,以具体地区分犯罪预备阶段与实行阶段。而将这种时空性的限制条件理解为侵害法益的“紧迫性”危险,在理论上被归入为着手认定中实质客观说。根据实质客观说的观点,所谓实行的着手,是指行为引起了侵犯保护客体的一种紧迫性危险。有关着手认定的学说主要有主观说、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三种。在具体论述着手认定标准前,有必要对学说上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和评析。
(一)主观说与形式客观说
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着手判断的学说向来有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论,其中客观说内部也有分歧,即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的分歧⑯。
主观说以主观未遂论为基础。主观未遂论认为处罚未遂犯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在具体的犯罪行为中就是指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因此,主观说在认定着手时,同样以行为人的犯罪意思为中心,只要能够肯定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原则上就可以认定为未遂犯。由于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只能借助客观行为来表现,因此主观说在着手的认定上多采取犯罪征表说,即只要犯罪意思表露出来就可以作为未遂犯处罚。例如,“犯意的成立因其遂行行为而得以确定性地认定之时”⑰,具有“犯意的飞跃性表动”之时⑱,就可以认定为着手。通说对主观说的批判主要在于,该理论不仅使得预备与未遂的界限既不明确,而且过于扩张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处罚范围前置)。但这与其说是理由,还不如说是批评者基于自身立场的一种结论,主观说真正的缺陷其实在于主观未遂论本身的缺陷,也就是主观未遂论无法从理论自身的立场解释未遂犯减轻处罚、不处罚不能未遂(或免除处罚)立法实践,并且“除了欠缺理论依据以外,以行为人本身对于其行为之情绪反应作为着手判断的标准,其标准也欠缺相当的实证可能性”⑲。总之,主观说现在已基本上失去了学者的支持,主张根据客观性标准来决定实行的着手的客观说已成为学界通说⑳。
形式的客观说主张在构成要件行为中就能找到着手认定的标准。因此该说认为,行为人如果已经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一部分就可以认定为着手。形式客观说主张以是否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作为着手的标准,这会导致很多犯罪的未遂阶段被推迟,又会不当扩张一些犯罪的未遂成立的范围,从而在具体案件中产生不合理的结论。“质言之,采用部分构成要件实现说延后着手,但只要构成要件范围扩大,着手几乎会提早认定,构成要件本身虽然能够节制既遂犯的可罚界限,但在未遂犯部分则不完全有效”㉑。此外,固守实行行为的犯罪定型机能是形式客观说的理论初衷,但其在实际展开中往往无法贯彻到底。例如,作为形式客观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团藤重光教授曾指出,“即便其本身并不显示构成要件性特征,如果从整体上看,可以将该行为理解为定型性地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那么不妨将其认定为实行的着手”㉒。但是这种说法不仅代表了一种向结论合理性妥协的态度,而且其实质内容已经和后述实质客观说相差无几了。
(二)实质客观说
形式客观说将未遂犯的处罚时期提前到直接引起构成要件结果行为的前行为上,但如果要从实质上理解其依据,就必须回答“为何这么做,理由在哪里”这一关键问题。在日本刑法理论中,持客观主义刑法观念的学者一般将上述问题求诸“引起既遂的紧迫危险”㉓将上述问题求诸“引起既遂的紧迫危险,该观点被认为是着手认定中的实质客观说。实质客观说认为未遂犯属于一种具体的危险犯,换言之,仅当行为引起了侵害法益的紧迫、具体的危险时,才构成未遂犯㉔。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如果开始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一般就会引起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但是在一些特殊犯罪类型中,例如隔离犯、间接正犯以及教唆犯,紧迫性危险发生的时点和构成要件行为实施的时点并不一致。
【案例1】妻子预计其出差在外的丈夫两天后回家,于是提前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丈夫经常喝的威士忌中,想以此方法谋杀亲夫。两天后丈夫回家后果然按期设想喝下毒酒,但经抢救及时并未毒发身亡。
本案中,妻子在开始投毒的行为是符合杀人构成要件的行为,但是只有当丈夫在即将喝下毒酒时才能认为其生命法益陷入到被侵害的紧迫危险之中。因此,本案中的着手时点是在构成要件行为之后才产生的。与此相反,着手时点有时也会在行为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之前被肯定。
【案例2】被告人意图谋杀自己的丈夫甲,于是找来被告人A商量如何实施杀人行为。经过共同谋划,A打算先在汽车上用氯仿将甲迷晕,然后再将汽车开到海边将甲连同汽车一起倾覆到海里,以此造成交通意外的假象。在按照原计划将甲迷晕(①行为)之后,A随后开车来到海边,将汽车以及被害人甲一起倾覆到海里。(②行为)事后查明,甲系因为涉入氯仿摄入过量窒息而亡。
本案中的①行为原本只是杀人行为的手段行为,但日本的判例以“其是与直接杀害行为密切相关的并能左右杀害行为的实施”为由,将其认定为杀人的实行着手行为㉕。总之,实质的客观说认为,着手的判断并不以开始实施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行为为坐标,而是以是否到达紧迫性的危险状态为限,在某些犯罪中实行行为的开始实施固然也意味着行为侵害法益客体的危险达到了紧迫性的程度,但是在更多的未遂犯罪的场合则需要建立专门的判断规则。其实这也说明实行行为是既遂犯的固有要件,着手是未遂犯的成立要件,既遂犯的构成要件并不会必然推导出未遂犯的构成要件,对受保护客体的紧迫危险的判断需要建构专门的判断规则。
实质的客观说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着手的判断应否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坚持实质客观说的学者在违法论上一般主张结果无价值的客观违法性论。因此,实质客观说论者往往不承认有所谓的主观性违法要素。而且,在彻底的客观违法论者看来,行为的客观危险体现了未遂犯的违法性,因此危险的判断基础和标准都应当是客观的。“在认定实行的着手以及具体的危险时,一律不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㉖。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即便坚持客观未遂论,在判断着手时如果不考虑行为人的计划,便无法认定是否已经出现结果发生的危险㉗。本文亦主张在一些特殊的犯罪中,有必要承认主观性违法要素,例如未遂犯和目的犯㉘。同理,在认定着手的某些场合(未实行终了的未遂)Ⅰ下文中所提到的需要考虑行为计划作为判断资料的未遂犯,都是指未实行终了的未遂犯。,行为人的计划是不可或缺的主观性要素。
(三)未遂犯的客观构造与犯罪计划的考虑
必须强调的是,即便在着手判断中考虑行为人的行为计划,也完全不会对客观未遂论造成任何冲击,更不意味着倒向主观未遂理论,在未实行终了的未遂的场合,行为计划的考虑根本上是由未遂犯的客观构造决定的,具体论述如下。
实质的客观说以行为引起既遂结果的危险是否具有时空上的“紧迫性”作为认定着手的标准,但如果一概拒绝将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内容纳入紧迫性原则的判断,则有违未遂行为的客观构造。未遂犯是一种客观上未完全展开的犯罪行为,仅从行为的客观部分,很多时候(特别是在行为人有一系列的行为计划而又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对保护客体的侵害危险是否具有紧迫性,因此就必须将犯罪人的行为计划纳入判断对象,才可能针对“紧迫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同样的客观行为,其侵害法益的危险是否具有“紧迫性”,会根据行为人的犯罪计划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结论。所以在坚持紧迫性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加入行为人的计划考虑,作为判断紧迫性危险的重要资料。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计划的理由如下:1.仅凭行为的客观面,不但无法认定行为侵害的是何种法益,甚至无法对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展开判断。例如在强奸罪、抢劫罪等复行为犯的场合,其客观上开始实施的都是暴力行为,不考察行为人的犯罪意图,仅凭暴力行为的客观面本身无法判断其对保护客体造成了何种法益侵害的危险;2.同样的客观行为,如果不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就无法对紧迫性危险作出正确判断。例如,甲将某女强行拽入自己车中,如果甲的计划是马上实施奸淫行为,则可以将强行拽入的行为认定为着手;如果甲的计划是准备开到10公里外的市区找个宾馆实施奸淫行为,恐怕就不能将其强行拽入的行为认定为着手。3.在着手的认定中,行为计划作为主观性要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行为指向机能。在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全部展开(未实行终了)的场合,判断行为是否有发生侵害法益的紧迫性危险必须考虑行为人的计划。行为人的计划在这里具有主观上的超过要素的性质,其实质上是表明了行为人的行为意志,而只有行为的意志因素才能决定行为的走向以及是否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及其程度。
(四)着手理论:公式抑或原则
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处于一般情况下可容忍的预备阶段还是已经进入实质可罚性的未遂阶段的问题上,评价主体的法感裁量以及法律政策倾向等要素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承认“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规则都不能真正准确区分预备与未遂,而只能大约说明两者的界限”㉙。是一个不断被证实的论断,则这种说法也恰好说明着手的判断并非一种有着明确边界的抽象概念式的判断。面对犯罪行为的复杂形态和实施方式,司法判决和法学学说都必须满足于能够对一定种类情况确定出能够尽可能地符合法律意思和目的的指导方针,并在具体案情中,以一种评价方式的整体观察审查从行为的具体危险㉚。换言之,在认定未遂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是否具有紧迫性时,尽管无法求得一套固定的、精确的判断规则,但不可否认一个具有最大“公信力”的结论是客观存在的,以侵害法益的紧迫性危险作为区分预备与未遂的基本原则也并没有在恣意性和不确定性的诘难下而变得不可接受。人们可以通过总结审判经验,为着手判断提供尽可能详尽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以影响“紧迫性原则”的变量形式而被归纳的。例如,行为人是否主观上已经迈过了通向“现在开始”的门槛并在客观上已经采取行动;该行动本身亦无须任何中间环节而径直导入构成要件的实现;除此之外,有时还要以实施行为和结果出现之间在时间上的临近性作为根据。紧迫性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化为以下三个子规则:一是为了切实并且是容易地完成构成要件结果的引起行为,前行为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二是在实施完前行为之后,对于完成构成要件的行为和产生结果,没有了能够成为障碍的情况;三是在前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的引起行为之间具有时间的、场所的接近性。
当然,上述具体规则更多的是以未实行终了的未遂作为建构原型的,“在未遂是以其他表现形态出现的场合,开始公式就不适合了,应当进行变更或者修改。”例如在不作为犯、间接正犯以及原因自由行为中,着手的判断规则需要结合具体的犯罪类型特点作出适应和修改,这也说明着手的判断原本就不应当以一种抽象概念的思维模式展开具体规则的建构,毋宁说以“法益侵害的紧迫性危险”作为着手时点的基本原则,其在不同的犯罪类型中会有不同的外在特征,由此而无法形成一套适用所谓犯罪类型的精确和统一的着手判断规则亦属必然,这也是所谓类型思维与抽象概念思维的主要差别Ⅰ在大陆法系,类型思维在法教义学中的应用随处可见,有关类型的特征、类型与抽象概念的区别以及类型思维在立法和司法中的运用。可参阅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48页。。
四、着手理论的独立性
(一)着手与不法的关系
最近有学者认为,“实行的着手不仅是作为区分预备与未遂的临界点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不法的成立根据而承担着建构不法的任务”㉛。但如果是以区分预备与未遂作为界定着手的角度,则着手理论似乎与不法理论的联系并不像该学者所认为的那么紧密,理由如下。首先,着手更多的是一个时间性概念,是从行为与被侵犯的保护客体之间的时间——空间上的联系来确定处罚的时点,作为着手时点的判断资料,行为侵害法益的客观危险以及行为人的犯罪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处罚根据上采取印象理论或客观未遂论,行为的客观危险、行为人的犯罪计划都必须作为着手时点的判断资料,否则便无法展开判断,而一如前文所述,这并不是出自主观未遂论或者客观未遂论的要求。其次,着手时点的判断本身并不涉及有无危险的判断,而在未遂犯领域中,正是对危险概念的解读才使得未遂犯理论成为不法理论的试金石。例如,行为人误以为佛像是人而向其开枪射击的行为,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越过了预备阶段,在这里已经毫无疑问的存在一个着手时点了,至于最终是否成立未遂犯,则需要回答“误以为是仇人但实际上是朝佛像开枪的行为”是否具有危险,这个问题是以不能犯作为平台的展开讨论的Ⅰ当然也可以在论理逻辑上认为着手的判断亦包括行为有无实质危险的判断,不能犯不处罚也是因为其没有“着手”犯罪,着手理论作为不法论的风向标的说法在形式也可以承认,但实际上发挥风向标作用的仍是不能犯理论,而非“区分预备与未遂”的理论。。
(二)着手理论对未遂犯处罚根据论的超越
如前文所述,在德国处于通说地位的印象理论被认为是主观未遂理论的变种,但如果具体考察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上的主客观混合理论,则可以发现无论其论证抑或结论基本上没有受到未遂犯处罚根据理论的影响,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对着手判断的影响越来越小。
首先,根据德国刑法典第22条的规定,尽管未遂的成立决定于行为人根据其设想是否直接开始了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但该条规定被认为是以未实行终了未遂作为原型而建构的,而在这种片面地实现的外部事件,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计划来理解未遂的临界点㉜,这至少说明以犯罪计划作为着手时点的判断基础亦如本文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未遂犯的客观构造。此外,法律定义决定了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是判断着手的出发点,但这决不意味着行为人可以自己决定,从何时起,他的行为就是未遂,有关对每个受保护法益的直接威胁的观点,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并非不重要㉝。行为对保护法益的直接危险”作为判断着手的标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行为人的犯罪计划这种纯粹的主观的东西,不宜考虑成其直接地决定实行得着手的判断、毋宁说,重要的是达到此阶段的行为的客观过程”㉞。例如,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51年的一则判决中(胡椒案),尽管当时判决肯定了未遂的成立,但是罗克辛教授对此判决观点作了如下评论,“只要被害人——即使在行为人的设想中——还坐在电车中,就谈不上直接的危险。直到出纳离开电车的那一刻,他们的抢劫才直接迫近。承认力图因此今天在文献上会被绝大多数人所否定”㉟。在这里,罗克辛教授判断的出发点仍是犯罪人的设想的犯罪计划,但采取的是“行为对保护法益的直接危险”作为区分预备与未遂的标准,如果该观点被划入主观未遂论的范畴,则只能说是对主观未遂论的曲解。
其次,德国的主客观混合理论认为“按照行为人的想法直接开始构成要件行为即构成未遂”,行为人的设想被认为是着手判断的出发点;而反观日本刑法中持实质客观说的学者,也已经基本接受了主观犯罪计划的考虑。“犯罪计划”这种纯粹主观性的东西在着手判断中被广泛承认和接受不能被认为是倒向主观未遂论,但能否认为“考虑犯罪计划”只是作为判断危险的紧迫性判断的一个辅助性资料呢?在行为全部实施完毕但没有产生既遂结果(实行终了)的场合,或者根据行为的客观情状即可判断其是否发生侵害客体的紧迫性危险的场合,是否就此能够进行着手判断而无需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计划了呢?
总而言之,未遂犯的客观构造决定了着手的判断必须以行为人的犯罪计划为出发点(判断基础),但“在行为人的设想中行为是否对保护法益造成了紧迫性危险(直接危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着手判断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着手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处罚根据论(或者说不法理论)的限定而兼顾主客观要素,体现了着手理论在未遂犯领域中独立的一面。而处罚根据论乃至不法理论对整个未遂犯处罚的限定将更多地将体现在对待不能犯的态度上,并以此来影响未遂犯理论和立法的整体发展趋势。
余论:以实质客观说解构整合性的实行行为概念
以【案例2】为例,日本的判例先是通过考虑行为人的计划,得出①行为即为着手,既然是着手之后产生了构成要件结果,则成立既遂犯㊱。通说观点认为,既然刑法关于处罚未遂犯的刑事政策性要求着手提前到实行行为(能够直接引起构成要件的结果的行为)之前的行为上去(①行为),同时行为人也具有通过实施①行为造成既遂构成要件结果的意思,而客观上也能肯定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因此就能肯定故意既遂犯的成立。但是仔细推敲该判例所支持的通说观点,仍不无疑问。
首先,通说观点通过着手的认定扩张了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未遂犯的成立要件是从未遂犯的立法政策中推导出来的,即处罚的早期化和不处罚所有的未遂犯。“换言之,未遂犯的实行着手,是以未遂犯处罚的必要性为根据,由法益保护的观点而决定的,因此,未遂犯的实行着手决不是根据既遂犯的成立要件推导出来的”㊲。这就说明未遂犯的处罚是出于形势政策需要的一种扩张处罚事由,未遂犯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基本类型,既遂犯才是基本类型,既遂犯的构成要件不是根据未遂犯的成立要件推导出来的Ⅰ同时,也不能说未遂犯的成立要件是根据既遂犯的构成要件推导出来的,因为在这方面做过尝试的形式客观说,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困难重重。。既然未遂犯的实行着手行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既遂犯的实行行为,那么由着手行为所引起的构成要件结果也就不是必然地符合(故意)既遂犯的构成要件了。
其次,即使是能够肯定杀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将实施引起构成要件结果行为的前行为的认识和意志等同于既遂犯的故意也存在疑问。例如在【案例2】中,行为人设想的是通过②行为实现杀人目的,在②行为还仅仅停留在行为人内心的①行为阶段,行为人仅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杀人行为(实行行为)之前的准备行为(尽管是着手行为),行为人此时的意志因素也只限于通过①行为以便更顺利的实施②行为,而死亡结果只是行为人的一个愿望,并非行为人实施①行为的意志(甚至为了达到掩盖犯罪事实的目的,行为人在实施①行为时是对死亡结果提前发生的)。因此,就①行为所产生的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行为人由于缺乏相应的意志因素(只有未遂犯的故意而没有既遂犯的故意),不成立既遂犯,只成立未遂犯和过失犯的竞合,按照未遂犯处罚。
最后,将着手行为等同于既遂犯的实行行为的做法会使实行行为丧失作为既遂犯的行为类型这一重要机能。例如,同样是强迫妇女上车的行为,在被害人已经陷入紧迫性危险的情况下可能被认定为强奸的实行行为,但在还没有达到紧迫性危险程度时又仅仅是一个预备性行为;甚至是非暴力行为,如欺骗妇女上车然后奸淫,都有可能成为强奸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应当承认未遂犯和既遂犯有互相独立的构成要件,应当根据既遂犯固有的特点,来确定提前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形是否成立既遂。
总而言之,在着手的认定上采取实质客观说,其结果就是消解了实行行为在未遂犯领域的机能,即是否开始实施实行行为并非着手认定的标准。以往的实行行为理论被日本刑法学者山口厚称为看不到内容的“黑盒”,即以实行行为作为犯罪的本体,从重视解释论的形式上的整合性见地出发,实行行为被借用到犯罪论的不同领域中解决理论上不同性质的问题,导致实行行为理论本身有具有一体化的模糊性,并由此而掩盖了具体问题在实质上的差异㊳。所以,应当消解这种一体化的实行行为论,回归到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具体问题中需求理论上的解答。
[注释]
①㉗㊳[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第274页,第50页。
②㉜[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第621页以下。
③[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东京:有斐阁,1975年版,第320页以下。转引自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④[日]西原春夫:《刑法总论》,东京:成文堂,1977年版,第295页。转引自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⑤[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2版,第295页。转引自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⑥[日]曾根威彦:《刑法总论》,东京:弘文堂,1993年新版,第232页;[日]野村稔:《刑法总论》,东京:成文堂,1990年版,第338页。转引自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⑦[日]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东京:成文堂2005年版,第248页。
⑧㉝[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第261页。
⑨Lehrbuch des gemeinen in Deutschland gültigen peinlichen Rechts,9.Aufl.1826,S.42 ff.
⑩⑬[德]托马斯·魏根特:《刑法未遂理论在德国的发展》,樊文译,《法学家》,2006年第4期,第143页,第147页。
⑪⑳[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第243页。
⑫陈家林:《为我国现行不能犯理论辩护》,《法律科学》,2008年第4期;刘晓山,刘光圣:《不能犯的可罚性判断——印象说之提倡》,《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王拓:《不能犯抽象危险说之坚持——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报》,2007年第2期。
⑭陈璇:《客观的未遂犯处罚根据论之提倡》,《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⑮㉔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页,第319页。
⑯㉞[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钱叶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第177页。
⑰[日]牧野英一:《刑法总论》(上),东京:有斐阁,1958年全订版,第254页。
⑱[日]宫本英修:《刑法大纲》,东京:弘文堂,1926-1928年版,第178页。
⑲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489页。
㉑许恒达:《重新检视未遂犯的可罚基础与着手:以客观未遂理论及客观犯行的实质化为中心》,《台大法学论丛》,第40卷第4期,第2408页。
㉒[日]团藤重光:《刑法总论纲要(第3版)》,东京:创文社,1990年版,第335页。
㉓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预备与未遂的区别在于有无危险的“紧迫性”。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东京:有斐阁,1972年版,第313页。
㉕㊱㊲[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刘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82页以下,第82页。
㉖[日]浅田和茂:《刑法总论》,东京:成文堂,2005年版,第336页;[日]内藤谦:《刑法总论(上)》,东京:有斐阁,2002年版,第1222页。
㉘黄悦:《主观违法要素理论初探》,《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12期。
㉙[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㉚[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㉛劳东燕:《论实行的着手与不法成立的根据》,《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第1237页。
㉟[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何庆仁,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