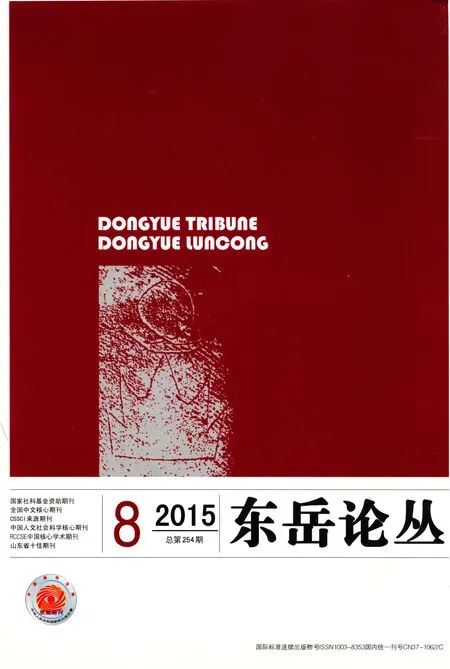千古《硕人》谁知音?——《诗经·卫风·硕人》题旨新解兼论“兴”的本质与作用
李宪堂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卫风·硕人》对女性之美的描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难以超越的经典,故而成为各种《诗经》选本必选的名篇,然而,自两汉以来,各家对其主题的阐释叠床架屋,陈陈相因,却几乎没有一人能得其的解。千古《硕人》无知音,实在令人为之扼腕!
关于此诗的主题,历来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怜悯”说。 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毛诗序》继承了这一说法,认为《硕人》:“闵庄姜也。 庄公惑于嬖妾,使骄而上僭。 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故国人闵而忧之”。 后之解诗者绝大多数接受了《毛诗》的看法,如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范处义《诗补传》、 严粲《诗辑》、朱善《诗解颐》、朱鹤龄《诗经通义》、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等。 二为“劝谕”说。 据刘向《烈女传·齐女傅母》记载,庄姜初嫁,重衣貌而轻德行,其傅母加以规劝,为作此诗,使其“感而自修”。 刘向之说本于《鲁诗》《韩诗》,汉代以后今文经学系统内诸家,如何楷《诗经世本古义》、魏源《诗古微》等,多采此说。 三是“赞美”说,如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此诗“颂庄姜美而贤也”,并无“悯”、“谕”之意,持类同意见的有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等,现代学者多采此说,如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及褚斌杰《诗经全注》,还有任自斌与和近键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等,皆题为“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①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褚斌杰:《诗经全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任自斌,和近键主编:《诗经鉴赏辞典》,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四是“婚嫁说”,回避了“美”、“刺”、“悯”之类标签性判断,径直定性为一首“婚嫁诗”,如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是“庄姜初嫁,人见其嫁时及其嫁后短时期之幸福生活而作”②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靳极苍《诗经楚辞汉乐府选详解》称这首诗是“写齐桓公之女、东宫德臣之妹、嫁于卫庄公时的盛况”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杨合鸣《诗经新选》也认为“这是庄姜初嫁之诗”④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以上四种观点中,第一、第二两种是汉代儒生将《诗》经典化、教科书化的产物,千百年来陈陈相因,尽管时有旁通曲解,总的看来与诗的本义愈去愈远;第三种“赞美说”只就皮相立论,实属外行人看热闹,虽言之津津却不得要领;第四种显然过于空泛、笼统,实如隔岸观火,得其光景而无由入其真境。
200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唐文先生著《原来诗经可以这样读》一书将《硕人》的主题归结为“王家迎娶的礼赞”①唐文:《原来诗经可以这样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切近题旨的一种解释,遗憾的是唐先生一笔带过,没有通过对诗篇内在脉络的剖析进一步凸显主题,因而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的观点是,《硕人》是卫国公室的婚礼颂诗,它颂美的不是庄姜本人的富贵与美丽,而是姬卫国族的兴盛和繁荣。
一、从诗的内在脉络看《硕人》的主题
为便于阅读,兹将全诗原文抄录于下: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 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鱣鲔发发。 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第一章夸示庄姜身份之贵,第二章颂扬新娘容貌之美,自古以来对此都没有异议。第三章前两句描写新娘入朝的礼仪与车马仪仗之美,解诗者基本也能形成共识。 对第三章最后一句及整个第四章的误读和曲解,是导致《硕人》知音难觅的原因所在。
“大夫夙退,无使君劳”一句,看起来似乎是光鲜奢华的色相铺排之间随意插入的谐趣语,往往被轻易放过,因而成了绊倒众多解诗者的第一块石头。这本来是类似于现在闹洞房时的玩笑话,意为:“大家早散了吧,新郎晚上还有体力活要做呢,不要使我们的国君过于劳累了”,这种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插科打诨,本之人情,谑而不虐,却被毛诗一派学者温柔敦厚地解释为臣下对君主的体贴之语、冀幸之辞,如郑玄释云:“无使君之劳倦者,以君夫人新为配偶,宜亲亲之故也”②《毛诗注疏》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发挥曰:“此言庄姜自齐来嫁……国人乐得以为庄公之配,故谓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无使君劳于政事,不得与夫人相亲”③《诗经集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虽离题未远,然隔靴而挠,实不得痒处。 刘向《列女传》④《列女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奂《诗毛氏传疏》⑤《诗毛氏传疏》卷五,道光二十七年陈氏扫叶山庄刻本。、冯登府《十三经诂答问》⑥《十三经诂答问》卷二,光绪丁亥年朱氏槐庐校刊本。以为此“君”指君夫人即庄姜,实属望文生义,强作解人。
实则这是全诗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从对眼前盛事的渲染、经由夫妻床笫之事的暗示,转入对未来愿景的祈望;第四章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鱣鲔发发”是一组起兴句,引起性与生育的主题——流水活活,鳣鲔发发,象征着庄姜及其随从侍妾们旺盛的生育能力;下面的“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进一步渲染了这群姜姓姑娘像野草一样不可抑制的蓬勃生机;最后一句是全诗的归结点,将摇曳多姿的情感旋律推向高潮:“庶姜”的到来将生下一群威武强壮的勇士,保证家族的绵延与强盛。
总之,本诗先是渲染女主人高贵的身世,然后赞美其非凡的姿容,接着转入对婚庆场景的描写,并以对君主的玩笑映衬新娘子令人亟不可待的尤物之魅,最后以鱼水起兴归入主题:对宗族繁盛、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景的期待——全诗有铺陈,有承接,有高潮,一气流转,精彩纷呈,其主旋律在回环往复之际戛然而止,而将向未来敞开的想象的空间和袅袅不尽的余音留给了读者。
大多数解诗者简单地把活活流水、发发鱼群视为庄姜来归时路边风景,这不仅使先秦歌诗中独有的民俗文化厚味寡然无存,而且使整首诗在结构脉络上变得扞格难通。前面已经“翟茀以朝”,都入洞房了,再回过头来描写路上的风光景致,何其拖沓繁芜之甚! 天下哪有如此庸弱不伦的经典! 清代学者恽敬怀疑第三、四章位置倒错,说明他发现历代诗解都是牵强凑合,只是囿于成见而找不到突围之路。
“庶士有朅”是全诗情感旋律的顶点,它是祝福,也是祈愿,强调的是庄姜及其侍妾来归后对卫国宗室的贡献:生下一群生气勃勃的儿子。 然而自汉代至今,得其的解者几乎未见其人①清人沈彤曾指出“所谓‘庶士有朅’者,谓众子中有朅然健以武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以比庶姜之媚惑其君也”(沈彤:《果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但他认为的“朅然健以武者”指的是侍妾们生的儿子,因而还是落入了“闵庄姜无子”的老套;现代学者唐文意识到最后一句“其实也是对生殖的一种期望”,但他认为这是“对仆从高大英武状貌的赞美”中隐含的结论(唐文:《诗经原来可以这样读》,第83页),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古人的窠臼。,如毛传的解释是“庶士,謂媵臣;朅,武貌”,此后历代学者的阐释几乎都是对这句话的疏解,都把“庶士”理解为陪嫁的“卫士”或“随从”,即便现代的许多大家名作也未能脱此窠臼,如程俊英的《诗经译注》释“庶士”为“随从庄姜到卫的诸臣”,释“朅”为“桀”②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杨任之的《诗经今译今注》释“庶士”为“齐大夫送女者”,释“朅”为“勇武矫健貌”③杨任之:《诗经今译今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如此一来,整首诗形解神散,气脉全无。即便诗的主题是人们所认为的“怜悯”或“赞美”庄姜,在经过前面对庄姜身世之贵、容貌之美、车马服饰之华丽的极尽夸饰形容之后,再来一句“随从的卫队孔武有力”,岂非画蛇添足? 陪嫁的随从即便值得一提,又何以有资格占据归结全诗的重要地位?
那么,这里的“士”是否可以理解成“儿子”? 我想没有任何问题。 在甲文、金文中,“士”有等写法④分别采于《续甲骨文编》第3913条、士父钟、臣辰卣。,像耒耜插入土中之形⑤关于“士”字的本义,主要有“牡器象形说”(见郭沫若《释祖妣》,载于《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8页)、“象人端拱而坐说”(见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源》,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本第四分册)、“斧形说”(见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五卷三期,1936年)等,唯杨树达引吴承仕“插物地中说”(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第三卷《释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近是。。《说文》:“士,事也”。对以业农为生的部族来说,耕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故以农作之事代表所有的“事”。 《论语·述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盐铁论·贫富》引作“虽执鞭之事”,彝器中毛公鼎、番生敦、夨彝中有“卿事”,在传世文献如《尚书》之《牧誓》、《洪范》及《诗经》之《十月》、《假乐》、《常武》、《长发》中写作“卿士”,足为“士”、“事”一义之证。 力农主要是男子之事,故“士”又指男子⑥如《小雅·甫田》有:“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卫风·氓》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溱洧》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特别指未婚的男子,此为第一层引申义。 诉讼为民事之重者,故“士”又有“断事官”之义,如《尚书·尧典》有“汝作士”,马融注:“士,狱官之长”;《孟子·告子下》有“举于士”,赵岐注:“士,狱官也”,此为第二层引申义。 能干事的人都是与平民不同的有身份的人——尽管要“做事”比较辛苦,因此在春秋以前, “士”指统治阶级最低层的贵族成员⑦如《尚书》之《酒诰》有“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大诰》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泰誓上》有“王曰:‘嗟! 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此为第三层引申义⑧进入春秋后,随着以头脑谋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涌现,在原来的社会体制内析出了一个新的文士阶层,被称为谋士、智士、术士、礼教之士、有道之士等,这是第四层引申义。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形成和分化情况,读者可参考刘泽华先生的《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庶”意为“众多”,当“士”作“男人”解时,“庶士”指的是“男子汉们”、“小伙子们”,当然必须是行过冠礼具有成人资格的,如《诗经·召南·摽有梅》有:“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当“士”指称某个特定社会阶层时,“庶士”则泛指“一般的士”,如《荀子》卷十二《正论》有“庶士介而坐道”,杨倞注曰:“庶士,军士也”——“士”是国家兵役的承担者,所以等同于“武士”、“军士”。 具体到某个宗族内,当嫡庶相对而言时,“庶士”则指除嫡长子外的所有成年男性,如《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七《成公四年》徐彦疏有“王立七庙……适士二庙一坛……庶士、庶人无庙”。
总结以上,“庶士”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 当强调统治集团的阶层区分时,指的是贵族阶级最底层的社会成员;当在宗法体制内强调成员的地位和名分时,指的是一般贵族之家所有庶出的成年子弟;而当男女对举特别是涉及家族、婚姻、生育主题时,可泛指“小伙子们”、“男孩子们”。西周时期徐国所鋳青铜器沇兒钟有“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⑨邹安:《周金文存》卷1,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78年版,第21页。,指的就是除作器者“诸兄”之外的同族诸弟①西周时人聚族而居,敦宗睦族为最大的政治,贵族之家宴飨祭祀往往诸父、诸兄并举,如伯公父簠有“我用召卿事辟王,用召诸考、诸兄”(《殷周金文集成》第4628,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984-1994年);《诗经·小雅·楚茨》亦有“诸父兄弟,备言宴私”。。徐国不受周室册封,被灭之前一直称王,故这里的“庶士”绝不是阶级分层或嫡庶区别的概念。
在《硕人》中,“庶士有朅”承“庶姜孽孽”而来,强调的显然不是“士”的社会地位和宗法名分,而是用其第一层引申义,意为“一群强壮的男子汉”。这群男子汉不是作为庄姜身份的标志、更不是作为豪华婚礼的点缀出现的,而是作者情感所寄托的对象,体现着卫国公室对家族兴盛前景的展望与祈愿。
对《硕人》的阐释之所以沦入陈陈相因的曲解泥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绝大多数解诗者是学者而非诗人,不懂诗作者是如何把握其情感旋律的,心无灵犀,是故容易囿于成见;二是间或出现的具有诗人心智的解读者,往往又缺乏必要的人类学、民俗学知识背景,舟楫不利,是故未能问津讨源。
二、从“兴”的作用和“鱼水”意象的文化内涵看诗的主题
第三章的前两句“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鱣鲔发发”是一组起兴句,也是全诗的诗眼所在。古往今来对《硕人》一诗形成的种种曲解和误读,主要是由于对这一兴象的文化内涵及其在诗中所起的作用的暗昧无知或理解不到位所致。
“兴”本是儒家《诗》学所发凡的名目。 《论语·阳货》载孔子论诗,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者引类明志,“观”者比事见理,强调的是《诗》的教化功能。其后《周礼·春官宗伯》及《毛诗训诂传·序》将“风”“赋”“比”“兴”“雅”“颂”标举为《诗》之“六义”,实乃孔子《诗》学之流绪;郑玄注《周礼》,有“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之论,仍是美刺说陈套,然去古意未远。 孔颖达把“六义”分疏为“三体三用”,谓“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大小不同而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因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所谓“异辞”,显然是指“修辞”上的不同,“兴”被理解为“成此三事”的手段,是主体表达情志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取譬引类,起发己心”②孔颖达:《毛诗正义·周南·关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后关于“兴”之本义和作用的研究,可谓治丝愈繁,岐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为主流,以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③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亦即“托物兴辞”④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说为代表,相近的观点有东汉郑众的“托事于物”⑤郑玄:《周礼注》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礼注疏》卷23。说、宋代李仲蒙的“触物起情”⑥引自(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说等;第二种以“兴”为“隐喻”、“隐语”或“象征”,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有“‘兴’则环譬以托讽”之论,认为“‘比’显而‘兴’隐”,闻一多则径直称“‘兴’就是隐语”⑦闻一多:《诗经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朱自清则认为“兴是直说此事以象征彼事”⑧朱自清:《关于兴诗的意见》,《古史辨》(第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5页。;第三种观点把“兴”看作没有实际意义的“起头语”、“套语”,在诗中只起一个引起下文或凑韵的作用,持论者有顾颉刚、钟敬文、刘大白等⑨四人的文章见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451页。;第四种观点倾向于从“兴”所内涵的民俗文化因素研究其起源与本质,如赵沛霖认为“兴”是源于宗教观念的习惯联想的“规范化的外在表现形式”⑩赵沛霖:《兴的分类、本义和起源研究述评》,《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王建认为“‘兴’是人与自然(包括人为的事物)之间对应关系的一种显现”[11]王建:《〈诗经〉中的“兴”与人和自然的对应》,《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美国学者王靖献则参考西方诗歌研究中的帕利—劳德理论①由帕利(Milman Parry)和劳德(A1bert Bord)两位学者创立。 这种理论认为口头文学的重要特点是大量运用“现成词组”(stock Phrase,又称formula)和“套式”(type—scene)。 “现成词组”指的是一个或数个组织在一起的词汇,在许多诗篇或同一首诗中反复出现,意思基本相同;“套式”指的是诗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景物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是象征性的,歌者借助于习惯和联想,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把“兴”与古代诗歌中普遍存在的“现成思路”及“套式”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兴是借助于习惯,以某个象征性景物引起听众联想和共鸣的手法”②引自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就现有各种观点看,无论是“起情说”、“隐语说”、“起头说”还是“套式”说,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把“兴”仅仅看作一种“修辞术”,一种有关遣词造句的“表达方式”,是结构诗篇整体的“部件”,因而在诗篇中只具有局部性的、修饰性的意义。 以这种学术化的“我执”之见去理解“天人一体”时代出现的诗篇,难免日趋支离而隔膜。
要理解《诗经》,不能局限于文本,必须进入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为《诗经》特别是《国风》中的篇章大部分不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而是生命激情的自然流露。 《毛诗序》在谈到《诗经》创作的缘起时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③《毛诗注疏》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诗经》所展示是一个天人一体、万类共鸣的生机世界,人类同禽兽虫鱼一样沉浮在大自然的律动里,他们“舞之蹈之”的欢歌咏叹,同鹿鸣雁叫一样构成一个地方的生态景观。 “国风”之“风”不同于现代物理学所定义的“流动的空气”,也不仅指地方性的风俗习惯,而是指自然万物所散发出的“有生命的气息”——在《诗经》的世界里,人和万物处在一种相互感发、相互应和的神秘联系中。
所谓“兴”,指人在外部自然物触发下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以源于原始思维律的“类联想”为机制进行的,如河边沙洲里野鸭雄雌之间的和鸣,会使人油然而兴室家之思(《召南·关雎》);山坡上正在追寻配偶的雄狐,会使思妇想起行役在外的丈夫(《卫风·有狐》);看到棠棣树那簇生的累累果实,就会联想起兄弟和睦的天伦情意(《唐风·枤杜》);春日里生机蓬勃的花草,还有那暖烘烘、懒洋洋的氛围,会激起少女们思春的情绪(《豳风·七月》)……总之,“兴”者起也,人处在万物之中,触物起情,比类兴感,随时随地近乎条件反射般产生感应和联想,这就是“兴”之所兴。 可以说,“兴”是生命本身在与万物交感中振出的弦音,这种弦音因为联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感受而为群体所享有④春秋以前,人们以宗族为单位息息相关地生活在一起,共享有限的知识和经验。 孔子谓“诗可以群”,是因为《诗经》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切身相关。,并在语言的反复交往中被打磨成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现成词组”,如前面提到的“棠棣”、“雄狐”等,它们像琴键一样一旦被拨动就会引起群体的共鸣。 若起兴的物象与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联系因年深月久的积淀而固化为“套式”,就成为表现某些文化母题的载体,如以鱼水兴婚媾与生育,以采摘兴婚姻与性征服等。
因而,在《诗经》中“兴”不是一种技巧性的“创作手法”,它在诗中的作用是整体性、根本性的,不仅内涵或影射着诗的主题,而且规定着诗歌抒情的基调和色彩——至少,它内含着主题的线索,引起情绪的氛围与指向。 《诗经》中不同章节之间词汇的变换只是一种装饰性变奏,是对“兴”之主题的反复申说。
归结起来,《诗经》中的“兴”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为“触物通感”,指见到似类之物感发相关之情,如前面提到的《关雎》《有狐》《枤杜》等,有时候起兴之物与所歌咏的对象看起来不相及,实际上也有一种相互映射的关系,如《周南·桃夭》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女子盛装而嫁,正如鲜花盛开;花落结实,正如女嫁生子。 第二为“设象比义”,即由某种“象”——在本质上“象”是观念所熟化之“物”——昭示作者情感的倾向和色彩,如《麟趾》有“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为贵人之象,麟趾象征能持家继世的贵族子弟,与“振振公子”有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 第三为“比事见理”,指把两件类似的事——前一件为自然现象——放在一起,使其本质上的相似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如《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墙茨”之不可扫正如“中冓之言”之难以与外人道,因为不得不有所忌讳。 第四为“借景起情”,指以某种相关的“景象”映射并强化主题,如《陈风·东门之杨》开篇即“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东门为男女欢会之地,一提到东门自然使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静中愈动的飒飒树叶声则烘托出幽会者兴奋而又不安的心境;再如《卫风·淇奥》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起兴,下面反复赞美“有匪君子”的风范和光彩,向来认为这首诗是臣下赞美卫武公的,实属牵强附会,因为那样一来第一、第二章的最后一句“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显得很滑稽——君主即便品行高尚、文采斐然又有什么可念念不忘的? 并且最后一章后半部分“宽兮绰兮,猗重较兮。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用于对君主的赞美也殊为不伦。 其实,“瞻彼淇奥”已经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诗歌主题展开的方向:水曲山坳、竹木丛生处,向来是引人联想的暧昧处所,猗猗绿竹孕育着有待发生的浪漫故事。 这是一种富有民俗特色的色情暗示,由此引出对异性对象的爱慕和向往,正是民歌的基本路数,而“宽兮绰兮”、“善戏谑兮”(心胸宽阔又富有幽默感),不正是古今中外女子眼中男性魅力的主要标志?
总之,《诗经》中的起兴句直接或间接与主题相关涉,要透彻理解一首诗的主旨,必须先把握其中起兴句所内涵的文化意蕴。 在有的诗篇中,存在不同的起兴句,看似渺不相关,实则被统摄在同一个主题下,如《采薇》前三章以“采薇”引起,第四章却突然换成了“彼尔维何,维常(棠)之华”,显得很突兀,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嶶”象征妻子,“棠棣”隐指兄弟——簇生的棠棣之花隐喻着兄弟相依的天伦情意的美好,它们都是构成“思归”主题的元素。
当然,在《国风》的某些篇章特别是以士大夫为写作主体的《雅》诗中,有一些“兴”看起来是以一种成熟的“创作手法”的面貌出现的,有时候作为现成的套语直接代入抒情的节奏里①如《小雅·采薇》中的起兴句“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后面还有“薇亦柔止”、“薇亦刚止”,并不是实景叙述,不是在采薇食用之时感物兴怀,而是直接代入这个意象以引起思归的主题(采摘一般象征男子对女子的占有,这里指向占有的对象,即家中的妻子,室家之思通过对妻子的思念体现出来),这似乎可视为一种“创作手法”,但显然这种“套式”积淀着一种公共性的情感,作者以自己的切身处境激活了它。 作者不是在创作什么文学作品,而是在用自己生命的触角拨动大众的神经。 《诗经》中的起兴句都是内涵魔力的道具,作者以某种场境、氛围或音乐节奏释放出它们的魔力,从而创造出与每个人血肉相联的情感世界。 在看似简陋乃至稚拙的形式之下,内涵着鲜活生命的力与美,这是千古未曾道出的《诗经》魅力的奥秘。,但毫无疑问那不是作者主观情志的直接表达,作者只是借助剪贴来的现成片段拼凑出一种公共性的情感氛围——诗歌的抒情主体并不在现场,在现场呈现的是人隐没于其中的世界本身,人只是一个为万物之“风”所振动的芦管,世界通过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而,即便读《诗经》中那些最个人性的作品,如《小雅》中的《出车》《采薇》等,使我们感动的也不是作者爱恨情仇的主观性宣泄,而是世界的混乱以及人在世界中的无助与忧伤——这才是儒家标榜的“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真意。
因此,《硕人》一诗的主题,就内涵在最后一章鱼水意象构成的起兴句里:水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使人联想到新婚夫妇的激情欢爱,进而兴起婚姻美满、家族兴旺的美好憧憬。 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已证明,几乎在所有原始文化中,“鱼”都因其象形(鱼口像女阴)与强大的生育能力而成为女性匹偶的象征,进而成为祈愿家族昌盛的吉祥符号,而“鱼”和“水”连在一起往往被作为男女情事的隐语②这样的例子在各国民俗中俯拾即是。闻一多先生在《说鱼》(《闻一多全集·诗经编上》)一文中对《诗经》及历代民歌中象征男女婚姻的鱼水意象作了梳理,并与古埃及、希腊以及一些原始文化中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诗经》中涉及观鱼、钓鱼、烹鱼、食鱼的意象,绝大部分是男女婚姻关系的表征。
有很多学者把这一段视为风景描写,实在是差之千里。 严格地说,“风景”在《诗经》时代尚未出现,因为其时“我”与“物”之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客对立——“物”不是通过主体意识的中继转换进入人的情感世界的,而是在一种神秘的联系中与人偶然相遇。 《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曾被王夫之誉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而“倍增其哀乐”③王夫之:《薑斋诗话》卷1,《四部丛刊》景《船山遗书》本。,其实在这里人之哀乐与杨柳无关,它们只是作为时空转换的标志而出现,并且由于它们的在场构成了人生大舞台的背景纵深,凸显出了世界的空旷和苍凉——在《诗经》中,所有的“风景”都是一种与特定空间相关的景“像”,是挡在作者面前的“他者”,而不是接纳并映射作者情感的对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