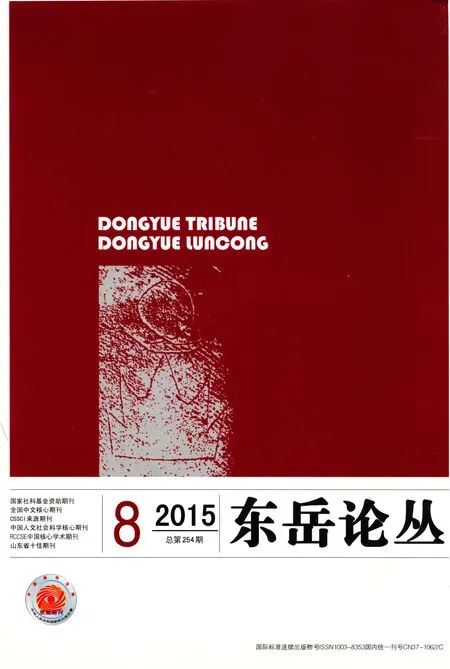先秦诗歌演进谱系与孔子删《诗》
黄 洁,王于飞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047)
2014年第五期《文学遗产》刊发了一组专论孔子删《诗》的论文,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热议。本文拟从整个先秦诗歌生活演进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孔子删《诗》的特定意义和价值。
在拙著《事实、图景与观念——对先秦诗学传统的还原性研究》①黄洁:《事实、图景与观念——对先秦诗学传统的还原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笔者描述了先秦诗歌发生发展的大致历程。不妨以孔子删《诗》为这一历程的下限,进一步归纳出以下几条并行的线索:从总体上看,先秦诗经历了由先民诗—先王诗—祭祀诗—礼乐诗—诗教诗—专对诗到“诗三百”的演进;从载录与传播方式看,先秦诗大致经历了由随出随佚—音乐记忆—乐舞表现—王官采集—礼乐定型—文本传写—乐诗集成—诗、乐散佚,再到孔子删定的历程;从诗歌生活的主导人物看,上述进程又在先民—帝王及贵族—乐官及礼官—师傅与国子—政务与外交人员,复归于删述诗乐的孔子师生之间次第转换。
以上概括可能失于粗略,但先秦诗歌演进的主线却大致可以从中得以呈现。以下稍作展开。
一、诗歌进入社会权力体系
首先从最早产生,而又随出随佚的远古诗说起。
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的楚人陈音曾经讲过一个关系到早期诗歌发生的故事:
越王请(陈)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之谓也。于是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②[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卷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28页。。
如果这则材料可以被视作中国最早诗歌生活的记录,那它就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促成这首诗歌产生的特定语境不仅感情色彩强烈,更带有一种原始宗教情绪。作为诗歌作者的古孝子借助整齐的句式、铿锵的音韵和歌唱性、呼告性的言说形式,向幽冥中的先灵与神秘宇宙表达特定的情绪化诉求。这喻示着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先民对自然、神灵的呼告和祝祷而出现的。而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宗教基因,使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进入了原始宗教社会的当然领地。
另一方面,《吴越春秋》成书于东汉,除此以外,我们没有看到比上述材料更早和更为可靠的记载。可以想见,像《弹歌》这样的早期诗歌大都无法幸存下来,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记录手段和传播媒介,因而只能在随出随佚的状态下散失殆尽。
第二个阶段,音乐和舞蹈成为诗歌的重要承载方式和传播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歌的记忆存储器。
《吕氏春秋·仲夏·古乐》梳理了从朱襄氏、葛天氏一直到周文王、武王和成王的古乐演进历史。这些古乐大多具有诗、乐、舞合一的体制特征,特别是周公《大武》《三象》及“文王在上”等诗作,都有现存的文献可考。同书《季夏·音初》,又以“候人兮猗”、“燕燕往飞”为“始作为南音”和“始作为北音”的记录①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5页。,等等。在这样的表述中,诗歌从属于乐的系统,而为乐的概念所包含。事实上,这些诗歌如果不与那些歌舞形式融为一体,进而随着这些乐歌乐舞的传承而被保存下来,恐怕仍然逃脱不了随出随佚、被人遗忘的结局②关于诗与乐的关系,可参阅拙著《事实、图景与观念——对先秦诗学传统的还原性研究》中相关章节。。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早期诗作都能融入乐舞组合中去的。只有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作品才有可能被这些乐歌、乐舞所采用③这只是就早期诗歌的主体而言。乐歌、乐舞或许并非上古诗歌唯一的记录传承方式,前文所举《弹歌》《候人歌》等就不一定是经过乐歌、乐舞的采用才流传下来的。。
第一,显赫的作者。如《汉书·礼乐志》追溯乐的由来:
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
所谓诗乐、诗舞的作者阵容历历可见。
第二,重要的内容。如《汉书·礼乐志》所云:
《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④[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二,见《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69页。。
现在来看,早期诗歌能够流传下来的,也主要就是这些非同寻常的篇目了。
第三,关键的用途。如《周易》豫卦象辞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吕氏春秋》更是将先王作乐的目的表述为“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作为舞以宣导之”、“以祭上帝”、“以康帝德”、“以昭其功”、“以见其善”,等等。在这样的表述中,“敬天常”往往与“达帝功”并称,呈现出清晰而连贯的线索。在诗、乐、舞的组合套路中,宗教与政治始终是联袂而行的。
与此同时,一套社会文化机制也逐渐形成:早期社会的首领们以政治权力为中心,以宗教祭祀为精神导引,以诗、乐、舞相配合等综合文化手段,行使和发挥着一些复杂的社会功能。
就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诗歌被纳入了社会核心权力的运作机制,同时,也在这套机制的社会运用与历史传承中,获得了被记忆、被传播的条件。
第三个阶段,诗、乐、舞成为祭祀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现象其实早已存在。前文所引《吕氏春秋·仲夏·古乐》提到颛顼作《承云》、尧帝作《大章》,都是为了“以祭上帝”,据说形成于神农时代的《蜡辞》(载《礼记·郊特牲》)、商汤时代的《祷雨辞》(出《荀子》)等诗作也是服务于各种祭祀的。
但正如陈来先生所说:“夏以前是巫觋时代,商殷已是典型的祭祀时代,周代是礼乐时代。”①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大约在商周时期,各种祭祀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之说。特别是商人尚鬼,每遇大事都要占卜祭祀,现存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相关记载。《商颂》中现存的全部5首作品,几乎就是一部系列的祭祖诗。
而周朝的祭祀之风也并不稍减。如《礼记·曲礼下》就说: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②[汉]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五,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年版,第1268、1269页。
在如此频繁而又隆重的祭祀当中,自然少不了诗、乐、舞的协同参与,这一时期遗存下来的诗歌数量也大大超过以往。如《大戴礼记·公符》《祭辞》3首、《周礼·考工记》和《大戴礼记·投壶》所录《祭侯辞》2首、《仪礼·少牢馈食礼》所录《嘏辞》,以及《诗经·小雅》里面的《楚茨》《信南山》,《大雅》中的《棫朴》《文王》《云汉》《既醉》《凫鷖》,《周颂》中的《丰年》《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执竞》《思文》,等等。
如此众多的祭祀类诗作被记录下来,除了继续得益于乐、舞甚至文字记录的帮助以外,各种越来越隆重的祭祀活动,无疑成为其强有力的助推因素。从天子的朝堂,到士人的家庙,无不“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③《礼记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1416、1417页。在如此重要的社会活动中,诗歌当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段文字中,祭祀的动机除“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之外,还包括“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等一系列非宗教目的。这说明至少在商周时期,各种祭祀已经不再是单纯向神灵或祖灵表达消灾、祈福、报谢的宗教活动,它还明确发挥着敦化人伦、规范社会等现实功能。而这一点,与社会政治权力的行使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民智渐开的商周时期,祭祀活动反而比以往受到更多的强化,这本身就说明这一宗教活动已经更多地服务于世俗生活需求。正如楚国观射父所言:“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④《国语》卷十八,上海:上海书局影印,1987年版,第205页。,神圣的宗教力量已经与建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的政治力量进一步融合,并最终服务于后者,成为社会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作为各种祭祀活动的要素之一,诗歌几乎参与了这种社会权力行使、延伸的全过程,并进而成为这一权力运作体系的有机成分。涉及并服务于这些祭祀生活的诗歌作品,也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最受重视的文化现象之一,被郑重其事地记录和保存下来。
二、诗歌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的角色递变
随着时代的演进,祭祀文明的宗教色彩进一步弱化,社会进入到礼乐文明阶段。
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产物,礼乐文明在民智更为清醒,也更为理性的状态下,被有意识地建构了起来。据《礼记》《左传》《尚书大传》等文献,各种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尚书大传》记载:
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⑤[清]孙之騄辑:《尚书大传》,文渊阁《四库全书》6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411-412页。。
大量文献和事实证明,在先秦礼乐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诗歌作为不可或缺的要素,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礼乐活动当中。如《礼记·射义》对“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等制度化规定,《仪礼·乡饮酒礼》在宾主祭、饮、拜、答之际对各种诗乐的具体要求,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记载不只悬诸空文,还有大量的应用事实。如《左传·襄公四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先秦典籍中比比皆是,可见诗歌在当时礼乐活动中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马银琴等人提出,先秦诗歌的结集,就是在先秦礼乐制度的建构中完成的①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那么,礼乐制度的作用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昬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②《礼记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1414、1415页。
从其他类似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先秦周公的礼乐之道也就是为政之道,其作用就在于别等级,明秩序,借助礼乐使日常生活制度化,社会制度生活化,从而达到“治政安君”、“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目的。
礼乐政治的基础,源自宗教祭祀。在祭祀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诗歌,在新的时代里又成为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继续发挥着它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但源自祭祀时代甚至更早的诗歌并不是非礼乐时代诗歌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诗经》的构成看,有相当多的作品跟祭祀无关,也没有成为礼乐用诗。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分析的:
诗之被于弦歌也,不过以为宴享宾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为祭祀之诗,《小雅·鹿鸣》以下,《彤弓》以上诸篇,为宴享之诗,此皆其经文明白,而复有《序》说可证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国《风》,《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鲁颂》之四篇,则《序》者以为美刺之词,盖但能言其文义之所主,而不能明其声乐之所用矣。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乐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4、1245页。
马氏所列举的后一类作品,很大程度上与先秦时期的采诗观风制度有关。
据文献记载,先秦采诗观风制度也是跟祭祀和礼乐活动息息相关的。据《礼记·王制第五》: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④《礼记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1327页。
这种陈诗以观民风的方式同样源自古老的传统。《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里的话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⑤[晋]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1958页。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
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⑥[汉]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2287页。
通过这些方式采集来的民间诗歌,会在“乡移于邑,邑移于国”之后,“献之大师,比其音律”(《汉书·食货志》),再进入到“国以闻于天子”的程序。而当听政观风之事毕,这些来自民间却又经过整理的歌诗自然被记录和保存下来,有的还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系统:诗教。
《尚书·舜典》“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作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而这段话本身就是在“典乐,教胄子”的语境下说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子教的兴起和发展,诗歌在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中也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礼记·内则》规定国子们“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礼记·王制》要求:“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①《仪礼正义》,卷十三,《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1342页。。《国语·楚语》中记载申叔时陈说教导太子的方法时就专门提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②《国语》,卷十七,前引书,第191页。
因这样的教育,诗歌成为王公贵族的必修课,也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基本素养。如孔子就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学习诗歌的作用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晋国赵衰举郤縠为元帅,也说“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君其试之。”③《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1822、1823页。
如此教育,不仅培养出一批批饱读诗、书、礼、乐的行政人才,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先秦后期诸侯外交君臣应答之间赋诗言志的风气。《国语·晋语四》中,秦穆公与晋公子重耳以赋诗相对答,《左传·襄公十九年》中,晋国范宣子对鲁国季武子以赋诗相酬唱,《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晋侯与齐、郑两国国君以赋诗相谈判,凡此种种,都可证明这一真实的诗歌生活样态。以至于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授政以达,出使能对,已成为“诵《诗》三百”的重要功能。
综上所述,随着先秦社会的不断变迁,先秦诗歌在主流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原来触机而动,自然生发的质朴歌谣经社会权力的选择性采用,先是作为荐上帝、配祖考、康帝德的娱神手段,继而成为祭祀文明中的宗教介质,嗣后融入礼乐文明的核心构成,再经转化,成为文化教育体系的修习功课,又在礼崩乐坏之余散入诸侯家,演变成折冲尊俎以及生活日用中的优雅辞令。
但是,如果对上述演变过程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基本特点:
一,诗歌由个人走向社会,由当下延伸至历史,是以其社会文化功能权力化、政治化为基本导向和依托的;二,诗歌成为当政者的社会文化工具,在意志、情绪宣导价值基础上,先后在宗教协同、政治规范、文化教化和人际沟通等方面发挥过不同的社会作用,并因此受到社会的认同、接受和尊重,它在这一时期的总体价值和功能是服务于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护,而不是其文学上的创造或艺术上的审美;三,在这一演进历程中,诗歌的宗教色彩逐渐减弱,而现实的政治色彩则不断加强。无论诗歌的社会角色如何变化,它都始终围绕着社会政治权力中心,并成为这一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发挥着凝聚社会意志、协同社会力量、构建社会秩序、维系社会规则、润滑社会机体、传承社会文化的基本应用属性。
这时候的诗歌肯定不是“纯文学”的,就算它蕴藏着纯文学的内涵,却生就一双“天足”,漫步穿行于数千年来的社会日常生活。正是这种未经束缚的社会应用属性,才使先秦诗歌长时期发挥着远远超出“文学”意义的多种文化功能,也使之受到大众的认同与接受、社会的保护与传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作为“诗”的国度的悠久文化传统。
三、孔子对“诗书礼乐”系统的修复与重整
到了孔子的时代,周王朝也已进入天下大乱的时期。在当时人看来,社会政治权力的涣散,导致社会秩序和等级的混乱,再进而导致礼崩乐坏、纲纪废弛与天下板荡、诸侯纷争等一系列社会并发症。
如与孔子同时的晏婴就说:“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史记·孔子世家》)《论语·微子》所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也反映出“礼乐缺有间”的时代里,执掌礼乐诗教的专职人员流失消散的情况,而《汉书·艺文志》更揭示出王官之学沦为诸子之学的历史事实。
孔子生长于礼乐制度完备的鲁国,深受礼乐传统的影响,对其所包孕的等级制度内涵有着深切的理解和认同,因而坚持传统的礼乐观,试图以“克己复礼”的方式恢复以往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伦常。因此,对包涵诗歌在内的礼乐传统的维护,也就成为其振衰起弊的现实手段。
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①《孝经·广道要章》:“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顺礼,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汉书·礼乐志》引作“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并且在仕进不遂的情况下“退而修诗书礼乐”(《史记·孔子世家》)。
如果不局限于孔子删诗这一焦点,那就很容易看到,孔子对“诗”的整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书、礼、易、春秋的整体删述同时推进的一个“系统工程”。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②[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七,《二十五史》,前引书,第227、228页。
关于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有另一种说法: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③[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前引书,第2715页。
《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使“《雅》《颂》各得其所”的乐,孔子几乎涉猎了当时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而其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无非是出于对“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现实忧惧,出于“克己复礼”,恢复“先王之道”,建立理想政治的终极目的,而其着手的核心则是重整先王时代的文化权力系统和政治文化机制。
如孟子所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番话除记录孔子的惶恐之外,也揭示出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孔子是在天子和王官缺位,社会政治文化权力失控的前提下,以一介士人的身份,接过了以往由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运作的政治文化机制。
孔子“追迹三代之礼”,以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明确意识,以“可施于礼义”为准绳,序书、正乐、删诗,“以备王道,成六艺”,建立或者恢复起一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使“后虽百世可知也”的浩大文化工程。
种种迹象表明,孔子记礼、传书、删诗、正乐的行为都有相当明确的选择性,绝不是对传统的简单修复。“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又以“《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这表明孔子在材料选取的上、下限,具体材料的增损去取和编排序列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并不是完全着力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与其说孔子所作的工作是在恢复传统,不如说是在规划和建设一种新的传统。
从诗与乐的角度看,孔子定乐,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过是使《韶》《武》《雅》《颂》一类乐曲在音乐上回复传统礼乐文明的旧观,在使用上回归到传统礼乐制度原有的规定状态;孔子删《诗》,以“可施于礼义”为去取标准,也就是使《诗经》系列的作品在意义和应用功能上符合“可施于仁义”的要求,否则即被淘汰;又“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还是为了将诗乐合一,使分离已久的诗乐关系能够复归于和合,使涣散已久的诗乐传统能够复还《韶》《武》《雅》《颂》风动天下的旧观;孔子注重诗教,就是希望利用它兴观群怨的作用,将人们导向“思无邪”的状态,以此“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危亡乱世建立起政治文化的纲纪和规范。经过这样的努力,“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并能使“后虽百世可知”,以达成“备王道,成六艺”的政治文化目标。
至此,先秦诗歌的政治文化基因终于得以保全、恢复和延续。尽管社会剧变,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百官流散,孔子却以一身之力,使斯文不坠,延至后学,终于经过秦汉社会的再造,继续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当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