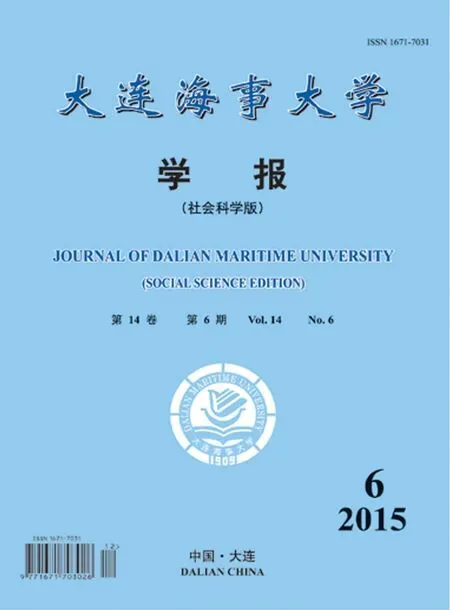宋明市舶贸易视角下的海洋国际法观念
俞世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宋明市舶贸易视角下的海洋国际法观念
俞世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历史上,中国在对待海洋的态度上,只是依据利益衡量的现实主义思路管制海洋,萌发的早期国际法观念体现出利益的狭隘性,从北宋市舶贸易的兴起与明朝时的衰落,足以证明之后中国在国际法领域内失去话语主动权的必然性。应通过对海洋法治、利益衡量工具及国际法观念进行逻辑上的调整,通过赋予海洋利益新的内涵,来构建起新型并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法观念和价值环境,从管制海洋走向经略海洋。
市舶制度;海洋法治;利益衡量;国际法观念
现在的国际社会,无一不重视海洋,甚至内陆国也如此。国际法律文件对此也做出了权利保证。早期的中国文明是建立于土地文明基础上的,强势的文明发源地多分布于远离太平洋西岸的地区,诸如半坡文明、河姆渡文明、龙山文化等,缺少内海的地理特征使得中国的先民“亲河惧海”。作为典型的河流文明国家,从公元前221年起,来自西北高原的秦向东征伐,统一了当时已知的陆地,濒海的三个诸侯国,燕、齐与楚被纳入新王朝的领土,这也就预示了今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与海洋日渐疏远的趋势。
近代化给中国带来的深重教训,告知了统治者及国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忽视海洋和海权在近代化进程中必然导致落后;二是忽视制度和法治的建设也必然导致曲折和失败。不过,在海洋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两者始终没有很好地衔接。尤其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之下,海洋法治早已不是一国内部的专有事务,而是被赋予更多超出原有概念体系的范畴,演变为国际法观念的内涵。如何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成为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
一、海洋法治的国际法观念演变
中国是否是一个海洋国家,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从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大国;并且从15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由西方殖民者寻找新大陆推动的世界大航海时代里,中国民间的海洋经济活动和海洋社会组织更趋活跃”[1]。也有学者将中国定性为“地锁国家”,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不是海洋国家,一直到“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2]。无论这些争论是否具备充分的论据,中国走向海洋的过程并非“内发性”,而是被动地纳入到全球海洋帝国的秩序体系中。现代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法治化,在涉海的权利义务上制定符合各国权益的法律框架和原则,且越过了国家管辖的边界。[3]该法治化的最佳证明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的制定标志着国际社会试图通过海洋法治的手段来解决非正规的变化[4],因为这些变化超过了原先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做出的任何设想。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国际法进入到蓬勃发展的时代,海洋法治已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从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到宾刻舒克的大炮射程论,再到1945年“杜鲁门声明”,海洋法治在不断的演变中前进。格劳秀斯否认西班牙所主张的海上独占权及英国所主张的近海及渔业独占权,其主张海洋为人类之共有,各国人民有自由航海的权利。[5]其提出的法治背景是新兴的荷兰与英国在海上所进行的自由竞争,荷兰需要自由而无任何约束的航行权,以保证其在全球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维护其国家利益。宾刻舒克以“陆上国家的权力以其武器所及的范围为限”[6]划定的领海宽度,对前者的学说构成了挑战,“主张接近一国领土的海洋,即沿岸海,与其以外的海洋即公海有区别”。海洋自由论所形成的国际法治基础,在更新的学说中逐步变迁,由绝对自由转变为相对自由。从另一角度上来看,即是国家利益在法治平台上的一次博弈与较量。绝对和相对本就是利益的一层哲学表述,由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在形成过程中,利益为导向的政治表达始终是明确而又实在的。无论是格氏还是宾氏的学说都围绕着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正义与和谐[7]间寻求利益。海洋利益的选择在国家行为上表现为对抗与合作交替的情形,最终以共同合议的方式进行了固化。
中国在对待海洋的态度上与西方各国迥然不同,有人以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认为“传统中国最具海洋意识的群体当属闽南人。闽南山区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崎岖硗确之地多,故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为家者,十而九也”[8]。可见,中国接触海洋的早期地点和人物并不位于国家的统治中心。这使得之后的海洋国际法观念,始终平行于现有观念,两者之间的独立征象较为显著,此情况一直延续至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但海洋的历史和地理因素并非是限制中国早期国际法观念发展的桎梏,相反海洋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的衡量才是决定中国海洋法治进程的本质。以下将从宋明两个朝代开设市舶贸易的角度,来具体阐释这种衡量的过程。
二、非内发性的国际法观念——北宋市舶制的诞生
北宋时期是中国海洋意识和国际法观念初步发展的朝代,政府鼓励人民进行海外贸易,并且成立了贸易管理机构,即市舶司。同时在对外贸易立法中制定了《市舶条法》,该法例中含有较多的涉外法律因素,造就了国际法观念形成的土壤。同时该法例的诞生也是经过北宋政府反复的利益衡量,并体现在国际法观念中。但这种观念带有无可避免的“非内发性”,即宋人的航海贸易行为并非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选择,贸易的本意是为了交换,而宋朝的贸易只是表征上体现出交换的行为,其背后深远的利益影响是陆上贸易的萎缩,而不得已表现出向海外寻求经济利益的被迫性。不过这种被迫性,也使得中国第一次打开了接受近代国际法观念的扉门。
首先,北宋海上贸易的繁荣源自平等主权意识的萌芽。古代中国无论是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总量上来讲,相比于周边的蕞尔小国,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是实至名归的。中国众多的王朝统治者一直视己为凌驾于各邦之上的天朝皇帝,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文明中心”意识,导致国际法的纲要是存在的,或者说是有“国”法而无“际”法。[9]这种状况直至北宋时期发生了逆转,“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中原王朝终于被迫接受了其他国家与其享有平等的主权地位,中国也正从此时起开始重新审视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在平等的营商环境中,海上贸易也就借此时机兴起和繁荣。
其次,《市舶条法》的内容反映了早期国际贸易法的雏形。政府鼓励外商来华经商,对到港的“藩舶,每商至,习以客礼见主者”(《宋史·苏缄传》)。北宋在北方面对着强大的游牧民族,陆上丝绸之路已被完全阻断,从西汉时期便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重新进入到统治者视线中。虽然在与日本、高丽和南洋各邦之间的贸易交易中,逐步形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但始终未能开展成文法的制定,这对国际贸易法的完善和成形造成了众多困扰。因此,宋政府之后开始了“详议利害,先次删立抽解条约,更取索重详定施行”,最终在国家的经贸利益前走出了法治化的一步。宋朝通过出口瓷器和丝绸两大主要商品,换取了来自海外的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逾石、牛皮及筋骨等。(《宋会要辑稿·职官 四四之二三、一七》)与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学说相似的是,宋朝以优势商品换取的国家经济贸易利益,正好用来弥补每年的岁贡,以及北方产粮区受战争影响所损耗的传统土地收入。海上贸易的巨额利益促使中原王朝正视与他国的交往,只有秉持平等主义的国际法观念,才能保证持续不断的财政收入。因而,此时的中国在衡量利益的背景下,已经触摸到了西方法学意义上的、建立“平等国际法”的门槛。
再次,《市舶条法》也凸显出立法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利益矛盾。北宋支持和鼓励海上贸易的初衷无疑就是增加国家收入,维持整个封建王朝的财政运转,其所评估和衡量的利益较为单一,即为货币性收入。立法的目的是为货币的固定流向提供相应的法治保障,相应地,此时国际法观念所表现出利益纲目的分立和对峙,法律对国家利益的保障是以限制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在没有完整法治体系的当时,市舶司管理者的腐败不可避免,“泉、广舶司日来藩商寝少,皆缘克剥太过”(《后村大全集·赵孟传除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制》)。另外,法例在实施中过多依靠行政手段,诸如禁榷、抽分和博买,而国际贸易法的原本初衷是保证海上贸易商货之利益,与西方中世纪的国际贸易法相比,《康梭拉德海法》《奥内隆法典》《维斯比海法》更侧重于保护商人在自治城市间贸易的权益保护,并设立专门的商事法庭来审理案件。但市舶制发展到后期,竟成为官员垄断海上贸易利益的权力寻租工具,如岭南节度使王锷对“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旧唐书·王锷传》),海外商客的个人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并在国家和官僚体系的利益剥拷中步履维艰。因此,《市舶条法》在各种形式的利益衡量下,选择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从而使得该法例更加近似于外贸管制法或海关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宋面对违法蕃商的处理方式,表现出司法主权意识的发展轨迹。从原先的“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来,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程史·卷一一》),再到遵循唐代的“化外人”原则,直至“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从中可以发现司法管辖权作为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原来的宽松到后来的严格属地管辖权,这些都是构成国际法的基础权源。中国人的国际法观念在同时评价海洋利益和主权利益,也促进了主体意识的产生。只不过,这种现象由于非内在性的特质存在而很快地消失,最典型的情况莫过于明朝。
三、利益再衡量下的国际法观念——明朝市舶制之殇
明朝在建立之初就恢复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原先的国际法观念,此时又有了一次根本的转变,国家利益在明朝市舶的废立过程中,再次经历了衡量与比较,只是此时的利益维度不再局限于经济利益。
明初市舶由于海禁制度和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使得海上贸易的走向发生了逆变,从原来中外商舶往来的盛景变为“只有少数朝贡外船来华,而无一艘中国船出海”[10]。明初政府将国家的海洋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于是摒弃了海洋经济利益。国际法观在“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的政策下,反映出明朝政府对于海洋利益理解上的偏颇,利益结构上的抉择导致国际法观念出现了倒退,自我强国的认知、海洋安全的不稳定性以观念制度化的形式对今后国际法观的走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后中国的国际法观念逐渐走向了闭塞和不开明,“国本主义”的倾向更为明显,强调国家利益是国际法服务的唯一目标。[11]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其与中国海洋战略的滞后是一并存在的,很显然无法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
再者,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外交,并没有带来成熟的国际法观念,虽然与南洋各国间的交流与联系增多,但实质上却是国家主导的海洋行为取代了民间海洋行为,这种态势是为了换取外国与中国建立“宗主”和“附庸”的关系,从国际法的理论上来看,类似于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一种法律关系,可以称为一种国际监护关系。而建立此关系后,持有明政府颁发的“勘合”和本国政府的“表文”才有资格成为“贡舶”,且必须遵守明朝廷指定的航路、港口、限定船数、限定日期、限量输入。海洋利益的交换系统中,充斥着国家意志,国家实际上行使着绝对化的主权,海洋安全利益在永乐年间已不十分突出。随着中国的远洋事业进入黄金发展阶段,中国人踏海的足迹一直延伸至东非和中东海岸,海洋的政治与外交利益又成为中央政权衡量标准的重要参数。郑和的远航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反而招致“费钱粮数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何益”(《殊城周知录》)的诘问。
上层统治阶级意识中的国际法即是将主权扩展至别国领土上,因而郑和船队实属武装商船,出现了在别国管辖事项上横加干涉的情形。另一方面,在没有形成确实有效的国际法规则时,明政府采取两种法律手段经略和治理海洋。其一是官办航海业中的国内法规则,如颁发外贸特许权的行政法规、皇帝的口谕等。其二是国际礼让规则的施行,国际法规则让位于国际礼让,这并不等同于主权让渡的现代国际法观,而是封建时代主权不对等的政策导向,即朝贡贸易的“怀柔天下人”。现代国际法中认为国际礼让是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应有的相互礼貌,礼让规则也是法律的一部分。*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ed Soviet Republic v. Cibrario, Annual Digest, 2(1923-4), Case No.17.这在海洋利益的国际交往中,可视作中国在利益衡量上的又一次法治试验。可以看到,虽说礼让规则的国际法属性摆脱了软法之嫌,但中国的国际法观念在远航中传播的依然是不完整的国际人格身份,这种不正常的国际法观念在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后,遭遇到了近现代国际法观的强大冲击,直至最后的瓦解,从此中国也丧失了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话语权。
此外,在明朝中叶,原先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中设立的市舶司,其目的是“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明史·卷八一》)。官方垄断了海洋利益,但又无法从朝贡贸易中获得实际收益,这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使得市舶司的货币税收职能严重减损,最后导致了广州、明州和泉州三港的市舶司被全部裁撤。此情形延续至明末,随之是庞大的民间与私人海商集团的崛起。在与海洋政治利益的衡量中,中国的上层统治者始终无法摆脱固有的国际法观念,认为利益衡量的维度虽有所发展,但依然秉持海上贸易是“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既裕足食之计,实寓弭盗之术”[12],将海洋作为经济以及政治利益的来源。换言之,依然将平息海上武装和税收作为海洋利益的焦点,民间海商与外国贸易惯例、规则的形成计划并不属于国家的国际法观念范畴中。国家的成文法典中依然将违反禁海的事由作为刑罚的唯一条件,诸如“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蕃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巳行律处斩,乃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大明律·问刑条例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附》)。至于后来横行海上的中国武装海商,如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则利用了国内政治形势,明政府也寄希望于武装海商来维持东南沿海的政治利益与安全,同时将海洋的经济利益让予中国海商,明末的市舶司实际上已失去原有的功能,而外国商船甚至“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台湾外纪·卷一》)。此类贸易许可证的颁发不经由政府,而由私人海商予以发放,彰显中央政府依然将海洋利益置于土地利益之后,主动摒弃了海洋行政管理权,国内成文法的制定被海商集团的贸易习惯法所取代。
国际法著名学者奥本海认为,国际法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公共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经济利益。这两个因素的发展与国际法的发展成正比。公共道德的标准提出,在明末那个时期无法进行科学的衡量,也缺乏相应的衡量工具。并且,由于海洋经济利益最终逐渐在国家收入中萎缩,转而由私人走私获取对称的利益,原先宋元时期政府所主导并得益的海上贸易从官办转向民办,但国际法观念的更新却无法看到,相反变为更加保守闭塞的自我主义。这种自绝于海洋的做法源自国际法观念上的偏见,因观念意识并没有与国际关系相脱离,只是将利益因素与国际关系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致使中国在面对历史发展时丧失了主动构建国际法律秩序的机遇,从而让西方殖民者将本国法、国际法观念移植到东亚、南洋以及其他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中国也至此之后再无国际法的主导权。整个明代市舶制度的衰落也表现出,政府在对国际法上的意识和观念,被利益衡量这一无法逾越的桎梏牢牢锁在了本国陆地上。随着清朝的建立及海禁的全面推行,海洋上难见中国商船的身影,而中国的国际法观念要等到1840年以后才会有近代化的演进。
四、海洋法治、利益衡量与国际法观念的逻辑调整——对“一带一路”的反思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因其本身并不是古代“一带一路”的重复,而是更多地表现出新的特征。中国海洋法治的逐步形成和构建中,始终交织着国家对海洋利益、陆地利益的衡量,以及国际法观念的认同和逆转。利益衡量作为法律评价的工具影响着国际法观念,而国际法观念又根据利益种类和量度的差异进行着国本主义的意识表达。只不过此种国际法观念的变动模式在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外交秩序中早已不再适用,政府也不会将海洋利益简单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之类的逻辑等分法再次用于海洋战略的方案中。因为此时的海洋利益不仅仅是政治与经济的利益融合,更是法治和观念、价值的利益融合。
美国学者温特认为国家利益主要包括“维护现状、改变现状和集体认同”三种建构因素。[13]海洋利益在宋明两朝设立的市舶制度,无疑是维护与改变现状的利益索求,而集体认同在宋明时期的中国是无法达成的目标。温特还认为基于集体认同的国际利益具体表现为愿意帮助那些其认同的国家,即使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这种认同不是外部强制、利益诱惑,而是认同对方是自己的“伙伴”、“朋友”,乃至为“命运共同体”。认同从利益中产生,但并不涵盖利益,只是从构建主义的视角将利益等同于观念。宋明时期的国际法观念只是作用于国家的海洋利益,并随之变化。而构建主义的理论阐明了现代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立法话语权的争夺中,必须将利益与观念进行融合,也就是国家利益的逻辑构成中必须在现有内涵中,纳入新的观念与价值利益,并体现在本国的国际法观念中。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建设中,学界将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建设等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反思封建时期的国际法观念及国家对于海洋利益的单一诠释,可以说在“一带一路”中,不仅要在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利益上进行衡量,而且要在观念和价值利益上进行重新调整,并与前者共同作为传播的对象,这样可以防止因政治、经济利益出现波动而导致不确定的国家利益损失。因为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观念等同于物质利益,有利于确定各种替代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并影响相关国家的政策。国际法观念重新纳入到观念利益的做法,可以有效实现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再度升级,并在重新搭建的海洋法治和海权体系下,保障我国的海洋利益,这也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一带一路”的建设虽其表现为政治与经济利益在亚欧非大陆上的再次分配与整合,但其本质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大国际法观念”。中国一直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互惠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些都必须体现在国际法的观念利益中。这与美国构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不同,因该协议的观念利益是建立在美国利益为中心的秩序基础上,后者的国际法观念是围绕在近现代西方霸权所维护的国际秩序之中的。所以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应始终不能忽略国际法中的观念利益,并将其作为新的衡量方法和工具。
[1]陈东有.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J].江西社会科学,2011(1):32.
[2]郑永年.中国的海洋地域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J].外交评论,2014(1):45.
[3]HOUGHTON K. Identifying new pathways for ocean governance: The role of legal principle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J]. Marine Policy, 2014, 49(4): 118.
[4]鲍基斯.海洋管理与联合国[M].孙清,吕春花,孙洪,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2.
[5]刘达人,袁国钦.国际法发达史[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63.
[6]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M].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8.
[7]何志鹏.国际法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52.
[8]庄国土.中国海洋意识发展反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6.
[9]陈致远.中国国际法溯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7:10.
[10]彭德清.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245.
[11]何志鹏.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114.
[12]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
[13]方长平.国际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115.
2015-06-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20047);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Z13017)
俞世峰(1984-),男,博士,助理研究员;E-mail:yushifeng1984@126.com
1671-7031(2015)06-0048-05
DF9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