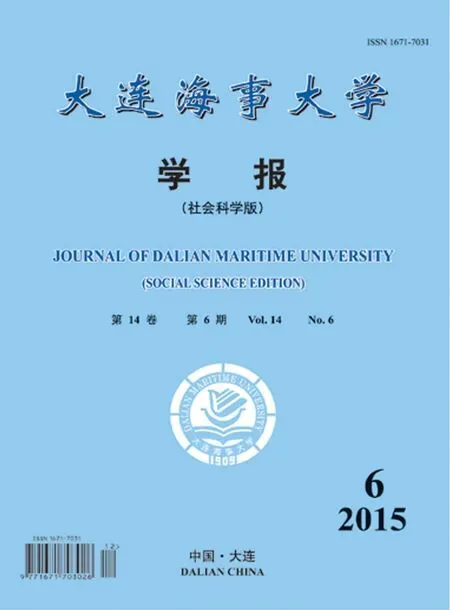制度变迁:中国传统纺织手工业包买制的演进
于 颖
(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制度变迁:中国传统纺织手工业包买制的演进
于 颖
(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纺织手工业发展中包买制的出现与兴起为典型范例,进一步证实生产组织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内在关联性。考证包买制的起源,回顾鸦片战争前包买制在丝织业中的萌芽与发展,重点考察清末民初乡村棉纺织业中包买制的兴起,从中揭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乡村工业化的动力所在,即除市场化和技术进步的因素之外,制度变迁尤其是包买制的兴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制度变迁;包买制;经济发展;棉纺织业;手工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主流学术领域中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假设的可接受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按时序的经济实效时,包含了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时间不起作用。从而使他们在为经济学理论赋予了精确优美的数学形式的同时,却将现实世界误判为是静止的和无摩擦的。因此,新古典理论对动态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适宜的工具。近些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日益走向成熟,并且已经成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本文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剖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历程,并择取其中典型的生产组织制度变迁的范例,即包买制的出现和兴起,来揭示制度变迁在传统乡村手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一、包买商制度的起源
所谓“包买商”,是指向小手工业者贷给或供给原材料以至工具,给予一定酬金或工钱,然后收取成品转向市场销售的商人。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包买制大约是在17世纪英国的呢绒制造业中逐渐出现的。[1]383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起源于更早的时期,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包买商作为一种组织制度至少在13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存在了。[2]332到14、15世纪,这种组织形式更加普遍。一些富裕的呢绒商到市场上购买羊毛,然后分发给在各自家中工作的纺工,让他们纺成毛线。呢绒商付给纺工工钱后收走毛线,再把毛线分发给在各自家中工作的织工织成粗呢,在给织工支付工资后,将粗呢收集到进行精整、漂洗的场地。后面的工序大多集中在呢绒商设立的简陋厂房中,有若干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这是由商人直接支配的生产,在英国乡村,人们将这种组织形式通常称之为“家内制”。[3]到18世纪,包买商制度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很多行业中已经广泛存在。如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绸缎生产、花边加工、呢绒织造、剪刀生产、制鞋制帽、造纸印刷等各个行业中都流行过这种包买商制度。其中,纺织业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成为包买商制度最盛行的行业。同时,在西欧以外,包括亚洲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以及非洲国家都出现了。[4]
国内学术界关于“包买商”的提法,一般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是农村手工业向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过渡的两种途径的后一种,而且这“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5]373马克思将这种直接支配生产的商人称为“发货人”,后人将其译为“包买商”。[1]24为了说明包买商的含义,马克思曾进一步用英国和法国的实例解释道,“十七世纪的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只是商人,他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织工实际上是为这种商人劳动”。“在中世纪,商人不过是行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包买商’,商人成了资本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5]374列宁后来曾将包买主划分为五种形式,但他所说的包买主与上述的包买商还有些不同,他所指的包买主原不是商人,而是小生产者。由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不便进城销售,而“由少数富裕户的代表独揽销售”,并作为大城市的商人的代表,向小生产者供料、放款、收货。在这里,商人并未直接支配生产,他们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的。这种支配尽管可以控制市场、价格以至原料供应,尽管可以占有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但它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1]24-25
在中国明代,尽管商人资本已经十分活跃,出现了一些以徽商、晋商、浙商为代表的大商人资本,但这种商人资本只是活跃在流通领域,并非控制生产的包买商。到了清代,包买商这种组织形式在丝织业中开始出现了。如据浙江吴兴《双林镇志》记载,雍正十年(1733年)的进士沈泊村诗云:“商人积丝不解织,放与农家预定值;盘盘龙凤腾向梭,九日辛勤织一匹。”[1]374可见,当时这一地区的农家丝织户,已经受商业资本的操纵或控制。另据江苏《震泽镇志》记载,清道光年间,乡村农桑之户,“亦有兼事纺经及织者。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谓之料经”。“有专精此者,其受值较多于他工。”另《南浔志》云:“细丝亦称经丝,可为缎经。……买经造经者曰经行。”“自纺经丝售于经行,曰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曰料经。”[6]259,265这说明,在清代的双林镇、震泽镇和南浔镇等江南各地的纺经者中,已经广有乡经、料经之别。乡经乃是以农家自产的丝纺成后出售,这属于独立的小手工生产者。而料经则是贫苦农家从丝行处领取原料,“代纺而受其值”,即纺成后领取加工费,其技术精湛者因产品数量多质量好而“受值较多”。显然这是典型的由商人向小生产者发放原料,经加工后收回成品,计给工价,受取工值的包买商制度。这与欧洲原始工业化过程中相当流行的包买商制度是十分相似的,它是商人资本支配丝织业生产,把小生产者变成他们事实上的工资劳动者的一种形式。在清代,江南的苏州、南京、镇江、杭州等地的丝织业中,这种包买制形式的手工业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普遍。
在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区,亦可搜寻到包买制的踪迹。如广东《嘉应州志》记载:“程乡茧绸为岭南所贵。……考程乡茧质厚有皱纹,坚韧朴实,制为衣袍,数十年不敝。昔年广行于四方,自俗尚华靡,惟海南人仍购之。”“纺丝者,皆女工,曰打绸,工价远逊曩昔。”又《嘉应州乡土志·商务志》云:“出口货,不一类。土茧,质坚固。销南海,达京都。”注云:“此茧出贵州遵义府,州贾买归,用水煮熟,发人缫丝织成。”程乡县即嘉应州,该县原属潮州府,清雍正十一年,废县为州,并升为直隶州。这则资料所述“程乡茧绸”应为程乡地名改为嘉应之前,因此,纺丝女工按工价打绸,也是雍正年间的事情。后来由于嘉应(程乡)出产的茧市场销量扩大,本地乡村所产的蚕茧不敷供应,才远贩自贵州。史志中所说的那些收购蚕茧,“发人缫丝织成”的“州贾”,其实就是包买商。在康熙年间,广东所产的丝绸曾远销京都和海外。《广东新语》中记载:“广之线纱与牛郎、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6]277-279在如此发达的丝织业基础上,生产组织的成熟应该是自然的。彭泽益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曾描述,在道光年间佛山镇的丝织工场中,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于织绸工作,有人曾疑惑这么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在传统的小农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现在看来,可以做一个合乎逻辑的猜测:当时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包买制的生产组织,即通过丝织业中的账房将众多的小手工作坊、个体劳动者、家庭妇女、小生产者和各种手艺人组织在一起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或者说,制度变迁对于扩大生产规模和促进生产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二、清代中期包买商对丝织生产的控制
在清代中期,商人支配生产的组织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史料中对商人支配生产的直接记述很少,但仍可在相关的史料中搜寻到其发展的轨迹。如在江苏的碑刻资料中,有一则道光二年(1822年)苏州官府镇压机匠罢工斗争的碑文记载:“查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行本甚巨,获利甚微。每有匪匠,勒加工价,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以侵蚀为利藪。甚将付织经纬,私行当押,织下纱匹,卖钱侵用。稍向理论,即倡众歇作,另投别户。”“自示之后,各乡匠揽织机只,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收执。揽机之后,务宜安分工作,克勤克俭,记工受值,不得将货、具、经、纬私行侵蚀,以及硬撮工钱,借词倡众停工。”这是一份站在官府和机户的立场上,对机匠为了提高“工价”而聚众停工闹事进行镇压的告示,事件的起因是机匠“会聚多人,向轮年机户李升茂庄上滋闹”。为此,有26位机户主人署名向元和县府控告这些滋事机匠。[1]374-375这一碑文史料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商人支配生产的状况。这里的“机户”实际上是放料收货的绸缎铺号,即后来被称为“账房”的包买商人。他们将经丝、纬丝等原料以至某些工具交给机匠织造,在织成收货后支付“工价”。既然已经有了“轮年机户”,说明其行会组织已经相当完善。这里的“乡匠”估计是遍布城乡的个体丝织业生产者,他们领到经纬后在自家织作,并在织成交货后“计工受值”。在一个县城能有26人署名状告“匪匠”倡众闹事,以至于不得不求助官府来镇压,可见“乡匠”或“匪匠”的人数不少,规模也不小。为了防止“机匠”侵蚀,规定他们到机户行会所在地“机房殿书立承揽”字据,说明当时“机户”和“机匠”之间的契约性交易也已相当规范。显然,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包买商制度。
在清道光初年以前,官方文书将发料收货的纱缎铺庄一直沿用“机户”的称谓。但在民间,苏州、南京等地的丝织业中,包买商的典型称呼为“账房”。如《吴门表隐》中就有“经造纱缎账房”的记载:“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部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这里的“机户”与上述的“机户”不同,他们不是包买商,而是受“账房”支配的小生产者。清代中后期,在丝织业中,这种“账房”形式的包买商制度相当发达。据调查,到清末,仅在苏州开业的“账房”就有57家,支配机户近1000家,共有织机1524架,使用男女工徒7681人,年产纱缎30 900匹。其中开设历史较长的账房有12家,最早的一家石恒茂记开设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乾隆年间(1767—1793年)开设7家,嘉庆年间(1802年、1810年)2家,道光年间(1837年、1845年)2家。在南京,机户最多,而且“账房”的出现可能比苏州还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奏请派曹寅之子任江宁织造的折中就有“机户经纪”一称,可能就是后来的账房承管。如史料中云:“民于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普通多称机房,有自织、代织之分。代人织者,原料由人供给,此种雇主,江浙等处称为账房,皆饶有资本之绸商,各埠有代彼趸卖之店,名为分庄。惟总店则皆称账房,而不称总庄。南京等处之规模较大者,称为大账房。”[1]376-377范金民、金文在《江南丝绸史研究》中认为,在清代前期的江南各地,特别在民间丝织业中,账房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已经成为较为常见的、普遍的形式,可以说,其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组织中已经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7]
清代的“账房”是通过控制丝织业生产工序的各个环节来支配丝织业生产的。丝织手工业的生产工序大致分成织前准备和织的工序。织前准备工序主要有养蚕缫丝、炼染、掉经或络经、掉纬或络纬等。养蚕缫丝纺经的工序是在农家完成的,其中植桑养蚕的劳动是比较辛苦的。据李伯重的考证,种植水稻每亩仅需11.5个工作日,而种桑养蚕每亩约为93个工作日,两者的劳动投入比率为8.1∶1。[8]黄宗智的实地调查结果也表明,除桑树栽培外,仅养蚕期间的劳动就已足够艰辛,“蚕箔连同蚕儿重达三四十斤,一张蚕子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斤桑叶”[9],蚕茧成熟后,要赶在从收茧到出蛾的短短十余天内将茧缫成生丝,并将两根细丝合股,用纺车纺成经丝。在许多地方,这些高度紧张的劳动都是由农家妇女完成的。在经丝产地,许多农家将自产的丝纺成经纱出卖,因此有“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之说。经丝纺成后需经炼染,练是练白,并加槌,使丝光泽,有专业槌丝工,亦有练白房。染练后的经丝要成缕,要把它绕在籰子上,称掉经或络经,多由农家妇女为之。将许多的籰丝在木架上牵引成几十条并行的长丝段,叫做牵经或整经;把并行的丝接到织机原来的经线上,叫接头;如为新机,须先结综,再穿筘、穿综,这需要技术熟练的人来做。纬丝的处理比较简单,除练选、拍丝外,只是用纺车把它绕在梭管上,叫做掉纬或络纬,也多是由妇女为之。[1]365,387这些主要由乡村农户承担的织前准备工序,表面上看是小生产者独立的经济行为,但事实上它已经是商业资本所控制和支配的网络的一部分了。
那么,账房是怎样支配生产的呢?账房支配丝织生产的过程大致分成以下几个环节:首先,称之为“丝行”的大商业资本,垄断着乡村的经丝市场,他们是乡村农户和账房之间的中间商。每到新丝上市季节,他们就向农民收购经丝,再卖给账房。也有的账房自己直接派人下乡收丝。接着,账房将丝交给由他们支配的染坊加染和捶练。经丝染练后由账房发给车户(又称纺经户或掉经娘)进行车经络纬,这一环节实际上还是在账房支配下的家庭劳动。账房将纺好的经丝交给牵经工匠进行牵经接头,这是需要熟练技巧的劳动,是“世代相传,各归主雇”的行业,他们实际上相当于账房的常年雇工。账房最后通过承管(也称料头)组织和管理众多的机户进行丝织。承管本身也是机户,他们须熟知机户的手艺、行为,如有机户拐带丝经潜逃,承管须负赔偿责任。承管不仅从账房获得佣金,还能从众多机户方面得到奉承,因为没有承管的介绍和担保,机户就不能从账房那里开账贷料。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末,南京一个承管的收入有达到十几石米的。大多数机户是小生产者,平均每户织机不足两台。账房通过承管向众多机户发放原料,收取成品,并按绸匹数计发工资。这种放料代织的经营方式把丝织的各个工序都组织起来了,它把农家妇女、各种手工艺人和手工作坊都置于其支配之下,变成他的工资劳动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它本身也就具有产业资本的性质了。这一切都是在不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不改变原来的生产技术的条件下悄悄地进行的。[1]382李伯重认为,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丝织业中的手工工场没有多大发展,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账房制度的优越性,它使得那种集中生产的手工作坊并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而且,在这一时期,真正独立的个体小生产者,可能已经为数不多。[10]正像布罗代尔所引用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分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种种事实表明,家庭劳动已陷入一张无形的蛛网之中,而蛛丝则掌握在几个包买商手里。”[2]334可见,在清代前中期,包买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在江南市镇的丝织业中已经相当成熟,并在中国丝绸织造的繁荣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清末民初棉纺织业中包买商制度的兴起
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的考证,在棉纺织业中,明代曾有“以棉换布”之事。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也有几则史料记载着织户以布换棉或者以纱换棉的事例。但这种以布换棉的情况在市场上所占比重很小,况且这里的商人并未垄断市场,商人与农民织户之间也无固定关系。这种交换多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即仍是按时值作价,只是省去了银钱做中介而已。因此,这还不属于典型的包买商形式。这就是说,在清代前中期的棉纺织业中,还未发现有包买商形式。[1]25,398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侵略的触角从沿海延伸到广阔的腹地,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包买商制度在乡村棉纺织业中广泛地发展起来。清末乡村棉纺织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典型区域是华北的高阳、宝坻和潍县,从有关的历史文献看,这些地区大约从19世纪的70、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廉价的机制纱进行织布生产,大约在1907年后,铁轮织布机在高阳等地区推广开来,使生产效率比传统织机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促进了乡村手工织布业的迅速发展。[11]据天津档案馆留存的一份历史资料记载:“因齐集绅商,提议有绅商筹办制造轮机,并由各商购办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予手工。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织纺,各商收布不用负担而有售主,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不二年,土布畅兴。”[12]109这段文字表明,“按斤领线”,“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予手工”,此乃包买商制度无疑。而且这种包买商制度使绅商资本和贫户劳动力得到了有效的优化配置。另据吴知所著《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中记载,在19世纪晚期,在高阳以及周围的清苑、蠡县和任邱等地,随着布匹市场需求的扩大,布线庄等商号通过“撒机制”的方法,大量收购布匹。而典型的“撒机制”就是指织户从商人处领取棉纱,按照一定规格织好布匹,并交回到商人那里,然后领取工资。当地人把这种方式叫做“织手工”或“织茬子”。通过“撒机制”这种方法,高阳县城的纱布商号不仅扩大了对乡村织布家庭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周围集市的渗透,逐步形成了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织布区域,并促进了这一区域棉纺织业在清末民初出现了迅速发展的高潮。同时,不仅在华北地区,江南闽浙一带的乡村织布业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包买制形式。如闽浙总督卞宝第在任的1888年至1891年间,福州所设的60多个织布局,多是商人向农户发纱收布,实为散工制,也就是包买制形式。[13]可见在当时的织布业中,包买制形式已经相当普遍。
那么,包买商制度是如何推动乡村棉纺织业发展的呢?首先,包买制加速了乡村棉纺织业的技术进步。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乡村手工织机发生了从投梭机到拉梭机再到铁轮机的变化,每一种机器的效率都比前一种提高一倍左右。尤其是铁轮机的普及使用,大大缩小了手工织布与电动织布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铁轮机以脚踏为动力,织布者可以腾出双手来操作,从而使布幅大大加宽。木机只能织出一斤左右的小土布,而铁轮机可以织出八、九斤的布,这种规格与机织布已经很接近了。铁轮机的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新式技术的普及应用受到乡村农户资金短缺的限制。包买制的出现恰好解决了乡村织户在织机方面的资金短缺的问题,即上述的“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织纺”的问题。乡村织户大多资本金短缺,但有了包买制后,所需纱线可以“按斤领取”,不必支付用于购买原料的货币资本。而价格昂贵的新式铁轮织机,可以通过包买商“贷机”或“租机”的方式,将机款或租金从以后的织布工资中逐渐扣除。这样,高效率的铁轮织机就迅速在乡村织户中得到了普及。其次,包买制增强了乡村棉纺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其他自织自卖的乡村织户相比,在包买制控制下的织户产品具有比较严格的质量控制手段和相应的市场信誉。包买制的发展事实上将织户和包买商的交易关系内化为一种可信任的关系,它将乡村众多织户变成了一个组织体制的雇员,包买主对其织户的技术水平和人品的了解,就像工厂组织内部的厂长对下属的了解一样,只不过这种工厂的厂房分散在众多的农户家庭。而与手工工场相比,包买商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其灵活善变的生产规模。它可以随着市场上布价的涨落和需求的变化,随时扩大或缩小其生产的规模。“包买商人控制的布线庄及其分号从空间上看,就像一条条巨大的章鱼,只要市场出现机会,它们就会立即将其触角伸向四面八方,而在其他时间则龟缩一团以节约成本。”[12]136包买商制度正是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成为手织业最为主要的生产和市场组织,并和机器织布业抗衡几十年而不败。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在1900年至1920年之间,中国乡村棉纺织手工业中的包买商制度发展得相当迅速。河北的高阳、宝坻,山东的淮县,山西的平遥,江苏的江阴、常熟、武进,浙江的平湖、硖石,广西的玉林等地都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最兴盛的地区。[14]以河北高阳、宝坻为例,在1912—1920年间,“织卖货”和“织手工”(“织卖货”是指包买商供织机,织户领纱织布,机价由领织工资中扣还;“织手工”即包买商放纱收布,织户领取工资)这两种典型的包买制均有较快增长。织卖货的织机数由955台发展到4517台,织手工的织机数由1458台增加到17 387台,到1912年,织手工的机数占总机数的34.5%,到1920年,这一比例就提高到79.4了。[15]可见其扩张的速度有多快。高阳的纱布号大多是由原来的钱庄、粮商转化而来,到20年代初就已经控制了当地2万多架织机,年产300万匹布的8成。宝坻的67家布号,1923年时,也控制着领纱织户7650户,织机8180台,占当年织机总数的71.8%。[16]再看江浙一带的情况,在这一地区,历史上早就有以花换布或放花收布的习俗,20世纪初洋纱日渐流行以后则更加普遍。放纱收布尤其在江苏的江阴、常熟、常州和浙江的平湖、硖石等地最为盛行。江阴的第一个放机是1895年的公信布行,1908年后流行开来,到1918年后,除了农家自产自销的大布以外,江阴小布几乎全是放机织造的。布庄放一小包纱(144两)大约收布10匹,约10天织成。1918年时给织户工资1000~1200文,约合银1元,织户另可得织半匹至一匹布的余纱,约值0.2元。布庄放一小包纱可净赚0.2~0.3元。大布庄如高慎昌控制布机2000台,最多每天收布3000匹;钱德丰有机产4000户,旺季日收布6000匹。常熟放纱收布始于1910年,常州始于1912年,收布及工资情况与江阴相仿,惟两地亦放大布。浙江平湖是水乡,布庄放纱收布由船户发收并作保。一小包纱织布12匹,约20天织完。1920年时,上等布加工费1.2元,一般布只0.7~0.8元,织户另得余纱约1支。因收布须20天后,布庄垫本较大,毛利率亦较高,约10%。平湖约有80%的织户做“放机”,年产达160万匹。海宁县硖石镇为土布集散地,亦流行放纱收布,每小包纱收稀布10匹,工资1元左右,余纱四五两。[17]广西玉林县织户家有布机一二架不等,生产销售亦受包买商控制,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织户向商人领取棉纱,按商人要求的规格织成布匹,缴布后按规定领取工资;一是织户以布换纱,一般以2斤布换棉纱2斤2两,如果布的质量低劣,则只能平换。[18]可见织户的工资相当低下。
在清末民初,包买商制度不仅盛行于传统的棉纺织业,在一些新兴的针织、花边等各类手工制造行业中,也广泛地出现了包买制的经营形式。针织技术大约是在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包括毛巾、袜、汗衫裤等产品,大致分布于我国沿海一些城市及城郊的农村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平湖和天津附近的农村。据考证,到1913年,在上海及周边无锡等地有记载的毛巾厂有13家,雇工都在二三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三友实业社,除在上海郊区拥有1800台织机的12个手工厂外,还以发料收货的方式支配农民家庭木机四五百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针织业迅速发展。上海1917年已有针织厂70余家;天津1912年只有针织厂2家,到1920年先后增设18家;浙江平湖、硖石、嘉兴、嘉善均有针织厂数十家,而且其中不少是家庭户。上海、浙江平湖均盛行放机制,即将手摇机租给农户,发料收货,从织户应得工资中扣去租金。放料收袜以上海“南汇袜子”为盛,振艺商行曾控制南汇家庭织机的1/3。以生产童袜知名的同兴袜厂年销25万打,其中3/4是在南汇加工的。浙江平湖光华厂放机约1000台,当湖厂放机600台,每机每月收租2元,织户日可织袜一打,得工资0.22~0.26元。[19]花边业则起源于清末时期的烟台,民初传至江浙一带,花边的生产经营从一开始就是以包买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在山东烟台,“向有经纪人自备原料,分布各地女工,然后依制之优劣,给与工值,从事花边工作制女工,每日所获工值自三角至五角不等”,据估计,在1926年,烟台附近的村庄中,从事于织花边者约45 000人。民国初年,花边业传至上海以后,近郊的川沙、宝山等县的妇女多以此为业。截至1930年,川沙县从事花边业的场家约47家,从业的女工人数达23 050人,平均每家490人,多数场家系“收发花边”的商号。花边业鼎盛的时期,无锡有花边商150家,最大规模者拥有资本达万元(一般为500~1000元)。浙江农村亦相似,从事花边业的经营者“虽名为花边厂,实际上则为商号,所有织造女工,大都散居各乡,厂方将原料发给织户,到期或派人收货,或汇集送厂,至于工资,则论码计算”。除此之外,在制茶、制瓷、铜器、制笔、爆竹、皮毛、绉纱、纸绢花、梳篦、发网、草帽辫、蜡烛等手工制造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包买商制度的经营形式。[20]可见,包买商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广泛性。
四、结 语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包买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从清代开始出现的,尤其在江南的丝织业中,名为“账房”的包买制性质的生产组织已经成为较为常见的、普遍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包买制在当时的丝织业生产组织中已经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纺织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继续演进,在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包买商制度在乡村棉纺织业中广泛地发展起来,尤其在华北、江浙一带发展得相当迅速,由此带动了波澜壮阔的乡村工业化进程。可惜,这种进程刚刚开始,就被大规模的战争打断了。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以丝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组织,一直在经历着漫长的潜移默化的制度演进。尽管家庭经营形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家庭内部的生产经营性质以及手工业在家庭生产中的相对地位却一直在发生着由量及质的变化。一方面,在家庭内部,手工业作为副业主要满足自给自足需求的自然经济性质逐渐萎缩,而商品交换经济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超出家庭规模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地衍生和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无数家庭作坊的繁荣和一些手工工场的出现,也表现在包买商制度在丝绵纺织业中的形成和发展。包买商制度与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相比,其制度变迁的性质更隐蔽,它使乡村手工业表面上仍然具有家庭生产组织的外观,而实际上却被庞大的商人资本所控制,而广阔乡村家庭中的纺织劳动者,事实上只是这个看不见厂房的大工厂中的工资劳动者。包买商制度凭借着独特的质量控制手段和灵活善变的生产规模,以及低成本的经营管理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包买商制度与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一样,是家庭经营和近现代工场制度之间的有效过渡形式,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强调包买商制度的历史作用,并不意味着它的优越性超过了工厂制度,只是相对于传统的家庭生产经营制度而言,这种组织形式朝着近现代化的方向,在制度变迁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形形色色的交换[M].北京:三联书店,1993.
[3]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2-203.
[4]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44.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郑昌淦.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7]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385.
[8]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J].中国农史,1985(1):1-11.
[9]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53.
[1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0.
[11]赵志龙.高阳纺织业的变迁轨迹:1880—2005[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2):77-82.
[12]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M]//吴承明.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7.
[14]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413.
[15]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J].政治经济学报,1935,3(1):63-67.
[16]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M].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6:38.
[17]徐新吾.江南土布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491.
[18]千家驹.广西经济概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16.
[19]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55.
[20]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6-318.
2015-09-01
于 颖(1964-),女,博士,教授
1671-7031(2015)06-0011-07
F426.89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