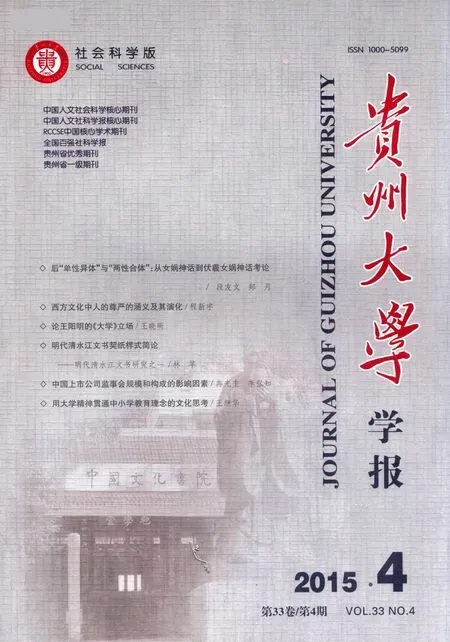苗族宗教祭辞中所涉地理标识探析
杨庭硕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 416000)
石启贵作为早期关注湘西苗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学人之一,他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集结成文,而其中一大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湘西苗族宗教的整理。由于该文集十分浩繁,本文试图以后人麻树兰、石建中和王明珂等所整理和编译的《椎牛·第一堂 吃猪》[1]为线索,去考订这篇宗教祭辞中所涉及到的地理标识——植物、动物和山川形胜,去复原苗族历史上的生息地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尝试,缺陷,甚至是错误肯定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点为上。
在麻树兰等人整理的这个文本中,《椎牛卷》就有上、中、下三卷之多,而仅是第一堂《吃猪》就占据了一本书。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不再将全文粘附出来,而仅是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才是做相应的摘引。至于其它内容,读者只需去查阅原文便可知晓。
一、苗族祭辞所涉植物名称考订
在《吃猪》文本中,提到了很多的植物名称。据不完全统计,有木椒花、竹子、青枫树、途料树、枫树、荞麦、栗、苏子、芝麻、棉花、杉树、楠木、茶树等,而在一般祭辞中经常出现的各种神树一类名称则鲜有提及。对这些植物进行整理和归纳后,再结合目前生态学、植物学等学科的已有知识体系,发现这些植物大多是今湘西境内较为常见的植物。如果对文本所载的这些植物所属生态系统和区域框定之后,似乎可以回应此前学人所认为的,苗族是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定居的民族的结论[2]103。进一步讲,前人的这一结论似乎有欠十足的说服力,因为这些祭辞中所含植物大多是今湘西境内常见之物种,因而生息在今湘西境内的苗族,应当是当地的一个古老民族,是否是从北方迁徙而来,还需要做更多的考证研究工作。
我们知道,我国的华北平原,最具典型的植物莫过于当地随处可见的榆树、杨树或柳树之类了,但在这篇祭辞文本中却不见任何踪影。这就说明,这篇祭辞所形成的时代,祭辞的编纂者们显然还未曾见到过这些植物,而如果能够见到,并成为生活中习见之物,那么这些植物理当会在文本中有所反映才对。反过来,祭辞中提到的这些植物基本上都是今湘西境内十分普遍的物种。
在今贵州省黔东南一带至今依旧盛行的《苗族古歌》中,文本讲述有当地苗族的人祖神话故事,而所涉及到的关键物种——枫香树,正是他们的始祖来源,即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是从枫香树飞出的一只蝴蝶与水沫游方恋爱后,进而产下12枚卵,经鹡宇鸟的孵化后,其中的1枚卵生出了始祖姜央,而其它的卵则分别产出了雷公、蛊毒、老虎、牛、象、龙等其他物种[3]484-485。在这里,具有鲜明地理标识的植物——枫香树,是探索当地苗族古老生息地的一个重要信息,因为我们可以从现代植物学理论知识中,确知枫香树的生长区域和基本信息。枫香树是金缕梅科枫香树亚科枫香树属,分布海拔高度在220到2 000米之间。为落叶乔木,喜欢温暖湿润气候,性喜光。耐干旱瘠贫,但却不耐寒,黄河以北不能够露地越冬,不耐盐碱及干旱,分布于我国秦岭淮河以南一带,多分布于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4]244-245。结合当下的苗族分布格局,今天苗族所生息的区域,正好也是枫香树十分普遍存在和生长的地理空间范围。同时,这些枫香树还往往被赋予了神性,是保寨之树,具有了神的功能,因而往往被加以保护起来。具体到今湘西地区的苗族生息区而言,他们不仅将枫香树认定为具有神性,而且还将其进行了性别区划,即视枫香树为“母亲树”,而“椿树”则相应的被尊称为“父亲树”[5]29。椿树是苦木科臭椿属,中文学名“臭椿”。它是一种喜光,适应性强,不耐水淹的植物,长期积水会导致根部腐烂而死亡。它的分布范围在海拔100到2 000米之间,年降雨量在550到1 200毫米之间生长样态最好,在石灰岩地区生长样态也良好,是石灰岩地区生态恢复的重要树种。我国北部、东部、西南部、东南至台湾省一带有分布[4]407。在湘西苗族聚居区,椿树遍布于房前屋后、耕地,乃至山间林地中,足见椿树在他们的心神层面,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认识①椿树在苗族生息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是超出了一般认识上的“意义”。不仅在湘西苗族生息区,他们赋予了椿树这样的象征认识,我们在黔东南一些传统苗族社区调查过程中,同样感受到了当地苗族对椿树力量和神性的尊崇,而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传统房屋结构中中梁——一个家庭一切生命的中心——的材质选择上——所有房屋的中梁材质都是用椿树做成的,因为“椿芽为王,梓木为匠”(老木匠师傅江绍明语)。从中不难窥见,当地苗族对椿树的认知,已经上升到了另一种高度,而不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意义”。。
在该祭辞文本中,这两种树都有提及,但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一带极为常见的槐树、榆树等树木却没有见诸记载。据此不难推断,槐树和榆树在这篇祭辞成形之际,编纂者显然尚未接触过,因而它们没有进入祭辞文本当中,反而是当地习见的枫香树、椿树等植物进入了文本之中。如果就这一层面去理解,那么今湘西境内的苗族世代生息在这一区域是极为可能的,因为这一带正好是石灰岩地带,正好是椿树等植物易于生长的区域,因而它们进入这个祭辞文本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椿树、枫香树等树种具有这种地理标识功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植物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地理标识功能——葛藤,无论是野生状态下的,还是半野生状态下的,而且当下还处于当地苗族的社会运行中,而在该篇祭辞中也多次提及葛藤,足证历史上的湘西地区,葛藤肯定是当地最为常见,而且极为普遍的植物,更是为当地苗族所熟知和利用的植物。
关于葛藤的历史典籍记载,最典型的莫过于清人严如熤在其所纂《苗防备览》一书的记载了。该书的“卷二”《村寨考上》中,有“边徼之间……所以绝膠葛而杜釁端也……”[6]的记载;而在“第八卷”《风俗考上》中亦有“苗地人众,砍树木以供薪火,亦不能有古木千章。溪旁石豀多小白毛竹丛生,胶葛倍形深险”[6]之记载。在这两处记载中,与本文的研究直接相关者有二:一是描述了当地的石灰岩地貌,二是当地的葛藤。最值得注意之处还在于,作者严如熤(1759—1826年)乃是清末之人,该书成书于清军平定乾嘉苗民起义之后,作者根据自己的实际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而编纂此书。换言之,直到清代晚期,今湘西地区的葛藤依旧十分繁茂,不仅是当地苗民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是他们与清军作战、周旋的庇护所,致使清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才取得了该区域实际的经营权。即令是经历了清代的玉米、水稻等作物引进,人们不可避免要割掉葛藤,将原先耕地中种植的葛藤清除出来种植玉米,甚至是开辟为稻田种植水稻,但依旧还有大片的葛藤留存了下来。当然,由于这些高秆作物的引种,随着它们大面积普遍推广,因而不可避免的引发了当地生态的变迁。可是,即令是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迁,而时至今日,当地却依旧还有十分茂盛,而且面积极为广泛的葛藤,依旧还有乡民在从事葛藤的种植。它们不仅自己食用葛根,而且还将葛根纳入市场流通中,甚至是批量贩卖给加工厂进行加工。如今,湘西地区的葛藤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作为粮食去食用了,而是加工成了各种葛藤粉、葛藤面、葛藤馒头等等以葛藤为基本原料的葛藤产业。据此反推,历史上湘西地区葛藤茂盛之状,乃是一个基本事实。
既然葛藤作为今湘西地区的一种常见植物,那么它们能够进入苗族的宗教祭辞不仅不足为怪,而且顺理成章,符合文化事项产生和运作的逻辑。在这篇祭辞中,当描述鬼师要去将丢失的魂魄寻找回来时,需要通过将葛藤掀开才能去找到丢失的魂魄,即“葛藤扒搁两旁,刨土去找,刨沙去寻。棺被打坏帮着修,墓被挖坏帮着补。把藤重新扒回,将树重新栽上”[1]336-337。这就足以说明,在这篇祭辞定型之时,历史上这一地区早已是葛藤遍布,葛藤早已进入了苗族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而不可能是凭空捏造、想象出来的。
查《中国植物志》可知,葛藤是旋花科银背藤属藤本类植物,适合在丘陵地区的坡地或疏林、灌丛、石缝、砾石,乃至荒坡、废弃耕地中都可以旺盛生长,喜欢温暖湿润气候,分布海拔高度在300到1 500米之间。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中国贵州、广西、湖南和云南东南部等地[4]531。这一植物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地表有茂盛的匍匐茎,而地底下则是富含淀粉的块根,即令是地表部分枯死或冻死,地下块根依旧安然无恙,来年依旧可以继续发芽生长。此外,它还能够与其它乔木共生,因而往往形成浓密的葛藤丛林。这样形成的天然庇护所,当然也就成为乾嘉苗民起义之际,当地苗民用以躲避其间,袭击清军的天然壁垒了。更何况葛藤的块根富含淀粉,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社会,都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食物之一。从中不难窥见,葛藤早已在历史上进入了苗族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通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积淀后才被纳入了祭辞之中。也就是说,从这篇祭辞所记载的葛藤及其生物属性来看,当地居民在历史上所生息的地方肯定葛藤普遍,而且长势十分良好,而时下湘西地区的生态环境概貌,正好与历史上所描述的生态环境特征相吻合,因而也可以说明,今湘西地区是苗族先民居住的地方是极为可能的。
除了上述祭辞中所提到的两种植物外,还有其它的植物,如杉树和楠木,而它们出现的角色是鬼师去寻找魂魄时需要乘坐的船只,即“你们去借楠木船,去借帆布船,木船捆在石头上,帆船捆在树兜上。”[1]353-354“你们拿去上楠木杉木船,去上丝绸帆布船。抬三年大肥猪去,扛三载大胖猪去。你们抬去上楠木杉木船,抗去上丝绸帆布船……抗上楠木杉木船去……你们抬上楠木杉木船去……”[1]359-387大体在借船,乘船去找魂魄,经过七个神潭后找到魂魄,又返回来,再归还所借来的木船这个过程。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中也曾提到过这两种树,而且还直截了当的记载了苗族就是用这两种树木来建造船只的,而且是独木舟,“蛮地多楠。有极大者,刳以为船。”[7]175从中不仅反映了有楠木生长,而且楠木的长势极好。两相比较后发现,在苗族居民生息的地区肯定有大量的杉树和楠木生长,而且生长样态较为良好,方能作为建造船只去使用。
杉树是松科杉树属,品种很多,大抵分布在海拔2 500到4 000米之间,略耐阴冷、耐寒,喜欢空气湿度大的环境。以湖南、贵州、湖北、四川、广西等地生长最多,长势最好。楠木又名楠树、桢楠,樟科楠属和润楠属各树种的统称,有香楠、金丝楠、水楠等种类。喜欢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排水性能好的区域。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四川、湖北一带,海拔区域在1 000到1 500米之间的阴湿山谷地带[4]139-140。明武宗正德十三年三月,永顺土司一次朝贡的楠木就达400多根,“湖广永顺宣慰司使彭世麒等,献大楠木四百七十余根,赐所遣土官把事向晟等,彩币有差 戊辰。”[8]不难想象的是,当时湘西地区楠木盛产之景象,而当时苗族能够利用它们建造独木船,至少它的胸径超过一个成年人的体宽,足见这些楠木长势之大,而优质楠木的生长必然离不开合适的海拔区位和其它生态环境要素的合理匹配,而当下湘西地区苗族分布区也大抵在海拔2 000米上下。以此为据进而还可以断定,远古时代的苗族不可能生息在青藏高原,也不可能生息在西北干旱草原一带,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可能长出楠木和杉木。这与某些学人根据《尚书》中“窜三苗于三危”之记载,去猜测远古时代的苗族曾一度在我国河西走廊一带生息过,尔后才慢慢迁徙到我国南方地区[9]43的思路有较大出入。
总之,从该篇祭辞所记载的植物中,结合现代生态学、植物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体系,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基本上可以认定该篇宗教祭辞中所记载的植物基本上是今湘西地区苗族生息区的习见植物。从祭辞所载植物的生物属性和生长区域出发表明,将今湘西境内的苗族定位为是古代从北方经过战乱迁徙过来的说法,并不十分确切,还需要做更多仔细的考证工作。
二、苗族祭辞所涉动物名称考订
在整个祭祀活动中,祭品无疑不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因而祭品必然是研究宗教祭辞的核心内容之一,更何况每一种祭品所荷载的生命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生物属性和生长区域,因而这些祭品能够进入相关民族的宗教祭祀活动,除了排除那些外来物种之外,剩余的产品显然可以作为复原该民族早期生存环境特征的线索,因为祭品往往代表着对神、祖宗,乃至祖师最高的敬意,因而这些祭品肯定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因为这些被祭祀的对象生前也是与他们一样,享受着这些物品,死后也应当享受同样的物品①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外来工业加工物品,如罐头、汽水、可乐等也进入了祭品范围,但这些物品很容易与传统祭品区分出来。。
祭品不仅包含了各种植物果实的加工品,如米饭、酒、粟等,而且主要还是以肉类加工品为主,如猪肉、牛肉等。由于每一种动物也有自己的生物属性,也有自己的最佳生存环境,因而通过对祭辞中,动物物种的生物属性和生长区域的考订,也可以作为探索民族迁徙过程或民族原生地环境特征的又一线索。此外,祭辞中除了祭品中提到多种动物之外,还在其它环节也提到了多种动物。这些动物与作为祭品使用的动物一样,也具有相似的性质和分析之功用。通过这一内容的考订,结合上文的植物考订,共同去复原该民族的最初起源地。
在这篇宗教祭辞中,提到的动物类祭品有猪、黄牛、水牛等动物[1]199,也提到了老鼠,以及魂魄的寄存物——蜘蛛。因此,只要能够对这些动物生物属性的把握,再结合文献的记载和民族志资料的汇总,我们就可以做到进一步对苗族生息地的复原。也就是说,祭辞中提到的某些动物,也往往具有地理标识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溯源苗族传统的生息地。
阅读整个祭辞文本,出现频率最多的祭品莫过于猪、黄牛、水牛、鸡等动物,也有黄蚁、蛇蚁、蚂蚁、菜花王蛇、构皮蛇、花蛇、斑蛇、鹞、鸡、狗、鱼、野猫、狐狸、蜜蜂、竹鸡、山鹰、驴、马、八哥鸟、猴、猿、穿山甲等。这些动物在今天湘西一带生息的苗族居住区都是习见的动物,特别是文本中提到的黄牛、水牛和穿山甲,乃至猿猴等,都具有明显的地理空间标识意义。
祭辞中表达到,水牛和黄牛也并不是他们自己所产出的,而是需要爬山涉水、历经挑选才能购买得到的。黄牛是从“各卡”的手中购买来,并认定只有他们产出的黄牛才是最好的牛,当然也就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回赠祖宗和鬼师的上等祭品。水牛则是从“各列”的民族中购买而得,并同样认为只有“各列”产出的黄牛才是最好的。通过对整个文本所叙述区域的全面考察后,结合该区域的民族分布格局,及其历史发展脉络,甚至是当地的族际互动关系,祭辞文本中提到的“各列”其实就是指侗族②有学人曾考订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朱辅的《溪蛮丛笑》或《宋史·西南溪洞诸蛮》等宋代典籍中所称的“仡怜”,就是今天所称侗族的前身(可参见:汤宗悟:《考古发现与侗族族源》,《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张民主编:《侗族简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而“仡怜”与“各列”发音又相似,因而“各列”很可能是指今天所称的侗族。,而“各卡”则是指土家族居民③因为土家族自称为“毕兹卡”(彭官章:《土家族族称演变》,《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在发音上具有类似之特征。。
侗族作为古百越体系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生计方式的应对环境为濒水生态系统,为了完成濒水耕作(如水稻种植),因而饲养水牛必然是生计方式中的重要组织部分,而且非常符合生计方式类型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他们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强项。而土家族作为古氐羌系统民族之一,生息于山区地段,长于饲养黄牛,因为黄牛的生性正好适合于山地饲养,长于爬山,体格十分健壮,因而肉质更为鲜美,作为祭品当然也是最为理想的。此外,结合今天的民族志进而还可以发现,在今天的湘西地区,苗族、土家族与侗族都依然是互为近邻。换言之,该篇宗教祭辞中,通过对黄牛和水牛及其饲养民族的空间分布所构成的族群关系,与当下的三个民族的分布格局大抵重合。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该篇祭辞所反映的苗族是自古就生息在今湘西地区的。如果他们曾经真的生活在华北平原一带,那么华北平原习见的动物——绵羊,必然是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牲畜,而且是备受呵护的,那么作为“伙伴”的绵羊为何不见于该篇宗教祭辞之中,作为表达对祖宗,对祖师的尊敬与馈赠之礼物?如此,这显然是一种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
绵羊是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羊亚科。它是一种喜欢干燥,而且能够抗寒冷,但却十分惧怕炎热和潮湿生态环境的动物。即令是在北方干燥的环境下,如果羊圈棚湿热、湿冷或是在低洼处的草地上放牧,都易于感染疾病,患上寄生虫病或是关节炎。湘西地区夏季十分炎热,降雨量大,而且地表湿度、空气湿度都十分大,整个环境表现为十分潮湿,至于低洼处河谷地带,那更是潮湿,因而这样的环境显然不是绵羊最佳的生存环境。因此,这一地区在现代温室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是很难饲养绵羊的。因此,绵羊不是当地传统上的习见动物,直到现在也不是,因而在这篇宗教祭辞中没有出现绵羊作为祭品,也就获得了来自现代动物学知识和理论的支持。
此外,祭辞中还提到了穿山甲。穿山甲是穿山甲科穿山甲属的动物,学名为鳞甲目,生活习性为在山麓地带的草丛中,或者是比较潮湿的丘陵杂灌丛一带。在我国,大多分布在云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贵州、四川、云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一带,因而在苗族的宗教祭辞中出现穿山甲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们的生息区正好是穿山甲的最佳生存环境之一。
等等这些动物还有很多,如猿、猴等,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分析,恕不一一。需要指出之处则在于,只需要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分析,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该篇祭辞中出现的这些动物在今湘西地区都极为常见,而北方,乃至西北、东北,亦或是青藏高原一带常见的动物,却没有在他们的祭辞中有所表现。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认为苗族曾经从华北平原,乃至北方迁徙到湘西地区居住的结论,还有很多的问号需要解决。
三、苗族祭辞所涉山名名称考订
对整篇祭辞做统计后发现,祭辞中提到的地方非常宽泛,如“回到打仲渔神地方,转到打会猎神住处。渔神聚集下峡谷,猎神聚集下山沟,回到坡脚土地爷的地方,转到村边寨祖神的住所……”没有提到一个非常十分确切具体的地名名称,包括山岭、村寨所在位置,或是具体的河流名称,等等都没有出现,而且也没有用苗语标注的山岭名称,仅是出现了几个传说中的神或鬼,亦或是灵魂停留地而已,即令是提到的山,大多数也是泛指。比如,提到的“茶内山坡”、“及囊峡谷”、“及斗山坡”、“及干峡谷”等,都是一些难以考证的不确定的地名。当然,文本中也提到了“乾州”、“吉首”等十分具体的“汉语式”地名。
关于“乾州”一名出现的时间,据《清史稿》载,“(乾州直隶厅)……辰沅永靖道,明为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府沪溪县。康熙三十九年改为乾州。四十七年置厅,治镇溪所城,仍隶辰州府。嘉庆元年升直隶厅。辖苗寨一百一十有五”[10]2204。据此可知,“乾州”一名出现的时间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而至于“吉首”一名出现的时间则更晚。有学人曾考订,“吉首”之名乃是苗语的音译,意为“幸福之地”,因苗族迁徙至崇山地区之后,曾经过着一段无异族干扰的幸福生活,故称此地为“吉首”[11]127。作者进而还指出,吉首旧称“所里”。1951年初,县政府由乾州迁往所里镇,1952年8月1日,湘西州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湘西苗族自治区(州级),治所里镇。1953年2月25日,经上级批准,“所里”沿苗语更名为“吉首”,1982年改为吉首市[12]285。也就是说,“吉首”一名正式出现的时间乃是建国后的1953年。
该宗教祭辞作为苗族传统的传世文本,“乾州”与“吉首”两个汉语式地名出现的时间如此之晚,因而可以断定肯定是后世祭师在整理文本时所为,在这个祭辞文本出现的早期应当不会有这两个名称。
相比之下,汉族的早期典籍反而对湘西地区的山河,做出过极为明细的定位,特别是这一地区进入王朝经管之后,这些地区的地名在汉语典籍中就逐步露头了,而且传至今世。比如,据《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13]159此后,随着时代的演替,辖境内的山系才被逐步赋予了“武陵山”①查《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得知,早期历史典籍中出现的“武陵山”实际地望却并非今日所称的“武陵山。”详情参考: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8页。这一名称,并在民间流传,现在还进入官方文本。关于“崇山”的出现亦是如此,此前就有学人曾依据在湘黔川毗邻地带有“崇山”一名,而认定早期有部分苗族曾在战国时期迁徙到这一地带[14]58,但在这篇祭辞中却没有提到“崇山”这一名称!
据《明实录》载,“(洪武十一年十二月)置崇山卫于湖广孟洞之地”[15],但该卫存在的时间却并不长。据(乾隆)《乾隆厅志》载,“(洪武)二十三年,因饷运艰难,复行裁革,置崇山千户所。”[16]从洪武十一年设置,到洪武二十三年废止,崇山卫存在的时间仅为十三年之久。同样的,崇山千户所存在的时间亦不长。据(同治)《永绥直隶厅志》载,“(洪武)三十年,革崇山千户所,置镇溪军民千户所”[17],即崇山千户所存在的时间跨度为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三十年之间。然而,以行政建制出现的“崇山卫”之名废除了,但崇山卫设置的地点却被称为了“吉伟”,并流传了下来,其含义是“崇山卫所在的城池”。以此为据不难推测,该篇宗教祭辞骨架定型的时代肯定比明代还要早,以至于后期汉文典籍中习见的“武陵山”“腊尔山”“崇山”等地名,在这篇祭辞中反而找不到踪影,并进而可以证明这篇宗教祭辞骨架定型的时代,苗族及其生息区还没有被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因而在他们所编纂的这个祭辞文本中所反映的宗教观,理所当然的也没有加入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具体山名,而且是以汉语表述下的具体山名或地名。
不仅对山名是如此,该篇祭辞对河流的命名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该篇宗教祭辞中,当提及为了寻找到丢失的魂魄时,鬼师巴岱雄要邀请他的祖师经历七个湖泊的艰难寻找后,最终才在第七个湖泊当中找到了丢失的魂魄。追寻的行动工具便是他们借来的楠木船、杉木船和帆布船等。据此可以做出判断的是,连接这七个湖泊的必然是水路,从第一个湖泊连续乘船下去,便可以最后抵达第七个湖泊。当在第七个湖泊找到丢失的魂魄后,又乘船沿原路溯回到村寨内。返回后,还要将借来的船只和其它武器归还给山脚的人家,然后再从山路回到家里。在整个寻找丢失魂魄的过程中,不管是河流,还是所到的湖泊,都没有出现具体的地名,而仅是以“第一”“第二”“第三”……“第七”,这样的顺序数标号。这同样表明这篇宗教祭辞形成的时代,苗族内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也没有领土内具体山林、河流的命名方式,因为假若是有了明确的政权存在,那么这些山川形胜必然会成为“疆土”,而且还被辅以相应执政民族的文化烙印,以便达到对领土的有效经营和控制。可是,当我们具体考察今湘西境内的苗族生息区后却不难发现,祭辞中提到的这条河流很可能是指今天所称的酉水。
当代的民族志资料表明,今天湘西酉水上游地区依旧是苗族的主要生息地,而酉水在它的全部流程中多次经过山间盆地,而这样的盆地,在古代很可能会形成大小不同的湖泊,尤其是在水稻等外来作物没有推广到这一地区以前,因为水稻推广进来之后,这些山间峡谷的盆地或是小湖泊,则往往被人为建构成稻田去加以使用。亦或是随着玉米的引进之后,将湖泊水排干,建构旱地,以便耕种玉米。如此一来,这些湖泊随着外来物种的引入,为了迎合外来物种的生长习性而不得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的田野调查很难以找到规模连片的酉水流域湖泊了,也很难以恢复历史的原貌,因为这一带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湖泊大多是溶蚀湖,而地底下则是纵横交错的伏流和暗河。一旦这些湖泊水被排干,打通了湖泊与地下伏流和暗河之间的通道,那么湖水将会迅速下泄,很难以自然恢复,重新恢复湖泊样态,除非是找到这些通道,进行堵塞,但经过不断的开发和利用后,找到这样的通道也是需要不小气力的。由此可见,这篇宗教祭辞基本骨架定型时代,远古的苗族早就生息在酉水流域了,而且这些苗族显然不是生息在濒水地带,而是和今天的苗族一样,是生息在崇山峻岭之中,要到达可以乘船的濒水地带要走很远的山路,要不然就不会提到他们去购买牛时,还得翻山越岭的去,也不会出现“从坡脚借的刚梭镖,回坡脚还钢梭镖”的记载了。对此,我们只能认定,湘西地区的苗族,早期应当是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是当地一个古老的民族。
四、余论
宗教祭辞中包含着众多的有关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除了上文所讨论的植物、动物,乃至地名外,也还提到了物产,如蜂蜡、苦瓜;也提到了工艺,如化铁、打铁、舂稻、舂粟等;也还提到了它们的生计方式,如打猎,而且还提到了打猎的必配伙伴——狗;也提到了他们的传统神,如打仲渔神、打会猎神、棉神、粟神,等等众多历史文化信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历史文化信息免不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因为族际互动始终存在,而当纳入王朝之后,国家意志也会随之而介入。如此一来,外来文化的介入始终存在,并通过他们的消化和吸收而逐步纳入到本民族的文化系统之中,并得以延续。对于这些外来的文化事项,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对该民族所处生态环境的复原和考订,并加以族际互动的旁证,甚至国家意志渗透的提取,秉着整体观的视角,便可以做到逐一解析出来。为此,对宗教祭辞文本所留存下来的文化事项进行逐一考订,可以为我们去了解,乃至复原该民族的最初生存环境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特别是最具有地理标识意义的植物或动物,它们能够进入该民族的宗教祭辞当中,那么这些植物和动物必然是他们生存环境中十分常见的,而且很早就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被寄予了不同的符合本民族文化逻辑的“意义”。当这些物品进入他们的宗教祭辞文本后,便会世代留存下来,即便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外来物种的进入,但是某些原生的物种却依旧会在他们的祭辞当中留存下来。这就为我们今天去追述该民族的原生环境提供重要的线索和机会。更何况由于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生存空间,而通过这些物种的分布范围就可以逐步框定该民族的大体生息范围。再结合族际活动,通过对其他民族的相关历史信息进行梳理。如此,通过三方的综合佐证,我们便能够对这些宗教祭辞中所反映的该民族的原生生息区,可以获得一个复原的线索。本文仅是一种尝试,不当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石启贵.锥牛卷(上)[M].马树兰,石建中,整理译注.王明珂,协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伍新福.论苗族历史上的四次大迁徙[J].民族研究,1990(6):103.
[3]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4]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黎明明.苗族古歌的枫树原型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9.
[6](清)严如熤著.苗防备览[M].道光版,绍义堂藏版.
[7](宋)朱辅.溪蛮丛笑研究[M].符太浩,编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8]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十.
[9]江应樑.西南边疆民族研究[M].珠海:珠海大学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
[10]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龙和铭.吉首苗族语地名浅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12]湖南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制.湖南省地图集(内部发行)[M].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00.
[1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4]何光岳.三危、三苗的来源、迁徙和融合[J].湖南民族研究:试刊,1983.
[15]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一.
[16](乾隆)《乾隆厅志》.
[17](同治)《永绥直隶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