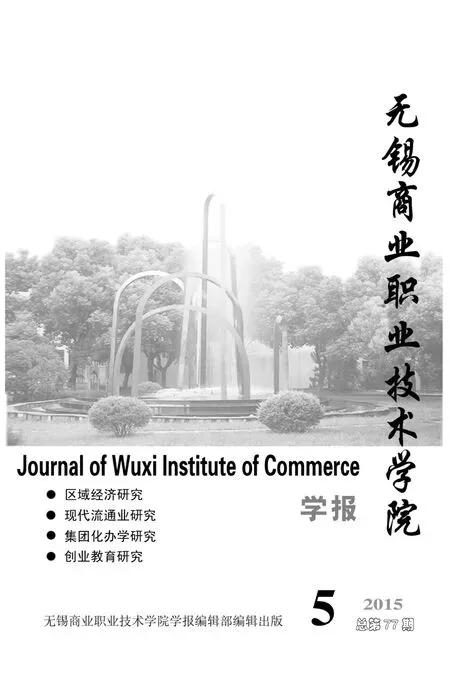自我追求的悖论
——小说《不朽》的自我主题解析
史永霞,舒梦萍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文史哲研究】
自我追求的悖论
——小说《不朽》的自我主题解析
史永霞,舒梦萍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不朽》描写了各类人物对“不朽自我”的追逐或回避,探究了“不朽”的真谛。文章以自我主题为研究线索,分析《不朽》中人物追求“不朽自我”的不同方式以及自我存在的不同状态,揭示典型人物自我追求的悖论,并通过对小说中描写的现代社会异化状态的分析,指出在现代社会个体始终难以摆脱自我追求的悖论。
昆德拉;《不朽》;自我;悖论
米兰·昆德拉是捷克著名小说家,后移居法国,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不朽》是昆德拉思考与探索人的存在问题的一部小说。现实社会中的人一般把追求“不朽”作为超越死亡与确立自我存在价值的基本方式,在昆德拉看来,现代人所追求的“不朽”多通过创造“不朽的自我形象”来实现,所谓“不朽”意味着融入世俗历史,一再被人记起与翻看。但是,那些刻意追求不朽自我,企图留在他人记忆中的行为往往是可笑的,追求“不朽自我”的代价往往是失去自我、本性和自由。在小说《不朽》中昆德拉就刻画了一系列因追求不朽而迷失自我的人物。不过,昆德拉也通过女主人公阿涅丝的选择展示了面对不朽的另一种姿态,揭示了自我存在的真正意义和自我追求的难解悖论。
一、追求不朽,迷失自我
不朽,在昆德拉看来与灵魂的不朽毫无关系,“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不朽,是指死后仍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那些人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 (摩拉维亚村长梦想的不朽);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心中留下回忆。”[1]56不管是“大的不朽”还是“小的不朽”,都是企图进入他人的世界,存活在他人的记忆中。在小说《不朽》中,一些人物致力于追求不朽的自我,他们把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自我价值的定位与他人的注视相关联,然而,正是在这个关联过程中体现了自我追求的悖论。
(一)洛拉:在爱情中追求“小的不朽”
主人公阿涅丝的妹妹洛拉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爱情而斗争,但实质上,她更多的是为了不朽而斗争,她是“小的不朽”的追求者,希望在认识她的人心中留下记忆。在洛拉看来,不朽就是活在姐姐一家人的记忆中。为实现这一目标,她以爱情不如意、婚姻不幸福的形象出现在姐姐一家人面前,以此博取他们的同情和怜惜,从而进入他们的生活,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还是小孩子时,洛拉就对姐姐的爱情充满好奇,“小洛拉躲在一丛灌木后面等待她姐姐归来,她想偷看他们接吻,随后目送阿涅丝登上台阶走向屋门。她等待着阿涅丝回头挥舞手臂的时刻。对这个小姑娘来说,这个举动不可思议地包含着她对还一无所知的爱情的模糊概念,并永远和她温柔迷人的姐姐的形象连接在一起。”[1]103后来,洛拉长大了,她爱上姐姐的丈夫保罗,为此,她感到幸福又惆怅,因为“她惟一能爱的男人却同时是惟一她不能爱的男人。”[1]104之后她结婚、流产、离婚,换了几个情夫。在洛拉心里,相比于阿涅丝,她是不幸的,不断变换的情人不仅不是她幸福的证明,反而是不幸的标志。因为阿涅丝拥有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她却总在为一段段逝去的爱情伤心。离婚后,洛拉一有空便到阿涅丝家里去,她照料外甥女布丽吉特就像照顾亲生女儿一样。洛拉就这样在感情受伤的幌子下,通过一件件生活小事慢慢侵入阿涅丝的生活和记忆,直到她再次遇到爱情。
洛拉爱上了保罗年轻的朋友贝尔纳,一个比她年轻十岁的男人。但如昆德拉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违反常规,违反爱情的禁忌,心醉神迷地进入被禁止的王国。可是我们又如此缺乏胆量……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情妇,找一个年纪比较轻的情夫,这是人们可能推荐的最容易的,而且也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违反常规的方法。洛拉第一次有了一个比她年轻的情夫,贝尔纳第一次有了一个比他年龄大的情妇,他们两人都是第一次生活在这种很刺激的罪孽之中。”[1]147与其说洛拉爱贝尔纳,不如说她爱禁忌爱情带给她的刺激感,正因如此,她从不试图了解贝尔纳,当保罗问她是否想多知道贝尔纳家族的事情时,洛拉断然拒绝。两年后的一天,贝尔纳莫名其妙地被一个陌生人授予蠢驴证书,他深受打击,洛拉不仅没有安慰他,还将贝尔纳的寡言少语看作他不再爱她的证明而闹得不可开交。于是贝尔纳快速地从他们的爱情中撤退。分手后,洛拉表现得十分悲伤,甚至想到了自杀。其实,洛拉并非深爱贝尔纳,她爱的只是知道自己活在贝尔纳心里的那种感觉,“‘我不放开你,’她心里说,‘我不让自己被排除掉,我将为了保留你而斗争。’”[1]172正如阿涅丝所言,洛拉“并不想‘离开’。她想到自杀仅仅是因为这对她说来是一种‘留下来’的方式。留下来跟他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整个儿倒在我们的生活里,把我们压垮。”[1]203爱情是洛拉让自己存活在她认识的人的记忆里的手段,是她通往不朽的工具。当她获得贝尔纳的爱情,她可以活在情人的记忆里;当她失去了爱情,她又能以一个悲惨的形象活在姐姐一家人的记忆里。洛拉把爱情变成一种突出自我的姿势,一种外向虚假的表演。她的“自我”与他人息息相关,她所追求的“自我”实质上是被他人注视所限定的“自我”。
(二)贝蒂娜:依傍名人营造自我“大的不朽”
贝蒂娜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小说中她被塑造为一个终身为不朽奋斗的女人。贝蒂娜凭借与一位不朽名人的爱情关系进入公众的视线。第一次拜访歌德,贝蒂娜就以不想坐沙发为由坐到了歌德的膝头,听到歌德称她为 “可爱的孩子”,她就以孩子的形象介入歌德的生活,同歌德开始了一段伟大的 “忘年恋”。贝蒂娜对歌德说:“我有永远爱你的坚强意志。”[7]71昆德拉特别提示,这里比“爱”更加重要的是“永远”和“意志”两个词。可见,贝蒂娜对歌德的爱只是一种意念,她爱的不是歌德,而是歌德所代表的“不朽”。她怀着非同一般的野心和激情,与不朽的歌德紧紧相依,期望将自己的形象与歌德的形象联结在一起,一同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在贝蒂娜的眼中,爱情的真实已不再重要,爱情不过是她追求“大的不朽”的手段,通过爱情,她能走近歌德,进而融入历史,成就永恒的生命。在她看来,不朽也是可以营造的,只要依傍那些名人,就能获得不朽,于是她爱上了歌德,崇拜贝多芬,拯救波兰的革命领导人……贝蒂娜对名人有强烈的好感,因为她知道每一个名人都承载了她不朽的希望,是她走向不朽的垫脚石。昆德拉指出,“促使她为提洛尔的山民辩护的,并不是山民,而是对提洛尔山民的斗争热烈支持的贝蒂娜的‘具有吸引力的形象’。促使她爱歌德的,不是歌德,而是爱上年老诗人的孩子气的贝蒂娜的‘迷人形象’。”[1]41她希望借助这些不朽的人物来超越自我存在,让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历史永恒的记忆。实际上,贝蒂娜对历史和永恒的追求不仅未使她融入“永恒的历史”,成就所期待的“不朽自我”,反使她丧失了自我的真实。在她追求“不朽自我”的过程中,美好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谎言,对他人的帮助也变成了有目的、有计划的表演。在贝蒂娜身上,真实情感被物化和扭曲,这也从本质上消解了其自我的本真。
(三)歌德:压抑自我,走向不朽
歌德是德国著名文学家,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在昆德拉看来,歌德的伟大文学成就使他注定不朽,他无须像贝蒂娜那样靠依傍名人来成就自我的不朽,“要说歌德想到不朽,那是他所处的地位所允许的。”[1]74在小说中,昆德拉将歌德这一人物归入为追求不朽而压抑自我的类型。歌德五十岁时身体发福,有了双下巴,为了以最佳的形象走向不朽,他开始减肥,很快又变得身材苗条;为了不朽,他可以忍受像“难以忍受的牛虻”一样的贝蒂娜;为了迎接不朽,他放下正在创作的自视为巅峰作品的手稿,应拿破仑的邀请赴会,然而这是一次荒唐无聊的会面…… 。事实上,对歌德而言,不朽是一把双刃剑。韩水仙在《米兰·昆德拉:逃离不朽》中指出,“对于歌德这个注定不朽的伟大人物来说,不朽一方面意味着走向光荣的殿堂,另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生之约束。歌德意识到他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过,他要为永留后世的他的不朽形象负责,这种责任心使他失去了本性。他知道各种传记、逸闻、回忆录将会把他的所有言行变为等待后世拷问的文字。他害怕做出荒谬的事情,背离那种他视作为美的温情脉脉的中庸之道。他感到了贝蒂娜的企图和威胁,却不惜任何代价跟她和平相处。他甚至一直留意着不让自己穿一件弄皱了的衬衣走向不朽。只有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穿越‘从生命此岸通往死亡彼岸的神秘之桥’的时刻,他才意识到‘不朽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幻想,一个空洞的字眼 ’。”[2]39-40
歌德注定不朽,但他知道不朽也分种类,有像莎士比亚那样依靠自己伟大的作品走向不朽,也可能是像第谷·布拉赫这位丹麦天文学家一样,因在晚宴上羞于上厕所憋尿而死,最终成为可笑的不朽者。他所追求的是伟大的不朽,因此他就要时时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避免成为可笑的形象。但经过修饰的自我形象已不再是真实的自我形象,而是他人所希望的“不朽者”应呈现的形象。在“不朽”的荣光下,自我形象变成了迎合大众喜好的模式化形象,变得模糊而虚假。
小说中的洛拉、贝蒂娜和歌德都是对“不朽”的顽强追逐者,他们都希望在他人的记忆里留下自己的身影。然而,他人的肯定和注视一旦成为个体确定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个体必将随着他人审视的目光而不断改变自己,在寻求他人关注的过程中,个体关注的是自我的形象和行为能被他人看到并记住,却往往忽视了自我的真实。
二、拒绝不朽,捍卫自我
《不朽》中的主人公阿涅丝是一个渴望追求自我、思想奇特的女人。她渴望宁静自由的生活,但现实的世界却充满喧嚣和虚假。她拒绝“被看”,认为他人的目光对她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那些匕首般的目光带给她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伤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无法躲避无处不在的摄影机和他人探究的目光。于是阿涅丝明白了,“个人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权了,他已经属于别人所有了。”[1]37阿涅丝想逃离家庭,逃离他人的视线,甚至逃离这个世界。她每年都要去瑞士两三次,不是因为那里有她的情人,而是因为在那里她可以远离世俗尘嚣,找到心灵的归宿和自我的安宁。就像弗朗索瓦·里卡尔描述阿涅丝时所说:“她暂时离开了,坠入田园牧歌之外,并且在这不在场中找到了真正的惟一的安宁与和谐。”[3]405
与妹妹洛拉增加自我属性、塑造自我不同,阿涅丝试图减去她身上所有表面的和外来的东西,以接近她的本质。她不使用手势,不洗冷水澡,不戴墨镜,不听摇滚乐……她坚定而勇敢地与现实世界分道扬镳。在阿涅丝看来,“自我”是宁静而孤独的,她拒绝现代性喧嚣,因为那是以不朽为潜在欲望而造成的。在阿涅丝看来,大众的关注不仅不能让个体获得“不朽自我”,反而会让个体付出沉重代价。“不朽自我”是人们在媚俗世界无限膨胀的欲望的代名词,对它的追逐只会让人们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而这恰恰是阿涅丝所厌恶的。她拒绝追求媚俗的不朽,渴望回到大自然,回归生命的本真。只有在那一刻,躺在小溪旁的草丛中,感到溪流淌过她的身体,带走所有的痛苦和污秽,阿涅丝才感受到真实的自我存在。
在阿涅丝看来,“爱情或者修道院:这是人类拒绝上天的电子计算机,逃避它的两个方法。”[1]269在这两者中,阿涅丝选择了爱情。但事实上,阿涅丝和保罗的爱情只建立在一种爱情的意愿之上,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危险。他们始终没有达到爱情上的统一,不管是阿涅丝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还是保罗绝对现代化的追求,他们对彼此的生存理念都不认同,他们不过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已。阿涅丝曾经以为自己爱着丈夫,在瑞士度假时,她很想念保罗,把他们共同喜欢的兰波诗集随身携带,以纪念他们骑着摩托车跑遍法国的日子。但是随着阿涅丝对“自我”的不断剖析,他们的爱情逐渐变得苍白,她把代表爱情的诗集扔在了手提箱里,又把手提箱扔在了车后座。当外星客人问阿涅丝来生还想不想和保罗见面时,阿涅丝听从了内心深处的呼唤,断绝了见面的念头。阿涅丝想逃离她的爱人,独自去过自由的生活,但对保罗和女儿的牵挂成了她和尘世相连的细线,于是她在自由与爱情之间游离,陷入极度的矛盾中。爱情曾是阿涅丝坚定的选择,但当爱情成为奔向自由道路的绊脚石,变成追求真实自我的负担时,她对爱情的幻想也无情地破灭。这也让阿涅丝认识到,当人们的爱情不再出自本心,不再代表他们的真实情感,而变成一种对爱情的意愿时,“自我”的真实会由此丧失,爱情也必须被放弃。临死之际,阿涅丝和正在奔向她床边的保罗比赛着,终于,在保罗到达十五分钟前她胜利地死去,彻底地将保罗隔离在了她的生命之外,也彻底拒绝了尘世的不朽。
三、难以摆脱的自我追求悖论
在现代大众传媒社会里,一切都是可以包装的。在《不朽》中,就有专门从事包装事业的人——意象学家。他们为政治家、名人、明星代言,帮助他们塑造不朽的形象;他们通过广告、宣传、测验等制作出超越现实的意象。事实上,这些创造出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自我,只是意象学家的想象,是现代人为了迎合意象学家的标准刻意创造出来的形象。“我们的‘我’是一种普通的、抓不住的、难以描绘的、含糊不清的表象,而惟一的几乎不再容易抓住和描绘的真实,就是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形象。”[1]145在小说中,不管是小人物,还是名人、政治家,为了一个不朽的形象,都需要时时小心。正因为人们对不朽的追求依靠他人,因此自我形象也非自己可以控制,一旦个体发现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不一致,自我存在的意义也面临崩溃危险。就像保罗被大褐熊说成是 “自己的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时意识到的,“别人眼中的他和他自己眼中的他是不一样的,和他以为的别人眼中的他也是不一样的 。”[1]141而贝尔纳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他人评价为“十足的蠢驴”。这也让他们明白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和在哪件事上惹恼了别人,在哪件事上讨了他们的喜欢,在哪件事上使他们觉得我们可笑。我们的形象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神秘莫测的。”[1]142这时,“自我形象”实际上成了一个“他我形象”。
个体一旦将自我价值定位在他人的关注,那么如何吸引他人视线,便成为了最紧要的问题,突现“我”的独特性变得十分必要。因为人们很容易审美疲劳,相同的东西无法引起人们关注,更难以在别人的记忆里留下痕迹。于是洛拉刻意模仿姐姐阿涅丝的手势,带上显示悲伤的墨镜,喂养暹罗雌猫,高谈她的爱情观,不断在她的“我”上添加新的属性,并竭尽所能来使这种属性被周围的人承认和喜爱,以使她的“我”更为显眼。
个体要追求“独特”,就需要他人认同自我的特性,然而,个体要借助他人目光获得个体的价值,又将面对他人对自我隐私空间的侵犯。面对如此情况,个体究竟应如何处理“自我特性”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只要个体将自我存在的价值依附于他人,并通过他人的价值评判来实现,矛盾将一直存在。为创造与众不同的“我”,人们须极力增加自己的属性,而为获得大众认同,人们又必须宣传这种属性,号召大多数人来模仿,于是这种特性很快又成为一种共性。这也说明,完全以他人的目光来评判的“自我”,并不能显示最真实的自我价值,也不能通达大众注视下的不朽,因为无论是以他人的审美标准来塑造的 “自我”,还是为了迎合大众目光改变的“自我”,个体呈现的形象都不是最真实的自我形象,对他人注视下的不朽的追逐,只会造成自我真实的消解。
死亡是生命无法逃脱的劫难,面对脆弱的生命和短暂的人生,人们一直试图找到对抗的方法,不朽就是一种对抗方式,而如何追求不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创造一个不朽的自我形象。对于昆德拉笔下的人物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后不能达到自我的不朽。不管是注定不朽的人还是默默无闻的人,不朽都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为此,贝蒂娜以爱情的名义将自己与正在走向死亡却也是走向不朽的歌德紧紧绑在一起,洛拉也用爱情和悲伤让自己永远活在姐姐一家人的记忆中,歌德为了不朽,努力塑造着不朽的自我形象。
然而,不朽者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到底是怎样不朽的形象呢?当死后的海明威和歌德相遇,不朽的可笑也随之呈现。“您知道,约翰,”海明威说,“我也逃不过他们无穷尽的指责。他们不是看我的书,而是写关于我的书。比如说,我不爱我的前后几任妻子;我对我的儿子关心不够;我对某个批评暴跳如雷;我不够真诚;我目中无人;我是个强壮汉子;我自吹在战争中受伤二百三十处,实际上只有二百零六处;我有手淫的恶癖;我对母亲蛮横无理。”“这就是不朽,有什么办法呢,”歌德说,“不朽是一种永恒的诉讼。”[1]91
事实上,那些不朽的名人生前无法想象到,死后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朽的荣光还是无尽的批判和耻笑?在贝多芬死后,人们批评他的音乐,贝多芬的光荣不是建立在音乐成就之上,而是有赖于那个渲染他桀骜性格的传说;人们记住海明威也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为海明威传记中描写的种种怪癖、恶习和混乱的私生活;人们也很少去阅读歌德的《浮士德》《诗与真》,却更关心他的各种逸闻趣事,特别是他和贝蒂娜那段惊人的爱情……当死后的歌德和海明威发现原来不朽不是对他们的作品的致敬,而是对他们隐私的无情窥探,生前全力以赴营造的不朽的自我形象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成为一种讽刺。
人们曾企图通过追求不朽自我来超越死亡,甚至为此付出失去自我、本性、自由的代价,但真实的不朽却如此可笑,昆德拉在此以两个已去世的不朽人物的对话,向人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不朽,极具讽刺意味地揭示了不朽的可笑性及追求不朽自我的荒谬性,也对追求不朽自我的种种行为的意义发出了终极拷问。
在人类的生存境况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有着无数可能,但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如何让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可能中得到最大延伸,探索自我生存的价值?这是个体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昆德拉小说《不朽》就是对这种生存困境的思考与探析。无论是洛拉、贝蒂娜、歌德等人追求不朽、迷失自我,还是阿涅丝拒绝不朽、捍卫自我,所面对的都是自我追求的悖论,而如何解决这一悖论,昆德拉并未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他只是通过他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不同的线索,引导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展开独立的思考和探索,让人们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有智慧和内涵的人生。
[1]米兰·昆德拉.不朽[M].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韩水仙.米兰·昆德拉:逃离不朽[J].书屋,2007(1):39-40.
[3]弗朗索瓦·里卡尔.阿涅丝的必死[M]//米兰·昆德拉.不朽.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05.
(编辑:张雪梅)
The Paradox of Immortal-Self Seeking:An Analysis of the Self Theme in Immotality
SHI Yong-xia,SHU Meng-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Milan Kundera’s novel Immortality is not only a good description of various characters’pursuits for and avoidance of“immortal self”but also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true meaning of immortality.Following the theme of self,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t ways of pursuing immortal self and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selfexistence in Immortality and exposes the paradox of typical characters’self-seeking.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lienation of the modern society as described in the novel,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be free from the paradox of self-seeking in the modern society.
Kundera;Immortality;self;paradox
I 106.4
A
1671-4806(2015)05-0101-05
2015-06-19
史永霞(1975— ),女,湖南娄底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日本文学;舒梦萍(1991— ),女,湖北孝感人,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