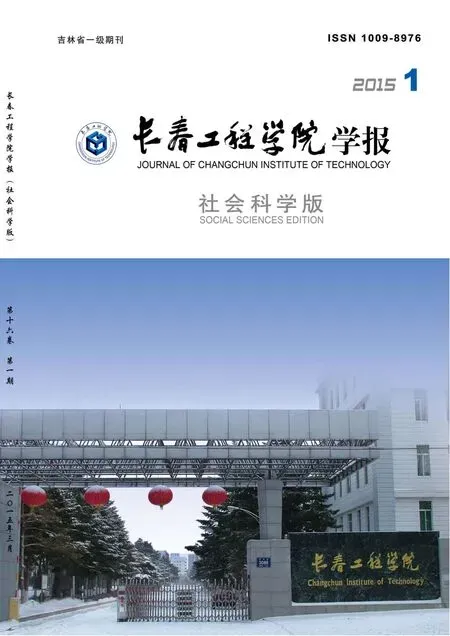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苏碧莲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末尾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的指认是我们理解马克思这一重要文本的基础。由这一经典指认出发,国内外理论界都对马克思这十一条箴言式的、论断式的短文倾注了巨大的关心。
一
在研读文献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学者们将最多的笔墨倾注在对《提纲》第一条的研究上。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而《提纲》的第一条又对于理解整个《提纲》具有重要意义,是《提纲》中的总纲。然而,人们对这一条的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由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不同理解。
奥伊则尔曼[2]认为《提纲》的第一条就已经表明,在完成《神圣家族》以后经过一段短时期,马克思在制定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吴仁平[3]这样理解这一条:第一,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直观性”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第二,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片面性以及批判费尔巴哈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确立了科学实践观。第三,《提纲》第一条最杰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条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考察自然、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张涛[4]认为《提纲》第一条标志着马克思已经打开了新世观的视域,并指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两个始源性概念便是感性活动与实践。安启念[5]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既批判了不从人、人的实践活动和主体方面出发理解世界的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离开唯物主义立场抽象弘扬人的能动性的唯心主义,强调不能忽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赵兴良[6]针对理论界流行的把《提纲》第一条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见解,提出对《提纲》第一条的基本观点不能只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理解,而要把它首先看作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革命变革。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观点,才能正确理解《提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邹季荣[7]将《提纲》第一条视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一个特点是以批评旧唯物论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一共批评了两种唯物论。一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其中也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一是单独批评费尔巴哈而没有论及其他唯物论。这一条在结构上就分为上述的两部分,但在思想内容上这两部分又是完整统一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注意到随着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西方学者重新回到《提纲》,并对《提纲》的第一条做出了新的阐释。研究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关注了《提纲》第一条的思想,并理解马克思在其中所表达的意识的对象问题,提出要把意识的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还认识了新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理解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缺点,这是理解视野的根本转变和理解史上的进步。然而,由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反对区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思维方式,还把意识活动看作实践或是实践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提纲》中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思想[8]。张一兵批判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错误理解,指出这种变革常常被人们狭义地解释为是马克思对两种哲学话语的改造和嫁接,剖离了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上消解掉机械性的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得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来。他以胡克和莱文的观点为例,前者指认《提纲》第一条的意义在于“给唯心主义者在其对意识的分析中所作出的天才发现,提供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9]。后者则说“马克思把德国的唯心主义对活动的强调与洛克——边沁对社会环境的强调混合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式的唯物论的独特性”[10]224。
《提纲》第一条在理解中往往被视作《提纲》的总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在解释《提纲》时也往往倾向于突出这一条,并从此延伸出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意义。因此,对这一条的深刻研读必不可少。实践观点作为贯穿《提纲》的核心,在理解这一条的过程中也不可绕过,这会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误读。这种将实用主义者的头衔硬加在马克思头上的做法在许多西方学者处都可以见到。他们广泛地利用了《提纲》第一条关于认识的对象直接或间接地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对象,并且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被认识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跟实用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梅耶尔企图证明马克思“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知识观,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思想的真理性只有通过效用来检验”。斯泰恩则更为露骨地将马克思误认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并指出马克思正是在《提纲》中,说明了实用主义的原则[10]406-407。为了摆脱实用主义的迷障,我们可以先回顾马克思所批判的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是如何“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费尔巴哈写道,“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而使实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那他就是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功用主义、效用,乃是犹太教之最高原则”[11]。正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贬低“犹太人的表现形式”的批判,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咬住他的表述形式和术语,而不管提纲的实际内容。
目前研究《提纲》的论文出现了这种趋势,即注重《提纲》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启示、指导意义。这种关注对深化《提纲》的研究有很大好处,但是有些研究试图发掘《提纲》对广告艺术设计、装修、地理学等领域的启发,这是否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观实用主义化的倾向呢,值得我们思考。
二
李淑梅[12]高度评价了第二条,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将其当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意思来理解的。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狭窄。作者认为,马克思这段话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对整个认识论发展史的一个总结,是对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缺陷的揭示,是从实践这一新的视角对“认识如何可能”这一近代认识论的重大理论课题作出的科学解答,是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吴刚[13]肯定李文中对第二条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断定,又补充认为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历史观方面。作者认为第二条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改变人们的历史观。盛卫国[14]也认为只有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才可以使其与整个提纲的主题和内容相吻合。对哲学问题的实践解答不是小写的真理——对某一问题、方面的科学认知,而是大写的真理——历史的真理,是人类历史真理的真正呈现。马克思正是在对人做出受动与超越的二重性分析的基础上理解实践的。体现和贯穿人类自身的二重性矛盾的实践在其本性上内蕴着历史理性与历史价值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邹季荣[15]则不承认这一条的认识论意义,他肯定第二条没有论及知识,整条论述的都是思维。其中的“思维的真理性”、“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离开实践的思维”,讲的都是思维。因此,不能用认识范畴代替这里的思维范畴。从严格概念的意义看,思维与认识有许多重大区别,不能混同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理解为认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理解这一条必须从辨别思维与认识的区别开始。潘中伟认为无论是从论述的理论背景还是结合相关文本的论证来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所谈的思维的真理性针对的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论及思维与实践关系时的目的不在于阐述对经验意义上的认识成果的检验,而在于探讨如何证实理念的可行性与现实性。忽视马克思所谈思维与实践关系中的形而上学内容,在理论和具体实践方面都会造成诸多消极影响。
三
对《提纲》第三条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学意义上对人与环境、教育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刘丽琴[16]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条中,从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出发,提出实践是人和环境改变的基础,指出社会实践在人的发展和教育当中的重要作用,有力地批利了环境决定论,从而正确论证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为以往我们对这一条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孤立的和表面的层面上。孤立的理解是指没有把这一条和第一条联系起来,表面的理解是指没有从人与环境、教育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展示了什么样的唯物主义。作者认为必须把第三条和第一条联系起来理解,才能深入认识这一问题展示了什么样的唯物主义。提纲第一条阐述的是必须正确发展能动方面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人与环境、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展示出来的也是必须正确发展能动方面的唯物主义[17]。黄明娣[18]认为人与环境(也即主体与客体)是一种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辩证的统一或一致。它既是一种主体人对环境客体的改造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反过来影响主体,是主体的“自我改造”过程。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造”在实践过程中互为条件,同步进行,不断拓展加深。这就是马克思在《提纲》中,从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出发,批判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环境决定论”,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此外,对这一条翻译的研究也日益兴起。问题主要集中在本条最后一句的译法上。朱光潜将这句话译作“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或自我改造之间的一致,只有把这两种改变都看作革命的实践,才可以认识和合理地理解”[19]。孙熙国将其译为“环境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或者,“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鲁克俭将其译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四
第四条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仅仅指出宗教的基础是世俗社会还不足以消灭宗教,要消灭宗教必须使其世俗基础,即社会革命化。第五条与第一条内容基本一致,讲费尔巴哈不从实践出发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第四、七两条批评他不懂得只有通过改造旧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宗教;第九、十两条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背后的社会立场——不是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是立足于市民社会,因而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和单个人的直观。
第四至第十条通常被放在一起考察,很少出现对其中某一条的独立研究,如王东、郭丽兰[21]就将这几条看作对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论述。这几条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毁灭性批判”[10]216。科尔纽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摒弃费尔巴哈的哲学、他的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及他的人道主义,最重要的理由是,作为迷恋于保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费尔巴哈不可能接受一种主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尽管费尔巴哈的理论代表了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的缘故,他只能在一种既非辩证的、也非历史的、而且必然要使他用乌托邦式的和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去处理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面前,止步不前。把马克思的思想同费尔巴哈的思想割裂的这种彻底的对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在一些零星分散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一般原理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批判[22]156-158。在这个以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中的实践这个起着革命作用的概念为基础的《提纲》中,马克思表现出已决定性地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哲学[22]165。张一兵认为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实践观点,针对人的社团理论提出自己的人的本质理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批判与面对的“费尔巴哈”主要是《未来哲学原理》的作者,而《提纲》其实是马克思自己的“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的任务是把对宗教的哲学批判进一步深化为对思辨哲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批判。马克思这里则认为,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是把对哲学的人的批判变成对人的哲学的现实社会历史批判,从一种理论批判飞跃成实践的哲学的批判[10]214-215。
五
《提纲》最后一条简短有力的箴言被镌刻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卡尔·马克思墓碑上,这一条也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人生的真实写照。
就如何理解这一条,蒙运芳[23]认为不同于哲学教材中普遍是将其置于理论到实践的框架中去理解的做法,应将其置于实践到认识(理论)到实践的框架中去理解,这样不仅符合马克思原文的逻辑要求,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性的哲学要求,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特征。张立波[24]认为《提纲》第十一条的解释应置于“实践—认识”的思维框架,而不是“理论—实践”的思维框架。前者重在认识如何生成,后者重在理论如何向现实运动;前者重在否定和批判,后者重在转化和应用。马克思通过揭示社会认识何以生成,说明只有在现实地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人和环境、自然和历史才能逐渐趋向同一,也只有从这一视角,才能历史地回答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问题。
对《提纲》中的“哲学家们”的具体所指和适用范围,中国学术界颇多争议。作者认为,虽然马克思对“哲学家们”没有特殊说明,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泛指,而是有强烈现实性的特指,即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嘲讽和对德国哲学传统的揶揄。张一兵[25]认为这一条正是马克思在读完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中关于“从前的各种改造哲学的企图,只是在方式上或多或少地与旧哲学有所不同,而不是在种类上与旧哲学不同。而一种真正的新哲学,即适合于人类的和未来的需要的,独立的哲学,其不缺少的条件则是在于它在本质上与旧哲学不同”的观点后,以反讽的方式,借用费尔巴哈式的语言,摹仿着写下的。
对于“改变世界”的意蕴,学者们的理解更是歧异纷呈。高清海[26]把“改变世界”理解为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旧哲学是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的,所谓“解释世界”,就意味着他们要让现实的世界去屈从理性的抽象原则,“改变世界”则是从现实世界出发,而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何中华[27]认为,马克思在哲学观上实现了一种“格式塔”转换:由以往那种着眼于对世界的诠释的知识论式的哲学,转变为作为世界本身展现方式的、以“改变世界”为本质特征的哲学。徐长福[28]认为,马克思说出“改变世界”的名句时感悟到了“做”的问题——这一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明显地忽视了的形上问题。
作者认为,在理解这一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每一种思维冲动的特征就在于它立足当下,直面现实。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总是停留在某个既定现实的眺望处,曾作为中介者的费尔巴哈也只是个旁观式的观察者。第二,马克思哲学中具有强烈的现实实践与理论建构互动的特征。从博士论文中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再到《提纲》中解释世界和改变时间,清晰可见马克思对自身哲学建构的反复问责。马克思不仅要同过去的哲学告别,更要展望未来的哲学。第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的“而”应作扩张之意,不应作对立之意理解。不能用改变世界来忽视甚至否定解释世界的必要性。
总之,《提纲》文字简约却内容丰富,结构小巧却脉络鲜明,信手拈来却举重若轻。它不是一本“问答手册”,而是“行动指南”,马克思所书写的文本并不是封闭的沉默状态的“白纸黑字”,而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为一体的开放的无穷的意义世界。从对《提纲》的文献研究状况来看,这一处在马克思世界观革命关键阶段的重要思想文本,时刻与我们处于一种动态的对话、交流之中,还有巨大的理论研究空间。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8 -209.
[2]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405-406.
[3]吴仁平.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新理解[J].赣南医学院学报,1994(3):180 -183.
[4]张涛.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理解[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91-292.
[5]安启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思想再探:兼评我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实践观[J].高校理论战线,2011(6):24-28.
[6]赵兴良.论《提纲》第一条的本体论意义[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35-38.
[7]邹季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是一个完整的思想[J].理论学习月刊,1996(2):26-31.
[8]潘惠香.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提纲》第一条的接近与偏离[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3):29-32.
[9]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66.
[10]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44-145.
[12]李淑梅.对认识如何可能的回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新解[J].哲学动态,1990(5):13-14.
[13]吴刚.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是否具有历史观意义?[J].江淮论坛,1994(3):15-17.
[14]盛卫国.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历史观诠释[J].学术研究,2007(9):59-62.
[15]邹季荣.思维范畴中的唯物史观意蕴:对马克思《提纲》第二条的一种解读[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6):17-20.
[16]刘丽琴.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J].甘肃农业,2006(11):275.
[17]邹季荣.论马克思在人与环境、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展示出来的唯物主义[J].理论学习月刊,1998(1):29-31.
[18]黄明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造”的一致: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2):52-55.
[19]朱光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J].社会科学战线,1980(3):36-42.
[20]孙熙国.唯物史观的创立与人的本质的发现: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处误译谈起[J].哲学研究,2005(11):22-26.
[21]王东,郭丽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解读:马克思原始稿与恩格斯修订稿的比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6):733-738.
[22]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3]蒙运芳.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新理解[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4):64-66.
[24]张立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新理解[J].教学与研究,1995(4):50 -51.
[25]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6.
[26]高清海,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综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1(5):37-48.
[27]何中华.论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向度: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J].河北学刊,2003(4):66-73.
[28]徐长福.是、应该与做:对解释世界、规范世界与改变世界诸问题的形上离析[J].哲学动态,2001(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