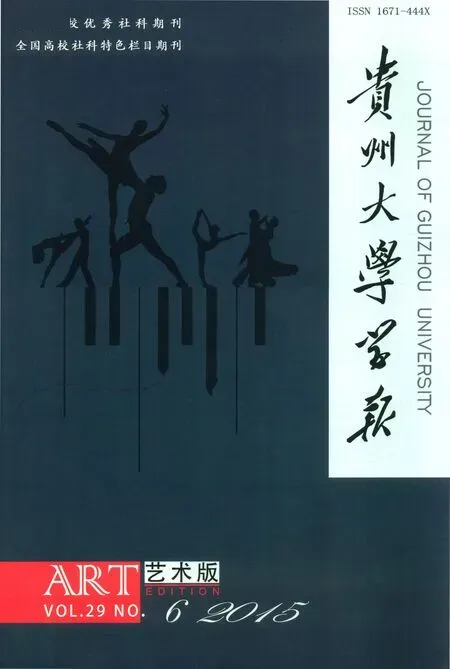重构当代美术史:基于艺术中“底层叙事”模块的思考
袁 荷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表现出多元化景象,艺术家们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找并确立新的意义。结合社会中的文化语境,一批艺术家开始“关注对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描述、思索和讨论,这种转变是中国的传统艺术里面都没有的”[1]29。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有意无意地使他们获得市场份额,成为当代艺术中较具影响力的人物。然而,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艺术家在对底层的叙事中,总是表现出一种精英主义立场,加之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其艺术作品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涉力度。尽管如此,“底层叙事”还是使艺术家们找到与社会问题对话的可能性,艺术介入现实正日渐凸显,其批判意识也进一步加强。
当代艺术所呈现出的新的叙事模式与功能,使描述底层的作品成为这一时期艺术作品中的多数。“底层叙事”承载的大量信息,涉及到社会学的范畴,形成了一股不同于传统艺术的话语力量。随着美术史研究视野的不断开拓,这种话语力量促成一种艺术模块。分析“底层叙事”,不仅可以尝试呈现当代美术的真实生态,还原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还可以参与中国美术史的建构,观照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逻辑。
一、美术史中的“底层叙事”
“底层”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斯皮瓦克①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出生于印度,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她便开始其底层研究,她的《底层人能说话吗?》(1985)、《底层研究:结构历史编撰学》(1985)、《后结构主义、边缘性、后殖民性和价值》(1990)等文章和著作在全球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她的底层研究中指出:“在最底层的乡绅、贫穷的地主、富裕的农民和上中产阶级的农民,他们都理想地属于人民或底层阶级的范畴。”[2]104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底层”的精准概念。但我们通常将“底层”理解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拥有上都相当匮乏,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阶层,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9。“底层叙事”则是借用了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关键词。“底层叙事”作为对“底层”的讲述或再现,在我国先是兴起于文学写作中,而后扩展向其他领域。
尽管许多艺术创作以文学作品为蓝本,但在底层文学兴起之前,艺术史中就已经出现了 以“底层”为表现对象的绘画作品。在中国当代美术之前,虽然单独描写“底层”的作品并不多见,但“底层”人物早就散落于美术史长河中,如唐代佚名的《舞伎图》,宋代郑侠进献的《流民图》,清代金廷标的《瞎子说唱图》以及黄慎作品中的乞丐、渔翁、贫僧等市井人物。20世纪初,在“启蒙”、“革命”、“救亡”等历史观念的笼罩下,美术作品中的“底层”形象同文学作品中的一样,被充分意识形态化。1930年代到1980年代,涉及底层人物描述的艺术作品逐渐增多,如江丰的《码头工人》(1931),陈烟桥的《拉》(1933),蒋兆和的《流民图》(1939),徐悲鸿的《愚公移山》(1940),罗中立的《父亲》(1980),陈丹青的《西藏组画》(1980),周思聪的《矿工图·遗孤》(1981)、《边城小市》(1983)等。到了1990年代以后,描绘底层群体的作品灿烂而纷呈,创作手法也多样化。其中以刘小东、张晓刚为首的一批新生代画家,将创作对象投射到普通市民身上或社会重大问题上;而以忻东旺、徐唯辛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更是直接塑造底层的工人、农民形象。
“底层叙事”总与“现实主义”相关联,遵循着人文精神和真实性原则。现实主义并非只能表现底层,但底层直到现实主义流派的出现才真正步入艺术圣殿,总是采用真实再现的技法表达艺术家的情感体验与思考。美术史中通常把以罗中立、陈丹青等人为代表的“乡土写实主义”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第一次高潮;1990年代以刘小东、张晓刚、方力钧等人为代表的“玩世现实主义”成为第二次现实主义的高潮;而第三次现实主义的高潮则来自21世纪初以忻东旺、徐唯辛、孙向民等人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表现了他们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认识理解、判断描述以及怀疑困惑。[4]130无论是“乡土写实主义”、“玩世现实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抑或其他,“新艺术家已经将描绘对象从政治人物、英雄人物中转移到了普通大众,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身上,使“当代艺术不只是形态跨界的表面文章,其深刻变化对于周遭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现实问题、历史问题和精神问题的介入,是艺术创作摆脱现代主义的纯艺术和精英化,成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生活反省和文化学意义的时代反应”[5]206。2007年11月,宋庄文化艺术节期间举行的“底层人文——当代艺术的21 个案例”展,集中了一批“底层叙事”的艺术作品,正是艺术家们力求走出纯艺术表现的一种探索,体现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与追踪,展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主义情怀。
二、“底层叙事”的话语特征
绘画的二维平面属性,从来不具备像语言一样的句法,使画面叙事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所呈现的最多不过是一个完整故事的片段,甚至是一瞬间。艺术家要通过“底层叙事”使“实在的事件能够‘讲述’自身或被再现得像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6]5一样,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图画’与‘语言’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类似性:没有指涉的语言或没有某种概念或几种指涉性概念的语言描述,都是荒谬的,同样地,图画也是如此”[7]212,只有创作出具有指涉的画面,传达画家对底层民众苦难的理解以及自身的体验、思考和感悟,才能唤起社会对底层真正的人文关怀。
“底层叙事”的题材选取与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体验、人生经历以及时代潮流密切相关。在大多数艺术作品中,艺术家采用写实的手法对现实进行再现,想将笔下的人物还原到生活中,创作出带有灵魂的人物形象,然而,这种强烈的创作意愿往往得不到满足。《父亲》作为“乡土写实主义”或“伤痕美术”的代表作之一,其典型性就在于绘画中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在216 ×152 厘米的超大画布上,艺术家采用特写的方式,刻画了一位饱经风霜、脸膛黝黑、皱纹密布、纤毫毕现、淳朴木讷、摄人心魂的老农民头像,那晶莹剔透的汗珠和长期劳动后残留在指甲内的污垢瞬间增加了形象的感召力。《父亲》不仅仅是父亲,更是万千底层人民的象征,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回应,折射出人民的精神面貌,反应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罗中立在塑造这一形象的时候,“没有更多的动机,就是想画这样一个题材……就想表达普通工人农民回到真正主人的时代”[4]65,这与他经历了“文革时期”对“高、大、全”或“神”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厌倦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形象,渴望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分不开。而十年的大巴山农村生活,更是促使他将画笔转向普通人、转向底层的重要原因。与罗中立有着相似经历的陈丹青等人,其作品同样表现出对底层的眷顾。这使栗宪庭由衷地赞道:“陈丹青和罗中立作品中流露出的对普通人的那种‘亲和感觉’,我以为是写实主义在中国最有意义的试验。原因是,作为那时艺术家的主体——知青,在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之后,自然把自己和底层普通人的亲近关系,沉积出一种美感。它使艺术家有意无意摆脱了居高临下的角色意识。”[8]
当代艺术的“底层叙事”实质是艺术社会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艺术作为表达人类情感的一种媒介,并且是有意图的行动之产物,它的社会角色通常表现为,艺术的生产和使用对其所属的社会有影响,以及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特征具有表达的价值本质。而艺术对其所属的社会有影响,并非只为受众带来审美体验,或者表现某种意识形态,而是能够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涉,引领人民走向美好生活。艺术要实现其社会功能,关键是艺术家在作品生成过程中的行为与欣赏该作品的接受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由于艺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场景中,并且其背景体现在特定的信念和价值中”[9]48,艺术家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艺术家来说,社会责任是第一的,其次才是其他”[1]27。当艺术家面对底层民众的人性弱点、思想局限、过错乃至罪恶时,不能一味地表现犹豫含混的态度,而应该通过手中的材料,克服身份转换的障碍、尽量保持客观的立场,对社会呈现出的诸多问题展开批判。自198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就突显出艺术家的批判意识,他们开始审视整个社会思潮,将艺术主题与社会大背景密切结合,然后转换为十分鲜明的个人视角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代艺术家对底层的关注,已经表现出对艺术社会功能越来越重视的倾向。
艺术作品能唤起一种自身固有价值的体验,将信息传递给欣赏者时实现其社会功能。“艺术家制造的那些实体的显在属性所唤起的体验必然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或这些作品被赋予的价值至关重要”[10]18,艺术实体的显在属性主要取决于艺术家如何讲述他所关注的事物,如何表现创作的主题,以及主题所指涉的相关信息。艺术家“要去除自己以往形成的知识分子式的对艺术的理解,让新鲜的东西进来,要改变自己”[11],采用平等的态度与底层进行对话,通过艺术手法和艺术符号的隐喻,展现底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构成艺术作品的价值,在满足欣赏者观看体验的同时,唤起一种自身固有价值的体验,更准确地传达艺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欣赏者应该明白,“艺术所传达给我们的知识是独特的,它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的意义相关”[12]4,艺术家对底层的讲述,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学的命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关注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实际和切身体验。当人们跟随艺术家的思维开始对其所处社会进行反思甚至付诸某些行动时,艺术才能实现真正为大众服务的社会价值。
三、“底层叙事”与精英主义立场
“底层叙事”通常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底层的自我表述,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斯皮瓦克在《底层人能说话吗?》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底层人不能说话”[2]128,出自正义考虑的责任与义务,使知识分子成为“底层人物”的代言人,由他们讲述底层的故事。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雕刻家、画家、摄影师和有关艺术家”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13]22而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其“精英权力本身就来源于精英获得各种公共话语的特权机会”[14]15,使他们有特殊的途径接触或获得一些话语类型与交流事件,从而影响着社会思想和人们的生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发展出自身作为独立社会阶层的职责、立场、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总是在进与退、仕与隐、君与民、庙堂与江湖、贵族与平民之间逡巡;他们的职责意识和价值取向,总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如此,中国的知识阶层一直没有处理好如何讲述底层的问题,他们缺乏独立的、自足的讲述视点”[15],这使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变得游离不定,让大多数艺术家处于传统意识形态主流和市场机制主流的中间地带,撕裂了艺术家作为整体的独立思考性,“一方面,艺术家希望将艺术与生活很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试图尽可能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另一方面,艺术家——那些被认为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又大致可以用‘雅皮士’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以便尽可能同一般生活区分开来”[16]110,这种分化无疑伤害到“底层叙事”的有效性。
精英主义的“底层叙事”,往往呈现为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艺术家没有深入到底层民众中,未能体验底层的在野生活,他们对底层的代言,只是一种观望,导致其作品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介入缺乏力度。大多数艺术家,尤其是以刘小东、张晓刚、方力钧为首的“新生代画家”,他们中大部分人处境比较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专业基础、扎实的写实功底,对西方当代艺术比较了解,他们比较关心自身或艺术本身,也试图通过艺术创作介入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并未经历“文革”,没经历过“上山下乡”,也没有直接参与“85 美术新潮”。然而已经获得的不少声名,和“中产阶级化带来的身份位移,及其与底层社会的生活思想经验隔阂”[15],使他们往往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底层叙事”,表现出无聊的、偶然的乃至荒唐的生活片段和讥诮的、冷嘲的、冷眼看待现实的艺术态度。即使是完全写实的刘小东,当他在表现社会底层、儿时伙伴,比如《抓鸡》、《烧耗子》、《金城小子》,或者涉及大型社会现实问题,如《三峡大移民》、《三峡新移民》、《入太湖》、《出北川》的时候,他的作品都带有一种叙事风格,而且把自己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环境里,有一种影像的叙述在里面,同时他又是在另一个现场。画家在场的缺失,只因为他想做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一个很客观的旁观者,他不想过多地介入。[14]47,51这使艺术家最终成为了画外人,其作品只是冷幽默式的对现实的嘲讽。
与旁观相反的另一种精英主义态度,则是居高临下的“人文关怀”。艺术家因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背景,在进行“底层叙事”的时候,往往会产生道德化的倾向,极有可能造成对描述对象的误解或歪曲,变成所谓的“底层秀”。随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成为社会的时髦话题,更多的艺术家融入到为底层代言的队伍中,开始了他们一厢情愿的表达。由于底层视角的缺失,写实主义艺术家往往采用一种俯瞰的姿态,带着一丝救世主的情怀,将民工形象,农民形象描绘为一种普遍带有愚蠢、麻木、呆滞感觉的人物形象。而属于“新现实主义”时期的一拨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把眼光锁定在“底层人物”的身上,他们中有的人来自极贫穷的地区,也有人为了收集素材,全面感受底层的生存情况,下井体验令人窒息的黑暗。他们对底层的读解往往源自内心深处对“底层人物”的过度悲悯与同情,容易产生拯救的心态,为唤起社会的关注,常常夸大底层艰苦的生活面貌,而呈现在他们作品中的多为肮脏的、可怜的、悲凉的、甚至是凄惨的底层形象。如果对底层的关注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精英文化为自己脸上涂抹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工具,艺术家本应保持的思想、人格、生存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而“底层叙事”介入现实生活的社会功能,旋即也被消解掉。
四、“底层叙事”与美术史的建构
对眼前正在发生,或者刚刚发生的当代艺术现象,能否纳入艺术史写作之中,一直存有争议。法国年鉴学派就认为,真正严肃的学者不应碰二十年之内的历史以避免因情感关系,写下不客观的东西。但“当代艺术在它所处理的传统文化中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几乎是傲慢无礼的非正式性”[18]322,这种非正式性使当代艺术能够系统地阐述自身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策略,参与到与社会现实的对话之中,并伴随着有争议的方法和结果重新获得一种面对世界说话的特定能力,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表述方式。而“只要艺术被认为是代表了每一个时代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自黑格尔以来这确实一直是个问题——人们就必然需要描述它的历史并赞美它的成就,或者像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概叹它在当前的衰落”[18]305,并且“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和不受欢迎的艺术类型和性质,就闭上眼睛无视学科继承的主体——我们所面对的当代艺术”[18]310。因此,书写当代艺术史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书写逻辑受西方史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按照线性时间观的编年法来进行年代学的叙述,如周跃进的《新中国美术史》,鲁虹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79-1999》,吕澎的《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根据门类、问题而展开的史述,如斯舜威的《中国当代美术30年1978-2008》;图史的方式,“即突出简洁文字与大量图片的结合,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19],如鲁虹的《中国当代美术图鉴》、《新中国美术经典》、《中国先锋艺术》,陈履生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王明贤、严善逶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等等。尽管他们罗列出当代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或是尝试建立一种语境框架来囊括研究对象,但其史述的整个框架始终没能逃出传统的藩篱。当代艺术因为其自身的特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反思象征符号的系统,文本内容具有极强的指涉性,使当代艺术史家的写作面临着应该如何“阐释”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艺术的历史连续性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追溯以前的艺术史叙述模式,所得出的结论将是暗淡无光的。
当代艺术史不应局限于作品史、作者史的传统写法,对于这个时期的艺术形态,应该放在社会的整体关联中进行全方位考察。面对当代艺术的反传统性,其艺术史的书写就其某些众所周知的形式和方法而言,它也许已经资源枯竭、筋疲力尽,它正寻求着一种新的技术上的“解读”。由于“一件艺术作品的历史意义往往是基于该艺术品在特定环境中的作用及‘其有效性’”[20]131,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应该从艺术的本体出发,从文本中解读出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所指涉的现实问题,抑或是根据文本表现题材进行化类分析,“就像艺术家要求自己创作不同于传统的艺术那样,这个历史也要求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史”[18]307,一种可以打破仅仅根据时间、空间或者事件进行编排的史述模式。
当代艺术是艺术与现实生活发生交互作用的结果,其艺术史的书写焦点,应该转向艺术和生活之间的“接缝”处。当代艺术家抛开传统的艺术经验,力求找到艺术与所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联系,将思维的触觉伸向传统艺术忽视的对象,通过对普通人物(更多的是底层)的再现刺激公众,迫使观看者去思考他所处社会的现实,使“艺术作品证实的不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人。而且人在他对世界的艺术搬用中并没有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更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世界”[18]297。所以,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还需讨论现实的重要性,讨论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和作用。
“底层叙事”作为当代艺术中的一种模块,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一个建构性力量。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千姿百态,但艺术与生活发生交互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底层叙事”。而塑造底层形象的作品着实不少,贯穿了整个当代艺术的发展,并有延伸的态势。如果对艺术作品、艺术家和艺术事件共同承载的社会属性进行划分,“底层叙事”将充分体现出艺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涉。对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来说,按照艺术的功能划分模块,无疑是一种新颖的、独特的视角,我们可能从中寻觅到其他的当代艺术的特质。而当代艺术的写作者在不仅受到前辈写作的“历史连续性”的影响,还对当代艺术还有切身体会的艺术经验,如果将传统的评价,结合当代的经验,并根据艺术社会功能的特质进行探索,就会不断地发现新的方向,使当代艺术史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面。
结语
当我们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形态乃至整个当代美术史时,之所以会格外重视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底层叙事”,并非因为关注底层成为时尚的话语,或者这拨作品高价热卖的关系,而是因为“底层叙事”的出现可以昭示着一种艺术趋于成熟的转型,即“底层叙事”的艺术作品已经成为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变的标志特征为,艺术不再局限于自身本体的表现,而是对社会现实问题有更全面更急切的介入,它已经走出了神圣不可触的艺术圣殿,常常通过独特的语言流露出深刻的忧患意识,真正实现和大众的沟通与共情。尽管中国当代艺术的“底层叙事”还欠火候,表现出诸多问题。但是,笔者想格外指出的是,“底层叙事”进入艺术作品,通过艺术与生俱来的“话语权”以及独有的社会功能,参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引导,不仅是时代的感召,也是艺术及艺术家所应肩负的责任。此外,“底层叙事”构筑的艺术空间还提示了自己在美术史中的“在场”。因此,当我们在进行当代美术史书写时,就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时间,或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应注意到整个当代艺术所呈现出的面相繁复的真实状态。而从艺术功能上划分模块,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提供一种新的思考途径。
[1]方力钧.像野狗一样生存[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斯舜威.中国当代美术史30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5]王林.底层人文:当代艺术的21 个案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6][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7][英]萨林·柯马尔,伊万·卡斯科尔.艺术史的语言[M].王春辰,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8]栗宪庭.从张建华的作品想到写实主义的‘国民性’[J].美与时代,2008(02).
[9][英]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李东晔,王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加]大卫·戴维斯.作为施行的艺术——重构艺术本体论[M].万军,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11]巫鸿.走进现实——巫鸿与刘小东对话[J].荣宝斋,2010(02).
[12][英]奥斯汀·哈灵顿.艺术与社会理论——美学中的社会学争论[M].周计武,周雪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陶文昭.精英化世纪:现代知识阶层与社会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14][荷]范·戴克.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M].齐月娜,陈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5]周保欣.底层写作:左翼美学的诗学正义与困境[J].文艺研究,2009(08).
[16]吕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城与市场化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7][法]杰罗姆·桑斯.对话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8][德]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M].常宁生,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9]覃京侠.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及其问题——访鲁虹[J].大艺术,2006(01).
[20][英]乔纳森·哈里斯.新艺术史批评导论[M].徐建,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