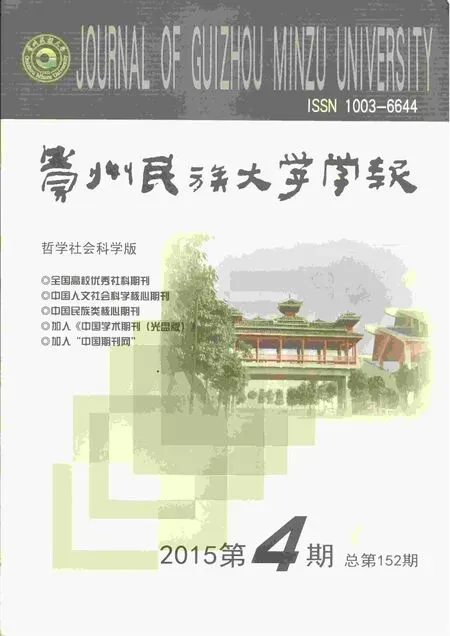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①
范香立,郭晓燕
(1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2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唐代疆域辽阔,周边地区分布着发展程度不同的众多民族。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关系到唐朝统治稳定和国家安全。为了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唐统治者从大局出发,采取和亲之策,与边疆民族建立婚姻关系。尽管和亲政策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毋庸置疑,它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双向文化认同,也含有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两种认同虽然还处于朦胧的、表层的阶段,但有利于唐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一、唐代中原汉民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
所谓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P68文化认同则指对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一致性或趋同性的确认。由于中国民族成份的多样性(既有单一民族,也有复合民族、民族集团及族群等[2]及文化的多元性,“文化认同并非单纯的指对本己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他文化或异己文化的认同。”[3]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不限于单一民族内部的认同,还可指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尊重、包容及认可等。文章所指的文化认同是中原汉民族与边疆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可及互相吸收。
(一)中原汉民族对边疆民族习俗等方面的认可
和亲实际上就是中原汉民族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可,与唐联姻之民族大多以游牧为主,其中有些民族“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4](卷195,5220),与中原汉民族尊老敬老的孝文化完全背道而驰。某些民族还实行“烝报婚”,“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5]P1864或“蒸其叔母”[6](卷195,5197),即子可妻其后母,弟可妻其寡嫂,这种婚俗与汉民族之伦理道德更是相抵牾,但唐朝统治者愿以宗亲出嫁到边疆民族,说明唐人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认可,当然这种认可只是唐王朝尊重其习俗,而不是向其学习。正如金城公主远嫁异域后,时人于休烈所说“公主下嫁从人,远适异国,合慕夷礼”[7](卷196,5232),可见唐人对公主从“胡俗”的认可,亦为唐朝尊重少数民族之风俗习惯之佐证。和亲公主入蕃后,均能接受异族之伦理习俗,如“丞报婚”,太和公主初入回鹘时,按回鹘之俗身着“胡服”与崇德可汗完婚,可汗死,公主改嫁夫弟昭礼可汗、再嫁夫侄彰信可汗,后又嫁盍馺特勒可汗,太和公主入乡随俗就是对回鹘文化习俗的一种认同。
和亲拉进了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边疆民族所信奉之宗教开始在中原各地广泛传播。如回鹘的摩尼教,唐玄宗曾禁止汉人信奉。开元二十年(732年)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逛惑黎元,宜严加禁断。”[8]P48然自和亲之后,因回鹘信奉此教,“故京师为之立寺”[9]P66,唐政府不但遂允许其教在京师长安、洛阳建造寺庙,而且亦允许其在河南、太原等地置寺。信徒渐多,出现全家信奉其教的情况,如《太平广记》卷107《报应六》所载,唐宪宗元和时,“吴可久……,奉摩尼教,其妻亦从之。”[10]P727正是由于中原王朝及百姓对回纥宗教信仰的认可,摩尼教发展迅速,以致“江淮数镇,皆令阐教”[11](卷699,7182)。
(二)边疆民族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认同与吸收
中原汉民族认可边疆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的同时,中原文化、宗教等亦得到边疆民族的认同。边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求婚,要按照中原汉民族的婚礼习俗,即“六礼”之程式,而且要事先进行培训。据《资治通鉴·隋纪》载,隋文帝时,突厥入中原迎娶隋公主,“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12](卷178)突厥学习六礼之后,隋朝方嫁公主与之,突厥此举就是对隋朝礼仪的尊重与认同。虽所记为隋时事,然唐承隋制,唐与和亲民族所用之礼仪亦为“六礼”,边疆民族要想与唐和亲,必须认同中原礼仪,而且礼仪应当周全。如唐玄宗时,突厥毗伽可汗遣使求婚于唐,因使者身份不高、礼仪不周而被拒绝,玄宗云“然一为婚姻,将传永久,契约须重,礼数宜周。今来人既轻,礼亦未足,所以未定日月,令其且还”[13](卷29,328)。边疆民族与唐王朝和亲之后,即为唐之女婿,必须尊卑有别,恪守子婿之道。回鹘曾因助唐平史朝义之乱,便恃功“不修蕃臣礼”[14](卷979,11506),贞元四年德宗许咸安公主与之,回鹘可汗“礼甚恭”,并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15](卷195,5208)亦见和亲对回鹘的文化影响,回鹘人已知需恪守翁婿之间的尊卑之道。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时,松赞干布亲自迎亲,见到送亲使者李道宗,恭敬奉行“子婿之礼”,深识尊卑之道。松赞干布还建造大昭寺,供奉文成公主所带的释迦牟尼佛像,其见唐服饰之美,即“释氈裘,袭纨绮”[16](卷196,5222),并派其贵族子弟来中原学习。南诏有子连父名之传统,这恰恰为中原汉民族所忌讳,南诏王丰祐就因为钦慕唐王朝礼仪,遂弃蛮俗从汉俗,“不肯连父名”。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认同的表现。唐与边疆民族之间实行入汉地则随汉俗,入蕃则随番俗的原则,其实就是对彼此文化的相互认同。
随着民族交往的扩大与加深,中原汉民族与各边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趋向自觉,并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开元时,宫人骑马时“皆著胡帽”[17](卷45,1957),契丹所用之“奚车”也“渐至京城”[18](卷45,1957)。《明皇杂录》载玄宗时,“士庶好为胡服貂皮帽,妇人则步摇钗,窄小襟袖,识者窃叹。”[19]P66表明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原汉族人民所喜爱,并得到广泛的传播。元和时,许多胡人定居长安,并于此地娶妻生子,出现了“长安中少年俱有胡心”[20]P14之现象。正是这种民族间认同壁垒的打破及文化认同的增强,使唐人出现了胡化之现象,而边疆民族亦出现了汉民族之特征,“筑宫殿以居”[21](卷226,7282),“衣朱碧,类华人”[22](卷247,7971),正如诗人陈陶所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23](卷746,8496)由此可见,文化认同对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
边疆民族在认同中原汉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对李唐王朝的国家认同。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少数民族……内附、归附、臣服、降服于中原王朝,成为王朝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对象就是王朝国家。”[24]P11-17唐王朝由于自身实力的强大,通过和亲等开明开放之民族政策,使各民族纷纷“纳贡述职”,成为唐朝的蕃属,认同李唐皇室的政治权威,并服从忠诚于唐王朝,因此就产生了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感,这种国家认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接受唐朝册封。唐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和亲之后,各民族均需得到唐王朝的册封以示正统。唐与吐蕃和亲之后,松赞干布被唐高宗授予驸马都尉,并被册封为西海郡王。自此以后,吐蕃新继位的首领都需要经过唐朝政府的册封。唐武宗时,吐蕃赞普达磨去世,因没有子嗣,其相立乞离胡(达磨妃之侄)为赞普,未“遣使诣唐求册立”[25](卷246,7970)。吐蕃人不予承认,其大臣论恐热认为“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26](卷246,7970),于是起兵讨伐乞离胡。可见吐蕃赞普继立需经唐朝册封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唐每与回纥、契丹奚等民族和亲都要对其首领进行册封,宁国公主出降回鹘时,唐肃宗以李瑀为册命使,册封回鹘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册封实际是唐王朝确定对边疆民族的统治,及边疆民族承认唐王朝对其行使统治权力的认同。
其二,朝贡。边疆民族作为唐室女婿、外甥,朝贡是维持双方关系的关键环节之一,唐朝每有大事小情,均需前来朝见。唐太宗征辽东还京后,身为唐朝女婿的松赞干布立即遣使来贺,并对唐太宗进行一番吹捧,“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27](卷999,10342)之后又向唐太宗进奉金鹅。唐每有新帝继位,和亲民族亦需朝觐,唐高宗继位时,唐婿吐谷浑首领诺曷钵立即遣使朝贡。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嫁于吐蕃赞普弃隶宿赞后,吐蕃自此“频岁贡献”[28](卷97,1732),契丹、奚、吐谷浑等民族在与唐和亲之后更是朝贡不绝。
其三,派兵随唐作战。和亲后,边疆民族与唐朝形成甥舅关系,唐朝每有征伐或遇有急难,和亲各族有“为国出力”及救难之义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命王玄策出使西域,结果被中天竺劫掠,松赞干布立即遣兵出击天竺,取得胜利并遣使向唐献俘。突厥曾上表唐玄宗,翼希唐实现“天下一统”,对于所有叛唐之逆贼,突厥会“尽力支敌”。宁国公主、太和公主等和亲回鹘之后,回鹘立即遣兵随唐作战。如宁国公主出嫁后,回鹘可汗遣其子与宰相率领“骁将三千人助国讨逆”[29](卷195,5201)。太和公主和亲回鹘后,唐遣裴度出兵讨伐幽州等地的蕃镇之乱,“回鹘请以兵从度讨伐”[30](卷973,11436)。
其四,维护李唐王室。高宗继承皇位之后,为表示对李姓皇室的维护、忠诚之心,吐蕃松赞干布特意致书司徒长孙无忌等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31](卷196,5222)圣历元年(698年),突厥默啜可汗因和亲对象不是李唐皇族而起兵反抗,声称:“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末总尽,唯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32]P1074遂拘武延秀并起兵,此举虽是默啜发动战争之借口,但不可否认边疆民族对李唐王朝产生的国家认同感。唐回和亲后,回鹘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乱军,郭子仪于扶风犒赏回鹘将领,其叶护云:“国多难,我助讨逆,何敢食!”([33]卷217,6115)可见回鹘助唐王朝平乱之急切心情,此种表现源于回鹘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心理。
和亲之后,周边少数民族尊奉唐朝,甚至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贞观后期,漠北各部尊唐皇帝为“天可汗”,并修筑“参天可汗道”加强与唐朝来往,即以唐天子为天下之主,这就是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之表现。从各和亲民族与唐交往的文书之中亦可管窥,如吐蕃向唐所献之文书中常常提到“和同为一家”[34](卷999,10344),而唐统治者也一直强调与边疆各民族之关系为“一家”,不断强调“华夷无隔”、“地合一家”、“华夷一家”等观念,随着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认同的增强,四夷“慕义向风,尽为臣妾,纳贡述职,咸赴阙庭。”[35](卷23,265)“尽为臣妾”虽然带有明显的尊卑色彩及大汉族主义,但却符合唐统治者“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四夷“纳贡述职”表明边疆和亲民族已蕃属于唐,如此便有了唐大一统下的多元王朝国家格局的形成。
三、唐代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关系及其局限
唐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形成,离不开边疆民族对其政权的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又离不开文化认同,两种认同之间既统一又矛盾,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认同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一)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关系
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文化认同是边疆民族对唐王朝国家认同的前提。边疆民族通过与唐王朝和亲等交往活动,逐渐认识到中原王朝的先进性,内心开始产生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与向往之情,如松赞干布因与文成公主之成亲,特意除去本民族“赭面”之习俗。回鹘与唐和亲之后,其人“衣朱碧,类华人”,这些都属于文化认同的范畴,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构建了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没有这些基本的认同,就不会产生国家认同。其二,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可以增强其对中原汉族的文化认同。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使其获得王朝国家的援助,据《阙特勤碑》载,“我们同唐人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的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36]P119说明唐为突厥提供了大量财力支援。金城公主入吐蕃后,唐又增加赤岭等地与之互市。这种国家认同,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促进了和亲民族的发展,必然加强其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其三,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最终归宿,文化认同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唐统治者冀希通过文化的传播“使之渐陶声教”[37](卷213,6794),即以文化来影响边疆民族,使其提高并加深对唐王朝的认同、忠诚,最终实现“天下一统”之目的。
两种认同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影响并弱化国家认同。主要是由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冲突所引起,由于民族差异性的存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原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间的风俗习惯、观念各不相同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矛盾及摩擦也是不断的。如回鹘毗伽阙可汗去世后,回鹘贵族想让宁国公主为其可汗殉葬。宁国公主坚持依“中国法”[38](卷195,5202)为其夫“持丧”,唐回间不同的风俗习惯在具体问题当中发生冲突,为解决两者间的矛盾,最后宁国公主采取折中之法,按照回纥习俗,“剺面大哭”[39](卷195,5202),后因无子归唐。肃宗时,宗室李瑀送宁国公主和亲回鹘,回鹘可汗欲坐于榻上接受诏书,李瑀因而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回鹘可汗“合有礼数”[40](卷195,5201)。最后可汗“起奉诏,便受册命”[41](卷195,5202)。边疆民族与唐王朝之间的文化认同冲突如果协调不好,或处理不当,就会使冲突的升级,进而引起边疆民族对唐王朝国家认同的弱化。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衰退,边疆危机加深,唐朝对少数民族那种开怀广纳的胸怀,也渐渐趋保守,士大夫大倡“华夷之辨”,就唐与南诏和亲之事展开长达六年的论战。大臣崔安潜认为“蛮蓄鸟兽心,不识礼仪,安可以贱隶尚贵主,失国家大体。”[42](卷222,6291),“且天宗近属,不可下小蛮夷。不言舅甥,黜所僭也”[43](卷222,6291)。唐诏之间就南诏对唐求婚有“牒”无“表”,称弟不称臣争论,南诏希望通过此举获得与唐平等之地位,而唐则以藩臣视南诏,双方在争辨之时,南诏攻陷唐安南城,唐军溃败,最终唐作出妥协,答应南诏可不称臣,并与之和亲。可见,当发生文化冲突时,必须妥当处理,否则就会引起边疆民族对唐王朝国家认同观弱化,从而引发战争。
(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局限
唐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原汉族与边疆民族交往更加密切。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和交往的限制,边疆民族对中原汉民族与唐朝的文化认同主要集中表现在服饰、礼仪、经济等表层的生产生活方式上,还未上升到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民族的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认同与吸收。这种认同相对松散,并没有内化成全民族的共同心理意识,对边疆少数民族来说,其国家认同还有一定的屈从性及随意性,即边疆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是以唐国家实力的强弱为依据的,当唐王朝强大之时,就会出现“五服远朝王”、“蛮夷九译,咸来从”的盛大场面,反之,就会出现轻则与唐争雄长,重则抄掠州县、攻伐不断。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之所以缺少内在性,其原因有二:首先,大多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有其自身的一套组织机构、原则及意识形态,决定其对唐王朝国家认同的往往是本民族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又以自身利益的向背来决定其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因此,只有超越少数民族自身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各族人民才能融合到汉民族中,并逐渐与汉族人民的国家认同趋于一致。
另外,唐朝统治阶级的“内中华而外夷狄”观念的存在,亦使唐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认同存在隔阂。虽然唐朝统治者的民族观念相对其它朝代更为开放,但由于时代、阶级等因素的影响,唐代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民族平等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即便是唐代最开明的政治家太宗李世民,其内心深处的华夷之分还是挥之不去的,一边主张“不必猜忌异类”[44](卷197,6216)、“四夷如一家”,另一边又认为“夷狄人面兽心”[45](卷197,6201)、“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46](卷195,6149)。华夷之分观念在华夷两安、夷不乱华之时还不甚明显;当边疆危机严重之时,不但唐之士人大呼华夷之辨,就连具有混血血统的最高统治者也强调华夷有隔,唐武宗曾说“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犹有限隔,况蕃汉殊壤,岂可通同?”[47](卷699,7183)而且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消除的。尤其到宋代,此种意识更为强烈,宋人胡寅认为唐对少数民族赂以金帛、约为兄弟、嫁女与之是为“三耻”,“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妇之义,人伦之本,曾是以为和戎之具耶。”[48]陈亮亦认为夷狄不习礼仪无人伦,“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49]P74是不可能的。而且持华夷有别观念的还有一大批影响宋代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等,所以宋朝宁愿多送币帛、割让土地,也不许和亲。由此可见,唐王朝在将众多民族政权整合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后,并未能也不可能构建起各民族趋于同一的心理或思想意识,所以,边疆各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唐代边疆民族“认同”之价值
通过和亲等方式构建起的中原汉民族对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及其对李唐王朝的国家认同,加强了中原与边疆的交流与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实现了“认同”之价值,其表现主要有如下方面。
其一,淡化了民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民族同化。
边疆民族对中原汉文化及唐王朝国家的认同方式,是从边缘向中心,从较高社会阶层向一般成员浸润的[50]P149,通过和亲,处于边缘地区的各民族形成了对中原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提高了其对唐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物通过与唐王朝的往来,逐渐形成对唐的国家认同,这种由外向内、自上而下的认同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统一国家的认同。认同范围逐渐扩大,使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民族间的隔阂不断弱化,边疆民族不断接受和学习汉族的农耕、纺织、家禽畜养等生产技术,其生活方式不再以单一的畜牧经济,出现了农牧结合之特点,而中原地区亦大量吸收边疆民族之长。唐诗中记载颇多,如王建诗中所说“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51](卷298,3374)诗中所描绘的景象恰恰是唐与各边疆民族相互认同及学习的体现,亦是民族同化之表现。
其二,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民族情感。
中原汉民族与边疆民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增强,及边疆民族对唐王朝国家认同的强化,加速了中原与边地民族间的交往和联系,使唐与各民族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唐人入职于边疆民族政权,如曾在南诏任清平官的郑回,因精通儒学,被聘为南诏贵族子弟的教师,这无疑促进了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其秉政用事之后,对南诏汉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南诏的各种制度大多效仿于唐,在推动唐诏友好关系的发展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纥任检校右仆射的药罗葛灵,本为中原汉人,入回纥后被赐可汗姓,且“在国用事”,贞元八年(792年)来唐,德宗对其赏赐甚厚,这无疑对唐回双方交流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唐任职的少数民族人才数量更是惊人,据《唐代蕃将研究》一书统计,出身少数民族的武将达2 536 人[52]P37,而其实际人数当远远超过此数,如若加上文官,其数目将更为可观。无论对唐王朝或少数民族政权来说,重用外族人才,无疑会促进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认同感的加强对增进民族间的情感,促进团结具有积极意义。唐太宗曾称,他对“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53](卷194,5164),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
其三,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由于边疆民族对唐王朝国家的认同,唐王朝对其给予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帮助,如前所述,唐给予少数民族大量的财力支援,并增加互市场所,使彼此丰给,对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唐通过和亲公主给边疆民族带去大量中原文化典籍及技术人员,如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所带的典籍数量相当多,据载“经史典籍三百六”“诸种食物烹调法,与及饮料配制方”、“汉地告则经三百”、“工巧技艺制造术”[54]P68-69,另外还有大量的医学典籍、药方等。金城公主和亲时,“杂伎诸工悉从”[55](卷216,6081),大量文化典籍及技术人员的入边,无疑会促进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升当地人们的文明水平。而且唐统治者亦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教化,唐太宗曾教诲文成公主“应教儿孙,读书习染善性,”“止恶修善勤奋”[56]P22,和亲公主的言传身教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汉化教育。
另外,由于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向往,各民族纷纷派遣子弟或贵族来唐学习。弘化公主与吐谷浑首领诺曷钵之子慕容忠“童年入侍”[57]P114于唐,得以学习汉文化。和义公主和亲宁远后,其王便派子弟入唐“习华礼”[58](卷221,6250)。吐蕃也遣子贵族来唐学习,这些人员在中原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名士交往,迅速汉化,学满回归后,一定会将汉文化之精华带到本民族,并通过对施政者的影响,渗透到本民族的方方面面,所以有学者说“吐蕃之开化,实唐文化熏陶启导之功也。”[59]P469可见,边疆民族的“认同”对推动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1]陈国强. 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何叔涛.民族过程中的同化与认同[J]. 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人类学高级论坛2003 卷,2003.
[3]陈世联.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
[4][6][7][15][16][17][18][29][31][38][39][40][41][53](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清]朱一新. 无邪堂答问[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9][唐]李肇. 唐国史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1][13][27][34][35][47][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宋]李昉. 册府元龟[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唐]郑处诲. 明皇杂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20][唐]陈鸿. 东城老父传[C]//虞初志:卷6,北京:中国书店,1986.
[23][51][清]曹寅.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24]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
[28][宋]王溥. 唐会要[M]. 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
[32][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42][43][55][58][宋]欧阳修.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48][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Z]//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9][宋]陈亮. 陈亮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0]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52]章群.唐代蕃将研究[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54]索南坚赞. 吐蕃王朝世系明鉴[M]. 刘立千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56]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 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7]夏鼐. 考古学论文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59]任育才.唐朝对吐蕃和亲策略之运用[A].唐代研究论集(第2 辑)[C].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