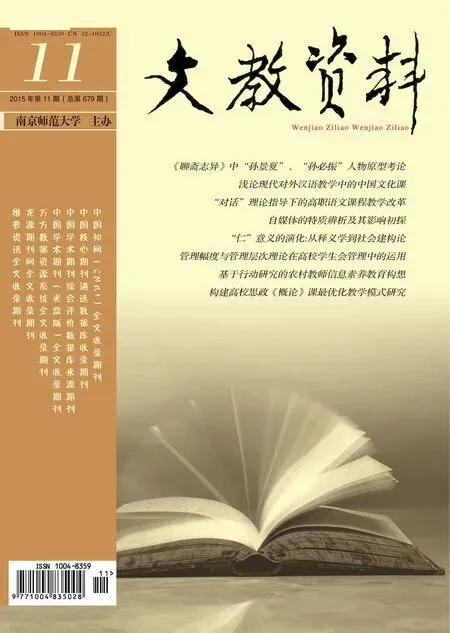聆听与蛙声共鸣的女性悲歌
——浅析《蛙》中的女性悲剧
戴佳文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聆听与蛙声共鸣的女性悲歌
——浅析《蛙》中的女性悲剧
戴佳文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人物塑造必定离不开背负的命运,《蛙》中的女性承受的苦痛无法通过忏悔抵消,反而作为一种悲剧性符号深深印刻在历史铜鼎上。文章旨在探究《蛙》中的女性悲剧,将小说中的女性分为三类探讨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作为生殖机器的女人、被扼杀在母亲腹中的女娃与被迫流产的母亲。悲剧原因有共同规律,也有特殊性,莫言虽以不同方式表现其悲,但殊途同归。
莫言 《蛙》 女性 悲剧
一、对于女性悲剧的指向性
莫言在《蛙》的研讨会上曾指出:“作品虽然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作为集中表现的主题,但并非要写计划生育事件的过程,而是‘盯着人’,也就是以塑造人物为核心来写。”正如廖先怀先生所说的:“抛开历史性的计划生育史的角度,从个人生命和人性角度探析《蛙》是最接近著者思想的,毕竟,小说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重述。”[1]
《蛙》这部作品以计划生育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女性作为计划生育背景下的主体。小说中,她们的悲喜来不及被生活粉饰就被计划生育浪潮打翻,悲剧由此产生。
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在得知母亲背弃忠诚丈夫与他人私通后,因内心激愤而叹出一句:“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莎士比亚设计这句对白旨在责备女人们自我意识缺失与自甘堕落。无疑这是女性在命运面前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但我们何曾静下心来思考过,这种备受批判的“脆弱”是否真的只能归咎于女性本身?另外,“脆弱”的内涵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甘堕落,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对白设计中被合理地无限缩小,而笔者想要提及的却是容易遭受忽视的女人独有的脆弱性。从大的角度看,女性的脆弱并不止步于易受欺凌,还包括与命运抗争却依旧丧失希望的失落感。脆弱酿成悲剧,由此奏起一曲曲女性悲歌,细细想来,这种悲歌放到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农村是不能只推责于女性本身的。
二、女性悲剧的分类阐释
笔者将作品中拥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分为三类:作为生殖机器的女人(包括农家妇女与牛蛙公司的代孕者),被扼杀在母亲腹中的女娃与被迫做人流的准母亲。这里每一类女性都值得他人为其奏响悲歌,而其悲剧性的体现也殊途同归。
(一)家庭以多子为荣,以女子为机器。
1.背负生育重担的家庭妇女
小说描写的是1962年后的“地瓜时代”,是一个生育高峰期,生孩子成为东北乡的一种潮流,男男女女热火朝天地忙活生育,那种狂热劲就像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金钱的追求,用现代视角看显得十分滑稽。
作为生养孩子的关键人物,各位母亲铆足了劲为家庭增添香火。她们在不自觉情况下成了生养的机器,但还是乐此不疲。这是值得审视的,退一步讲,多数人(包括多数女性)都坚持认为女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体现为生育下一代。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母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整个高密县东北乡居民对生育的看法,这种看似民主放任的手段实质是为“生男”铺下的厚实铺垫,因为只有不断生养才能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生男防老。在王仁美请求袁腮取出避孕环再一次怀孕之后,母亲对匆匆回家的蝌蚪吐露自己支持媳妇再次生养的想法:“你大哥二哥都有儿子,唯你没有,这是娘的一块心病,我看就让她生了吧。”蝌蚪虽点头却担忧妻子腹中孩儿的性别。不仅暴露一个老母亲对年轻母亲顺理成章的“压榨”,还说明“生男孩”对这个家庭的重要性,更凸显王仁美作为一个自愿的生育机器的悲哀。
一方面,女性对自我价值探索不足。这一点能从那些自愿为家庭多多生育的母亲身上印证,如王仁美。这类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依旧停留在封建传统文化上,她们认为不为家庭增添香火的媳妇有罪,不生男孩是罪上加罪,这种思想对女性的束缚性极强。另一方面在于男性(抑或整个社会)对生男孩的迫切渴望,传统家庭妇女作为传统生殖机器的悲剧性由此可见一斑。
2.牛蛙公司暗中培养的代孕群体
在计划生育实施到一定程度后,高密县顺应国家发展潮流,短时间内各类工厂与公司拔地而起,其中就有袁腮的牛蛙公司。顾名思义,这个公司与“蛙”的联系十分紧密。同时,在小狮子为能顺利成为牛蛙公司一员而对蝌蚪灌输“必备知识”后,读者对“蛙”的内涵的理解才真正达到作者初期预想的层次:“她像背诵似地说: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那种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小狮子的反应可以推断出这些听起来知识性十足的言论肯定吸引了不少与牛蛙公司往来的客户。找牛蛙公司代孕的男女们必定包含对“蛙(娃)”的崇高爱意,他们被粉饰过的丑恶本质蒙蔽了双眼,甚至觉得这个机构存在的合理性足够强。从蝌蚪与竹筏青年(即牛蛙公司的业务员)的对话中,我们更可以清楚窥见这类怂恿者与花钱代孕的富翁们的扭曲心态。男人们的轻松口气使我们感受不到哪怕一丝负罪感。当竹筏青年殷勤地向蝌蚪献上一个省钱生儿子的秘密时,我们才会明白负罪感已无法作为衡量牛蛙公司罪恶的标准,追求经济效益与家庭香火的渴望已然将这一群男子变成剥夺女性权力的恶魔。
小说由此牵出陈眉。这是一个集合近乎本书中所有悲剧意象的女性——出生坎坷又遭父嫌弃的女娃、成为廉价代孕机器的毁容女人和被夺走孩子的疯母亲。在小说最后一部分,作者以话剧形式让我们看到陈眉的疯癫。这本是一个坚强的双胞胎妹妹,却惨遭命运接二连三地扼喉。毁容对于一个美丽女子已是不小的打击,之后她忍辱为父治病,却遭到袁腮公司的讹诈,被迫与亲生孩子分离……这一切悲剧一起压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发疯是必然的。陈眉的疯癫是悲到极致后的稳定状态,作者这样设定或许已是体现女性悲剧的最好方式。代孕者的命运就是如此:没有地位,无法与骨肉相亲。小说虽以陈眉为重点描写对象,但她并不是特例,反而是一名散落在人群中的普遍悲剧人物,这世上必定还有千千万万个像陈眉一样饱受苦痛的女性,因此这悲歌的曲调是广阔悲壮的。
(二)计划至少有一子,只生女孩为不孝。
在计划生育浪潮下,被扼杀在母亲肚子里的娃娃数不胜数,女娃作为一个被家庭不重视的群体,其承担的苦痛必定不只是生理上的死亡。
作为与男娃相对的女娃,她们一开始被扼杀在母亲腹中的不仅是同男娃一样鲜活的生命,更是一种尚未出生就必定承受的否定:父亲对女儿地位的否定、家族对女儿继承权的否定……犹记小说中描述袖珍女王胆艰难生下第二胎的悲壮场景,当姑姑匆忙为她接生下一个女孩后,作为新生儿父亲——这个理应为妻子顺利生产而欢呼的男人却 “颓然垂首,仿佛泄了气的轮胎。他双拳轮番击打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万端地说:天绝我也……天绝我也……老陈家五世单传,没想到绝在我的手里……”
由此笔者联想到柔石笔下父亲沉女的情节,血腥场面令人毛骨悚然:“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也答不出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叫着的女儿,刚出世的小生命,用他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沸水里了!”[2]这样惨烈的悲剧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父亲们对香火的极端渴望。可以推测,倘若小说中的人们在生育之前能清楚知道腹中胎儿的性别,那么有些父亲一定十分愿意接受妻子堕胎——因为女儿出生了也是无用的,同时家庭也能有理由规避被罚款的风险。
(三)天恩与人祸。
女性受孕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恩赐。地瓜丰收时代的东北乡人沐浴着天恩,毫不懈怠地生育。此后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却用暴力强行将多余的恩惠铲除。
天有恩泽,人有红心。姑姑的一颗红心奏起她一生的悲歌,她始终秉持着为党服务的理念,极力扼杀计划外的腹中生命。姑姑像是一只狼,怀有多余生命的母亲难逃她闪着绿光的双眼。张拳之妻耿秀莲身怀六甲,为躲避姑姑一行人的追杀而长时间凫水,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蝌蚪之妻王仁美大费周章才得怀有二胎,反抗过后的她接受了姑姑的思想,还是在通往“康庄大道”的路上牺牲;陈鼻之妻王胆在激流勇进的竹筏上用袖珍的身躯尽力保护腹中胎儿,在艰难产下一女后失去生命。年轻母亲们的悲歌在这三个可悲例子中得以体现。
姑姑多次为流产的年轻母亲们献血,而在她们牺牲后却显得心安理得——她的堕胎大业完成,同时她救病人时确实尽了力。由此可见,姑姑的心红得可怕,她已然成为计划生育的执行机器,其忏悔与赎罪的方式到最后显得十分可笑。小说末尾姑姑那次未遂的自杀似乎将她的一切罪责都化为云烟,但蛙声依旧常鸣。这些细碎的情节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姑姑赎罪意识的真实性。姑姑是小说设计得最复杂的人物,她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在迎接新生命与结束新生命之间分裂,巨大的落差在她心里必然留下极深的阴影,这可以从她晚年时不时会记起当初众人对她如送子娘娘一般敬爱中推断出来。她与郝大手结合之后对于每个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一个手上沾满献血的“杀人狂魔”的悲哀。拥有悲剧人生的人不一定从未制造过悲剧,相反,与其他女性比较起来,姑姑身上的悲剧更让人怜悯。
三、结语
我们的忏悔不是讨饶,应建立在人的自尊之上[3]。小说中各类女性的悲剧如同彻夜嘶吼的蛙鸣一般,再没有更好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回顾那种源于生命的痛。那一代女性的悲剧已经无法用任何一种赎罪方式抵消,她们被印在那段历史中,只要历史还在,这些冤魂的吼叫就不可能被平复。
即便脱离了这部作品,这类想法也是十分悲观的,世界本身就应当被怜悯地看待。佛经有云:观一切有情,自他无别,同体大悲。也许只有将他人的苦痛与自己等同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女性的悲痛,才能更深刻地领悟莫言在《蛙》中想要表达的悲悯情怀。
[1]廖先怀.生殖崇拜视角下原始生命的回归——莫言《蛙》之探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6):68-70.
[2]柔石.为奴隶的母亲[C].高永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小说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07-127.
[3]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J].东岳论丛,2011(11):18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