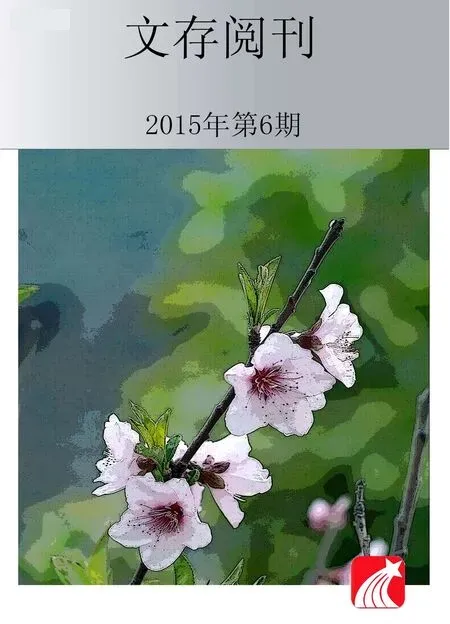我读三毛
□杨蓉
我读三毛
□杨蓉
一
说起三毛来,恐怕无人不晓。其散文在过去年间,曾风靡台湾、大陆两地,任你刻意不刻意地,总会吹到耳朵里一些。前一段儿,我偶尔在网页上“看”到据说是三毛生前最后的一段电话录音。那声调,细软而清澈,脆如童音,甜若蜜饯,一下子便勾起了我读她的书的欲望。于是,急慌慌从网上买来一套她的集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的,共十一册,点灯熬油地翻阅起来。或者,对于一个已近不惑之年的人来讲,才刚开始阅读和热衷于“三毛”,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了。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年龄与阅历作为基础,反倒能读出一些少年人体悟不到的好处来。
三毛的文字,写得很“自然”。这个自然不是大自然的自然,是说她写得很真实,笔调与文风很随意,怎么想就怎么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似乎根本看不出排兵布阵的痕迹。说得再具象一点,就是她的文字像森林,不像园林。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不真实的东西她是写不来的。也就是因为这些文字是自己的亲历,是自己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所以很能感动到人。当然,过于真实的文字,也有它一定的弊端,那就是略乏修饰的美感。不过,懂得欣赏的人,会更多关注这文字真诚的内在与韵味,而忽略这种美中的不足。
三毛的文字,也很“性情”。所谓性情,就是说她的书写总在一刻不停地表达自己的心,展现自己的心,也忠于自己的心。她写平常的琐碎,总有意无意就会流露自己的内心与性情。就连旅行的时候,她也时时不忘己心的喜恶。比如《万水千山走遍》里写厄瓜多尔之行时,某个黄昏,她爬上城外小山丘的公园,坐在大教堂的前面,呼吸着凉薄的空气,望着天上不断变换着色彩的云,想着白日的所见,旅行的疲累渐渐舒缓下来的一瞬间,她说:“再没有比坐看黄昏更使我欢喜的事情了。”你听,绕了一大圈子,马上就又回转到了自己的内心体悟上来。然而,所有性情式的文字,只一点我不太喜欢,就是太直白,或者过于肆意的抒情。再比如,同为《万水千山走遍》里,她见到一个卖爆米花的人三餐不济、居无定所,就说了这样一段话:“我静静地听着他,看他擦泪又擦泪,那流不干的眼泪里包含多少无奈、心酸和乡愁。”这样的句子,抒情性非常强!怎么读着都有种中学生作文的感觉。或许是年岁渐长,或许是习惯使然,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常常习惯于收着笔,收着感情。所以,从这一点上论,我倒不太喜欢她类似的文字。
三毛的文字,除了“自然”、“性情”,还更加“生活”。她的文字,着眼在生活上,落笔在生活上,生发在生活上。比如,她大多的文字都在讲述吃、穿、住、行,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的事,都很琐碎,很具体。无论是《雨季不再来》中那个少女,还是《撒哈拉的故事》中那个少妇,或者是《梦里花落知多少》中那个失爱的女子,她都将自己的欢乐与悲痛、幸福与坎坷,毫不避讳、毫不保留地书写出来,叫读着的人,几乎是跟着她的生活看完她的集子。就连她的旅行散文,撒哈拉、马德拉、墨西哥……她一路走来一路书写,皆似离不开一日三餐,离不开吃、喝、拉、撒、睡。这些个事,件件可谓是行程巨细,热闹非凡。倒是所到之地那种生硬物态的东西,很少描绘。而且,像类似秘鲁之行中,她与坐对面的两个妇女那样的互动,在她的旅行文字中随处可见。并且,但凡是自己路遇的,擦肩的人、事,都离不开“我”热烈地参与其中,大有那种万物美好,她在当中的感觉。
三毛这套文集共十一册,我最喜欢《我的宝贝》一本,其中展示了她一生收藏的琐碎物件,有盘碗,有布帛,有脸盆,有陶罐,有酒袋,有衣服,有配饰等等,并一物配一短文,故事性很强,很有读头。其中,我比较喜欢那两个印第安人的布娃娃,说是她在南美洲旅行时买到的。那两个布娃娃是一种手织布缝制的,是两位母亲,一个深情有点窘,另一位则眼带笑意。一位母亲怀里抱个孩童,另外一位母亲则怀里抱着一个,背后背着一个。两个布娃娃母亲的样子,都很有意思,也很温馨。我不知道三毛为什么会喜欢这对布娃娃,也不想去揣测,只依稀记得,她在《不死鸟》中说:“我只想是个实际的人,我要得着的东西,说起来十分普通,我希望生儿育女做一个百分百的女人。”遗憾的是,她最终没能实现这个对于女人来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愿望。
二
说三毛,如果不提提她与荷西的爱情,恐怕是不行的。
我们先来读几封集在《稻草人》里的信,那是三毛回乡探望父母期间,荷西远隔重洋寄来的:“我十分想念你。你走以后我还没有吃过东西,邻居路德送来一块蛋糕,是昨天晚上,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要等你平安抵达的信来了才能咽下。”“这是你每天该服的药名和时间,我现在做了一张表,请按表去服用。”“快回来吧!我希望把有生之年的时间都静静地跟你分享。短短的人生,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啊!快快回来啊!我想念你!”“你要我怎么求你?你以前种的花都开了,又都谢了,你还没有回来的消息。”
你听,荷西,一个西班牙小伙子写的情信,其中那个辗转、牵挂;那无尽的相思、抵死的缠绵;那个叫爱情折腾得无抓无拿的劲儿,似乎一点不逊咱们的大作家沈从文先生写给他那位三三的。而且,这信几乎是一天一封。后来,眼见恳求是没有办法了,聪明的荷西居然杜撰出一个美女邻居,每日“钻”进他的信文,照顾他,陪伴他,与他朝朝暮暮过起了日子,这才激起了三毛的醋意与保卫爱情的力量,迅速地乖乖地回到了丈夫的身边。
三毛与荷西的婚姻生活,那些吃喝、摆设;两个人之间的斗嘴、游戏,通过三毛文字的生发与升华,琐碎而美丽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叫看过的人无不生出赞叹的心意及羡慕的口水——哦,原来平淡的婚姻生活,竟然也可以过得这么浪漫,这么有情调呀?就拿他们的结婚礼物来讲,不是什么鲜花、锦衣,也不是什么钻戒、豪车,居然是一副沙漠中风干的骆驼头骨!这真是闻所未闻之事。那个骆驼头骨,在《我的宝贝》里有展示,白玉一样的头骨上,两个眼洞黑黑的,小小的,像是在微笑一样,流露着无限的温情,叫人第一眼看见,就喜欢得不得了。想来,能够想到送这样别致的、有意思的、绝无仅有的结婚礼物的荷西,该是个多么有情多么有心的人。
当然,荷西的浪漫情感绝不仅限于此,他会将三毛拾来的棺材做成家具。他甘愿被三毛骗,吃她口里所言的止咳中药(牛肉干)。他作为一名潜水工程师,婚后在海边工作,上班的地方离他们的家有好一段距离,可每到工地检修或其他机会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他都会脱掉潜水服跑回去看三毛。他和她在水边游戏,他会轻按她的嘴唇,然后潜到海底。荷西潜水本事很大,可以在水下憋气很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深谙水性的人,后来,却不幸溺水而亡了。
就像读《浮生六记》不忍读到芸娘的死一样,读三毛的文字,我也最怕读到荷西的死,怕读到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里那歇斯底里的大悲,及抵死难舍的大恸。每每捧起这些文字,回望她与他六年的婚姻生活,就不自禁地想到四个字:情深不寿。
三
三毛这个人,似乎比她的文字更耐读。
三毛是个很热情的人,性格大大咧咧的,感觉永远是个十八岁的青春少女,她似乎永远精力充沛,所以总在不断地行走,并不断地交往不同地域不同性格的朋友。自己病了,给自己开药。沙漠里的人病了,她也敢给人家开药。她还敢给产妇接生,也帮助过羊产崽。就连自己第二天结婚了,新郎问她要穿什么衣服,她的回答仅是四个字:随便穿穿。
其实,你如若沉下心来细细斟酌,就不难发现,三毛这种大大咧咧的脾性背后,却还有着十分细腻、感伤的情怀。比如,她听演讲会落泪;遇见教堂,会跪拜,也会落泪;甚至看见油菜花开得美丽,也会落泪。还有,她总乐意像个孩子一样,在自己父母面前撒娇,在荷西面前撒娇。《背影》一文里,她这样描写母亲的背影:“母亲腋下紧紧地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地各提着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地弯着小腿再慢慢一步又一步地拖着。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从她这细致柔软的笔调,就不难窥见她柔婉而细腻之心。
三毛的外象与其内心也是一物的两面。她这个人,看似独立而果决,为了认识沙漠,就独自背包去了沙漠。她热爱旅行,一生走过了五十多个国家。可是,她的这种独立与果决的后面,更多的则是对亲人、对家庭的无限依赖。就拿她的恋情来讲,从十几岁到几十岁,她都是在不断地投入爱情,又不断地失去爱情里过活着。频繁的感情更迭,在一个人来讲,可充分看出其内心总在寻找一个依附点,她完全可以忍受贫困的物质生活,却极度不能使感情有所空缺。再拿她给父母写的信来说,无一件事不是具细讲来。有一封1973年12月26日的信,她居然把自己圣诞节前后24日、25日、26日三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都一一讲来,那个啰嗦劲儿,就像个长不大的孩童。其实,人越是这样事无巨细地表达,就越说明她恐惧孤独,需要不断地倾诉,需要在与人的频繁唱和中才能生存。
三毛除了热情,也很深情,她对每一段感情都奋不顾身地全情投入,她的内质里似乎天生地具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结。十几岁时,她爱上了学校里的光头小男生,每天都会在暗夜中祷告。二十几岁时,真正意义上的恋爱,爱得轰轰烈烈,分得却落落寞寞。三十岁时,满心欢喜地找到了要嫁的人,怎料,那人在婚前病故了。她无力承受,用自杀来解决。幸在大难不死,幸在又遇到了荷西。而荷西恰恰又是个极温情的男子,他宠她,让她,纵容她,令她心里热烈而奔放的情愫有所附着、展呈,有所宣泄与寄托。可是,好日子才刚开始,荷西却又死了。
世间之物,凡用之过度,必易折、易损,不能持久。感情是,生命何尝不是?
三毛在《不死鸟》一文中说,荷西走后,她便深陷沉痛的思念之中无法自拔,甚至万念俱灰。有一天深夜,她与父母亲谈话间隙,忽然提及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她的母亲听了这话,眼泪顿时迸了出来,但却不敢说一句刺激她的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喃喃地说:“你再试试,再试试活下去,不是不给你选择,可是求你再试一次。”那一刻,三毛的泪水如瀑布一样地流出来,坐在床上,不能回答父母一个字。
我想,她能与父母说出那样的话,定是思之又思之后的决定。说过那话后,她也一定听从了母亲的哀劝,努力地试着去活下去,试了,又试,再试。然而,终究还是试不下去了……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电脑里反复播放着她生前的那最后一通电话的录音:“眭澔平(其友—引者注),我是三毛,你在不在家?人呢?眭澔平……你不在家……好。……我是三毛……”那声音,细细地,柔柔地,可显得很急切,很失落,也很无奈,像急需找个人来倾诉一番、唱和一番。可转了一圈,什么人也没找到。最后,只能自己孤独地呆着,孤独地面对暗暗长夜的黑。
人心是个深渊,无人可抵达,只能自己临崖,自己解决。
就在那一晚,她用一条丝袜,结束了生命,年仅四十八岁。
搁笔之际,忽然想起在《亲爱的三毛》里,她回复一个读者的来信时,说到这样一句话:“你又问我,不快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以死为解脱?我很诚实地答复你:有过,有过两次。可是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死,并不是解脱,而是逃避。”这封回信,没有时间落款,无法确定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可是,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死亡的路,她说死不是解脱,是逃避,那么,三毛又在逃避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