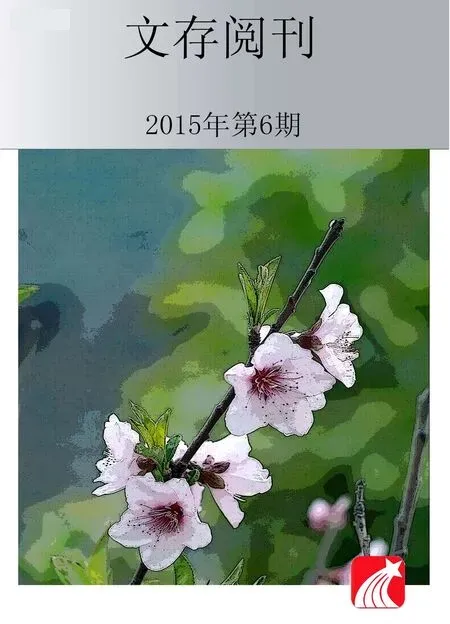张伯驹先生的文化活动与《春游琐谈》第七集
□薛永年
张伯驹先生的文化活动与《春游琐谈》第七集
□薛永年
张伯驹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收藏鉴赏家、词人、京剧名票、京剧学者、书画家,而且是文化活动家。他的文化活动建树很多,我关注过有两个重要活动,现在谈一谈,不是作为研究者去评论,而是作为见证人来叙述。顺便也报告一下《春游琐谈》的有关问题。
两大文化活动之一是发起成立书法研究社。1956年,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张伯驹与前清翰林、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云诰发起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该研究社成立于那一年的9月16日,隶属于北京市文化局。不久就搞了书法比赛,我也入选了,所以印象很深。
现在看来,这个书法研究社的成立,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几乎成为主流意识,二是软笔换硬笔硬笔换电脑的书写方式之变。中国画人才尚有美术院校中的中国画系科培养,而书法人才的培养一度只能寄生在国画科系中。北京书法研究社,是在书法教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立的研究传承中国书法艺术的组织。
这个书法研究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群众性的书法组织,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前身。它才一成立就搞书法展,办讲座,奖掖后学,从孩子抓起,组织北京中学生书法比赛。我当时就参加了比赛,展览和颁奖由张伯驹亲自主持,地点记得在厂桥。这个组织为书法艺术的继承发扬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奠基性的工作,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赢得了社会各界及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周总理还担任了名誉社长。
另一大文化活动是成立“春游社”并且组织编印了众多学术精英参与的《春游琐谈》。张先生通过约稿,联系了众多的学者、专家、文化人。这些人中,有八九十岁的前清翰林、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云诰,民初国务院秘书长、历史学家、文献版本学家卢慎之,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新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也有年轻的四十出头的红学家周汝昌等。
《春游琐谈》属于笔记杂著类的著作。笔记杂著古代就有,以随笔记录为特点,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古语,述史事,写情景,由分条的短篇汇集成书,但从来都是一家的著作,不是诸家的合集。这种文史体裁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以来被边缘化了,不大有人写了,也淡出了主流文坛,很难有机会出版。
1961年张伯驹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工作之余,他和当地学者于省吾、罗继祖等人,组织了“春游社”。所以叫春游社,一是他收藏过《春游图》,二是他来到春城工作。春游社除去雅集,再就是并邀京、津、沪等地的一些学界朋友,分别撰写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等随笔文章,在1961至1965年间,陆续编成《春游琐谈》六集,在北京油印印行。
张伯驹发起并主持的《春游琐谈》,不仅联系团结了各地的文史艺术专家,以编辑笔记刊物的形式推动了老一代精英学者的随笔写作,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特别是没有写入学术著作的口耳相传的文坛掌故和见闻,而且开创了多家笔记杂著合集的体例。
《春游琐谈》的自序自署壬寅,也就是1962年,应是第一集编辑过程中或编好后所写,以往人们根据自序的时间以为《春游琐谈》第一集印行在1962年。其实不对。我发现,每一集最后都有作者简介,一一注明别字、籍贯和年龄。第一集张伯驹自注年龄六十六岁,应该是虚岁,按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计算,加上六十五岁,可知第一集编成在1963年。第一集印行后又陆续编成并且印行了第二集到第六集。按第六集作者简介张伯驹先生的自注年龄六十七岁,可知第六集编成在1964年,听说印出来已是1966年了。
在二十世纪文化史上,以上两事应该大书一笔。
关于《春游琐谈》第七集。我接触《春游琐谈》第七集在1969年,当时该书在吉林省博物馆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军宣队领导,组长是搞历史的苏逸兰女士,文革前就是党支部委员。组员之一是出身贫农的刘振华,他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也是1965年参与工作的,与我关系很好。刘振华发现第七集后,就把这个稿本拿出来给我看,我还抄了一些。他为什么给我看呢?说起来这与文革初批判张伯驹先生的时候把我顺带触及了一下有关。
1965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因为只专不红,思想不纯正,被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大四的时候,我被系主任金维诺先生推荐整理书画鉴定家张珩讲课的笔记,认识了奉命综和整理张珩遗著的王世襄先生。在去东北工作前,我来到芳家园,向王世襄先生拜别。王先生说,早听王逊先生说过了,那里的第一副馆长张伯驹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为你写了一封信,拜托张先生关照你,你先看一看,我随后寄去。我记得信里说:“薛君永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成绩优异,旧学亦好,倘加培养,可望有成。”
同年9月,我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不久打听到馆长室在西安大路小楼,于是前往拜见。张伯驹先生说,已收到王世襄先生的来信,不过馆里早已安排年轻人随我搞书画了,你先按馆里安排努力工作吧。同时送给我《春游琐谈》和《洹上词》等书。后来又同他谈过一次,是请教书法史。不久他就回北京了。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张先生被从北京召回来,遭受严厉批判。我奉命抄大字报,不少都是批《春游琐谈》的。有一次开批斗大会,人事科长发言,把我也扫了一下。她说:“有个大学生,由北京大右派介绍我馆给这个大右派,这个年轻人,你要注意呢。”
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知道了我与张伯驹先生的这层间接关系,以及我的爱好和专长。文革深入后,馆内学者虽然也批张伯驹先生,但是知道他有学问,虽然也批《春游琐谈》,但是知道《春游琐谈》的文史资料价值。所以才主动借给我第七集,给我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春游琐谈》第七集是稿本,手抄在荣宝斋出售的瓷青封面元书纸朱丝栏本子上。封面有张伯驹先生题签:“春游琐谈七集上”,里面收入十五篇文章,从字迹看,都是张伯驹先生手抄的,最后一篇《跋南园诗文钞》,好像没有抄完。
第七集的内容,与前几集基本一样。在《春游琐谈序》中列出的“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八类内容中,只是金石与风俗没有文章,其他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游览都有文章。书画有:《卡尔姑娘为慈禧太后画像》、《秋林高士图轴》、《元颜辉煮茶图》。考证有:《朱明镐<史纠>》、《千元十驾非十架》。词章有:《名士循例文字》、《樊山诗集跋》、《跋南园诗文钞》。掌故有:晚清琉璃厂书商交结官宦的腐败案——《记清末厂贾李钟铭案》、科举制度乡试细节——《磨勘试卷》、晚清的尊经教育——《王湘绮与四川尊经书院》。轶闻有:宫廷秘闻——《慈禧太后之侄女》、锋利的谐谑文字谭概的续编——《谭概杂录》。游览有:《苏州寒山寺》。
第七集的文章中,张伯驹三篇,罗继祖(罗振玉之孙,辽史专家)三篇,恽宝惠(清末授陆军部主事,禁卫军秘书处长,北洋政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新中国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两篇,戴正诚(著名诗人,先后供职于北洋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抗战中,任县议会议长)两篇,其余陆丹林(早期同盟会员,诗人团体“南社”成员,先后主编许多文史和书画刊物,也是上海国立艺专、重庆国立艺专等校的教授)、卢慎之(第一次为春游琐谈供稿的当时已经九十岁的卢慎之,是清末留日海归,法政科举人、民国初年国务院秘书长,后来专事历史研究,亦精通日录版本学)陈莲痕、傅武野、及跋南园诗文钞的不知名作者各一篇。
《春游琐谈序》中提到的在长春的朋友中主要作者有六人:于思泊(省吾)、罗继祖、阮威伯(鸿仪)、裘伯弓(文若)、单庆麟、恽公孚(宝惠)。第七卷仍有三人提供文章:本人、罗继祖、恽公孚。
我虽看了这本书,也抄过与美术有关的篇章,但没抄完,就还给了专案组。1969年冬或1970年春,张伯驹先生下放农村,不少馆员去了五七干校,我们搞美术的几个年轻人留下办展览。专案组即将解散时,组长苏逸兰就把几本《春游琐谈》包括第七集交给了我,她说“对你也许会有些用处”。
我来北京读研究生随后留校直至1985年我赴美国作研究员时家属来京,很多书籍仍然留在长春,举家迁京后一些纸板的书箱开始寄存他处,新世纪则存在地下室中。去年大水抢救地下室纸箱中的书籍本册,我才发现此书依然存在,只是略有水浸。我一直没有时间研究,已经出版的《春游琐谈》,只有前六集,现在就借纪念张伯驹先生诞生一百一十五周年活动之际,把该书稿本还给张伯驹先生的外孙楼开肇先生,也算是替苏逸兰女士和刘振华先生等实现完璧归赵。
(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副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兼理论委员会主任。此文作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