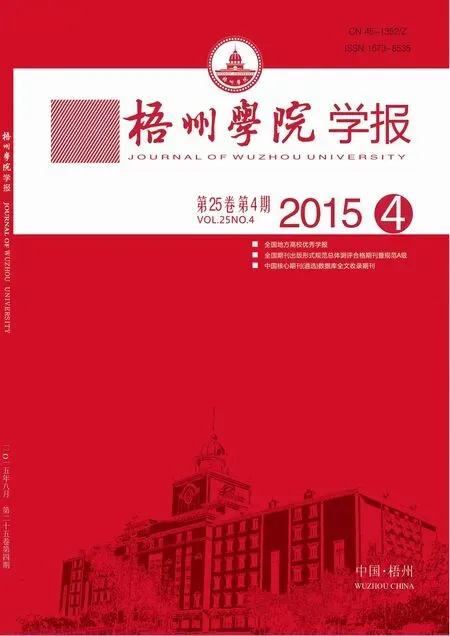建构诗与现实生活的通道
——论世纪初非亚的诗歌创作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建构诗与现实生活的通道
——论世纪初非亚的诗歌创作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非亚在世纪初自觉调整诗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力求在自己的诗歌中重建诗与现实的通道,通过客观、真实、克制的生活流书写构筑“当代性”“当下性”和“现场感”,塑造了新的现实,为当代诗歌建设中诗与现实的关系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非亚;诗;现实;通道;世纪初
诗与现实的关系一直缠绕于诗歌的发展历程之中,诗人们在二者关系的问题上由于不同的认识而做出不同的回答,从而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与特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诗人们重新认识与调整诗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主张诗歌回到生活本身,呈现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一诗学主张与倡导引发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转型,影响了诸多诗人的创作理念与实践。深受“第三代”诗歌影响的非亚对于诗与现实的关系拥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感的诗歌”[1],因为在他看来,“现实是艺术的通道”[2],是诗的通道,他甚至更明确地指出:“诗直接就是生命本能和生活方式,强调诗歌与日常生活的维系性。”[3]因而,非亚自觉调整了诗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他力求在自己的诗歌中重建诗与现实的通道,通过客观、真实、克制的生活流书写构筑“当代性”“当下性”和“现场感”,塑造了新的现实,为当代诗歌建设中诗与现实的关系建构
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一、生活流书写:诗与现实的打通
非亚在其诗歌创作中极其注重诗歌与现实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很依赖生活对诗歌的那种摩擦力[2],对此他曾多次谈及:“我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有赖于一种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4],“现实给了我写作的素材、灵感和思考;现实类似粗砺的磨刀石,能将一种迟钝的东西,转化为一种锐利的东西,没有现实作基础,我这些年的诗歌就无从谈起。”[1]正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介入,非亚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生活流书写方式的特征,非亚正是以此打通了诗与现实的通道。
“生活流”书写的概念最初源自电影艺术理论。德国当代著名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曾指出:“这种影片倾向于表现外部存在之无涯。……它有一种照相所没有的近亲性,即对生活的连续或‘生活流’(它当然跟没有尽头的生活是一回事)的近亲性。‘生活流’的概念包括具体的情境和事件之流,以及它们通过情绪、含义和思想暗示出来的一切东西。这意思是说,生活流主要是一种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连续,尽管从定义上来说,它也延伸到精神的领域。”[5]可见,克拉考尔所言的“生活流”是一种电影艺术的传达方式,侧重于反映人的外在行为与外部世界,但并不排斥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这种如实再现人的外在世界的传达方式正与侧重于自我表现人的内在世界的“意识流”方式相对应,后来被引入诗歌领域成为诗歌书写的重要方式。非亚的诗歌书写便侧重于人的外在行为与外部世界的再现,注重社会生存态的准确把握,是典型的生活流书写。
叙事因子的增强与抒情成分的削减是非亚进行生活流书写的重要特征。非亚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中国诗歌传统中长期占据主导位置的“抒情”进行了规避:“不要轻易地去抒情,尤其是自我感动、自我麻醉的那种抒情。那种情感往往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看上去似乎美丽,但却使你失去理智,它表现出来的做作、虚假,是诗歌写作的毒药之一。”[6]因而,他的诗歌基本上拒绝抒情,而突出叙事性,自觉在其诗中“引入了叙事或陈述的性质”,“转向对时代生活的透视和具体经验的处理”[7],常借事件流程而非情绪流程呈现诗意,如《每天的一些记录》。
刷牙4次
洗脸3次,去卫生间
8次,坐电梯
6次,打电话9次
想念一个人3次
躺到床上2次
坐下来8次,喝水5次
在窗口眺望1次,上楼梯
3次,看报纸1次
因一件事自卑1次
在纸上,写写画画
5次,听音乐3次,洗澡
1次,跑步1次
抱儿子5次,吃饭
3次,深夜脱掉衣服,做爱
1次,在床上
和自己探讨
死亡1次
非亚几乎是以列提纲或计划的形式将每天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流水帐似地罗列、铺陈,包容日常生活经验和琐事,毫无抒情但突显了叙事性、陈述性。《值得记录》《青年时光》《计划》《空白之处》《木偶之诗》《火车的旅行》等诗都是最大限度地收纳日常生活的经验,以一种漫不经心、深藏不露的叙述语调和描述方式传达内心对平淡、细碎的日常生活的感受。在淡化抒情的叙事性建构中,非亚承续了90年代诗人“用陈述话语来代替抒情,用细节来代替意象”[8]的话语方式,善于以生活细节呈现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凸显真实性、客观性与现实性,如《傍晚,几件事》在一种平淡的陈述
话语中通过吃饭、洗内裤、搬植物、擦洗羽绒衣、奶奶给儿子涂药膏、晾晒毛裤、老女人看电视等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细节拼贴,传达了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与生命感受。《矛盾》抓住“我”站在灯光下犹豫往北还是往南走的瞬间,呈现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矛盾状态;《一些日子》中则将“已过了十二点我从林苑宾馆出来,沿华西路向东走”“树站立着,我们穿过它们之间的虚无”“我们笑着,好像云完全不存在”“喝乔麦黑啤”“我醒过来,躺在床上想一些事”等日常生活的细节、瞬间印象组合、陈列,组装成了“日子”的现实状态;《选择》《7月31日和黄彬李书锋以及小徐在街边小饮谈到死亡》《车站即景》《江南路,我看见一个长发青年在单杠上抽烟》《一整晚都听到马达声》等诗都是捕捉瞬间印象或日常细节,以陈述话语和细致的描述表现日常生活的经验、感受与体验。
非亚的生活流书写是以目击者与参与者的身份进行的。非亚与“第三代”诗人反拨朦胧诗的代言人姿态一样,以平民身份介入诗歌,抒情主人公由神、半神、英雄、准英雄而降为普通人、平民,以目击者和参与者而非鸟瞰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呈现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如《7月31日和黄彬李书锋以及小徐在街边小饮谈到死亡》是诗人直接以参与者的身份出场于“街边小饮”和“谈论死亡”的现场。《信》《我解放我的裸体》《一种我也想要的》《在芝加哥,昨天下午的一段路》等诗中诗人都是诗歌现场的主角或参与者,凸显了诗歌事件、场景的真实性、现场感。而《闪光的夜》《车站即景》《江南路,我看见一个长发青年在单杠上抽烟》《一整晚都听到马达声》《他们要把一大块铁弄到货车上》等诗则是以目击者和见证人的身份介入诗歌现场,增加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在生活流书写所采取的诗歌叙述中,非亚还追求一种卞之琳在翻译外国诗歌和对照古典诗传统时所重新发现的“亲切”特征:“这里没有‘陌生化’,而是熟悉化、亲密化,跟它亲热亲热”[3],为了形成这种亲切感,非亚将日常口语入诗,如“有时我觉得我太平静了/太正常了/太那个那个了”(《致敬》)、“哈哈,太有意思了”(《局限》)等日常口语入诗的情况在非亚诗歌中随处可见,读来亲切、真实、熟悉。《父亲节,其实应该一起吃餐饭》是非亚诗歌中将其各种语言方式、特点综合呈现的典型诗例,他以对话(“我说,过两天我们去藤县,你也来吧,之后,我问他/在干嘛,他说吃饭,和爸爸一起,在外面/因为今天,好像是父亲节//哦哦,我说,那挺好,有爸爸总是挺好”)、自言自语(父亲节,其实应该一起吃餐饭)、旁白(“今天是你爸爸的节日”)、内心独白(有爸爸总是挺好,有爸爸应该一起去外面/喝一点啤酒,吃一个晚饭)等话语方式展开,没有华丽繁复的辞藻,没有煽情的语句,都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语,由此形成了“亲切感”。《1951:合照》则纯粹用平实的描述、介绍的语气再现翻开旧照片的生活场景,亲切自然,充满生活气息。《河》《局限》《早晨!早晨!》等诗都是用质朴而真实的讲述、平静而克制的叙事语气和生活场景的还原再现具体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人生经历,呈现日常琐碎的生活真实,呈现生活本身的自在、重复、平淡无奇的特点。
此外,非亚在诗歌语言、形式的处理上非常自由,与他作为“自行车”的倡导者所倡导的“自行”的诗歌理想与自由、自在的诗歌诉求是一致的,如《我觉得妈妈是勇敢的》一诗中“当衰老像一件被水洗皱的外衣”本是一句话,却被非亚拦腰截断为“当衰老像一件被水/洗皱的外衣”,“妈妈站在窗口前乘凉,看着她的孙子,咯咯地笑”则被截断为“妈妈/站在窗口前乘凉,看着她的/孙子,咯咯地笑”,再如“我觉得妈妈/是勇敢的”“死亡这样的问题,就像天外/来客,从未被妈妈/在饭桌和床头前提起”等诗句,分行、断句都非常自由随意,毫无拘束,也没有任何修饰,完全是生活语言的自然流动状态,这正是非亚进行生活流书写时保
证生活“流”的重要屏障。
非亚以生活流书写的话语方式在其诗歌中客观真实地再现了生活本身的流程与生态,打通了诗与现实的通道,建构了诗与现实关系的一种可能形态。
二、“当代性”:诗与现实的对接
非亚在其诗歌中非常强调“当代性”,他认为“如何体现和反映诗歌当代性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诗歌问题,而“诗歌当代性的展示,其目的无非是把诗歌和现实生活更敏感地对接起来”[2]。因而,在非亚看来,“当代性”就是诗与现实的对接。事实上,非亚所言的“当代性”更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当下性”与“现场感”。非亚总在诗中书写离自己的生活颇为切近的内容:“我的写作与自己的生活比较接近,会写到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9],他善于对客观事物、事件和过程进行现在时式的、具体的呈现,通过对各种平凡、琐碎、司空见惯的细节、现象的再现,反映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当下情状,凸显“当下性”与“现场感”,从而呈现“当代性”。
非亚话语场域中的“当代性”与李少君在评价90年代诗歌时所提出的“现时性”具有相通性,都强调对现实与当下的关切,这个“现实”“不是高调的伟大的所谓历史性事件的‘现实’,而是一种切近自身与个人的经验的或切近生活的客观的现实”[10]。“现时性”与“当代性”都属于时间性概念,强调“现时”与“现实”的对接,“时间”成为“现时”与“现实”对接的重要标识。非亚的许多诗在标题中便出现“时间”,如《7月31日和黄彬李书锋以及小徐在街边小饮谈到死亡》《早晨!早晨!》《夜晚9点》《2月1日,给爸爸的一个电话》《母亲节》等,在诗中,非亚将捕捉到的“现实”置放于某一特定的“时间”维度中,以不动声色的叙事和描述,在视线、场景的组接、切换间相对客观地呈现“现时”的、当下的、现场的现实生活,从而凸显现实之“真”,使诗与现实的通道相对接。
在非亚的诗歌中,更能体现非亚诗歌的“当下性”“现时性”“现场感”的重要标志物是“场所”,这是非亚诗歌中非常独特而醒目的一个意象系列。这些“场所”不是朦胧诗中暗示、隐喻的载体与漂浮的能指,而是其现实生活发生的现场,是完全卸载了文化、政治、历史意义与内涵的“场所”本身,因而现场感、真实感更鲜明,由此他在诗歌中真正回到了事物与存在的现场,使诗与现实真正对接。对此,非亚自己拥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诗与生活关系的明确,或者说生活对于诗歌的重要,使得对生活的热爱成为写作的一个前提;在具体的写作中,作为一种现象学的产物,有关诗歌‘场所’的问题也逐渐被意识,诗歌作为一种虚无之物,往往需要依赖于一个具体的‘场所’才开始得以生长,通过对‘场所’的激发,与‘场所’有关的一些细节的关注和描画,诗歌得以复活和重新记忆,因为生活本身广阔而巨大,而具体细微的‘场所’一旦锚固进诗歌,生活的那艘船就开始得以稳定下来,成为具有特殊存在意义的标本。”[11]在他看来,“场所意味一种更加具体的地域,而不是一种僵化的文化符号,当下、当时、地点、当场、在场,这些成为我们表现的内容。”[1]非亚的诗歌里经常写到南宁与南宁的道路、建筑物、地点等各种“场所”,对此他是有意识地如此去做的,这些地名、地点在诗行间的出现仅仅因为它们是诗中所叙述的生活发生的“场所”,所传达的信息不带有任何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而只是连接了诗与生活的关系,非亚自己对此深有感触:“(诗中)有大量的地名、地点出现,这些具体的地点,其实是和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是对生活的关注,激发了我们对于场所的关注,而不是文化符号的关注”[1]。正是这些出没于诗意、语词间的“场所”本身,连接了诗与生活,连接了诗人的诗意与现实,如“每一次走在大街,我都会在脑子里/这样想着:我会在每个/礼拜五,回北湖看你们,我会去/乘车,在秀厢路下来,/横过马
路,买水果,穿过/一幢幢楼房,按门铃,/走上楼梯,我会看着你们,/打开门,早早等在/那里,微笑着/……”(《给父母》)中的“北湖”“秀厢路”等实指地点的名词是诗人将内心的诗意与牵挂父母、看望父母的生活现实对接的“场所”,这些地名的存在使诗中叙述的现实更真实,更具有现场感。《江南路,我看见一个长发青年在单杠上抽烟》中的“江南路”这一具体地名使“我”所看到的“长发青年在单杠上抽烟”这一瞬间印象具有了具体、实际、真实的指向,而非艺术化的“失真”。《暮色中的城市》中的“南宁高速公路收费站”“森林公园”,《上帝也许只是一种运气》中的“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教堂”,《去小酒馆》中的“古城路”,《沿溪路》中的“沿溪路”“友爱桥”等都不是地域性的体现,只是事件发生的“场所”,已脱却了任何文化、历史、地域的气质,正如非亚所坦承的:“我早期受‘第三代’的影响,出于对现代主义的追求,对地域、本土文化这些过于传统的东西,本能上是有些排斥的。”[1]陈祖君对此曾有敏锐发觉:“非亚诗中所写的华东路、南京路、佛子岭以及他的父母、住房等,均刻意消除了杜撰的成分。在他看来,现实的呈现和转换比杜撰更重要,更富‘当代性’。”[12]
非亚通过“时间”“场所”等意象序列的设置使诗与现实对接,从而建构了其诗的“当代性”“当下性”和“现场感”。
三、重造新的现实与诗的建构
虽然非亚强调诗与现实的密切关系,采用生活流书写的方式呈现现实,构筑“当代性”,但他并非如于坚彻底拒绝隐喻、象征,拒绝艺术升华,而是原生态地“呈现”生活,他认为:“从生活到诗,不是直接的照搬,一旦和语言沾边,就涉及到新的转化。”“面对同样的现实和生活,其实涉及到诗歌表现和表现方法的问题。”他所欣赏的不是照搬生活的诗,而是“带有表现色彩建立于现实之上或者从现实生长出来的诗歌”,他认为:“仅仅只是知道了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够的,来自现实和生活唤起灵感的东西,仍然需要艺术的再现和表现,以便将现实以一种新的方式固定下来,或者说,重新塑造一种新的现实。”[2]可见,非亚在其诗歌中不是要简单地“呈现”现实,而是要通过“新的转化”和“艺术的再现和表现”来“重新塑造”新的现实,从而实现“诗的建构”。显然,非亚是意识到诗的艺术的重要性的,而非如于坚、韩东等“第三代”诗人一样拒绝诗歌艺术的升华。
至于如何“重新塑造现实”,如何“转化”,非亚归结为“发现能力”和“感觉能力、感受能力”:“转化,意味着消化,但消化和转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它不是一个等在那里的胃。比如,我每次写下的一首诗,几乎是瞬间完成的,语言、材料、事物、发现,一起构成全部,没有前后,不分彼此,完全依赖于直觉和一种技法。在这过程中,我感到,发现能力构成了一个诗人彼此之间的区别,以及诗作水平的高低。这种发现能力也可以说是感觉能力、感受能力。”[2]具体而言,非亚“完全依赖于直觉”和“技法”。非亚强调的“直觉”具体体现为“瞬间完成”“未写而已完成”,与废名对于诗歌创作状态的阐释一脉相承。废名曾强调诗的发生要“不写而已成功”“当下完全”“当下完成”[13],并曾以雕刻家雕刻艺术来打比方进行形象说明,这种观点虽然不无偏颇,却肯定了诗歌思维发生时的运行状态。非亚肯定这种状态,以裁缝打比喻进行了阐释:“这好比一个裁缝,或者时装设计师,面对布匹,不仅仅只是考虑做出一件衣服,而是如何做一件衣服,做出一件什么样形式的衣服,如何开始剪第一刀,在剪第一刀时,可能那件衣服,已经在裁缝的脑子里想清楚了。”[2]非亚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践行了这种诗观,认为自己每首诗都“几乎是瞬间完成”的。当然,这种“瞬间完成”肯定是经过前期长久的酝酿与准备才能喷薄而出的。
在新的现实的重新塑造与诗的建构中,非亚还极其强调想象力的作用。与于坚拒绝想象不一样,
非亚强调想象力:“想象力也是一种结构与形式,并且是,更大的结构与形式。”[2]并对想象力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想象力除了语言,还包含结构,培养一种语言的想象力,还不如培养一种结构的想象力,这个更难。”[6]非亚的诗充满了想象,如《死亡是一节一节的火车》《上帝也许只是一种运气》《死亡像一根接收不了信息的天线》等诗,将“死亡”与“火车”,“天线”“上帝”与“运气”做“远取譬”,将毫无关联的意象拈合为一体,若没有非凡的想象力是无法做出如此精辟的比喻的。在诗中,非亚总纵横驰骋联想、想象,以高强度、高跨度的跳跃性构筑富有想象力的诗意空间。颇有意味的是,非亚总在诗中想象自己年老后的景象,如《老》。
我的衣服
越穿越多
看上去,缺少烫洗
越来越皱
非亚将自己年老后的形象进行了想象,这种想象并非虚幻的、杜撰的,而是根据当下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形象来描述;《杂乱的……》一诗中更是形象地呈现了一个“老年的我”:“一个晚会的女主持邀请我上舞台/衣服松松垮垮/行动不便/讲一些没用的话/一座遥远的无名山又升起在/毫无头绪的/地平线”,将“老年的我”的动作、行为、形象、语言、心理、感觉等都进行了想象,栩栩如生地描画出老年人的生活景象;《老年公寓:献给我晚年的生活》《肖像》《给我的晚年》《一件东西》等诗则对晚年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行为、细节、情景、语言、感觉、景象都进行了想象、描述、叙述,显示出诗人内心对于生命的返观、自审与清醒。非亚在诗中甚至还想象死后的情景,如《有一天》中诗人想象了自己死后别人的生活依然照旧的情景,折射了诗人对于生命、死亡的思考。需要注意的是,非亚在诗中无论是对年老还是死亡的想象,都是一种未来的现实映照,这种想象并非空穴来风的“幻想”,而是以当下现实生活为摹本而构造的未来景象,是现实生活的点滴在未来世界的延伸,非亚以想象的触角打通了现实与未来的通道,这个通道便是“诗”。
此外,非亚杂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法,进行诗的建构。非亚将小说中“新写实”的手法纳入了诗歌写作,如《每天的一些记录》《值得记录》《一些日子》等诗都呈现鸡毛蒜皮的琐碎生活的场景、细节,手法颇似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小说中的“新写实”的意味。但非亚并非采用“照相”术克隆原生态的生活,而是糅入了现代主义的技法,如蒙太奇手法,将各种生活场景、细节进行组接和拼贴,《死亡和冬天一样漫长》是典型诗例之一。
昨天的一场降温,今天早上的
一场小雨
房间里阴暗的过道,厨房里电磁炉上的
已煮好的鸡蛋面条
中午天空发暗,雨云又低又厚
保姆刷洗着油腻的盘子,不上学的儿童
拒绝午睡的被子
上班的铃声又响了,我躺在被窝里
又睡了一会
傍边,是一具女人温暖的气息,和冰冷的
白色墙壁
坐在床沿,拿着衣服,肃穆的冬天才刚刚开始漫长的怠倦还看不到尽头
日历移动得真慢啊,死亡像一张白纸
没一点让我陶醉的血色和表情
非亚以电影镜头般的画面依次呈现生活的各种细节,蒙太奇般地将生活放映于诗行间,呈现了碎片化的生活面貌,呈现出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生活状态。《政治早餐》则以变形、荒诞、反讽、比喻、象征等手法描画了生活在新闻、电视、报纸等组构的拟像社会中的后现代生活体验,充满了讽刺和戏谑,带有后现代色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博德里亚认为当下社会已进入仿真与拟像无处不在的后现代社会,人们都生活在电视、电影、网络遍布的拟像之中,人们已分不清真实与虚拟:“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hyperrealism)的拟像特征”[14],非亚对此社会景观与体验进行了呈现,如《剪刀手爱德华》中写道:“在谈话的瞬间我们被电视里的影片吸引,剪刀手/爱德华像鬼魂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眼他的脸(受伤的)他的/剪刀仿佛我,正和电视机外另两个疯子构成/三角形。”这简直是对博德里亚观点有力的映证与注解,现实世界已与电视、电影里的虚拟世界融为一体,非亚敏锐地传达了生活在当下这个拟像无处不在的社会的后现代体验,这亦是非亚试图塑造的一种“新的现实”。《去》《吃药》《死亡像一根接收不了信息的天线》等诗都触及网络、电视、电影等媒介生成的仿真与虚拟世界以及这一世界中的生活细节、状貌、感觉与体验,非亚通过杂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法,“重新塑造”“新的现实”,从而实现诗的建构。
总之,非亚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姿态,为当代诗歌在诗与现实关系的审美关系问题上实践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当然,或许值得非亚反观与审慎的是,对诗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远近距离把握是否得当,是权衡诗歌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标尺,二者的关系过近则会折损诗歌的艺术与审美价值,因而,或许非亚在建构诗与现实生活的通道时需要慎重考虑二者的榫接问题。
[1]非亚,钟世华.非亚访谈录[EB/OL].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23926.
[2]非亚.现实的通道[J].自行车,2009(13).
[3]非亚.我们诗歌的基本原理[J].自行车,2004(8).
[4]非亚.生活,与写作[EB/OL].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23926.
[5]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89.
[6]非亚.写作忠告[J].红岩,2011(4).
[7]家新.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J].诗神,1996(9).
[8]张曙光.语言:形式的命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36.
[9]董迎春,李冰.诗无体·非亚的诗·自行车美学[J].南方文坛, 2006(3).
[10]李少君.现时性: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J].山花,1998(5).
[11]非亚.我、诗歌及往事[M]//中国年度诗人评审委员会. 2011诗探索·中国年度诗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58.
[12]陈祖君.边地现代本土——广西现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一个扫描[J].南方文坛,2012(2).
[13]冯文炳.谈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10.
[14]博德里亚.拟像[M]//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文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52.
Constructing a Passage between Poetry and Reality——On Feiya’s Poetic Cre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Luo Xiaofeng
(College of Arts,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Feiya self-consciously adjusted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reality, trying with greatefforts to re-constructa passage between his poems and the real life so as to convey“the nature of being contemporary”,“the nature of being current”,“the feelings of being present”and to build a new reality,which provides a new spa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poems and the reality.
Feiya;Reality;Passage;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227
A
1673-8535(2015)04-0049-07
罗小凤(1980-),女,湖南武冈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孔文静)
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