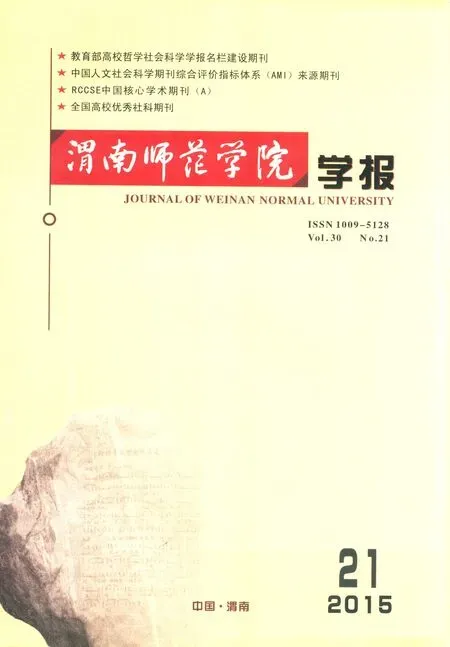面对死亡的时间终结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诗学
胡 志 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面对死亡的时间终结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诗学
胡 志 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死亡是人类的一种深沉情感与清醒意识。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最痛苦的灵魂,“生”和“死”贯穿于作品始终,对“生”与“死”的思考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人生感悟。鲁迅的生死观基于中间物意识,通过对小说人物“死亡”的叙述来反抗绝望,伴随着“向死而在”的生命体验,反证生命的价值,从而接近生命存在的本真。
鲁迅; 中间物意识; 反抗绝望; 死亡诗学
死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命现象,它是人类对自己终极命运的清醒认识和深切关注。死是无限对有限的否定与颠覆,促使人们正视人生无常给自身或他人带来的冲击与苦难。当人遭遇生命大限,面临即将死亡,内心难免产生不舍与眷恋,从而促使他们开始追寻生命的不朽与人生的意义。他们试图通过文字来捕捉当下的、片刻的、瞬间的生命感知,从而在书写的同时寻求时间的永恒。这种对永恒的追求背后掩藏着一个事实:寻求时间永恒的同时其实是在追寻自我,期待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只有了解自我及死亡,生命的价值才得以彰显。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最痛苦的灵魂,“生”和“死”这对哲学命题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对于生命问题(也就是“生”与“死”)的思考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鲁迅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往往基于自己对“生”与“死”的深切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人生感悟。
一、鲁迅的生死观
死亡是无限对有限的否定,是人类的一种深沉情感与清醒意识,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永远处于变动不居当中,而且在时间的流逝中得以实现。而死亡的绝对否定性,使个别存在的生命成为有限。
鲁迅指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302正因为是“中间物”,所以生命才会不完美、不圆满,甚至存在缺陷,正是由于上述遗憾,人类才会有前行的动力,人们才能正视死亡,参透死亡与生命的奥秘,并且认识到自己的“中间物”位置与自己作为“中间物”的价值。在鲁迅看来,“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到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1]354。“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1]355“一切都是中间物”是鲁迅对宇宙与人生的追问,意识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有限的,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在生死流转,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一个细微的组分。
鲁迅的死亡观具有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价值内涵。他充分洞察到了生与死之间的鸿沟,他通过对死亡的反观来建构生命自觉意识。他的生命意志,正是在这种对于生与死的自由抉择中建立起来的。无论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还是准备“在黑暗中沉没”,他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鲁迅的生命存在也自觉地以自己的方式来践履生存的意义。只有这种选择对于选择者而言才赋予其生命自由意志及其内涵,同时也是这种选择的超越性所在。因此,鲁迅把自己的第一个杂文集命名为《坟》,不仅是他对于死亡的选择,而且是他超越死亡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它重构并且显现了鲁迅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
众所周知,我们无法否定死亡,因为人对生存意义的理解是从对死亡的切身感悟中建立起来的,没有死亡意识,人类就无法意识到生存的价值,倘若人们一味去否定死亡,这倒成了死亡不可战胜的明证。在鲁迅看来,死亡是过去生命存在过的证据,在《野草》中,鲁迅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生命与死亡的关系: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2]163
正是因为“死亡”能够证明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死亡”能给“我”带来“大欢喜”;正是因为“朽腐”能够证明存在的价值,死亡的生命的“朽腐”能给我带来“大欢喜”。“死亡”与“朽腐”同时成了生命存在的证明,死亡不再单纯地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它一直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对死亡的思考也可以说就是对存在的思考,鲁迅正是在对死亡的深切感受与冷峻思考的过程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存在,也是在其灵魂、思想深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他正是从人类自身的存在境遇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处境出发进行终极思考。我们可以感触到鲁迅那种超越生死后的坦然与安详,这种超越生死的背后隐藏着他的生命哲学,那就是对于死亡的自觉意识。鲁迅相信“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1]386《过客》中的“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但是还是要倾听着内心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去前方寻找生命的意义。鲁迅还在《起死》中借庄子之口指出了死亡的意义,“活着就是死”,“死就是生”,这其中包含了生死相通,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同时进行的深层蕴涵。
死亡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意味着人生的终结。那么生死不明的晦暗状态,也就意味着生命的“非存在”性和虚无性,这是生存意义的死寂。对鲁迅而言,没有什么比“活着,但不存在”更悲哀,所以,他也只能以生命的消亡来应对存在的死寂,即以死的虚无来确证生的存在: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2]164
在这里,“生与死”的终极价值与意义已经被进一步展开,就生与死本身而言它并无实际意义,只有把生与死辩证联系在一起其意义才得以体现,死就是生的意义,活也是死的意义。鲁迅论及的生与死已经转变为对于“存在”与“虚无”的持续追问。
然而,时间易逝,生命短暂,个体终将死亡,这是任何生命无法改变的命运。进化论固然能让人看到微弱的希望,但我们也能感受到其对生命的残忍。作为一个人类灵魂的拷问者与人生命运的关切者,鲁迅在作品中尽可能示人以亮色,其内心却深潜着难以掩饰的死亡的悲戚。在1935年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序言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所处的境遇。
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3]262-263
综上可知,鲁迅对于“生”与“死”的体验异常深刻,在鲁迅那里,“生”与“死”是相通的,“死”只是“生”的特殊存在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意味着新生,“死”是“生”存在过的明证。只有正视死亡,才能超越死亡。
二、死亡在场
在鲁迅小说中,死亡犹如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每个人的头上。其作品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深重虚无与绝望,一种使人惊惧的死亡气息。在“死亡”面前,鲁迅随时保持清醒与冷静,不断质疑这个黑暗的现实与国民的劣根性,几近陷入“无物之阵”的绝望。夏济安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至在死亡完全抓住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僵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4]373鲁迅正是通过对“死亡”的叙述,来拷问灵魂深处的幽暗,从而摆脱缠绕自己的毒气和鬼气,摆脱虚无感的缠绕,追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此达到“灵魂疗救”的目的。
如果把《怀旧》也算进鲁迅小说篇目,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一半以上的作品提及或者详细地描述过死亡。夏瑜被杀及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馒头”卖了个好价钱,用来治痨病。而“灵丹妙药”没有拯救华小栓的性命,其死亡过程作家略而不写,只写了在第二年“分外寒冷”的清明,两位年迈的母亲去祭坟, “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1]472。与人物生前清晰的形象相比照,鲁迅的“死亡叙述”相当简单,既没有残酷的死亡过程,也没有隆重的祭奠场面,我们无法看到死者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哀,只有人物死亡后的无尽悲凉:有些是寂寂地、悄无声息地“死”了,有些或化为“一股凛冽的寒风”“一声鸦鸣”“一片丛冢”“一堆乱草”……鲁迅把“死亡”蕴涵在“荒寒”的虚空意境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字里行间蔓延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气,全篇弥漫着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气息,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余地和深沉的思索空间。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与《白光》中的陈士成都是落魄的读书人,前者穷到偷窃、赊欠,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后者在屡试不中之后妄想从地下掘出宝藏,寻找未果后到山里去,最终在白光的诱惑下失足葬身万流湖。这似乎是作者在暴露读书人的丑陋,也包含着鲁迅对于传统文人的批判,读书只是谋生的手段,尽管他们遍读圣贤书,并未真的能让他们豁达或者安身立命,这与鲁迅对儒家思想缺乏现实性批判不谋而合。当读书人遭遇生存危机时,其前面所倡仁义道德均被抛之脑际,为求生存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难看出,儒家所倡导的生死观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阿Q在被砍头时,无师自通地说出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1]526,阿Q所期待的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的轮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死后的期待,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乐观主义,体现了国人对于死亡的心态:死亡即回归,死也是一种超脱,是生命的轮回,循环不已。
子君的死亡我们不能归结为无爱的婚姻,至少前期他们是相爱的。其死亡除了父亲烈日般的严威外,涓生的冷漠和语言的暴力或许是最残酷的动因。涓生与子君度过婚后短暂的蜜月期后开始了冷战直至无话可说,涉及“失语”问题。在梅洛-庞帝看来,“失语”是一种“使用适当语言表达”能力的丧失,失去说某种语言的能力就是失去那种思想,不可能有“有某种思想但说不出”的情形。子君与涓生婚后忙于家务、不再追求思想上的进步,与涓生谈论的多为邻里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涓生日久生厌,最后发展到与子君无言以对。这正反映了鲁迅当时“绝望”的境地,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虽然希望对方放脚识字,但朱安一条都不具备。面对朱安,他只有沉默才觉充实,失语就是“沉默时感到充实”,在绝望中,生命是得不到语言表述的。但生活中,鲁迅又必须与朱安说话。对朱安他只能被动地回话,如同桌吃饭时朱安问他饭菜的软硬咸淡,他只用最简单一个字回应;或只说非说不可的话,这种话语实比无声还要沉默得可怕,因为这是彻底绝望之后的生活、绝望后不得不说的话,所以是“绝望的绝望”。然而,涓生没有鲁迅所谓“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1]338的勇气,最终说出了不再爱子君的事实,从而导致子君放弃生存的希望。
三、反抗绝望
死是对生的彻底否定,再壮丽的人生也会因死亡戛然而止,这就决定了人的虚无本质。然而,人潜意识规避死亡,并在其有生之年对死亡做出无声无息地反抗,具体体现在身体的意向性。梅洛-庞蒂认为:“意向性并不是源于一个独立于机械式的身体的精神实体,而是源于我们的身体本身。因此,我们对他人的发现也不是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来完成的。而身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前个体和前反思的,因此身体的知觉就不存在所谓唯我论的问题。”[5]因此,人的存在是客观的身体性存在。人一旦失去了身体的意向性,失去了身体与世界的关联,也就意味着人处于死亡或虽生犹死的状态。这也是鲁迅最担心、最惧怕的死亡状态:“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2]214面对这种行尸走肉似的生命在场,鲁迅甚至无计可施,只好采取虚无的姿态来应对。鲁迅欲求虚无,并不是一无所求,而是追求一个不能被任何在场之物满足的目标,或者说一个永远不在场的缺席之物。正如尼采所言:“至于他所追求的内容、目的和方法是什么,暂时还无关宏旨:关键是追求本身获得了拯救。……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人宁可期盼虚无,也不能没有期盼。”[6]74
当然,鲁迅更多时候以战士的姿态来反抗、摆脱虚无对生命的羁绊。鲁迅于1925年1月写的《希望》一文中流露出自身对虚无的抗拒,这篇文字从“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开始,记录下这些年来各种希望的落空: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2]181
于是鲁迅终于“放下了希望之盾”,他说:“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2]181这里鲁迅对希望作了第一度的否定,舍弃了作为虚构的自欺的假象的希望。这样,便使他将要沉入作为真实的暗夜之中,尽管在开篇鲁迅就感到一种分外的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2]181但是,便在这绝望的深处,鲁迅引述了匈牙利诗人裴多斐(Petöfi Sndor)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182这看似悖论式的诗句,否定了作为第一度的否定的绝望。但是这对绝望的否定并不是希望,那样将会陷入希望、绝望、希望、绝望……周而复始的怪圈,而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存在,包含了对希望自身的否定的希望。鲁迅继续描绘与前半段相似的暗色,对于希望的第一度否定依然持续不变。直到文章的结尾,他再次写下“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182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鲁迅虽然用了裴多斐同一诗句,但句末标点从句号变成了感叹号。第一次引述时,其中的“希望”是作为第一度的,即虚妄的希望概念而确立的,相对于否定它的“绝望”。到了第二次引述,惊叹号将整个诗句化为吁求,不再是平铺直叙,而是意志的自由跳跃与转换。在这里,“希望”变成了第二度的,是洞察了自身虚妄之后,包容了自身内部的绝望而确立的希望。
正基于此,钱理群注意到鲁迅小说文本独特的结构方式:“在他的小说(当然不是全部)里,不论情节发展,还是情感、心理的推演,往往有一个顶点,通常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情感、心理的绝望。在推于死亡与绝望的顶点之后,又反激出一种死后之生,绝望后的反抗(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它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对于生命的悲剧性体验。”[7]12那么,鲁迅用什么来完成“死后之生”“绝望后的反抗”?通过阅读鲁迅小说,不难发现,作家通常以反抗绝望的心志来面对死亡,而决非迁就、苟且偷安,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试图改变生命中的不幸。
孔乙己常以读书人自居,不甘与短衣帮为伍,坚信自己会有出头之日。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生活境遇一天不如一天,他也一天比一天颓丧,甚至沦落到以偷窃来糊口,纵使被他人惩戒与嘲笑,还是屡屡再犯,终于给人打折了腿,最后穷困潦倒而死。他对虚无的期盼纵然是徒然的,令人唏嘘扼腕,儒家经典中所呈现的虚妄世界成了麻醉读书人的精神鸦片,人们无法从书中寻求真正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导致孔乙己之流陷入消极、颓废的境地。然而孔乙己也曾试图反抗绝望,在生活中找寻自己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他试着教咸亨酒店小伙计识字来获得读书人的满足感,偷丁举人家来报复这个社会的不公……阿Q身处社会的最底层,饱受欺凌与羞辱,他也曾经反抗过,他不想一直靠打短工过活,想要走出自己的一片天。从城里“发达”后变成未庄人敬畏的对象,尽管名声不好。当再度陷入精神危机后,他想投靠革命党来改变自身所处困境。阿Q跌跌撞撞地想寻出一条生路。虽然他加入革命党起因于愚昧无知和对革命的误解,也是酿成阿Q杀身之祸的主因。但对阿Q而言,革命才是改变他命运的唯一捷径,这是人的生命欲求的自然呈现,只是阿Q下的赌注太大,最终输掉了自己的人头。
《在酒楼上》《孤独者》中,在“我”面对人物的生存困境或者人物的死亡后,“我”的心情却慢慢轻松起来,此时的“我”再一次回到“现在”。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2]34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2]110
在鲁迅的时间体系中,“现在”构成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的“反乌托邦”的情感体验,对现在而言只能以“忘却”方式去面对;而在经历绝望之后,“未来”则不复存在。因此,鲁迅执着于现在的时间理念最终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反抗绝望”,而最终落脚点是“向死而生”。
四、向死而生
生命存在的感知方式靠时间而呈现,每个生命个体的时间始自出生终于死亡,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并意味人存在的“时间”,并不是传统认知中由现在、过去和未来所构成的时间,人存在于“世界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因为人的存在是“向死存在”,此有(Dasein)的死亡才是此有存在的尽头,同时,只有囊括生死才是完整的存在。[8]273-274因此,当人们从日常生活的遮蔽中意识到死亡来临时,就无法避免去阐述“死亡”来确定自我的存在,藉由阐述死亡来证明存在的本真,阐明自我生命主体在时间流中向死而生的可能。也就是说,生命个体在临近死亡时,能对生与死有相对真切的领悟。
鲁迅正是在死亡中反证了生命的价值。有生必有死,生与死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的生死恰如白天和黑夜一样平常无奇,生有生的自由,死有死的自在。凡夫俗子面对有限的生命时,却在存在与死亡面前苦苦挣扎。鲁迅认为死亡是过去生命存在过的证据,他曾经在《野草》中对生命与死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2]163鲁迅在面对死亡和朽腐都有大欢喜,表达出对存在与死亡的超越以及对于死亡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道出了他那“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
雪莱(修黎)是鲁迅年轻时极力推崇的摩罗诗人之一,他生命虽然短暂,直捣人与自然、生与死的边界,他自幼徜徉山林,“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养成“无量希望信仰,暨无穷之爱”,使他“穷追不舍,终以殒亡”[1]86,雪莱基于柏拉图与培根关于死亡论述的基础上,认为生命的秘密要靠死亡来解开,为此他甚至自沉数次试图解开此迷。
人居今日之躯壳,能力悉蔽于阴云,惟死亡来解脱其身,则秘密始能阐发。[1]89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与雪莱的相似之处,他曾在《写在〈坟〉后面》中表达出一种更为深沉的伤感:
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1]303
这是鲁迅对生命的一种理解,他在《起死》中借庄子之口指出了死亡的意义,“活着就是死”“死就是生”。也可以说成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这其中包含的意思就是生死相通,生命的诞生和死亡是同时进行的,这正是鲁迅对生命本真的深刻领悟。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鲁迅人生的另一面,他通过魏连殳展开一场自我与人生的对话,“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2]96魏连殳的言语道出了鲁迅内心深藏的黑暗与隐忧,而“我”则是鲁迅平常的一面。“我”安详自在地活在世上,与世无争,虽看透了这个世界,但又接受命运的安排;偶有生活上的困难,但坚持一下也就过去了,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这也是鲁迅本人生存现状。而魏连殳才是小说落笔之处,他揭出了鲁迅内心深层黑暗的一面,尽管生活多艰,但他没有完全丧失生存的勇气,没有被生活所吞食,“我……我还得活几天”[2]99。言语中虽有万般无奈,但也展现出其忍耐与刚强的一面,生存越不容易,越能激起其内心世界的反抗与叛逆。而他在极其困窘之下,说出如此委曲求全的话语,尽管只有简短几个字,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命即将结束的抗争。我们知道,常人如果濒临绝境,反倒能激发出强大的生存意志,哪怕只能多活几天。鲁迅并不是残酷现实的旁观者,他也身处其中,也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苦痛,《孤独者》既是魏连殳对困苦生活的抗诉,也是鲁迅的自白。尽管魏连殳在孤独与忏悔中死去,“我”并没有放弃反抗到底的决心,虽然明白自己的结局也难逃死亡,但他要彻底的出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嗥叫,惨伤里夹染着愤怒与悲哀”[2]91。
而在《伤逝》里这种直面死亡勇气就减少许多,更多的是犹疑与挣扎。涓生和子君为了他们的爱情,勇于挑战世俗鄙夷的目光,也敢于背叛亲人与友朋。子君面对家人的劝阻,大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112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二人终究难逃曲终人散的悲剧,子君正是因为有了涓生爱,才有直面世俗的勇气,也正是因为涓生一句不再爱你了而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初读《伤逝》,深为子君的遭遇抱不平,也对涓生的人品表示怀疑。然而,对文本细读之后,一种伤感油然而生。经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涓生开始忧心两人是否真有新的出路。涓生被辞退后,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没有绚丽的爱情色彩自然逐渐褪去,两人感情也因受着爱情所带给彼此的折磨而终结。涓生对子君说不再爱你时是经过痛苦挣扎之后所说,他希望双方都能开辟出新的生路,再造新的生活,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而子君的死亡则是涓生难以接受的事实,尽管他曾经意识到。他在忏悔与追思中奋力前行,“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到来,无名的,意外的”,尽管盼来的无非是死的寂静,但“死的寂静有时也自己战栗,自己退藏,于是在这绝续之交,便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2]131。涓生在期待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至少这种期待已经给予他生存的勇气。
鲁迅以独特的心理感知与生存体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深刻地体味死亡,同时使他在创作过程中从“死”的历史材料中获得灵感。鲁迅以其最本能的方式直面自己的存在,从而通过小说展现出其最具个人生命价值体验的人生图景。鲁迅的一生伴随着这种“向死而在”的生命体验,在曲折的人生路途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与价值选择,从而接近生命存在的本真,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与价值,超越死亡带来的空虚与寂静。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5] 苏宏斌.作为存在哲学的现象学[J].浙江社会科学,2001,(3):87-92.
[6] [德]尼采.论道德的系谱[M]. 谢地坤,宋祖良,刘桂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7]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责任编辑 朱正平】
Facing Death Based on Death Poems in Lu Xun’s Novels
HU Zh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Death is a kind of deep emotions and human consciousness. As the greatest Chinese writers and the most painful soul of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Lu Xun advanced “birth” and “death” through his work, and it’s an important part in his thought and it forms the unique life feeling. Lu Xun focused on intermediate view of consciousness, and through the characters of “death” reporting to revolt against despair, with his life experience, found the value of life, which was close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ife.
Lu Xun; intermediate awareness; resistance to desperation; death poem
2015-06-2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的知识结构及信念的个性特征研究(14BZW106);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鲁迅文学世界的时间美学研究(14C0474)
胡志明(1973—),男,湖南益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10
A
1009-5128(2015)21-00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