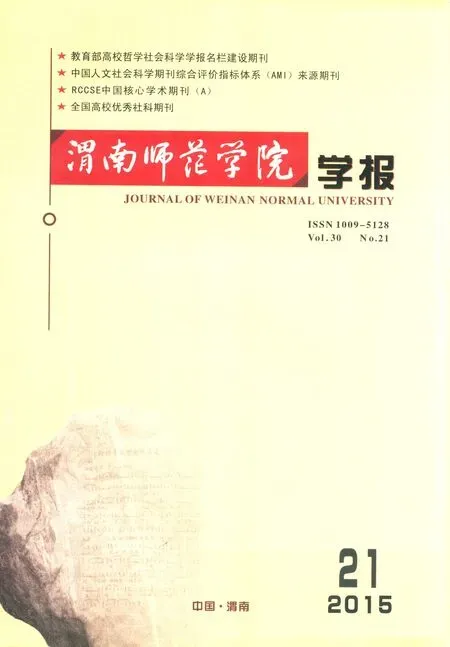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
——创造社两位陕西籍作家郑伯奇和王独清的交谊
郑 莉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秦地文化研究】
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
——创造社两位陕西籍作家郑伯奇和王独清的交谊
郑 莉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郑伯奇和王独清是同属于创造社的两位陕西籍作家。他们因对于民主革命的向往和共同的文学理想而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王独清在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中,阐发并支持郑伯奇的文学主张;郑伯奇也对王独清诗集《圣母像前》作了细致、恰切的解读,可谓知人之论。最终,两人却因不同的政治选择而走向决裂。通过这一过程的解读,可折射出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和文学的变迁。
郑伯奇;王独清;创造社;文学;交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陕西籍作家寥寥无几,贡献也少,而郑伯奇和王独清则是其中的佼佼者。郑伯奇是创造社主要成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在文学、戏剧、电影等诸多领域为新文学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王独清是创造社著名诗人。他们两人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在文学事业上,他们同属创造社,又都喜欢法国文学,是相互启发和支持的知己。但是,由于生活道路、思想性格和人生追求的不同,最终从友好走向决裂。
一 、向往革命的 “长安城中的少年”
(一)迥然不同的家庭出身和教育,成就相同的反抗和向往革命的青年
1895年,郑伯奇出生于西安城内,原名隆谨,字伯奇。其祖父是西安城南韦、杜之间瓜洲村的贫苦农民。父亲在16岁时就成了孤儿,先是进城在一满清王朝的官宦人家作佣,后来稍有积蓄开始贩卖“洋货”做小生意。父亲思想开通,母亲则是传统的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王独清1898年出生在西安,原名王诚,字笃卿。其祖上为蒲城望族,累世仕宦且以忠烈闻名。父亲王沣厚名为岁贡却赋闲在家,沉溺于文学,在长安城中以“名士”自居。母亲杨氏,本是王家婢女,却因怀孕生下王独清才被王沣厚纳为第三房妾。杨氏虽聪敏美丽,却因忧郁而早亡。青少年时期郑伯奇先后在西安、南京和上海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而王独清则在家接受传统教育,“他四岁发蒙,由其父亲自执教,课以经学”[1]。1910年,郑伯奇不仅参加农业学堂的学生罢课运动,还加入同盟会。1911年,他亲历西安新军起义并投身革命军政府的工作。1916年,郑伯奇在上海震旦学院初级预备班毕业,因为不满该学校恶劣的风气放弃深造,再加上陕西发生驱逐陆建章的战事而取消公费,就回到故乡西安。王独清同样参加了三秦公学学生针对教员的风潮,而且“崇拜着那些在辛亥革命前殉难的革命伟人,一面自己也想照样的去干一下”[2]160。1916年前后,王独清不仅结识了陕西的民党人物,还担任民党刊物《秦镜报》的编辑,因言辞激烈小有名气。就在这一年,历史的机缘巧合,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经人介绍,两个“长安城中的少年”很快成为朋友。由此,开启了他们生活、文学和革命事业上崭新的一页。
(二)东渡日本留学,成就“忠于艺术的朋友”
1917年,郑伯奇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取道上海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王独清由郑伯奇的父亲带到上海,然后独自乘船前往日本,并与郑伯奇住在一起。郑伯奇学习刻苦,一举考取了一高留学生预科,并取得官费。而王独清则生活散漫,无意升学,“一天到晚哼着李义山、温飞卿以及《疑雨集》《疑云集》等香艳体诗,而自我陶醉着;对于功课,却一点也不感兴趣”[3]747。王独清眼见升学无望,只好回国,1920年,王独清又转赴法国留学。 尽管出身、性格和对于生活的态度迥然不同,但是,两个同乡青年、两颗年轻的心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却贴得更近了。虽然天各一方,两人书信频繁,彼此关心对方生活,探讨、交流哲学和文学思想。郑伯奇的畏友、法国留学的曾慕韩,向郑伯奇打听王独清的情况时,郑伯奇在信中用了他从前介绍王独清给梦九时所说的原话:“他是最好的朋友,我从来以弟视之;请你也以我待他的样子待他!否!请你以待我的样子去待他!”至于王独清的为人如何,郑伯奇则引用了张梦九的话来答复:“我(张梦九)与独清底交情到他走底时候,感情愈厚了,了解愈深,同时并愈佩服伯奇之知人。”[4]由此看来,郑伯奇不仅当王独清是最好的朋友,而且一直像兄长一样地关心和爱护他。郑伯奇拜托曾慕韩待王独清要不仅要像对待郑伯奇自己一样,甚至是以郑伯奇待王独清的样子来对待王独清。王独清也称郑伯奇是“和我过去大多半的生活最有关系之一人”,而且是“真算是能‘了解’我的一个人”。
二、在创造社文学活动中的相互启发和支持
(一)书信往来探讨文学思想
1921年7月,郑伯奇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筹组的创造社在东京成立。在法国的王独清知道郭沫若、郑伯奇等筹办创造社,表示很想参加。郑伯奇也深知王独清爱好文学,尤其喜欢旧诗词,在法国写了大量的诗,乐意介绍他加入创造社。《创造季刊》上发表了王独清的诗,就是由郑伯奇转给郭沫若,经修改后登出来的。王独清就这样成为创造社的一个成员,并且和郭沫若时有通信往来。
1921年12月13日,王独清复信给郑伯奇,详尽地讲述自己到法国后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思考,他写道:“我自从到法后,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个痛苦竟使我去了向日虚浮、轻噪种种习气,对于人生发了些觉醒;多年来的迷梦也渐渐有些解破的转机。”毫无疑问,王独清在法国的贫寒、艰难的流浪生活对他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在尝到现实的苦味后,他的艺术观念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他认为:“艺术不专是人的娱乐品,是改造人生的工具;不专为安慰人底目前,为安慰人底前途。”还说“人生即文学;切实即艺术”,决心要“写出人间底痛苦;掘出人间的真诚”[5]。王独清之前喜欢舞弄笔墨,尤其爱读旧诗词,特别爱好香艳体的诗词,一天到晚哼着李义山、温飞卿以及《疑雨集》《疑云集》等香艳体诗,而自我陶醉的文学思想得到彻底改观。王独清觉得意犹未尽,19日接着写了第二封信,除了进一步阐述13日信中所谈的思想、文学观念外,他首先对日本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余裕”派、游戏文学进行批评。说他不喜欢“把诗当作专写浮泛的景色,表送迎底个人感情的工具”。他明确表示喜欢郭沫若的诗歌,但艺术主张不同于郭沫若,而是和倾向写实的郑伯奇比较一致。在回信中,郑伯奇认为王独清矛盾苦闷以至自杀的根源在于其环境和性格,在于“生之不安和爱之痛苦”,“你的诗有满腔的血泪,其悲切迫人甚深。你对于艺术主张‘诚实’真可算达到十分了”[6]245。郑伯奇还敏锐地指出王独清诗歌创作“现在已到了一个转机了”,即在“诚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中国的新文学排斥技巧,立脚诚实,但是立脚诚实的新文学又要求新的技巧。郑伯奇更希望王独清能在诚实上生出一番新的技巧。
(二)共同的“国民文学”主张
1923年底至1924年初,郑伯奇于《创造周报》发表《国民文学论》,抛出了他的国民文学主张。郑伯奇写作、发表《国民文学论》的初衷,在他给王独清的一封信里有清楚的说明,即“‘有提倡国民文学的必要’,因为有些作家,‘不能了解文学的使命’,‘不知道对于自己的予以有意识的注意’”[7]。郑伯奇在文章中写道:“艺术家既然也是人,一样地在社会上做现实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利害最切的国家,对于自己血液相通的民族,他能毫无感觉吗?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于现实生活体验最深切的。”由此可知,郑伯奇所倡导的国民文学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表现人生”的文学主张。所谓国民文学,就是“作家以国民的意识着意描写国民生活或抒发国民感情的文学”[8]58。创造社同仁对郑伯奇的《国民文学论》的反应各不相同。成仿吾态度冷淡、不置可否。郭沫若认为“国民文学”概念混乱,不适合作为文学运动的口号。穆木天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并写了《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和郑伯奇的复信以诗歌的形式同时在《京报副刊》发表。北京的周作人表示支持,钱玄同和林语堂则强烈反对。李初梨和冯乃超则表示局部赞同。远在法国的王独清发表支持文章《论国民文学书》。他针锋相对地回应钱玄同的说法:“若就事实来说,我对于钱先生首先遗憾就是没有认清我们底目标。他把我们所提倡的‘国民文学’与赞美拳匪’和非常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列为一类,确是个大错。”[7]王独清重申,“国民文学”是关注国内生活,体验国民感情。这与郑伯奇的主张是高度吻合的。甚至在两年后的1926年,郑伯奇和王独清聚首广州,王独清还曾极力劝说郑伯奇进一步发展国民文学。
(三)郑伯奇对于王独清的诗集《圣母像前》的批评
1926年,王独清从法国回国后,他的诗集《圣母像前》也在本年由光华书局出版,列入创造社丛书第十八种。应王独清之邀约,郑伯奇遂于1927年6月作《〈圣母像前〉之感想》的长篇批评论文。郑伯奇在文章的开头就写道:“因为和独清相知甚久,对于他这七八年来辛苦铸成的光辉灿烂的金字塔,很愿意说几句善颂善祷的话表示自己的喜欢,这似乎也是人情中应有的事。”[8]70在《〈圣母像前〉之感想》这篇文章中,郑伯奇首先认为:《圣母像前》是王独清在法国度过的波澜坎坷的流浪生活的记录。诗集中的作品是王独清私人的私话,但“我敢相信无论谁去读他的诗,都可以觉得在美的诗形和音律中间有一种泼剌的生活直射出来;因此可以说:他的诗是他的纯粹的生活的记录;更可进一步说:他的艺术与生活是浑然一致的”[8]73-74。其次,郑伯奇肯定王独清诗的价值、在诗坛的特别地位,不仅是表现生活,而是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的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为此,王独清在诗的形式、韵律和节律上用力最勤。而对于韵律,王独清更费苦心。不仅是郑伯奇,就连作者王独清也认为《我从Cafē中出来》是整部诗集中音律最好的一首。郑伯奇认为:“诗人的技巧,差不多达到了接近‘天籁’的极致。押韵非常错综复杂,读起来觉得句句有韵,节节有韵,而全篇整个又有很圆脱流利的韵在舌端去来。”[8]76郑伯奇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不吝以“天籁”“浑然天成”来赞美,不愧是“水晶珠滚在白玉盘上的诗篇”。再次,郑伯奇认为,王独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的诗人。郑伯奇根据王独清诗歌的内容“失恋的哀歌”和“要失了故国的浪人底哀愁”以及所表现思想和情调并不是虚无主义和强烈的宗教信仰,认为王独清的诗是“Symbolisme的形式,Lyrisme的内容”。王独清对郑伯奇为自己所下的断语,也不加以否定。郑伯奇说:“这种评语不是故为苛刻,也并不损及我们诗人的价值;不,他的价值也许反因此大增呢。”这是因为郑伯奇考虑到象征诗产生的社会、时代和思想背景和中国的截然不同,所以他说,王独清用象征主义的方法作诗,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反而正是他的好处。尽管如此,郑伯奇认为,但是全集里也并非没有与象征派非常接近的作品。“流罪人语”诸章和“最后的礼拜日”都颇得象征诗的神韵。郑伯奇还特别指出,王独清还运用丰富的联想这一表现手法,正是中国近来诗人所少有的。郑伯奇断言,王独清能发挥由象征派学来的这种联想的表现手法,“将来必可以给中国的新诗王国开阔一段广阔而丰富的新领土”。最后,郑伯奇针对王独清诗歌的过于技巧化和模仿进行了公正、审慎和辩证的分析。郑伯奇认为这两种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要辩证、具体地对待。就故卖弄技巧而言,郑伯奇说“这不足为一个作家的弊病”,尤其是在“审美薄弱创作粗糙的中国现在文坛,反是一种对症的良药”,而这也是被文学史所证明了的;至于缺乏创新模仿的痕迹太明显的讥评,郑伯奇认为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把古典的词句,象征派的技巧,抒情派的情感,三者熔为一炉而冶成他自己的诗作法,这也是新诗运动以来很有数的成功”。
郑伯奇的这篇关于《圣母像前》的批评,作于创造社正在“转向”期间,既体现了创造社“自我表现”的文学主张,又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想的运用;即使对王独清个人的批评,也是对十年来新文学历史的检阅。郑伯奇立足于世界文学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对王独清诗歌在内容和形式的客观、辩证的分析,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五四”和1927年这样两个过渡时代的文学进行了批评。郑伯奇对王独清诗歌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恰切的,但也有出于朋友私心过于溢美之嫌。
三、因不同的政治选择导致友谊破裂
1926年,应郭沫若之邀,久别的郑伯奇和王独清聚首于广东大学。重逢的喜悦自不必言说。但是,郑伯奇敏锐地发现,以前天真、直率、淳厚的少年朋友现在既虚伪又儇薄,野心很大、嫉妒心强,既不“诚”(他原名王诚)也不“笃”(他原字笃卿)。当郑伯奇向他提出忠告时,王独清反而嘲笑郑伯奇迂阔。此时,原本和谐的朋友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王独清开始醉心于追名逐利。在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后,当上了《创造月刊》编辑的王独清并不用心于刊物,却只考虑文学青年吹捧他的来信,只想利用创造社的关系抬高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在创造社元老郭沫若、成仿吾出国,张资平退出后,王独清企图拉拢郑伯奇,掌控创造社的大权做政治投机,但遭到郑伯奇的严词拒绝。气急败坏的王独清污蔑郑伯奇“跟国家主义派有关系,又和旧军阀有来往,很不可靠,叫大家最好少同他来往”。王独清还在1930年12月刊发的《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他底总帐》回顾创造社第三期的文学活动,在谈到郑伯奇时却说:“一向‘学艺好玩家’(Dilettante)兼‘消遣文笔者’(Amateur)的郑伯奇也跟着加入了这个运动。”[9]否定郑伯奇对于革命文学的贡献。后期创造社同人在认清王独清的真面目和险恶用心后,将他清除出创造社。气急败坏的王独清因此恨透了郑伯奇,遂特意到郑伯奇家里,将他们以前的合影、信件都全部索回,甚至将照片上赠郑伯奇的题词当面撕毁。此后,虽然都居住和工作于上海,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此后,王独清因为“托派”的问题,在文学界活动困难,文章不能发表,他的主要著述,除了早期的诗歌外,作品也几乎全部被上海国民党党部查禁,再加上时局艰难,王独清生活窘迫困顿,而且患有心脏病、神经束暗弱症,最终在1940年因伤寒病悄然而亡,年仅42岁。郑伯奇曾有一篇《关于王独清的自杀》来纪念他。
1952年,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活动》认为创造社内部之争的实质是在表面的人事纠纷和琐屑的经济问题掩盖下的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郑伯奇和王独清,因为共同革命理想、文学追求结为好友,最终却因不同的政治选择而分道扬镳。
[1] 李建中.王独清生平考辨[J].新文学史料,1994,(3):201-209.
[2] 王独清.长安城中的少年[M].上海: 海光明书局,1933.
[3] 钱鸿兢.创造社资料集(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4] 郑伯奇.伯奇致曾慕韩函[J].少年中国,1920,(1).
[5] 王独清.一双鲤鱼[J].创造,1922,(2).
[6] 郑伯奇.沙上足迹[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7] 王独清.论国民文学书[J].语丝,1925,(54).
[8] 郑伯奇.郑伯奇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9] 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他底总帐[J].展开,1930,(3).
【责任编辑 马 俊】
From Like-minded Friends to Going Separate Ways——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Shaanxi writers Zheng Boqi and Wang Duqing in the Creation Society
ZHENG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Zheng Boqi and Wang Duqing are two Shaanxi writers in the Creation Society. They became like-minded friends because of the common literature ideal and the yearning for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ng Duqing elucidated and supported Zheng Boqi’s literary viewpoint in the argumen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Zheng Boqi also interpreted Wang Duqing’s book of poems,InFrontoftheStatueofVirginMarydelicately and appropriately. But at last, they split up becaus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choice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rocess, we can get the change of Chinese ethos and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Zheng Boqi; Wang Duqing; Creation Society; literature; friendship
2015-05-10
郑莉(1973—),女,陕西合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I206
A
1009-5128(2015)21-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