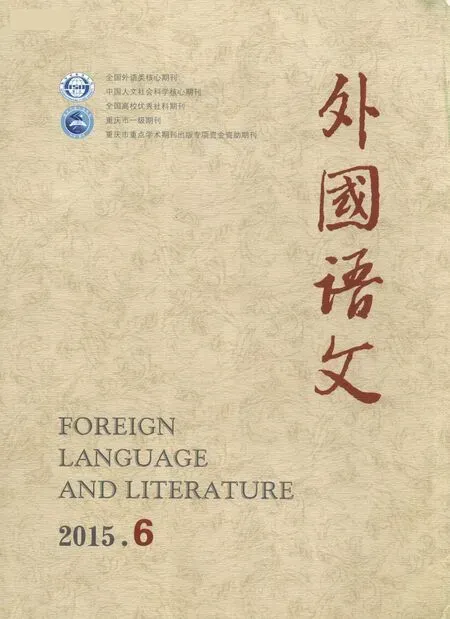F.R.利维斯与英美现代诗歌批评
王 庆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0)
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 -1978)近年来成为英美学术界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主要是由于文化批评(Cultural Studies)兴起的缘故。学界一般把利维斯与M.阿诺德视为当下盛行的文化批评的源头。利维斯可称得上十足的剑桥人,他生于斯,长于斯,除了参加一战和短期外出学术访问外,他一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剑桥,是剑桥英文学科和剑桥文学批评传统的奠基者之一。利维斯涉猎广泛、著述丰硕,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大学教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杰出成就,是一位真正的大师。诚如有批评家所言:“大家都承认,任何人想要理解20世纪英国批评的历史与理论,利维斯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Ian Mackillop and Richard Storer,1)利维斯在我国的研究刚刚起步,从剑桥归来的曹莉博士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主要谈的是包括利维斯在内的剑桥批评传统。①参见曹莉:《剑桥批评传统的形成和衍变》,载《外国文学》2006年3期;《鲜活的源泉——再论剑桥批评传统及其意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文学、批评与大学——从阿诺德、瑞恰慈和利维斯谈起》,等等。而国内学界对利维斯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英国小说研究及大学教育研究等方面的关注远远不够,鲜有成果问世。本文试图结合利维斯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思想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历史语境,对利维斯的英美现代诗歌批评进行辨析与阐释,进而勾勒出利维斯关于英美现代诗歌批评的基本观念及方法。毫无疑问,利维斯对英美现代诗歌的批评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在历史传统上牢固确立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地位,更为后来的现代诗歌批评实践提供了原则与标准。
一
众所周知,利维斯在20世纪初期就读于剑桥大学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思考文学批评事业,而那时英语文学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英语文学世界里诗人、小说家都在纷纷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文学思想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情趣。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德·普洛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E.庞德的《休﹒赛尔温﹒莫伯利》及部分《诗章》、V.伍尔夫的《达萝威夫人》和《到灯塔去》、J.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等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已经问世。在理论界,I.A.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科学和诗》、艾略特的《圣林》以及W.燕卜荪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和《田园诗的几种形式》等多种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提出了关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新理论,加之T.E.休姆、庞德等人在若干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崭新的诗歌创作与批评观念,整个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可谓空前活跃,同时也较为复杂,各种理论观点争奇斗艳,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这是一个文学转型与断裂期,恰如文学史家鲍尔迪克在《现代运动:1910-1940》一书中所述:“一种新的奇特的与过去的断裂感,现在成为现代文学意识的普遍现象。”(Baldick,2004:2)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惨绝人寰的一战之后,西方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萧条、平民失业,多数人不仅感受到空前的生存压力,更感受到内心迷乱、无所适从,乃至悲观绝望。要真正理解利维斯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思想,离开这个历史语境是很难想象的。彼得·福克纳分析了1910-1930年间西方世界的巨大变化,并指出:“人们可以感受到,1910年的世界比以前人们知道的那个世界远为复杂,尤其比维多利亚文学给读者展现的那个井井有条的世界远为复杂了”,特别是一战加速了原有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崩溃,因此“关于复杂性的认识将成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认识”(福克纳,1989:26-27)。当然,外部世界与环境只是构成利维斯文学批评思想的可能条件,而其自身的成长经历与世界观则是形成其文学批评思想的核心要素。
利维斯从珀斯学校毕业后,获得剑桥的奖学金,但一战使得他中断学业去法国做了担架兵,停战后他重新回到剑桥,继续学业。1919年他开始学习历史,一年后转入成立不久的英文系学习文学。1924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从英格兰报业的发源与早期发展看新闻业与文学之关系》。他毕生探究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力图通过文学改变读者情趣进而改变社会文化。这实质上可以说都源于其博士论文,“他终身关注的问题是,一份刊物如何既反映亦可以培养广大大众的文化意识,这部博士论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Greenwood,1978:8)。利维斯一直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还与他夫人奎·多利维斯不无关系。利维斯夫人也是剑桥毕业生,师从著名批评家R.I.瑞恰慈,其博士论文是《小说与读者大众》,论文从社会学入手分析通俗文学接受现象。论文认为,大众趣味的形成与职业作家利用写作技巧开发大众情感紧密相关。利维斯夫人还长期为《细察》撰写文章,其观点与利维斯相互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以此推测,利维斯创办《细察》以培养读者识别力为目标,也应是受到夫人有关通俗出版物与大众阅读兴趣关系的启发。《细察》刊发大量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细读”论文,表明利维斯培养和提高读者识别能力的办刊理念。
利维斯曾经赠送E.庞德一本小书《如何教阅读:E.庞德读本》。庞德因为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利维斯,便问:“利维斯是谁啊?他送了我一册读本。”(Paige,1950:246)庞德之问,确乎成了一个难题。这当然是从隐喻意义上来理解的。即是说,利维斯作为一个学者和批评家,我们很难清楚地把他归入某一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批评涉猎广泛,包括社会、文化、教育、诗歌、小说、大学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即使作为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的批评思想与批评理论也较为庞杂,很难划出边界。这一点,在2000年M.贝尔主编的《剑桥文学批评史》中也得到印证,同时代的批评家被分列在三个标题下面:T.S.艾略特被标为“现代主义者”,I.A.瑞恰慈和W.燕卜荪是“新批评家”,而利维斯和美国批评家L.特瑞林一起列在“批评家与文化制度”标题之下。陆建德(2009:23)在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译本序言中指出,利维斯“穷毕生精力在文学批评中锻炼心智,砥砺思想”,在“孤独地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他认为:“利维斯批评遗产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在20世纪的英国批评家中,他的实际影响恐怕无人可及。”利维斯之所以能够在多若繁星的英国20世纪批评家中产生“无人可及”的影响,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的学术贡献决定的。
利维斯一生勤奋笔耕,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著述。主要经典著述包括《伟大的传统》(1948)、《作为小说家的 D.H.劳伦斯》(1955)、《小说家狄更斯》(1970)、《教育与大学》1943)、《文化与环境》(1933)、《我们时代和大学的英国文学》(1969)、《共同追求》(1952)、《我的剑也不会》(1972)、《英语诗歌的新方向》(1932))、《重新评估: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等等。其主要诗歌研究成果是上列最后两部著作,另有一些诗歌论文发表在《细察》等期刊上,后有部分收入《重新评估:英诗的传统与发展》及《共同追求》等著作中。
不过,如若要评析和概括利维斯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看法和观念并不容易,因为,众所周知,利维斯一贯反对所谓“理论”和哲学,他甚至把自己称为“反哲学家”(anti-philosopher)(Day,1993:198)。当然,这并不是真正表明利维斯不重视理论或者在文学批评中抛弃了理论与哲学思辨。恰恰相反,利维斯成长在哲学氛围浓厚的剑桥大学,又与罗素等大哲学家多有交集,受到学院哲学氛围的熏陶是自然的事;而且,利维斯本人在《文学批评与哲学》一文中还直言不讳地承认“哲学方面的训练会使人成为更好的文学批评家”(Leavis,1952:212)。他强调自己的批评工作仅仅是“选择、整理并分析具体的例子”,但是仍然希望“这种方法已经促进了理论”(Leavis,1952:215-216)。不过,即使这样也应当承认,利维斯与其精神导师T.S.艾略特非常相似,理论上说不上系统,甚至还可以说比较零散。因而,通过细读批评文本,分析整理其思想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
1932年,利维斯出版《英语诗歌的新方向》,从历史传统上肯定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地位。在同一年,他发表《批评出了什么毛病?》(“What Is Wrong with Criticism?”)。在文中,他重点讨论了诗歌批评的弊端。他认为当时文学批评的毛病不仅仅在批评功能的缺失,而且“即使对于那些严肃对待文学的人来说,常常似乎他们严肃的文学兴趣也与现代世界出奇地不相干”,之所以说“出奇”,是因为:如若严肃对待文学,首要是从当下来思考,而且认为“文学有用”,文学首先应体现“时代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ge)。(Leavis,1933:72)在利维斯看来,具有“时代意识”正是现代诗歌的第一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英语诗歌的新方向》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考察分析当时的英国诗歌情形。该书的第一章《诗歌与现代世界》、第二章《一战后诗坛的局面》都从这个逻辑点出发,尖锐批评了维多利亚及乔治时代的英国诗歌传统。利维斯开篇就说,“诗歌与现代世界几乎没有关系”,接着他分析了当时的诗歌状况,指出19世纪以来的诗歌传统特征是“创造一个梦幻的世界”(Leavis,1982:14)。诗人们遁入梦幻境地,逃避现实,与时代丝毫没有关涉,缺乏“时代的意识”。维多利亚诗歌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相容的、桀骜不驯的、毫无诗意的,任何反抗都毫无价值,只有逃离”(Leavis,1982:18)。这就导致了现代诗歌的困境。
在维多利亚诗人中,M.阿诺德获得利维斯的赞许,因为他的诗歌坦诚地针砭时局,具有时代意识:“现代生活的怪异疾病,/和它病态的匆忙,散乱的目标,/头脑不堪重负,心灵麻木不仁”,“这个时代/充满怀疑、争斗、错乱和恐惧”。但是,利维斯认为阿诺德对现实的“回应”并没有与他的同代人有“根本的区别”,没有达到他关于诗歌是“生活的批评”的要求,特别是当他预言诗歌将代替宗教时,他更是遁入宗教的泥潭,逃离世俗的世界。因而,无论作为批评家还是诗人,让他引领英国诗歌走向新的方向,他都是“不合格的”(Leavis,1982:18-20)。利维斯指出,所谓的“时代意识”,就是要求诗人在诗歌中反映生活的时代,并创造出能表达现代人们情感方式和经验模式的诗歌技巧:“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一个诗人能表明自己完全生活在当代,证据应该包含在他的诗歌文本之中。创造出的诗歌技巧能准确表达现代人的情感与经验模式,敏感的现代心灵是极端晦涩的。”(Leavis,1982:24)那么,谁能承担这个历史重任呢?利维斯认为,这当然是T.S.艾略特。“他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开启了新的方向”(“He has made a new start,and established new bearings.”)。而艾略特之所以是一个“新的起点”,正是由于“他比同时代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无所不在的困境,且更加清晰地表述出来:他使自己代表了时代意识”(Leavis,1982:144)。《荒原》的“各种特征都反映了文明的现状”(Leavis,1982:71)。具备“时代意识”也使得 W.B.叶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风转向现代。利维斯指出,1912年出版的《绿色的头盔》是叶芝诗风转变的节点,这部诗集“不再是咒语般迷糊而梦幻的节奏,它属于现实的、清醒的世界,运用的是现代会话的节奏与表达。诗歌语言朴素、坚硬、有力,口吻略带讥讽,表达了一个人的痛苦与幻灭”。(Leavis,1982:36)利维斯十分认同T.S.艾略特把庞德的《休·赛尔温·莫伯利》称为“一首伟大的诗歌”,并指出它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莫伯利》首先是个人生活的总结。但它还有一种代表价值,反映了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前进方向的迷失,以及艺术家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Leavis,1982:105)显然,利维斯这里强调的也是《莫伯利》内涵的时代意识。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显示出深刻的道德关怀。这是利维斯评判诗歌和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与其前辈阿诺德和艾略特一脉相承。V.巴克利的《诗歌与道德:阿诺德、艾略特与利维斯批评研究》(1959)这样评价他们三位:
总体说来,他们三位都是道德家。然而他们都没有给出界定,他们都对全面解释诗歌的理论没有兴趣。尽管他们对诗歌中道德的地位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都对“道德”一词都赋予了独特的力量与意义。他们都发现,道德价值与任何作品的艺术价值共存。(Buckley,1959:18)
在《文学与社会》(1952)一文中,利维斯明确提出价值判断是界定文学作品的核心标准:“如果要给我所说的‘文学’下个定义,有关价值判断的术语会起关键作用”。(Leavis,1952:193)而他所说的价值判断主要是作品的道德伦理价值。在利维斯看来,“道德关怀”意味着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人性抱有强烈的兴趣,或者对生活抱有“严肃”、“崇敬”的态度,以及直面和揭示现实痛苦的坦诚品质。利维斯在评价叶芝1912年之后的诗歌时说,这个阶段诗人成熟了,是经历了人间磨难后的成熟。利氏举出了叶芝的《时光流逝带来的智慧》:“山巅那神圣的半人半马怪已经消失;/除了令人苦恼的太阳我已一无所有……现在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必须忍受羞怯的太阳。”利氏评价说,这是“现实的胜利”,“它像从药物中醒来,从烂醉中醒来”,“他认识到了真实的世界,但是太晚了,他的力量已经被浪费掉了”。然而这些诗歌却表明了诗人积极的生活态度,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积极的成就”,“叶芝先生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从失败中取得一场胜利”(Leavis,1982:37)。利维斯指出,尽管艾略特的《荒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荒原》仍然是一项伟大的积极成果,是开启英语新诗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诗中,一个完全生活在当下的人面对时代困境努力获得了诗性的胜利”(Leavis,1982:86)。利维斯(Leavis,1936:83)赞扬蒲柏关注“他那一代所信奉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念”,但批评他过于单纯追求文学秩序的感情,而约翰逊则注重一个文学秩序感情与一种深刻的道德意识,二者无从割裂(Leavis 1936:117)。利维斯在评价小说时对“道德关怀”有更明确的阐述。他的扛鼎之作《伟大的传统》中对英国小说传统进行了重新界定,确立了乔治·爱略特、康拉德等人的经典地位,理由是:“他们都有体验生活的巨大能力,都对生活持有一种崇敬而开发的态度,都明显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Leavis,1953:9)李氏所言的文学的“道德关怀”,绝不是倡导在文学作品中进行道德说教和普通的道德判断,而是一个蕴含要复杂得多的术语。他说D.H.劳伦斯之所以如此伟大,就是其作品所展示的强烈的道德意识,而其“道德关怀比普通的道德判断要深刻得多”,他对是非曲直背后的原因追根溯源,致力于展示“哪些生活规律遭到了忽视”(Leavis,1955:36)。利维斯并没有系统明确地阐述过他所说的“道德关怀”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评价众多小说家与诗人的论述中管窥其内涵。利维斯也要求批评家的责任与担当意识。他有句名言:“没有尽到自己责任的批评家就是一种生命之力的浪费。”(Leavis,1955:15)R.斯多尔指出,这句话可以概括李氏的批评观,并认为利维斯的意思是:“批评写作具有一种为人类生活方式提供积极贡献的潜能,实现这种潜能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某种责任。”(Storer,3)
三
利维斯的现代诗歌批评思想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即一部伟大的诗歌作品或者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具有原创性的同时必然浸淫于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当然是师承T.S.艾略特。艾略特在名作《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传统意识:“任何诗人和艺术家都不可能单独具有完整的意义。他的意义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以及以前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来评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要获得传统,一个作家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历史意识要求不但“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以及本国整个文学同时存在”。(Eliot,1950:4)一句话,创新必须根植于传统,现代诗歌必须在传统的观照下进行评判。利维斯的《英语诗歌新方向》与《重新评估: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是姊妹篇,前者写英语诗歌的“现实局势”,后者讨论英国诗歌传统与流变。作者在撰写第一本书时就已经规划了第二本书,两本书出版前后相隔四年。因为,在他看来,要正确评判现在的诗歌价值,就必须把它放到诗歌传统的历史长河中去衡量。所以,后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以对过去相关描述为参照,完成英语诗歌当下状况的描述”,“阐述当下诗歌,如若要有价值,就必须确认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如果担负批评之责任,就必须在观照过去和现在的同时才能确立和界定”(Leavis,1936:1)。利维斯认为,批评家必须从下面几个方面认识诗歌传统与现代诗歌的关系,这是批评家的应有之义:
尽力把当代的诗歌看着是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就是说,把当代诗歌看成传统决定性的、最重要的当代延续。在考虑传统诗歌时,尽力认识到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的深刻内涵,即传统诗歌的生命就在当代,它是鲜活的,恰如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三个观点是,批评家的目标,就是以其自身的绝对的建构,去界定和组列一个理想的非个人的活记忆。(Leavis 1936:1-2)
这是利维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论述,也可以说这段论述统摄了他所有的诗歌批评。在《英语诗歌新方向》一书中,无论是评论20世纪初期普遍认可的几位重要是诗人叶芝、哈代、德拉·梅尔,还是讨论他认定的20世纪代表诗歌“新方向”的艾略特、庞德和G.M.霍普金斯,利维斯都特别突出他们对诗歌传统的接续。其中,以讨论艾略特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伊丽莎白戏剧以及玄学派诗歌的借鉴最为透彻。需要说明,利维斯在谈论文学传统时承袭了艾略特的思想,即传统应该指整个欧洲的文学传统,而非仅限于英国文学。
利维斯对艾略特出版于1917年的《J.阿尔弗雷德·普洛弗洛克的情歌及其他观察》评价特别高,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与19世纪诗歌传统的完全决裂,是一个新的开端”,“诗歌的经典被遗忘,诗人享有任意选用对他有意义的材料的权利。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由表达现代感受、现代经验模式的诗歌,看到了一个完全生活在他的时代的诗人”(Leavis,1982:60-61)。但是,也恰恰是这部标志着英语诗歌“新方向”的诗集,利维斯发现了艾略特与西方文学传统之深刻渊源,即艾略特借鉴并发展了包括但丁、伊丽莎白戏剧、波德莱尔、丁尼生、拉弗格等在内的优秀文学传统。他认为,在这部诗集中“《一个妇人的画像》、《序曲》和《大风夜狂想曲》形成了一组城市幻灭的意象群。这组意象群把诗人与波德莱尔联系在一起。”(Leavis,1982:63)艾略特承认:“从波德莱尔那里,我开始懂得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更加肮脏方面的可能性,表达肮脏的现实与梦幻的融合以及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并置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前英语诗歌中没有被开发出来的。”(Eliot,1933:125-125)利维斯进一步分析了拉弗格对艾略特的影响:“他自己说,他特别受到了J.拉弗格的影响,在艾略特早期诗歌中证据是明显的。”“《情歌》中的自我嘲讽、自我怀疑态度,大都来自于拉弗格,技巧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Leavis,1982:63)利维斯比较了艾略特1920年出版的《诗集》中的《老头》一诗与米德尔顿的《儿童》:“这个比较非常有价值,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看出艾略特先生与成熟的伊丽莎白戏剧诗展开的相似性,而且能看出艾略特先生与众不同的力量。”(Leavis,1982:63)通过比较《老头》与米德尔顿及其同代人的诗歌,利维斯的结论是:这种比较看出,“艾略特先生的诗歌不是单纯模仿和陈词滥调,而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融化L.安德鲁斯的杂言碎语,其主要的表达方式和行进节奏都直接来源于现代日常语言。”(Leavis,1982:65)因而,辩证地看待诗歌创作中的传统与创新问题,是利维斯现代诗歌批评的理论原则。
语言是英美现代诗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英美现代诗歌批评的核心论题。现代诗歌批评家R.韦勒克指出,英美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对语言有浓厚的 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是语义学的,他们的兴趣在于对一种与理智的、科学的语言相对应的情感(emotive)语言的作用进行分析。这种理论的基础是 I.A.瑞恰慈奠定的”。(韦勒克,1987:333)韦勒克接着指出,艾略特属于这一传统,“在艾略特那里,我们发现了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在英国的翻版”(韦勒克,1987:339-340)。而现代诗歌评论家C.布鲁克斯则发展了瑞恰慈和艾略特的观点,将诗歌看成一个有机的张力结构进行分析,由此形成20世纪新批评的一些核心观点。后来,F.杰姆逊说得更明白:“现代主义的形式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杰姆逊,1987:140)
利维斯的现代诗歌批评中特别突出对诗歌文本、诗歌语言及诗歌技巧的关注,成为他又一个重要的批评原则。不容否认,后来的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受到利维斯的影响。A.萨姆森曾指出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因为“拥抱具体”而使得“抽象的概括增加了分量”。(Samson,1992:108)“拥抱具体”十分形象,高度概括了利维斯诗歌批评的要旨,即对诗歌语言与技巧的聚焦。一般认为,由于I.A.瑞恰慈对语义学的开拓性研究和其诗歌批评实践中对诗歌语言的细致剖析,及其门徒W.燕卜荪在名作《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对诗歌语词含混意义合法性的精细辨识,英美现代诗歌批评形成了语言中心论的传统。其实,利维斯对语言与文本结构的精妙解读,毫无疑问,也为现代诗歌的“语言中心”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维斯说:“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一个诗人能表明自己完全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证据应该包含在他的诗歌文本之中。”(Leavis,1982:24)而我们评判一部作品的价值,“不是如何区分实际情形的价值高低,而是对艺术家所用文字的微妙之处和文本组织的复杂之处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Leavis,1952:193)。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利维斯开展诗歌批评的重心所在。
无论是《英语诗歌的新方向》,还是《重新评估:英诗的传统与发展》,利维斯都特别注重从诗歌文本本身着手分析。在评析艾略特时,首先就引用《情歌》的诗行:“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应该把裤管挽起。”“这个能是诗歌吗?”利维斯问道,“然而,(该诗)也有些诗节,即使其意象和口吻都十分古怪,按照文选的标准也不能作为“非诗歌”而即刻否认”,他举出的是《情歌》的“黄色的雾……”那一节。利维斯评论说:“口吻的微妙与灵活、态度的复杂性,都令人震惊,而这正是诗歌意象的天然浑成。”(Leavis,1982:60-61)紧接着,利维斯认为艾略特的《一位妇人的画像》表现了诗人“对经验与技巧的完美掌控”,“妇人的话语表达方式与节奏是现代口语的,它们与诗歌的展开节奏完美匹配,而这节奏尽管自由并多变,但始终是非常严谨而精准”。(Leavis,1982:61-62)利维斯把庞德的《休·赛尔温·莫伯利》视为一部“伟大的诗歌”,并特别称赞其“技巧的完美”。(Leavis,1982:105)庞德的诗歌这样开头:“For three years,out of key with his time,/he strove to resuscitate the dead art/Of poetry;to maintain‘the sublime’/In the old sense.Wrong from the start。”利维斯评论说:“现在,他的诗歌技巧关涉表达一种成熟而复杂的感受力。诗歌的节奏,以明显的松散和随意的方式,正是微妙表达的绝招:‘与时代格格不入’通过严谨的格律方式传达到诗歌的每一根神经。”(Leavis,1982:108)利维斯的《重申批评家的任务》一文这样为《细察》杂志正名:“《标准》杂志做出判断,而《细察》杂志做出仔细分析”,“但是判断不能空洞无物。它需要具体的直接的选择。如果没有真正的恰当的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就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价值判断”(Leavis,1933:177)。这句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利维斯重视诗歌文本、诗歌语言及技巧分析的诗歌批评原则。
大批评家R.韦勒克曾经与利维斯有过一场不愉快的“文墨官司”,但是在韦氏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虽也批评利维斯“论战态度粗暴,不懂圆滑,有时甚至不懂礼貌”,却也盛赞其“成功确立了本世纪继艾略特之后最有影响的英国批评家的地位”(韦勒克,2009:398)。作为“艾略特之后最有影响的批评家”,利维斯在现代诗歌方面的批评思想十分深刻而复杂,绝非一篇小文可以阐述清楚。本文仅从其批评文本细读入手,结合历史文化语境,简要论述了其现代诗歌批评的一些核心观点。又因利维斯(Leavis 1933:48)认为,“没有‘现代主义诗歌’,只有两三个现代诗人”,为避免指代混淆,故而本文使用“现代诗歌批评”这个较为笼统的说法。
[1]Baldick,Chris.1910-1940:Modern Move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Buckley,Vincent.Poetry and Morality:Studies on the Criticism of Mathew Arnold,T.S.Eliot and F.R.Leavis[M].London:Chatto& Windus,1959.
[3]Day,Gary.The British Critical Tradition[M].Houdmills and London:The Mamillan Press Ltd.,1993.
[4]Eliot,T.S.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M].London:Faber and Faber,1933.
[5]Eloit,T.S.Selected Essays[M].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0.
[6]Greenwood,Edward,F.R.Leavis[M].London:Longman Group,1978.
[7]Leavis,F.R.For Continuity[M].Cambridge:The Minority Press,1933.
[8]Leavis,F.R.Revaluation: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M].London:Chatto &Windus,1936.
[9]Leavis,F.R.The Common Pursuit[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52.
[10]Leavis,F.R.D.H.Lawrence.Novelist[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55.
[11]Leavis,F.R.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82.
[12]Leavis,F.R.The Great Tradition[M].New York:Dooubleday & Company,Inc.,1953.
[13]Mackillop,Ian & Richard Storer.F.R.Leavis:Essays and Documents[G].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05.
[14]Paige,D.D.The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1907 -1941[M].London:Faber and Faber,1950.
[15]Samson,Anne.F.R.Leavis[M].New York:Harvester Weatsheat,1992.
[16]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M].付礼军,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17]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丁鸿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18]R.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M].杨自五,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9]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0]陆建德.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