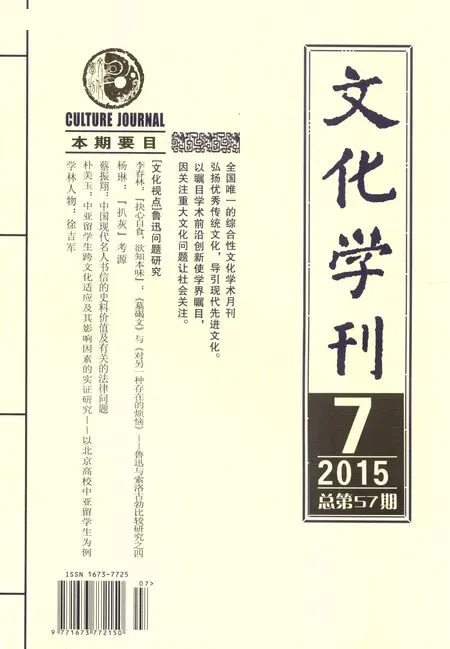女性失语到女性自我意识的呈现
——论契诃夫与乔伊斯·欧茨同名小说《牵小狗的女人》中的安娜
秦月宇珠 朴玉明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女性失语到女性自我意识的呈现
——论契诃夫与乔伊斯·欧茨同名小说《牵小狗的女人》中的安娜
秦月宇珠 朴玉明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牵小狗的女人》被美国女性主义作家欧茨于1972年以同名小说形式进行改编。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比分析这两篇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形象安娜,阐释契诃夫笔下的女性是处于失语状态,而欧茨改写后的安娜,则呈现出女性对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寻求。
安娜;女性失语;女性觉醒;自我意识
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反映出同时代俄国社会的现实。短篇小说《牵小狗的女人》是他1899年之作。小说从男主人公古罗夫的视角讲述他与牵小狗的女人安娜之间的婚外恋故事。1972年,美国著名女性文学作家乔伊斯·欧茨对其进行改写,亦命名为《牵小狗的女人》。欧茨虽然沿用原创题目、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但却从女主人公安娜的视角讲述。两部小说虽然情节相似,都以开放式的结尾结局,但两位作家对女主人公安娜的塑造却迥然不同,两部小说的主题也因此改变。契诃夫的小说主要表达男主人公憧憬爱情与未来新生活的主题,而欧茨则侧重于女性关怀,表达女主人公渴望寻求自我意识的女性主题。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比分析这两篇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阐释契诃夫笔下的女性是处于失语状态,而欧茨改写后的安娜,则呈现出女性对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寻求。
一、失语的安娜
女性形象一直是契诃夫笔下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小说中不写女性,就如机器没有蒸汽发动一样。……我的作品中不能没有女性!!!”[1]契诃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种类型:备受男性与社会制度压迫的女性,思想觉醒的女性以及行动觉醒的女性。小说《牵小狗的女人》中的安娜一度被解读为是第二种,“厌弃虚假空洞的婚姻生活,真诚地追求着真切自由的爱情”[2]的思想觉醒的女性形象,但此评价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安娜的形象是作家与古罗夫男性的价值观禁锢下的客体,即小说中安娜形象的建构,经历了契诃夫与男主人公对其的双重审视,安娜的话语和行为都呈现出被男性审视的痕迹。第二,小说情节发展的主动权是男性叙述视角,即契诃夫笔下的故事情节,是随着古罗夫的视角展开,古罗夫与安娜的相遇、相恋,皆以古罗夫的主动而发展。[3]此外,小说更多地是描写古罗夫的心理状态,他如何看待女人,看待安娜,看待这段婚外恋等。小说中安娜的话语与行动一直受男性掌控与制约。一言以蔽之,契诃夫笔下安娜的形象是处于客体的失语女性。
契诃夫笔下安娜的失语有四个方面。第一,小说题目中女人就是被审视的客体。小说题目《牵小狗的女人》看似主体为女人,但从小说的开篇来看,“据说在沿岸街出现了一位新人物:一位带小狗儿的太太。德米特里·古罗夫已经在雅尔塔住两周了,在这儿习惯了,因此对一些新的人物也发生了兴趣。他坐在魏尔奈家的凉亭里,看见沿岸街有个年青的太太走过”,[4]小说中的安娜已经被定位为客体,是男性审视下的女人,被男性言说。
第二,安娜在小说中被塑造成被男性需求的对象,即古罗夫乏味生活的调味品。[5]当古罗夫在雅尔塔第一次遇见安娜时,他就对这个“带着贝雷帽,牵着白狮子狗”的安娜产生浓厚兴趣,“她的神情、步态、服饰、发型都告诉他:她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已经结婚了,第一次到雅尔塔来,而且是单身一人,在这儿感到很寂寞……”,[6]这些都是古罗夫对安娜的第一印象,一位独自来到雅尔塔寂寞的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猎艳经历丰富的古罗夫敏锐的嗅到安娜身上散发的“寂寞”之意,古罗夫以此为契机向安娜展开攻势。在接下来的二人对话中,安娜就表达出她的寂寥之感,“时间过得真快,可在这里真没意思!”[7]安娜的话语与古罗夫所感受到的一致,呼应男主人公内心对安娜的看法,为下文二人之间的婚外恋进行铺垫。
第三,小说中安娜的话语无法被正确解读。契诃夫虽然让安娜有语言表达,但是她所想表达的真实内容却被忽略与误解。当安娜与古罗夫在酒店发生关系后,安娜曾忏悔“愿上帝宽恕我吧!……太可怕了……我在这里到处游逛,像神魂颠倒了,像发疯了……瞧,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瞧不起的、庸俗,下贱的女人了。”[8]安娜不想让古罗夫看轻她是一个不守妇道的放荡女人。然而她的忏悔在古罗夫则是一种“天真的语调”,他被这“不合时宜的忏悔所激怒”,觉得“腻烦了……要不是她眼睛里有泪水,他会以为她在开玩笑或演戏。”[9]古罗夫厌恶安娜的忏悔,他眼中的安娜是一个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虚伪女性。这与安娜的想法背道而驰,对读者理解安娜形象起负面作用。
第四,契诃夫在小说中更关注男主人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小说通篇是从古罗夫的叙述视角讲述他对这段婚外恋的看法,而安娜的感受一直是由古罗夫代言。[10]小说结尾处安娜的哭泣与话语都被强加上古罗夫的意志。古罗夫认为安娜哭泣是“因为激动,因为悲伤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太悲惨了;他们只能秘密地相会,像小偷一样不敢让人看见!”[11]这些都是古罗夫自己的想法,古罗夫是站在男性立场上解读安娜的话语与行为,他替安娜代言,他更未意识到安娜的哭泣是因她的内心痛苦与挣扎所致。因此,契诃夫笔下的安娜,是被审视、被言说的客体,是为满足男人私欲的附属品。
二、呈现自我意识的安娜
乔伊斯·欧茨是美国当代著名女性文学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对外界茫然困惑初涉尘世的少女和易受伤的年轻女性,又有坚强能干乐观的母亲型女性和有文化但又有别于传统性别角色、悲观的家庭主妇以及单身的知识女性”。[12]然而,在这篇被改编的小说《牵小狗的女人》中,女主人公身处一场纠结的婚外恋中。欧茨从女主人公安娜的视角出发,对安娜进行细腻的心理描写,呈现出安娜在婚姻生活与婚外情中的苦苦挣扎。欧茨对安娜的每一个举动、神情都进行十分细致地刻画,外现契诃夫原作中被埋没的女性身体体验。这种女性体验具体表现为安娜在婚姻及婚外恋生活中,通过自己身体所感受到的愉悦和不适表达自己的感情。当安娜与情人相逢于剧场时“她瞬间向前倾去,双手捂脸……假装他好像不在这儿。‘上帝啊,’她低语道。……现在她又清楚地看见他,她感觉她的血液冲入她的身体,大脑却一片空白,她快要晕了过去。”[13]此时安娜的举动就外露了她与情人相见时的紧张心情。欧茨笔下的安娜,是通过自己身体的种种感受向读者表达其情感。契诃夫小说中的此情节更多是关注古罗夫见到安娜时的激动心情,“古罗夫一看见她,他的心就紧紧地收缩起来,他很清楚,现在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了;……现在充满了他的全部生活,成为他的忧伤、他的欢乐、他朝思暮想的、唯一的幸福……”[14]此描写更侧重男主人公古罗夫,忽略安娜的体验。而欧茨小说中的描写则弥补了安娜被忽略的不足,她把安娜在剧院再次见到情人时因担心被丈夫发现的紧张心情,通过自己身体上的体验表达出来。
契诃夫笔下安娜心理感受被忽略的部分却是欧茨小说中描写的重点。安娜不再是契诃夫笔下被男性审视的客体,而是一跃成为会思考的主体。安娜在面对情人与丈夫时会有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被他们控制。[15]当丈夫给安娜打电话时,“他总是向她谈论着自己的计划、问题、生意上的朋友和他的未来。很明显他有未来。当他跟她说话时,她轻声附和以示鼓励之意,与此同时她也感受到自己心跳加速,生出羞愧之感,她羞愧地感受到她只是这个人专有的、私人的妻子。”[16]安娜在家庭中的角色是被丈夫固定好的——他专有的倾听人,但是当安娜听到丈夫谈论琐事时,也会因丈夫规划的未来感到激动,因为那也是她所渴望的生活,但她却是局外人。小说中安娜在丈夫面前一直是缄默的失语者,安娜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她认为,她与丈夫应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她只是丈夫的私人收藏品,丈夫所说的一切没有一件有安娜参与其中,没有一件与安娜相关联,安娜更无法找到自身的价值,这使她痛苦不已,这也是安娜出轨的一个诱因。当安娜和情人相处时,安娜并未改变其失语处境。安娜是在情人主动给她空间让她谈论自己的故事时,才与情人谈起自己的父母与丈夫,她女性的话语权需要男性的主动让步才能获得,但安娜的表白并未得情人回应。相反,他开始讲述“他的妻子,他妻子的野心、智慧还有如何利用孩子来反抗他……”[17]安娜再一次成为缄默的失语者,话题的中心又回到男人的生活。此时的安娜又扮演同样的角色,沦为情人的倾听者。
欧茨在小说中虽并未改变安娜的失语处境,但安娜已不再是被言说与被审视的客体,她通过自己女性身体的感受,讲述失语的痛苦和渴望摆脱痛苦的挣扎。安娜与情人发生关系时,她还在想“这不重要,她想得清楚,他不爱我,他没这意思……然而她好像吓坏了。”[18]他们发生关系后“她又有一种奇怪的、停顿的恐惧,感到这间房外的危险以及这张老旧的床……她觉得美丽正从她的脸上逝去,她的眼睛也渐渐失了光彩。”[19]这段不正常关系的开始,并非像契诃夫描述的那样简单发生,欧茨笔下的女主人公有思考,有感受,也有激情过后的恐惧。欧茨在小说的结尾让安娜欣然离开古罗夫,此时的安娜已觉醒,已不再甘愿依附于男性,做男性的附属品。她意识到要遵从自己的心、自己的愿望、自己的主体意识。[20]这种从女性体验感受,比契诃夫笔下安娜的忏悔来得更加真实。小说中的安娜以自己的身体体验和自我意识为媒介,向读者展现其婚姻与婚外情生活中的女性特有的体验,传达所感知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对比分析契诃夫与欧茨《牵小狗的女人》中安娜的不同形象可以发现,契诃夫所处时代是一个女性群体倍受压迫的时代,女性依附男性生存,没有独立意识,而欧茨笔下的女性显然认识到她们这种“属下”的处境,开始觉醒、挣扎、反抗,追求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这也揭示乔伊斯·欧茨改编契诃夫版《牵小狗的女人》的意义在于建立“女性自己的文学”的实践,因此,欧茨重新创作此小说是对女性自身性别特征的再现,具体表现为女性身体、女性自我意识的体验。改变安娜在原作中被男性审视,被男性书写的位置,实现由失语到展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表达欧茨对安娜给予的女性关怀。
[1]肖查娜.浅析契诃夫女性观及其三个发展阶[J].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7).
[2]吴慧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J].外国文学研究,1997,(1).
[3]刘雅悦.无条件的爱情,无过错的悲剧——《带小狗的女人》书评[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4).
[4][6][7][8][9][11][17]契诃夫.牵小狗的女人[M].朱逸森,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51.150-151.151.153.152.160.168.
[5]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10]Michael Meyer.The Bedford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M].Boston: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1998.149-175.
[12]单雪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世界中的女性群像[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4).
[13][14][16][18][19]乔伊斯·欧茨.牵小狗的女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63. 158.166.171.171.
[15]胡全生.女权主义批评与“失语症”[J].外国文学评论,1995,(2).
[20]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8).
【责任编辑:王 崇】
I106.4-03
A
1673-7725(2015)07-0131-04
2015-06-20
秦月宇珠(1991-),女,青海格尔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评欧茨的成长回忆录《逝去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