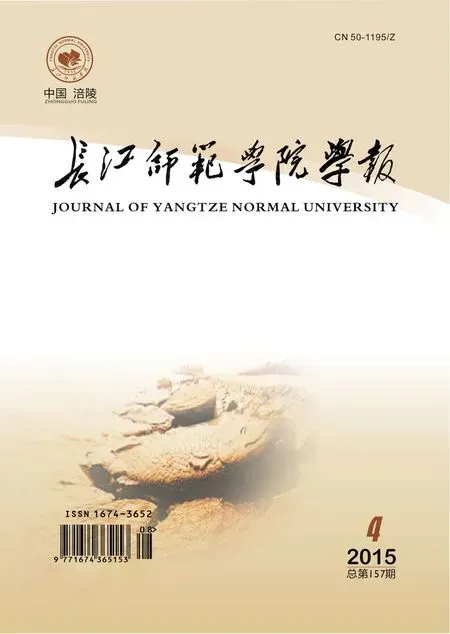寻根的里程:艾丽思·沃克系列小说的生态处所理论解析
周红菊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言
在其小说 《梅丽迪恩》中,艾丽思·沃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非裔女奴路维尼有讲恐怖故事的天赋,她的恐怖故事吓死了白人奴隶主的儿子,被割掉了舌头。在路维尼的故乡,人们认为人必须是完整的,舌头更是人的灵魂,没有舌头的人就和猪没有什么区别。路维尼把自己的舌头埋葬在一株被称为 “寄居者”的树下,这棵本来病怏怏的树却抽芽成长、茂盛起来,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木兰树。在她死后,风一吹过,“寄居者”的树叶沙沙作响,好像代替路维尼的舌头,继续为人们讲述故事。这个传说是非洲人民植物崇拜的写照,在他们心里,植物就是神灵,是上帝。经过革命洗礼后伤痕累累的梅丽迪恩,从这个故事看到了自己祖先的勇气、创造力和坚强意志,受到祖先智慧的启迪。她回到南方故土,坚持非裔文化,重建自我,最终找到了自我的历史位置。艾丽思·沃克相信,南方和非洲对于非裔美国人有着特殊的含义,南方是非裔美国人 “唯一的家”。
非裔美国人对于大自然的崇拜以及他们对于土地的依恋之情在艾丽思·沃克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艾丽思·沃克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以反映美国黑人女性的不幸遭遇和抗争为主要内容,但随着社会认识和了解的深化,她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在其作品成为显性的表达。对于被压迫和被贬损和被他者化的自然世界,沃克总是忧心忡忡,她说她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人类掐着地球的咽喉,一边摇动它,一边叫喊着 ‘给!给!再给!’他们不停地挤压!只要地球还有一口气他们决不罢休”。[1]在文集 《与文共生》她曾大声疾呼 “大地被毒害之时,它所养育的一切将无一幸免;大地遭受奴役之时!我们无人能享有自由!”[2]
随着生态理论逐步发展,生态的处所 (place)理论引起了西方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批评家的关注。著名生态学家布伊尔对生态处所的定义是:“通过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地形学的特殊性而限制和标志的对人有意义的空间。”[3]而王诺认为:“处所,简而言之,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它决定、影响、和标记着人的生存特征、生态思想和人的生态身份,同时这个自然区域也受到在其中生存的人的影响和呵护。”[4]艾丽思·沃克对于生态的关切体现在她的多部作品中一她在强调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非裔美国人对于故土的依恋的同时,揭示了工业和殖民发展对于环境的破坏以及破坏后隐藏的不公平。“处所理论则主要从人与特定自然区域的关系之角度思考人的生存、人的异化和人的身份确认。”[5]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意义上的 “处所”正是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成长和环境关系的写照。
二、艾丽思·沃克生态意识的繁盛枝叶
艾丽思·沃克的作品背景各异,但是几乎她所有的作品都有大篇的对美国南部和非洲的描写,她把其当做人物活动的场所或者魂牵梦萦的乡土。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女性,在美国受着多重压迫,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证。但是,艾丽思·沃克是个乐观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反映了人物历尽艰险的成长历程,主要表现为历尽艰难地寻找人生意义和历史位置。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非裔美国人常常会有 “我们是谁?”的疑惑。现实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就追溯回到非洲—他们梦想中的故土和美国南部的农村寻求自己的历史足迹和身份的印迹。在非裔美国人心里,他们的 “乌托邦”在原始的非洲丛林,早期的美国南部农村。
(一)迁徙过程中的故土依恋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非裔美国人历经两次大规模的动迁,在动迁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被迫与丛林和土地剥离,远离了鲜活性灵的生物,但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之上的生物对他们意味深远。他们的迁徙脚印里,注满的是对大地,对天体,对生活在天地间各种生物的深沉的迷恋和怀念。
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非裔美国人参入到工业社会后,他们不得不与土地剥离,散落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他们对非洲丛林和对南部农村故土的依恋和怀念一直伴随他们在工业化社会行走的脚步。在美国这样一个被称为 “色拉碗”的社会里,个人的身份认同几近成为人人追问的人文疑惑。迅猛发展的美国社会,为人们提供极为丰富的物质资料和舒适生活的同时,却让人们迷失了自己。无数的人在追问,“我是谁,我来自哪里?”非裔美国人更是难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摆脱掉奴隶制枷锁的非裔美国人,如果没有了对土地的依附,其灵魂飘扬在美国的工业社会里,不知道根要落在哪里。存在感缺失的非裔美国人在梦想中的非洲故乡和曾经生活的美国南部农村寻找自己的踪迹。
这种追寻是他们身份确认的必经之路。在他们的心目中,工业化美国没有他们容身之所,无法安放其心灵,称不上他们的家园。只有充满着神秘气息的非洲和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南部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在那里,他们生活虽苦,但是心灵是自由的;在那里,他们才有自己独特的与农业、自然紧密相连的文化,才能找到确认他们身份特征的历史印痕。海德格尔曾说:“‘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 ‘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6]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深受多重压迫,在美国主流社会里找不到自我认同的非裔美国人对于非洲和美国南部有如此深厚的依恋。
(二)土地对于受伤心灵的慰藉
非洲的丛林和美国南部的土地是非裔美国人在工业前时期的工作场所和栖息之地,是他们的家园,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底蕴和慰藉。
非洲的丛林是非裔美国人心目中的故土,是他们理想的 “乌托邦”。那里篆刻着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印迹,延伸着他们思念的根须。非洲的土地上蔓延着原始的树木,树木和人类的灵魂合体为一,天地自然和谐共生。非洲哲学的 “万物有灵论”正是当地非洲土著人对于大自然之神奇的膜拜和感悟,他们对自然顶礼膜拜,大自然回报以安定和爱抚。在非洲,人和自然万物都是平等个体,没有歧视,没有阶级,是非裔美国人思念和向往的神圣天地。
南方的土地让非裔美国人奴隶时期在田间劳动时有了些许空间和片刻心灵喘息的场所。获得自由后,南方成为非裔美国人的身体容纳之地,尽管生活依然艰苦,但是这片土地上与他们共生共长的植物和动物带给他们的内心无尽的抚慰。非洲的万物有灵哲学和植物崇拜使他们笃信:大地、植物可以为人带来福佑,这一点在艾丽思·沃克的系列小说中得到充分的佐证。
(三)艾丽思·沃克生态思想的伸展
艾丽思·沃克本人就在南部长大,长大成为作家后访问过非洲,并深深为非洲的风土人情打动。她对美国南部的农村和非洲有着深厚的情感。艾丽思·沃克借助乡土和自然的力量为自己的人物增添成长的动力,以表现自己的女性成长主题和她对于各种二元论思维的反抗和抵制,谋求大众的福祉。更何况,作为一个胸怀大爱的入世的作家,艾丽思·沃克本身就很关注环境的变化并且关注生态问题,这一点她曾经在多本文集和访谈中提到过,并把这种思维灌输于她的文学作品中。
艾丽思·沃克童年生活在美国南部的农村,在农村田野度过了自己难忘的童年。在南方星空下听着祖母的非洲传奇故事入睡,徜徉在南部广袤的绿色海洋,长大后依然有母亲的绿色花园相陪,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艾丽思·沃克熟稔绿色的土地和概念。作为一名关注社会环境问题的作家,艾丽思·沃克喜欢大自然,并且喜欢在大自然中冥思,但是,她没有像自然作家一样去大幅篇章地描写自然风光。她作品的人物在工业社会和农村之间穿梭,在现代工业社会受伤的心灵在土地上得以痊愈,是艾丽思·沃克的生态观的表现之一。另外,艾丽思·沃克特别关注生态问题背后的社会公平,她在其作品中对白人据以霸权而侵占、破坏非洲的原始丛林和不顾生态后果的攫取财富给以严厉的批判。
对于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思想,国内很多同仁对此做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评论,唐红梅、王冬梅、于爱琴、张艳等大约几十人从女性生态主义对此其各种作品的生态思想进行解析,但艾丽思的生态思想涵盖了种族、性别、落后国家和群落的众多复合元素和多层结构,正如王诺在其 《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一书中所言:“生态整体主义的和谐观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关系的和谐,特别是作为大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与其他自然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二是指与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密切相关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7]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出,生态整体主义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关注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它对非裔美国作家艾丽思·沃克作品中表达的对于种族偏见、性别歧视和人与自然、人的思索可以做出更为深入恰当的解释。
纵观艾丽思·沃克的五部小说,《紫色》《梅丽迪恩》《格兰齐·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我亲人的圣殿》和 《我父亲的微笑之光》,不难看出,艾丽思·沃克的生态关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五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作者作为人文学者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关切。非洲的风光和民俗的大段描写、美国南部优美的风景、人物在自然环境里得到心灵净化、找回自我的过程、现代工业对于环境的破坏、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女性在工业社会里所承受的种种遭遇、人类的身心无处安置的困境,都是作者对于人类整个社会的关注。黑人的生活与美国的种植园经济紧密相关,这一点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所以美国黑人进入工业时代后依然对美国农村的土地和生活深怀爱恋。非裔美国人只有在绿色生态的丛林和田野里,心灵才能自由地漫游于广袤的土地,得到大自然的抚慰;那里是他们的家乡,在那里他们能够得到大自然的神启,从而舒缓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得以摆脱现代生活的异化。
三、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思想盛开的花朵
事实上,艾丽思·沃克在她创造早期时候,就对生态极其关注了。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对人类的关切,更是其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索和对环境问题的密切关注。在文论著作 《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艾丽思·沃克把自己的妇女主义定位为 “爱一切包括月亮”在内的成熟的女性,并且她在 《紫色》《梅丽迪恩》《格兰齐·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我亲人的圣殿》《我父亲的微笑之光》中大量的关于美国南部景物的描写、对非洲故土的眷恋以及小说人物在自然中痊愈和获得能量的叙述,反映了她对于非洲故土及南方土地的深深爱恋。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成功阐释,并与其处所理论严密契合,这是因为,“处所理论与生态主义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地球就是一个大处所,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处所和家园,因此回归处所也意味着回归这个星球的自然家园。处所理论论及整个地球大处所时,实际上已经与生态整体主义合而为一。”[8]
(一)处所依附—非裔美国人对自然的崇拜
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意识首先体现在非裔美国人对于自然的崇拜。在耐蒂的非洲丛林的历程中,她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耐蒂在非洲的见闻,尤其是非洲人民与神奇的 “屋顶树叶”的紧密联系,从而向我们展示了非裔美国人乃至全人类与大自然由来已久的深厚渊源。
当耐蒂和塞缪尔夫妇走进非洲丛林时,耐蒂的眼睛里,是 “除了树还是树”的丛林,非洲的人民所居住的圆形小茅屋是一层层屋顶树叶铺起来的,屋子是用泥巴和石块砌墙,他们种的庄稼收成都不错。奥林卡人与大地树林和谐相处,过着自给自足,生态自然的生活。但是酋长贪心,把长屋顶树叶的土地都开荒种庄稼,很快奥林卡人就深受屋顶树叶被破坏之虞。先是大雨暴虐半年之久,淋坏了奥林卡人的房屋,恶劣的环境使得奥林卡人严重生病,甚至死去,奥林卡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人们希望屋顶树叶树赶快重新长起来,但是大自然的恢复速度总是大大地迟于被毁坏的速度,人们在尝过毁坏自然的恶果之后,对屋顶树叶树顶礼膜拜。对于非洲的布须曼人而言,自我是个人、族人和山川及自然万物融合一体的自我,是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的自我。这种崇拜,虽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大自然的恐惧而形成,但是,人们也由此得知: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不容破坏,否则,被破坏的自然同样会伤害到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本来一体的 (oneness)。
在 《我亲人的圣殿》中,丽思的梦境同样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情节。在她的梦境里,原始人的男女分而居之,但却和平共处。人们对大地有着崇拜和畏惧之心,他们顺从自然的规律,采食自然的果实和种子、狩猎来度日。沃克说:“我在写 《我亲人的圣殿》整个过程里,我都想着我们和动物的关系,四处来的动物都跑来这里,和我呆在一起。我很惊喜,这很明显我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是我所浮现的对于动物的热忱,这使我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各种动物,我是说原来这片土地上没有过的。”[9]《我父亲的微笑之光》的孟多部落是沃克创造的理想精神家园,是自然的象征,是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典范。而在《梅丽迪恩》中,梅丽迪恩的奶奶始终相信,人在大自然中可以得到神启,获得重生的能量。
艾丽思·沃克生态思想中的自然崇拜深受非洲的 “万物有灵论”影响,“万物有灵论”宣扬世间万物和人一样,有着生命和力量,带给现实生活中受尽压迫的非裔美国人以神启,使他们借助这种力量,得以度过艰难的岁月。他们的这种自然崇拜,既是原始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扬,又是对美国社会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的解构。
(二)“处所剥夺”—工业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王诺注意到,“日趋全球化的当代文明是一种越来越非处所的文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不包括生态城市)和消费文化,不仅剥夺了多数人的处所—或者逼迫人们进入非生态的城市生活,或污染糟蹋了人们童年或者祖先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处所,而且还使得那些较少受到文明污染的乡野居民越来越自卑、没有自信、越来越向往非生态、‘非处所’的城市生活。”[10]王诺所叙述的 “处所剥夺”或者 “非处所”的境况正是非裔美国人在现代社会里所遭遇由外到内的掠夺的真实写照。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描写中,溢满对处所—非洲故土和美国南部农村的欣赏和赞美,但是,在工业迅速发展的社会,非裔美国人的故土非洲和美国南部的处所皆遭到掠夺,其原有的生态和谐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非裔美国人在 “处所剥夺”后的失落和身份丢失的困境在艾丽思·沃克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 《紫色》中,当英国人以建设的名义破坏掉非洲人的家园时,奥林卡人由最初的新奇和漠然转为后来的愕然,他们的屋顶树叶和生存环境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此时,奥林卡人已然束手无措,任凭殖民者毁掉自己的屋顶树叶树和家园。现代工业殖民者的道路和铁皮房子在非洲的土地上,就像扎入奥林卡人的心脏的利器,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舒适自然的屋顶树叶的土房子,甚至他们的自我认同。在 《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中,科普兰在工业的城市丢失了自己,只能返回故乡,在土地上找回自己的信心和身份确认。在 《我父亲的微笑之光》里,非洲俾格米人的树林被贪婪的白人无情地砍伐,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树木 “被一棵棵地放倒”,艾琳不无担忧地说:“俾格米人不久会在地球上消失。”[11]在 《我亲人的殿堂》这部小说中,沃克谴责了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压迫。在阿威达对季蒂和她女儿卡拉特的回忆中,在非洲殖民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 《紫色》中一样的画面:白人野蛮地砍伐森林,并用经济作物取而代之,单纯重复种植经济作物完全破坏了生态平衡,迫使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范妮说白人和他们做法都不一样,盖了那么多的大楼使之下的大地窒息,她记起印第安人在搭帐篷时都要吟唱:“亲人啊,抬抬你的帐篷,让大地母亲沐浴阳光。”殖民和工业化对于非洲原始丛林和村落的破坏,是非裔美国人失去了理想的家园,从而影响到其身份的焦虑和信心。因为,“生态的自我认同则跟生态有关,主要考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处所,以特定的生态区域和整个地球生态为坐标,来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确认角色,以特定的处所和特定的景观来确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如何生存。”[12]而这种处所一经遭到破坏,生态身份将遭到质疑,失去了家园必将导致身份缺失。这是沃克笔下的非裔美国人的身份焦虑,更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困惑。
在 《我亲人的圣殿》中,沃克借范尼之口评价当时美国的殖民活动,“他们挖出地下的所有东西声称其占有,人们的骨骼、骨灰、金子、钻石、银子。而上帝只知道铀、钚。黑人不找埋在地下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费劲去找。”[13]这句话虽然充满种族主义的意味,但是同时表现了某些特定集团掠夺和攫取财富带来的环境破坏。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自我逐渐远离土地,“现代文明导致人类存在的处所性被大大消弱甚至被去除,割裂了人类生活与自然的依附关系,环境污染毁坏了绝大多数人的家园—在那里,我们的童年和祖辈一生的幸福取决于风景、气味、声响、历史、邻居和朋友的混合体,这种混合微妙、无形,却能触及灵魂深处,并构成一个处所、一个家园,而今我们即便有意返回也无家可归了。这就是处所掠夺。”[14]处所被掠夺的人们陷于 “非处所”的困境,在苍茫世间找不到自我。这是非裔美国人的困境,更是整个人类的难题。
(三)处所想象—大自然的抚慰
当代人被现代文明剥夺了处所,他们的处所被剥夺和非处所感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不断攀升。而有良知的作家们 “不得不通过想象来填补 ‘非处所’生存的遗憾,处所想象由此产生。”[15]这种想象,纵使虚构,也同样可以获得 “处所感”。王诺认为,“处所的想象是生态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生态文学的重要使命—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填补 ‘非处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心灵的空白,并激励现代人找回或修复处所。”[16]艾丽思·沃克的生态理想就在这样的想象中得到了升华。如果说 《紫色》里的非洲丛林是非裔美国人的故土理想的幻灭,《我父亲的微笑之光》则是对她生态乌托邦的重建,艾丽思·沃克理想化地在作品中书写了非裔美国人的自然由崇拜到幻灭,得到自然的神启,复又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变奏曲。
当谈到 《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里面她表现的对人类的未来和生存能力的态度时,艾丽思·沃克毫不客气地指出:“很可能白人男性作家对他自己的罪恶认识的比黑人男作家更清楚,毕竟关于毁掉地球的话题已经提了几个世纪了,而黑人作家和白人女性作家则把自己看作是这种罪恶的接受者,所以就站在基督、被压迫者和无辜者的立场上。格兰奇在受歧视和压迫的世界里逐渐生硬、冷酷的个性、对于家人的冷漠令人切齿。”[17]在他的第三次生命时,格兰奇回到贝克县,他在自己的田地上劳作,并建立起养育自己和家人的田庄或农场。这种生活赋予了格兰奇独立和自由,赋予他第一次承担生命中所缺失的人类最基本的责任能力。布朗菲尔德杀害梅姆之后,他完全扮演起了 “父亲”的角色,把在儿子身上所欠缺的爱护和关心全部倾注到孙女露丝身上。他照顾孙女露丝的时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是他的人性及灵魂的复兴。他不仅给露丝一个舒适的家和富足的物质条件,还让她上学读书,教她认识社会的现实,以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格兰奇将自己能得到的一切都给露丝,培养了露丝的思想和灵魂,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露丝有个安全幸福的未来。格兰奇的生命就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复活,土地、植物对于人的抚慰和成长作用由此表现尽致。
而在 《梅丽迪恩》中,艾丽思·沃克把经历了风暴、受伤的女主人公梅丽迪恩的复原和成长置于美国南部地区的农村。梅丽迪恩回忆了她祖母在大自然中类似冥思的一次奇怪的精神迷醉中获得能量、获得新生,并从此后经常裸身在院子里接受阳光的爱抚以求得健康的经历。梅丽迪恩在原野中去感受这种力量,当恐惧和紧张过后,梅丽迪恩找到了感觉,“从她左腿的后面某处,有种被叮的感觉,如果不是特地在这静站的话,她可能会因为疲劳或者紧张逃走。然后她的右掌,她的左身,开始感到好像有人扇他们一样。但是,她的大脑中却感到一阵轻松。保卫她的那些土墙好像向外冲去,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疯狂旋转着,使她从自己的躯壳中升腾起来,像飞一样。在这个运动中,她看到了家人的脸庞,树枝,鸟翅,屋角、草叶、花瓣、都向着她头上冲过来,她被卷进漩涡,就像他们一样自由、欢畅地旋转起来。”[18]然后,崭新的梅丽迪恩回来了。这段描写虽是印第安人的一种巫术,但实际上却是艾丽思·沃克平时冥思时的一种感悟:人在自然中找到自己,复原自我。
在 《我父亲的微笑之光》这部作品里,艾丽思·沃克在其中构建了孟多这样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家园。回到孟多,就是回归自然的怀抱,与深受创伤的大自然一样,孟多部落也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但是苦难洗刷后的孟多部落,把信仰、文化与传统看得弥加珍贵。父亲鲁滨逊曾迷失于代表现代文明的基督教,并传教说人类有统治整个地球的权利,遭到部落人们的强烈反对,表示对此根本不相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人应当生活在感情而非理性之中,通过摆脱理性的奴役,达到与自然的融合。孟多人郑重宣告于世:未来的大教堂将是大自然,人们最终将不得不回到树林、溪流和光秃秃的岩石那里去[19]。艾丽思·沃克通过孟多部落的兴衰旨在告诉读者:人类要主动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回复自然的怀抱,这样才能够重建与自然的和谐。
艾丽思·沃克在上述作品中以自然环境的破坏为背景,探索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与自然的关系。《紫色》淡漠的态度只会导致生态破坏,从而自我毁灭;《我亲人的圣殿》则是现代社会对于生态的破坏而导致人类对于自然态度的分化,人们的生态意识散落在现代的砖缝里;《梅丽迪恩》则重拾生态的理念,在现代社会里伤痕累累的梅丽迪恩求助大自然,渴求从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交流中获得能量,重新找到自我;《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以反思的态度回到故土,在土地上重新拾起做人的尊严;而 《我父亲的微笑之光》则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现代社会的生态乌托邦,尽管面对现代的诱惑,孟多部落仍然坚持自己的生态观和价值观,在神奇的土地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一幅大同景象。这几部作品折射了人类生态意识的转变过程,更是艾丽思·沃克生态思想在作品中的真实写照。“如果说,非裔美国人和本土美国人从他们的非洲和美国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万物有灵的信仰。这种信仰有助于感知的自然获得。对于科学家发现树木、植物、花朵都有情感的事实,我丝毫不觉意外,当他们被吼的时候,他们会萎缩,当要伤害他们的坏人出现时,他们会昏厥。”[20]
四、艾丽思·沃克生态思维的生命根触
艾丽思·沃克是个入世的作家,她关注生活的一切实际问题并在作品中作出回应。她的生态思想是相对较为显性的表达,但又不成体系。这种思想的形成多是来自于她的创作宗旨、成长环境和她不断延伸变化的思维方式。
正如艾丽思·沃克本人所讲,她说这个社会给了我们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她认为,“每个人都没有理由抱怨改变不了任何现实。比如说,成千上万的饥饿儿童、居无定所的人们、丛林央求我们让他们生存,河流哭喊以求洁净,天空号叫把臭氧层留下。我们有无尽的自我实现的方法。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是时间指给我们的道路。这是一个作为地球人完全实现自我的时候。到了该负责和管理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失去地球了。”[21]她时常为人们远离自然而感到遗憾,她认为远离自然是人们感官退化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住在城里,城里的一切都是人工设计的,我们常常会忘记了春天是多么的奇妙。”“但是,纽约城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孩子,常常根本看不到自然持续不断的变换,看不到春暖花开……但是想想你都生活在高楼大厦和纸堆里面,你也只是通过书本而不是通过亲身感触去学习知识,所以你不知道这种大自然的创造力有着一种相继的神奇力量。”[22]
艾丽思·沃克对于故乡非洲和南部地区充满了深情,她的作品的根须延展在非洲故土和美国南部地区,并得到其精神食粮的浓情滋养。非洲对于她是片神奇的土地,但她对其被掠夺的事实充满了愤慨。沃克说:“我认为非洲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出生地、世界上各民族的诞生地,所有事物都是如此。她只是被当做地球上其他民族的货源地,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走进来掠夺,丝毫没有要回报、补充、支持或者滋养的想法[23]。”正是艾丽思·沃克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挚爱,她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症结,并在其作品中对其积极回应,这不仅体现了一位入世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体现了艾丽思·沃克心怀天下的人文主义情怀。
艾丽思·沃克对于美国南部农村场景及非洲的熟稔得益于她的美国南部农村的生活经历和她对于那段生活的热恋及成人后在非洲的游历。沃克很幸运自己在加利福尼亚能看到很多的树木和广阔的天空,并且她的母亲就像 《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里人物梅姆一样,无论居所是如何的破落,总会用鲜花装点她们家的房屋。
艾丽思·沃克彻底的生态主义思想更多的是得益于她对于盛行于西方社会的二元论哲学思想的解构。她曾经这样来描述自己思想的转变:
“人们必须努力抛弃令人窒息的以天为神的宗教,不管它是什么,回到他们在自然的根本,把自然当做神圣的来源。《紫色》真的是一部教你信奉自己的神或者上帝或者别的神圣的物质的作品。你要舍弃查尔顿—赫斯顿—典型的上帝,丢弃耶和华,远离那些你祈祷时说服你说你是虚无……你是孩子,是大自然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小说的最后,西丽理解了上帝可以是任何物质……可以是所有的物质。这就是关于人们只如何需要宗教来拓展他们的社会项目和政治事项甚至他们的精神需求,但是事实上,神圣的物质就时刻在你面前。你不能把自己和地球分裂,如果你理解了这点,你就不再惧怕死亡。你可以是绿草,可以是奶牛,即便他们真的朝你开枪,但你就在这里。我在想,为了做一个地球的热爱者,他们会怎样惩罚我?”[24]
艾丽思·沃克对于上帝唯神思想的逐步解构和她对权威的无惧、她对自然的无上崇尚以及她自己在多次访谈中提到过受到日本和中国、印度等亚洲文化的影响的事实,使她心属自然,彻底瓦解了上帝的权威,把这种慰藉和救赎的神奇力量归属于自然,宣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息息相通,万物皆有神灵,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个体的关系。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整体观虽略显凌乱,不成体系,但是作为入世的现代作家,她敏锐地感触到了生态思想的变化趋势,并在作品中着力伸张,不失为一大进步。斯奈德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人类生存栖居的大处所。对于这个不可或缺的大处所的关怀和呵护,就是对于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非生命包括人类自己的物质的关心。我们应该向斯奈德一样,“开放全部感官,敞开心灵,去了解这片土地的前生今世,明确自己栖居者的定位,以一颗虔诚、谦卑的心去积累知识、亲身实践、最终将听到来自土地的声音,而大地也感受得到栖居者的脉搏,生态的栖居者与大地终将互相接纳。”[25]
[1]Mcquade,Donald,and Robert Atwan,ed.The Writer’s Presence:A Pool of Essays[M].Boston:Bedford,1997:215.
[2]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M].Orlando:Harcourt,1988:147.
[3]Lawrence Buell,The Future of Enviromental Criticism,Enviromental Crisis and Literature Imaginition[M].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5:145.
[4][5][7][8][10][12][14][15][16][25]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2、192、163、191、204、201、203、208、204、215.
[6][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
[9][17][20][21][22][23][24]Rudolph p.Byrd,ed.The world Has Changed: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M].New York:New Press,2010:112、259、252、306、83-84、191、306.
[11][19][美]艾丽思·沃克.我父亲的微笑之光[M].周小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32、118.
[13]Alice Walker.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M].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302.
[18]Alice walker.Meridian[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6: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