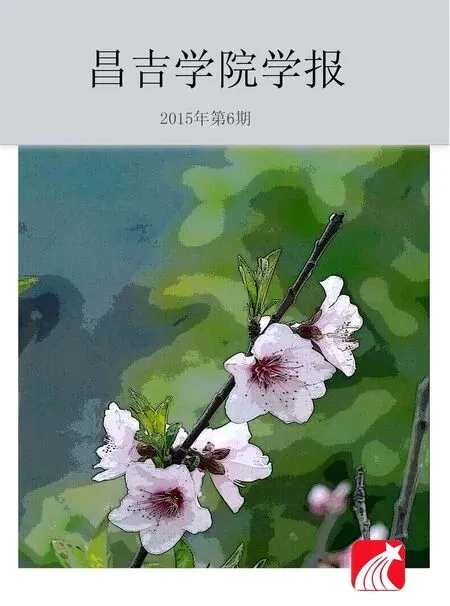试论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现象
全玲玲 刘宏平
(1.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2.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试论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现象
全玲玲1刘宏平2
(1.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2.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元代的戏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尤其出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面极广,她们所闪耀的光辉甚至掩盖了剧本中男性角色,是文学上的“重女轻男”。了解元代戏曲中的这一特殊现象背后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对欣赏元代戏曲及相关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元代戏曲;人物形象;女性形象;原因;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封建社会,女性往往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其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多是苍白而悲哀的。不过,当我们在欣赏元代戏曲时,却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感觉。在《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中“旦本”戏共五十多种,即使是在“末本”戏中,都出现了大量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元代戏曲中的女儿们爱憎分明、坚贞勇敢、大胆追求爱情、真正视功名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剧作家们都集中笔墨体现各类女性的“美”,给读者与观众展示了一幅尽善尽美的“百花图”,男性形象的刻画力度则明显不足,相对单调的男性角色成为了陪衬这些花儿的“绿叶”,使之越发美丽动人。
一、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重女轻男”现象的具体表现
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是多部戏曲所共同体现出来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女性角色的多样性和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上。
(一)女性角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元代戏曲中,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无论是平民少女还是贵族宫妃都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在元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如《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琵琶记》等许多普通人都耳熟能详不朽之作中有矜持美丽的莺莺、泼辣伶俐的红娘、机智勇敢的谭记儿、不顾世俗礼教大胆追求爱情的张倩女、坚毅倔强的李千金、坚贞善良的罗梅英、孝顺刚强的赵贞女、聪明自重的赵盼儿……女性角色人物数量众多,但无一不是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甚至带有一种叛逆的野性美,真正体现出了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相比之下,男性角色则显得单调且苍白,多为书生形象且多体现其性格中不让人认可的一面,即使多情却非常软弱,有时这种软弱的性格往往就是悲剧的根源。如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蔡伯喈,软弱的性格让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不敢违抗君王与父亲的伦理要求,最终致使家中支离破碎,在这个悲剧中他难辞其咎。其他的如志诚但痴傻耍赖的张生、软弱无主见的白士中、热心功名重礼教、道貌岸然的王文举、裴少俊、仗势无礼的秋胡,等等。不难发现元代戏曲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比男性更高大更鲜明,比男主人公更能打动读者,引起读者共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并非都是同一背景,她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下至妓女贫家女上至官家小姐宫廷后妃,身份各异,既有现实的女性又有神话的女性,还有魂魄的女性,都有着迥异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对妓女形象的塑造,一直以来,妓女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一群,所受羞辱和损害甚于任何一个群体,根本就没有社会地位可言。“偶尔,她们也能成为人们的话题,甚至得到某种称颂,但那并不是出自对她们的不幸的同情,更不是出自对她们抗争的支持,而只是因为她们或为达官贵人‘守志’,或为风流才子‘立名’,换句话说,是因为她们做了维护男子声誉的事情”[1]。的确,自从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妓女形象以来,大多是以“搔首弄姿”的艳态或为上述目的展示的,只有到了元代,才得到了重视,虽然以风尘女子为“正旦”的戏并不多,却能看到元代剧作家对她们的特别关爱,赞美她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肯定她们的反抗与斗争,这使得元代戏曲中的妓女形象热心善良、见义勇为并且聪明伶俐、多才多艺,极具人格魅力,扭转了以往文学作品对妓女的扭曲。这一点在关汉卿的作品中尤其明显,通过《救风尘》中赵盼儿等角色的塑造揭露她们的痛苦、愤慨与反抗,抨击社会对她们的歧视、迫害和侮辱,充满了对这一特殊群体命运的人道关怀,并带有些许浪漫主义的光辉。
(二)女性形象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元代戏曲成功地塑造了大量具有理想色彩的女性形象,并且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不是单一呆板,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她们既富有斗争精神又有一定的妥协性,如秋胡的妻子罗梅英能够反抗秋胡的无礼和仗势欺人,却在婆婆的以死相逼下妥协,与秋胡团圆;李千金敢把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抛至脑后,反驳裴尚书的污蔑,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她也不得不饮恨回家。她们既有原有的个性特征又有动态的成长过程,如温顺纯良的窦娥在看清黑暗的现实之后满腔怒火与怨气喷薄而出,骂天骂地,许下三桩奇愿,发出对这不平世道控诉和争取公平合理的最强音。
另外,戏剧作家对女性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使得女性形象更加真实出众,《拜月亭记》中的王瑞兰身为尚书小姐,在落魄无依时央求与蒋世隆同行,并提出“权说是夫妻”的建议,但当蒋世隆向她提出成亲时,又表现出来相府小姐应有的矜持,故作回避。同样的矛盾心理在崔莺莺身上也诠释得淋漓尽致,她外表矜持,内心热烈,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节奏,性格上既热情又冷静,有时一本正经,有时狡狯多端……她们的矛盾心理并非虚伪做作,而是与其自身的出身、地位、教养分不开,贴切地反映她们的真性情,有着更加真实、深刻的思想地位。
也正是因为写出了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成长过程,才使得她们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一颦一笑都入木三分,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在同一剧本中的男性形象的刻画则稍显薄弱,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既少有细微矛盾的心理活动过程,也看不出其性格发展完善的过程。如果说元代戏曲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男性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浅吟低唱,那么,女性则已站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痴笑怒骂,血肉饱满,具有立体感。因此,有自己独特个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能让观众为之笑为之哭的男性角色则少之又少,表现了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地位和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从这点就不难看出剧作家们对女性人物的“钟爱”。
二、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重女轻男”现象的客观原因
文学总是生活的反映,一定的文学现象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客观相联系的,元代戏曲中作者对人物塑造的“特殊偏好”也不例外,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文人的悲惨处境甚至元代的一些政策法例等等原因都会直接或间接引发这一现象。
(一)南北文化的碰撞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特色的时代,南北文化因子自由交融碰撞为汉族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各种社会风尚、思想观念等都在悄然变化,为元代戏曲提供了新的素材,是戏曲中人物形象“重女”的前提条件。
公元1279年元灭掉南宋,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建立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方民族生性粗犷豪放,不过多拘于礼节,也没有礼乐文明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卑尊之分。北方少数民族在男女交往方面,其态度也相对开放自由。女性在游牧民族中的社会地位相对比中原女子高,她们在爱情中表现的也更直接更主动。“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以其野蛮和落后的文化,松驰了儒家伦理纲常对妇女的重重束缚,使她们重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严和自由。妇女可以离婚、改嫁,婚姻不一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蒙古族中甚至还有入赘的婚俗”[2]。这些新鲜的异族文化思想的涌入,客观上对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合理因素起了改造的作用,人们不满一些腐朽陈旧、束缚自由、压抑人性的传统观念,便吸收一些草原游牧文化中新的思想观念。于是,草原文化中提倡敢爱敢恨、风格奔放的审美观念也逐渐被中原农耕文化所接受并吸收,女性的身心束缚也迎来了一次暂时的大解放。
终元一代,人们对贞节观念普遍淡薄,这种变化反映在平民妇女的婚姻生活中更是十分典型。元代对女性的教育和控制较之前代有了一定程度的松懈。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剧作家们都不得不创造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既有主体意识的觉醒又有张扬个性与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一定的理想色彩和进步意义。所以说戏曲中女性形象则既是对中国传统女性美的继承同时又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特色。
(二)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跌落
元朝的建立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来说是一大贡献,然而对那时的文人来说却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不堪的处境、黑暗的现实、社会悲剧时有上演等等状况让当时文人苦不堪言,戏曲中人物形象“轻男”现象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从人身权利到政治制度,强烈的不平等性弥漫了整个社会。“儒生不如人”是元代民间的俗语。《大义略序》中记载:“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辖。”书生们才华无处施展,乃至与娼妓、乞丐为伍,造成了无数的时代悲剧。许多著名的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都熟读儒家经典,满腹才华却处于一种进则无门、退则不甘的尴尬境地,最终也不得不“偶娼优而不辞”或“放浪形骸,期于适意”,笑傲风月,玩世不恭。文人身心受到摧残便寄托到文学作品中来,翻开元代戏曲,给人强烈印象的就是里面充满了文人的悲愤与辛酸,无论是哪类题材,文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胸中的激愤表现了出来。因此,可以说元曲就是元代文人困顿失意生活的一幅全景图。在此种压抑屈辱处境中,不少文人学子只能对时代进行口诛笔伐来渲泻满腔悲愤,把自己的忧愤哀思化入戏曲创作中,批判揭露封建士大夫的昏庸卑鄙,讽刺读书人的悲惨软弱。
虽然处境困顿,仕途无望,但仕途上自古就不缺少“心思活络”的读书人,他们为了荣华富贵抛弃妻子、忘恩负义的例子并不少见,正直的文人以这种现象为题材进行创作或揭露他们的真面目或抒发自己愤怒之感,如杨显之的《潇湘雨》,那么像这类戏曲中所塑造的男主人公自然就不那么光彩,反而衬托出女主公的无辜、楚楚可怜。戏曲中的“轻男”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如实反映和无声的反抗,也是对自身不幸处境的无奈叹息和自嘲。
(三)文人与艺人的交融
如果说元朝是当时文人学子的大不幸,那么文人学子的大不幸却是元代戏曲的大幸,正所谓儒生不幸文坛幸,元代是个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相结合的时代。大量知识分子流入市井瓦舍,浪迹于大邑通衢的勾栏戏院,靠填词作曲混一口饭吃。贴近下层社会的经历让他们直接目睹了一直就生活在最底层的奴仆歌伎们的悲惨生活,使他们的思想意识逐渐转向市民阶层,这对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现有记载,元朝一百三十四年间,所有戏剧作者均为男性,书生们同市井女子有着广泛接触,不自觉地“将这类女子的性格特征融入笔下,使剧中的大家闺秀少了一份虚伪做作、自怨自艾和逆来顺受,多了一份市井女性的勇敢泼辣,在爱情婚姻中大胆勇敢,敢作敢当,性格夹杂着野蛮泼辣,无所顾忌地坦诚对爱情的渴望,不是传统大家闺秀的形象”[3]。
在与青楼女子的交往中,书生文人们开始真正认识了她们身上可贵的精神品质,不再以世俗的眼光来审视她们,更重视妓女的技艺才能和为人处世之道,不再视她们为玩物。而且许多演员技艺高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夏庭芝的《青楼集》记录了元代一百多位优伶姓名、特长、与身世,有为色艺出众的女艺人立传之意,这是史无前例的。许多剧作家和妓女、演员关系密切,像“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就与她们有密切交往合作,关汉卿深谙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钦佩她们的才智,悲痛她们的不幸,“正是因为有了如此许多的亲身体验,关汉卿才能写出如此许多至今仍深得人们喜爱的本色杂剧,而以旦本尤为出色。王国维评价其杂剧是‘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宋元戏曲史》)。的确,关剧所蕴涵的深意,往往只有在细细的咀嚼回味中方能体会其中的沉重感与分量感”[4]。陈杂的市井生活、雅俗并存的民间文化滋养了流连于民间的封建士人,终于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女性命运及女性问题进行关注与思考。
(四)社会政治因素
一个时代的政治举措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代文学的走向,就如唐朝的科举取士制度便与唐诗繁盛局面有着密切联系。元代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重武轻文等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开放兼容的文化氛围使元代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更加细致更加大胆,他们抓住这一时代“契机”,抒写女性之美。元代特殊的社会政策无意间“催化”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氛围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政策最少的王朝,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5]。在多元政策统治下的元代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各种思想自由发展、相互碰撞,程朱理学的纲常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开放与兼容的文化氛围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使得套在妇女身上的各种枷锁有所松懈,让女性身心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空间和自由。这种变化表现在婚姻爱情中较为明显,《墙头马上》李千金、《西厢记》崔莺莺、《倩女离魂》张倩女等等在爱情中任情任性、不管爱情之外的门第和世俗观念,要求摆脱礼教的束缚,不仅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而且机智勇敢捍卫自己的婚姻。她们的举动对传统道德礼教来说不可谓不大胆,这是时代赋予她们的勇气和力量。同样地,她们与意中人私定终身甚至生儿育女,在封建正统观念中绝对是无法容忍的,但在戏曲中最终她们都获得了自己的爱情,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也是时代对她们的宽容与关爱。
还有,戏曲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6]。因此也就更不会被统治者看在眼里,所以对女性描写的大胆直露也非前代或其他文学样式所能比的。
三、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重女轻男”现象的主观原因
文学作品固然是生活的产物,更是作家们在认识生活、熟悉生活基础上的审美评价,自然就少不了作家主观发挥,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读者观众的喜好等因素也同样在影响戏剧的创作。
(一)文学发展轨迹与观众喜好
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并非一时一地的现象。前代的《诗经·氓》《孔雀东南飞》《霍小玉传》等作品都有这种倾向,如氓三心二意、负心而女主人公勤劳善良、坚毅;焦仲卿软弱、愚孝而刘兰芝则不仅美丽能干且痴情有骨气;李益毁约抛弃小玉、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功名而小玉温柔多情且刚毅不屈……虽然不明显,或者只是文人们无意间形成的,却也能看出文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可和其发展源流,这些都为元代文人提供了借鉴,出于对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同情或为抒发自己对女性的喜爱之情,元代的戏曲沿袭了这一倾向,继续不吝笔墨塑造“完美”的女性形象,而男性则作为陪衬出现。此外,书生文人们组织书会,审美趣味和思想相近的人往往会形成一个“集团”,他们相互唱和切磋合作,彼此影响,对男女人物形象塑造的“厚此薄彼”这一观点一经有人提出、接受或无意识形成便会在这一“集团”中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从而成为一种趋势。
在宋代的基础上,元代的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使通俗文学发展很快。“他们(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影响到包括戏剧创作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作用不可低估。”[7]市民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发生冲突,通俗的市民文学受到大众的欢迎。由于戏曲十分注重群众性和舞台性,人们更喜欢女演员的演出,喜欢喜剧,观众的喜好需求对戏曲情节结构的安排及人物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满足观众的喜好赢得市场,剧作家会大力创作写女性赞美女性的作品。可以说,元曲是文人、演员、观众共同创作的。就像人们希望有个大团圆结局一样,观众都难以接受血淋淋的悲剧直接在自己眼前上演,他们也不忍看到纤弱的女子有着阴险毒辣的性格和负心背叛的行为,更何况,无论是儒家伦理还是理学纲常都不允许这种情况,创作者和观众都没有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反之,对戏曲中经常出现的与现实相差无几的卑鄙无赖的男性大可一笑置之。
(二)文人相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让读书人有一种骨子里的自信和优越感,在文章方面如此,在德行方面亦会如此。元代戏曲大都取材于现实真实故事或根据前代小说改编,如《汉宫秋》取材于汉代昭君出塞的故事,《窦娥冤》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琵琶记》系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秋胡戏妻》的故事源自汉代刘向《列女传》并在民间流传,《西厢记》的原型是唐代大诗人元稹的爱情故事……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元代戏曲剧作家几乎都是男性,即使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生活困顿,但自古以来“清高”的心理让剧作家们不那么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剧作中的女性既温柔多情又美丽善良,不得不说是男性心中的理想伴侣,作家们经过主观评判,在她们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思和情感,赋予她们最完美的理想色彩,抒发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广泛观照与思考,即使在现实中不能如愿也期望在作品中成为自己的灵魂伴侣。相对的,对于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以书生文人为主,尤其是爱情剧,作家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是作者自己的影子,从内心渴望能如剧中人一样状元及第、美人倾心、春风得意;另一方面,悲惨的境遇让人难以平衡,出于“相轻”的微妙心理,剧作家又自觉不自觉呈现其不那么光彩的一面。
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避之,曰自然而已矣。”“彼但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经过心灵的陶冶,元代的戏曲就是剧作家的“倾心”之作,对女性人物的倾力描写既为身边的女性喝彩呐喊又借此抒发胸中之垒块,往往还流露出在现实中碰壁后的解脱自嘲,吐露心曲,寻找知音。
四、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重女轻男”现象的影响
元代的叙事文学万紫千红,一派兴盛,是当时的主流文学,而戏剧艺术则走向成熟,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元代戏曲中这种“重女轻男”现象的出现不仅会对其他文学种类和后世文学产生影响,也会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文学的影响
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是文学真正关注女性的开始。“元杂剧作家对剧中女性人物多肯定和赞美,少反对和批评,女性形象几乎成为杂剧中‘美’的代言。这种对女性的审美是与前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审美有极大不同的”[8]。
在元代以前,虽然也有很多描写女性的文学作品,如闺怨诗(词)、艳体诗(词)、宫体诗(词)等等,但这些却充分恰好体现了女性的悲哀和苦楚,只有元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追寻自身价值和把握人生命运的自觉意识,尽管她们的崛起或反抗总是显得势单力薄,但却有声有色,不屈不挠。她们尽显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聪慧美好、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有力地讽刺、鞭挞了男权世界。这种现象为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新风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传奇的演变,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等,戏剧家们依然把一腔热情以浓墨重彩倾注在剧中的女性身上,千金小姐杜丽娘不仅才貌端妍、聪慧过人,而且痴情、钟情、纯情,可以为之生而死、死而生,热烈执著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李香君爱憎分明,有着鲜明的政治是非观,矢志守节,勇于反抗,毫不畏惧。比较典型的还有洪昇《长生殿》中的杨妃美丽温顺,多才多艺,除了在爱情上专一真挚,在六军激变中主动请死更显示了她深明大义,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高贵品质。相比之下,戏中的男性则相对逊色,甚至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此都可视为对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的一种延续。“清初戏剧《临春阁》开始洗刷赵丽华的罪名,一反亡国妖孽的传统,使她以一个温柔可爱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蒲松龄的《颜氏》等小说中,女子显露出男子自愧弗如的才华。吴敬梓更进一步,他在《儒林外史》中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而在《镜花缘》的乌托邦中,妇女竟然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9]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遗余力地为红楼女儿悲痛呼喊……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文人作家对女性角色的继续关注,“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不惜笔墨来塑造她们。他们或多或少都从元代戏曲中吸收借鉴。总的来说,这一现象是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女性的真正认识,使人们从舞台从文学作品中认识女性的真性情,挖掘女性的美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二)对社会现实的影响
文学与社会现实总是相互交融、沟通互补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在当时名噪一时的作品,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这一现象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又反过来在社会中形成思想与行动的“新风尚”。也使人们认识到女性身上独特的美,产生要求提高女性地位的朦胧意识。
元代的市民文化滋养了戏剧艺术的发展,而戏剧中思想、审美情趣等因素也渗透在观众的生活中,其间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倾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元代人的言行思维,许多元曲中的人物如红娘、崔莺莺等为女性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女性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10]理学家痛感道德沦丧,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人们价值观念正在改变,不合理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女性的压迫更加松懈。正如“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11]现实中的我们为剧中人一颦一笑所牵动,为她们的笑而乐,为她们的哭而悲,更多的应该是为她们勇敢的举动所折服并受到鼓舞,接受前所未有的“新风尚”的洗礼,从而大胆地追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直露表达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求与追寻。这才会有理学家的顿足叹息道德沦丧。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鼓舞了女性,形成“新风尚”,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女性这一角色,真正改变人们对女性的传统保守看法。除了《长生殿》,“洪昇在《四婵娟》中也体现了自己要求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思想,剧中社会名流拜倒在四个才华横溢的女子脚下,从而显示出女子在才能和学识上并不比男子低”[12]。洪昇是明末清初的传奇作家,元代的戏曲高峰对他的影响应该较任何其他文学样式都要深刻,他的这种进步思潮不会是无源之水,期间固然有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思潮的因素,当然也有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重女轻男”所留下的痕迹。既然如此,那么元代人亦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正视女性,要求提高女性地位,或许愿意与妓女交好便是明证。
[1]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刘代霞.元杂剧婚恋关系中女性形象的复杂性及其成因[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1-54.
[3]高益荣.元杂剧的精神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程慧琴.最是柔韧女儿心——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4,(4):47-51.
[5]邱守仪.男权世界里的女性舞台——浅析元杂剧中女性形象的特点[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88-89.
[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董琦.论元杂剧的女性审美形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99-100.
[9][12]孟繁树.论《长生殿》[A].硕士学位论文集(戏曲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271-272.
[10]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宋瓷.岂独伤心是小青[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
I237
A
1671-6469(2015)06-0044-07
2015-09-25
全玲玲(1991—),女,湖南衡阳人,江苏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修辞学。刘宏平(1990—),男,湖南衡阳人,福建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