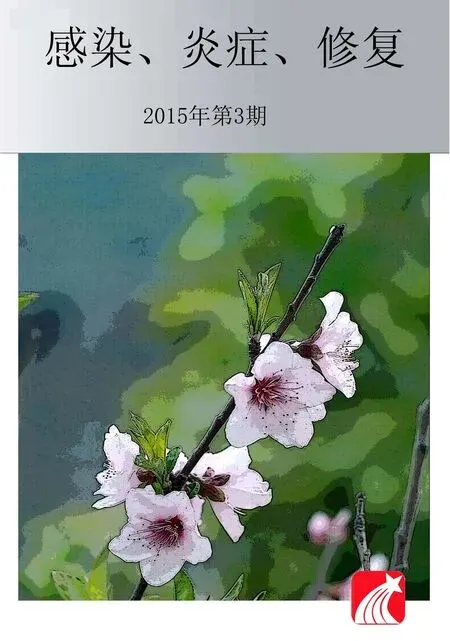烧伤创面感染的新认识
向 军 陆树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上海市烧伤研究所,上海 200025)
烧伤创面感染的新认识
向 军 陆树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上海市烧伤研究所,上海 200025)
烧伤后发生的严重感染仍是目前烧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随着创面处理技术等综合治疗措施日趋成熟,烧伤创面脓毒症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但脓毒症病死率并未得到有效控制[1]。烧伤创面严重感染是导致全身感染乃至脓毒症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烧伤创面感染再次深入了解。
1 烧伤创面感染的认识演进
1953年Jackson 首次报道,皮肤烧伤后创面自中心向外存在3个区带:即创面中央的凝固坏死区、最外层的充血带以及中间的淤滞带,淤滞带常在伤后48 h内出现血流渐进性淤滞加重而转化为凝固坏死带。1963年Hinshaw发现,未予任何治疗的烧伤创面在伤后24~48 h内可因局部发生进行性缺血而引起创面下坏死组织范围扩大。这些研究提示烧伤创面是一种伴有坏死组织存在的组织缺损性创伤,而非一般单纯的组织断裂切割伤;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烧伤创面早期血管闭塞的概念[2-3]。这些早期的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烧伤创面独特的病理生理、建立通过早期手术去除坏死组织来控制创面感染的手段提供了理论基础。
1962年Teplitz等[4]提出了“烧伤创面脓毒症”概念,即定植在烧伤创面的细菌向创面深部组织侵袭,引起脓毒症或脓毒症伴血行性感染。烧伤创面脓毒症是烧伤特有的一种感染方式。20世纪60年代Order建立了铜绿假单胞菌烧伤创面脓毒症模型,20世纪70年代初瑞金医院烧伤科也建立了铜绿假单胞菌烧伤创面脓毒症模型[2]。脓毒症模型的建立,加深了对烧伤创面感染引起的全身性感染的理解。“烧伤创面脓毒症”最初定义为每克痂下组织菌量>1×105CFU,并向邻近正常组织侵袭。瑞金医院烧伤科在痂下菌量与脓毒症临床症状的研究中观察到,每克痂下组织菌量≥1×105CFU而无任何创面脓毒症症状的病例高达67.6%[2]。因此,每克痂下组织菌量达到1×105CFU认为是临界水平,表明发生创面脓毒症概率的增加。
基于上述的研究与认识,人们开始意识到,从创伤后炎症和组织进行性损害严重程度而言,烧伤导致的后果更甚于一般外伤,其根本原因在于烧伤造成的坏死组织本身,坏死组织的存在对烧伤后全身的病理生理变化有着不利的影响。烧伤创面不仅可以引起局部过度的炎症反应,对局部组织产生损害作用,还可引起炎性级联反应。烧伤后早期局部和全身的炎症反应,既对创面感染有抵御作用,也会对感染的发展推波助澜。烧伤早期局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炎性细胞逸出血管,创面早期血流淤滞或血管完全闭塞、中性粒细胞功能受损和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等因素,均削弱了机体控制感染的能力,易使烧伤创面表面细菌定植发展成为感染创面,甚至细菌侵袭深层正常组织。当细菌侵袭创面下活组织时,不但出现局部炎症反应和全身炎症反应,而且可以进一步发生以微循环灌注障碍为特点的全身变化,导致脏器功能障碍[5]。
在烧伤创面局部,组织坏死和皮肤屏障的丧失为细菌繁殖和侵袭提供了条件,同时,创面局部血液循环差,全身应用抗菌药物难以或不能到达创面局部以控制感染。因此,烧伤创面局部应用抗菌药物成为预防创面发生严重感染的主要措施之一。1967 年,Fox制成了水溶性的磺胺嘧啶银(SDAg) 霜剂,一直沿用至今。局部抗菌药物虽然仅能减少创面组织内细菌数量,但在一定时间内可将创面组织细菌数量控制在发生烧伤创面脓毒症的临界水平以下,减轻细菌侵袭对机体的影响,减少发展成烧伤创面脓毒症的概率。
2 烧伤创面细菌生态格局的变迁与耐药问题
烧伤创面细菌生态格局随时代而变迁,反映了烧伤治疗方法的改变,局部抗菌药物和全身抗生素的选择是影响烧伤创面细菌生态格局的主要因素[6]。磺胺类、青霉素等抗菌药物问世后,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逐渐成为烧伤创面的两个主要菌种。1972 年以来,磺胺嘧啶银霜剂开始作为创面常规局部用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第三代头孢菌素、特别是对铜绿假单胞菌有良好抗菌活性的头孢他啶被作为首选抗生素,造成80年代中期烧伤创面细菌生态格局与70 年代相比有显著变化,即烧伤创面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显著减少,而肠杆菌科检出率显著增加。20 世纪90 年代,随着第三代头孢菌素广泛应用,烧伤创面检出的肠杆菌科和铜绿假单胞菌对第三代头孢菌素如头孢哌酮、头孢他啶耐药性显著增加;90 年代末,烧伤创面检出的革兰阳性(G+)球菌比例超过革兰阴性(G-)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检出的菌种中居首位[7],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显著增加,这一现象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①将第三代头孢菌素和亚胺培南作为烧伤病房首选抗生素;②烧伤病房普遍应用的局部抗菌药物磺胺嘧啶银对G+球菌的抗菌活性较G-杆菌差[5-6]。1993 年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如亚胺培南在烧伤病房中应用量迅速增加,造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在21 世纪成为烧伤创面检出的主要菌种[8]。目前的数据表明,烧伤创面细菌仍以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优势菌,MRSA在检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中高达70%~80%;革兰阴性杆菌中,铜绿假单胞菌或鲍曼不动杆菌占首位,鲍曼不动杆菌呈现超越之势,而且是多重耐药或泛耐药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CRKP)相继出现,并在烧伤病房、ICU呈流行趋势[1,9]。G-杆菌变化模式呈现两种趋势。一种为铜绿假单胞菌减少而肠杆菌科、不动杆菌属细菌增加,主要是肠杆菌属、肺炎克雷伯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另一种为铜绿假单胞菌呈上升趋势,肠杆菌科细菌无变化或下降。这两种变化模式主要决定于局部抗菌药物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有效性和细菌是否已产生耐药性,选择的全身抗生素对铜绿假单胞菌抗菌活性和肠杆菌科细菌耐药的程度,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敏感性。抗菌药物选择压力反映在创面细菌生态方面为耐药菌株呈现增加趋势,并不断选择出条件致病菌。
烧伤创面检出的G-菌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鲍曼不动杆菌。国内各烧伤中心报道的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8]。2007—2013年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连续7年的细菌监测显示,烧伤创面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率由10%上升至18%,与MRSA、铜绿假单胞菌一起构成最常见的三大优势菌种。烧伤创面检出的鲍曼不动杆菌绝大多数为耐药菌株,对常用抗生素头孢他啶、阿米卡星、环丙沙星等的耐药率均在80%以上,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已接近90%;同时,对头孢哌酮钠-舒巴坦耐药率也逐年增高,目前已经达到70%左右。
临床发现,在某些病例中,磺胺嘧啶银或磺胺米隆对MRSA、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和厌氧菌等的杀菌效果并不理想,细菌生物膜形成可能为原因之一。细菌生物膜是由细菌分泌的多糖、纤维蛋白和脂蛋白等物质形成膜状物质,吸附于生物材料或机体腔道表面,是将细菌自身包裹于其中而形成的膜样复合物。细菌生物膜是细菌的重要生存方式,也是细菌耐药性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生物膜具有屏障功能,能阻碍抗生素分子与膜内细菌接触,其微环境可影响抗菌药物的活性。与浮游菌相比,膜内菌的生长代谢及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明显改变,膜内菌对抗生素抗性提高10~1 000倍[10]。烧伤创面以及其他慢性创面细菌生物膜的形成造成创面外用药物难以渗入生物膜内部,不能有效地清除创面的细菌,进而出现创面持续感染、经久不愈,甚至发展成创面脓毒症[11]。研究发现,烧伤创面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在体外培养中,48 h左右即可形成生物膜,耐药菌株形成生物膜的能力、生物膜的厚度均明显强于敏感菌株[12]。细菌生物膜与耐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感染领域研究的热点。
3 烧伤创面感染治疗对策
烧伤创面的存在是烧伤病理生理发展的根源。烧伤创面感染治疗的基本措施包括:适时处理坏死组织并有效封闭创面,平衡失衡的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控制创面感染、减少创面细菌数量,改善局部微环境、促进创面愈合。
3.1 局部外用抗感染药物和抗菌敷料 应用局部抗菌药物的目的,是延缓或减轻微生物在创面的定植、侵袭,防止感染扩散、创面加深,为手术赢得时间。目前,以磺胺嘧啶银为代表的银制剂仍是局部抗菌药物的基本选择。当细菌已侵袭至焦痂深层或达焦痂下组织时应选用磺胺米隆,因其能迅速穿透焦痂,用药后在坏死组织和活组织界面达到有效杀菌浓度。莫匹罗星对G+球菌,特别是对MRSA有很高的抗菌活性,MIC50 为0.25 mg/L,MIC90≤4 mg/L,具有在低浓度下呈现抑菌效果的特点。莫匹罗星可作为烧伤创面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尤其是MRSA感染的首选局部外用药物。复方多黏菌素软膏主要含有多黏菌素B、新霉素和杆菌肽,对G-杆菌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但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株的效果不如磺胺米隆[5]。在耐药G-菌(包括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导致的严重创面感染时,应该选用磺胺米隆。体外实验表明,5%磺胺米隆溶液能破坏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形成的生物膜[13]。
国内外抗菌敷料的主要成分是银离子。将银离子敷料与醋酸氯己定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它们均有阻止细菌侵入烧伤焦痂深部的作用,焦痂下细菌计数显示银离子敷料组细菌减少更为明显。但即使在使用银离子敷料情况下,细菌依然能在烧伤创面形成生物膜,表明银离子难以杀灭细菌生物膜内的细菌[13]。笔者的体会是,这些新型的具有抗菌作用的敷料,如纳米银敷料,只能作为预防性或创面轻度感染时应用,严重创面感染时必须选用局部抗菌药物,如磺胺嘧啶银、磺胺米隆等。
细菌生物膜形成初期应使用渗透性较强的外用药物,或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破坏生物膜,促进外用药物进入膜内层。化痰药氨溴索具有干扰生物膜形成的作用,作用机制与N-乙酰半胱氨酸相似,其原理是该药能结合细菌细胞外多糖,使细菌不易吸附形成生物膜。体外实验发现,氨溴索分别与磺胺米隆溶液、醋酸氯己定溶液联合应用,均显示出协同灭菌作用[13]。Phillips等[14]利用含有表面活性剂组分十一碳烯酰胺丙基甜菜碱(benaine)的伤口清洁剂,可以去除细菌及其碎片,并破坏生物膜。该伤口清洁剂已经开始应用于外科临床。因此,针对耐药菌及其生物膜的创面外用抗感染药物的研发,具有良好的前景。
3.2 早期手术治疗 烧伤创面感染的控制有赖于创面的正确处理。烧伤后6 h,细菌便可在创面上生长繁殖,并逐渐向深部组织侵袭;伤后1周内,痂下组织细菌定量明显增加。创面进行性损害加重和感染的危险随伤后时间推移与日俱增。传统切削痂手术时机为伤后4~7 d,这一时机受到质疑。现已被临床普遍接受的是,烧伤后早期(伤后48 h内)一旦血流动力学稳定,即可考虑于手术去除创面坏死组织。特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若不能在一次手术中去除全部坏死组织,也须去除大部分坏死组织,使残留的深度烧伤创面不足以成为引发创面脓毒症的危险因素。研究提示,休克期切痂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减轻超高代谢、全身炎性反应和严重感染等并发症[15]。对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实施休克期切痂,已在国内主要的烧伤中心开展多年,其安全性、有效性均已被证实。
针对深Ⅱ度烧伤创面进行性加深和早期感染的问题,陆树良等[15]进行了一系列深Ⅱ度创面极早期(烧伤后24 h内)削痂的临床和动物实验,结果表明:深Ⅱ度烧伤创面伤后24 h内削痂,可以有效防止创面进行性加深、防止创面严重感染的发生,是最大限度保留间生态组织的有效方法,缩短了深Ⅱ度烧伤创面的愈合时间、改善了创面愈合质量。深Ⅱ度创面极早期削痂的方法,已经在国内几十家医院推广,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细菌生物膜形成是造成常用局部抗感染药物疗效不佳、创面持续感染的重要原因,而物理清除法,如清创术或充分的物理清洁则是减少生物膜负荷的最好方法。外科水刀的应用为物理清除法提供了新型的工具。水刀是一种利用喷射水流进行精准切割的技术,在水压调节至较小压力时,可以发挥物理清洗作用,且无热损伤性;创面内血管、淋巴管、神经等韧性较强的组织,在水压下可保持完整。
对于已经出现创面严重感染或脓毒症临床症状的烧伤患者,在全身应用抗菌药物和维持呼吸、循环相对稳定情况下,要抓紧时机急诊手术,清除创面坏死组织,特别注意去除或引流感染病灶,有效覆盖创面,这是治疗烧伤创面脓毒症的首要措施。全身抗生素的使用应参考细菌学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或遵循经验性应用抗菌药物的原则,并参考烧伤感染优势菌、当前烧伤病房中流行的菌种、细菌耐药性背景和病程处在哪个阶段等。
3.3 院内感染的控制 针对亚胺培南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除大量不合理使用亚胺培南等抗菌药物易诱导鲍曼不动杆菌产生多重耐药外,医院内细菌交叉感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6]。严格的感染控制和抗生素管理措施,能有效地防止由院内感染引发的烧伤创面耐药菌感染。依据院内感染防控的要求,对烧伤临床各类医务人员定期进行培训,规范各项操作,尤其是日常的创面换药,避免医源性感染。任何临床操作前后必须洗手,强化手卫生管理是减少交叉感染发生的关键。定期对烧伤创面进行细菌学调查,一旦确定有耐药菌株感染或定植,包括MRSA、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和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必须对患者进行接触隔离,对其医疗和生活用品实施有效消毒措施,避免传播。同时,严格执行抗生素分级管理制度。根据细菌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择有针对性的抗生素,尽量减少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使用,以保护现有抗生素的有效性。
4 展 望
随着烧伤重症患者救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ICU监护技术的进步、新型抗感染药物和敷料的研发,以及我们对烧伤创面基础研究的深入开展,由烧伤创面感染导致的创面脓毒症必将会得到有效控制。而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和不同程度的创面感染的正确判断与处理,仍将会是烧伤专科医师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1]Coban YK. Infection control in severely burned patients [J]. World J Crit Care Med, 2012,1(4):94-101.
[2]许伟石. 对烧伤感染的认识[J].中华烧伤杂志,2008,24(3):164-166.
[3]杨之骏,许伟石,史济湘.烧伤治疗[M].第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87-111.
[4]Teplitz C,Davis D,Manson AD, Moncrief JA. Pseudomonas burn wound sepsis (I): pathogenesis of experimental pseudomonas burn wound sepsis [J]. J Surg Res,1964,4(5):200-216.
[5]刘琰,章雄,张勤. 烧伤感染[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57-99.
[6]许伟石. 烧伤创面细菌生态和抗生素治疗[J].中华烧伤杂志,2008,24(5):334-336.
[7]于勇,盛志勇,柴家科,蒋伟,朱静. 1995-2011年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感染病原菌结构和耐药水平的变化[J].感染、炎症、修复,2012,13(2):93-96.
[8]郇京宁, 唐佳俊: 烧伤患者耐药鲍氏不动杆菌感染现状和对策[J]. 中华烧伤杂志,2011, 27(2):84-87.
[9]邱广伟,朱敬民,崔永珍,孙志刚. 烧伤创面革兰阴性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J].感染、炎症、修复,2014,15(3):177-178.
[10]Sanchez CJ, Mende K, Beckius ML, Akers KS, Romano DR, Wenke JC, Murray CK. Biofilm formation by clinical isolates and the implications in chronic infections[J]. BMC Infect Dis, 2013, 13:47.
[11]付小兵.细菌生物膜形成与慢性难愈合创面发生[J].创伤外科杂志,2008,10(5):416-417.
[12]向军, 孙珍, 宋菲, 郇京宁. 烧伤患者鲍氏不动杆菌pgaABC基因簇表达及其生物膜表型变化的研究[J]. 中华烧伤杂志,2011, 27(2):100-103.
[13]黄晓琴,向军,宋菲,郇京宁.烧伤创面常用外用药对鲍氏不动杆菌生物膜内菌的影响[J].中华烧伤杂志,2012,28(2):106-110.
[14]Phillips PL, Yang Q , Sampson E,Schultz G.Effects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on an in vitro biofilm model of skin wounds [J]. Advances in Wound Care, 2010, 1:299-304.
[15]陆树良.烧伤创面愈合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实践[J].中华烧伤杂志,2008,24(5):359-361.
[16]蒋伟,常东,张恒,王伟哲,于勇. 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J].感染、炎症、修复,2010,11(2):83-86.
10. 3969/j. issn. 1672-8521. 2015. 03. 002
2015-09-07)
向军,瑞金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上海医师协会烧伤科医师分会委员、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