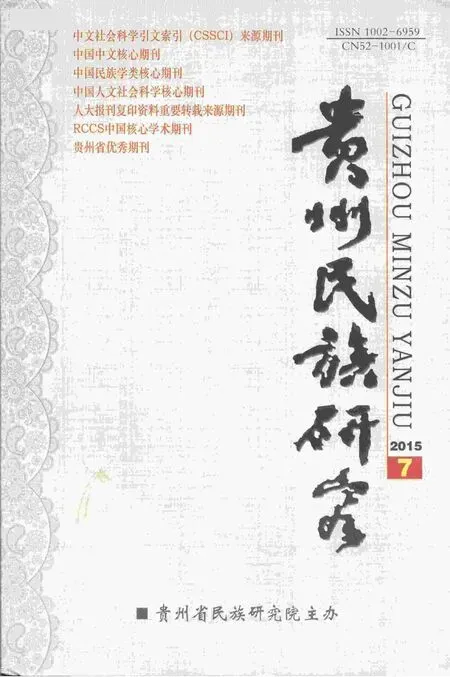再论黔南之战与黔南各民族的抗敌斗争
范松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关于黔南之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开始有学者关注,并发表了一些论述。近年来,随着地方对历史文化重视度的加强,不仅有较多的文章面世,还有由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数次相关的研讨会。然而,迄今对抗战后期作为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场有组织攻势的研究,仍显得有些不足。一是对黔南之战中国军民取得胜利的原因,缺乏客观深入的分析;二是对黔南之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定位,尚有一些模糊。本文拟通过黔南之战的背景与战况、黔南各族群众的抗敌斗争,对黔南之战作一些相应的探讨,以期这一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推进。
一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1]在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贵州不仅作为战略大后方,全方位支持抗战事业,为这场伟大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战争的后期也一度成为前线。在以独山为主的黔南一线,中国军队与当地各族人民,同疯狂的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并最终在独山深河桥,遏止了侵略者沿黔桂公路北上,进犯贵阳、威逼重庆的势头,给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战略行动画上了终结号。正确评价黔南之战,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抗战后期战局演变的节点,也有助于了解贵州少数民族武装抗敌所作出的贡献。
了解黔南之战的背景与战况,是剖析这场尽管规模不大,却在改变抗战整体局势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战争的前提。
1944至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已逐渐转移到同盟国一边。这时,西方的法西斯德国在苏德战场上已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意大利法西斯则已投降,东方的日本法西斯虽然在太平洋上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却仍然在拼命进行挣扎。随着美军在太平洋诸岛的登陆,“南中国海与南方诸海区域内日本原料基地之间的最重要的交通线已处于美军控制之下”[2]。日军为救援其在南洋各地的孤军,决定从中原的河南省开始,集中兵力先歼灭河南的中国军队,再发动衡阳大会战,打通粤汉铁路,继而攻占广西,打通连接越南的通路。这即是抗战后期日军的所谓“一号作战”,也是日本竭力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国抗战史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在这场始于1944年4月,历时8个月的战役中,日军以13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36万兵力,中国方面则投入了130多万兵力。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两个战场均遭到了惨败,损失兵力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同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柳州,进而占领南宁,表面上达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然而,就在日军分兵北进占领贵州独山,企图威逼贵阳,给重庆造成压力之际,进入黔南的日军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阻击,无法再向前迈出一步。
湘桂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已感到日军可能趁势经贵州北上的威胁。为确保陪都的安全,下令“成立黔桂边总司令部,调派汤恩伯任总司令,从第一、第六、第八3个战区抽调87军、29军、98军、9军、13军、57军进驻贵州,陆续在镇远、黄平和马场坪、都匀、独山两个区域集结”。[3](P378)11月22日占领南宁后,日军为扩大战果下达了北进贵州“向独山、八寨追击”的命令。
日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第13师团104联队及第7师团之一部约步兵3千~4千人、骑兵300余人,于12月3日占领独山县城。此前,独山大部份民众已提前疏散。黔南边区指挥官兼独山、都匀警备司令韩汉英下令焚烧独山县城,作“焦土抗战”,独山已基本上是一座空城。时任贵州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张策安,在给上级的电文中,描述独山撤退时的情景说:“自撤退启程后,以枪弹数量较多,连同署内公物、职员行李不下三百余挑。运输困难,行程缓滞。沿途乡镇保甲、民众早避一空。”[4](P383)
第二路侵黔日军为第3师团34联队等2000余人,由广西思恩(环江)社村乡出发,11月25日开始攻击黔桂边境的黎明关。国民党黔桂边区总司令部周国仲率587团进行顽强抵抗后撤退,撤退过程中仍在坡格、里根、浪洞等沿线对日军进行阻击。此役日军遭到重创,仅黎明关阻击战日军便被击毙中队长两名,士兵100余人,在蒙家坳阻击战中,我军又毙伤日军160余人。[5]
第三路日军主要为第3师团第6联队兵力约1500人,11月29日由广西进入荔波县境,之后转向进攻三都,于30日占领三都县城。12月3日,日军向都匀方向推进,一度占领茅草坪、雷打岩、半边街、鸡贾河等村寨。但在距都匀四十里的地方,被我军击溃,遂由丹寨向三都折返,于5日再占三都县城。
在黔南战役中由于日军已丧失了大部分制空权,而中国军队“依照规定铺设的对空目视信号,(盟军)空军获得地面上布板指示,向敌军阵地轰炸扫射,步兵得以在这掩护下冲锋陷阵”,[6]使日军陷入被动。12月2日,盟军空军炸毁独山深河桥,从而切断了日军向贵州腹地进犯的唯一通道,日本侵略者再已无力向前推进,被迫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收缩后撤。12月4日,日军撤出独山和荔波县城,12月8日撤出三都。至此,黔南之战以中国军民的胜利告终。日军向黔南的进军,不仅将贵州推向了正面战场的前线,并因这场战斗,终止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陆再次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的步伐,独山深河桥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二
黔南之战是抗战后期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场疯狂进攻,在这场攻防战中,除了中国军队的正面阻击和对敌人的分割围歼外,贵州各族人民尤其是遭到日军残害的黔南少数民族群众,奋起抵抗,用各种手段重创日军,给予了侵略者极其沉重的打击。
黔南之战中,首当其冲受到摧残最严重的莫过于独山。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和国民党军队在几大战役中的溃败,1944年秋冬,大批难民沿黔桂铁路、公路一线涌入独山县境,给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压力。加上国民党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导致局面极度混乱,人民或仓促逃亡,或避于近郊,扶老携幼、哭爹叫娘,情景令人惨不忍睹。而日军侵入黔南的半月时间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惨死在南丹至独山的黔桂公路上,仅独山县的死亡人数就达19880人,被烧毁的房屋多达16000余幢,数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被焚为一片焦土。这一切极大地激发各族群众的愤慨,也推动了黔南各族人民誓死抗拒日军侵略、保卫家园的决心。
独山沦陷前,当地民众即已提出成立“独山民众抗日自卫团”的要求,但迟至11月26日才获批准。“独山民众抗日自卫团”成立后,下设两个支队,各支队下设若干中队。12月2日,日军进入独山城后,四处纵火掳掠,上司乡中队率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向小股日军发动袭击,击毙日侦察兵5名,缴获步枪3支,子弹120余发,打乱了敌军的进攻部署。次日,自卫团获悉日骑兵60余人进至屯脚宿营,当即组织100多人分成三路,对敌军进行包围,激战一小时,毙敌骑兵9名,夺得战马5匹及手榴弹、钢盔等战利品。4日,在上道乡麻银一线抢劫的20余名日军,与60余名自卫团战士发生激战,敌军7人被歼,抢劫物资被夺回。
在荔波县,日军驻板寨待命长达20余天,四处抓捕群众、抢掠奸淫,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极大愤怒,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自发联合组成自卫队与侵略者进行斗争。11月27日,日军1500多人由广西宜北窜至荔波佳荣,经岜鲜进犯九阡。在十里长坡遭到少数民族群众的阻击,双方激战数小时日军才得以继续前进。30日,日军进至都匀县边境后,无力再前行,被迫折返三都县三洞、九阡一带。在九阡,日军连续遭到当地群众的伏击和抵抗,前后被歼灭100余人,伤若干人,少数民族抗日群众缴获的武器,包括步枪100余支、机枪3挺、骡马数十匹,甚至有太阳旗、防毒面具等。12月5日,荔波自卫队将一股日军围在董给硐,歼灭10余人。8日,洞塘边的青年又将日军围于洞阿,杀死日军1人,伤多人。[5]
三都县境的水族人民奋起抗击日军,同样取得了辉煌战果。日军进达石板寨的寨外、寨里水族群众以潘老发、潘秀辉等为首组织了数十名青壮年,以仅有的破旧步枪、鸟枪及土炮抗击侵略者。由于寨子有石围墙及土碉掩护,日军的久攻不下反而伤亡十几人,被迫露宿田坝。次日,日军炮兵部队赶到,群众被迫向后山撤退。经此一战后,各寨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抗击日军,“一时‘哈嘎日本’(水族语——杀日本鬼子)之声响遍水乡”。
三都少数民族群众的抗敌斗争虽较为分散,对日军的打击和威胁却很大,从有关文献的记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以石板寨保卫战为例,11月28日,日军进逼三都县九阡区石板寨(时属荔波县辖),该寨位于三都与荔波两县交界处,为荔波县佳荣乡通往三都九阡的唯一通道,居民以水族为主,共200余户。由于历史上常受兵匪骚扰,群众在寨子四周筑有一人多高,5尺余厚寨墙,墙上插若干圆木以固防卫。民众闻讯日军逼进寨子,事先组织力量将四门堵塞,并将青壮年分为5组,每组各50人轮流守卫。日军抵寨后,先欲强行翻墙攻寨,数次均告失败,遂于山坡上架机枪向寨内射击,又将机枪架于马背上边射击边向寨门推进。寨民集中火力射击日军马匹,迫使日军始终不能接近寨墙一步。次日拂晓,日军调来炮兵攻寨,寨民为避免过多伤亡,决定弃寨转移,退守附近十里长坡,寻机对来犯侵略者进行打击。“石板寨战斗,毙敌8名,缴获骡马6匹,石板寨亦有4名民众献出生命。”[3](P381)
继石板寨之后,三都各地水族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与敌军展开斗争,并都取得了胜利。其中包括永阳乡一带民众于12月1日伏击日军,两次共毙敌9名,缴获步枪7支、子弹200余发;三洞乡水更寨民众两次阻击日军,毙敌14名,缴获步枪12支、子弹390余发;尧麓乡民众于12月10日在营上坡与敌军激战两小时,打死日军10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子弹1箱、战马1匹等。
黔南之战中,由于敌强我弱,处于分散状态下的各族群众,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拒侵略者的暴行,用各种机动灵活的手段将敌人消灭在自己的身边,甚至不惜玉石俱焚,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发生在独山县郊一洞穴中的壮烈一幕,至今仍令后人叹为观止。当年,何毓昌、贾耀恺两位战地记者所写的《黔南战斗经过》一文中,曾有以下一段感人肺腑的记述:“在城郊的一个山谷间,有一大石洞原系我军的弹药库,撤退之时,仓惶未及破坏。一日,敌军百余人,劫持甚多妇女,逼往洞内强奸。有一孕妇行将分娩,求得敌兵的饶恕,允其自寻秘密地点生产。她在洞内徘徊良久,忽然发现此系弹药库的埋藏地,乃默默走出洞外遍寻火柴。忽遇一难胞迎面而来,她遂详告敌兵在洞内的种种兽行,并声明愿借火柴点燃药库与敌兵同归于尽。难胞闻讯,很愤慨,也很感动,遂请孕妇远行,自己亲往点火,霎时爆炸,全山崩溃,而与百余敌兵及大群妇女同时葬身于山洞中。”[7](P3)
三
在黔南之战中,就当时的战争态势而言,中国军民所处的境况显然是不利的。尽管这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日军方面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被迫解散,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开始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但由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来,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几场大战役中连续遭到了惨败,军心不稳,以至“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已成惊弓之鸟,望风溃逃,被日军一直追到独山”[8](P215)。或许受这方面原因的影响,在一部分论著中出现了黔南之战并非中国军民奋勇抗战取得的胜利,而是由于“日军按照军部计划,在达到战略目的后的主动后撤”一类的观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从战略上看,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目的有两个:“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标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9](P806)。虽然表面上衡阳陷落后,日军南北连接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但在日军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南宁后,西北方向即是贵阳,有公路可直通重庆,这才是日军突然挥师北向,向黔南发起攻势,威逼贵阳的原因。问题在于这一战争转向虽然引起了重庆方面的恐慌,以至因形势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开始)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9](P807),但黔南之战却出乎意外地以中国军民的完胜而结束。
如果摆脱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将黔南之战置于抗战全局中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军民在这场通过流血牺牲、奋勇杀敌所取得的事关国民政府陪都存危的胜利,既有其重要的主观因素,亦有客观的必然性。具体说来,至少应包括以下3方面。
首先,黔南之战发生在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后期,战争所在地贵州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南面的最重要屏障,贵州的得失已超出了一般战役对敌我双方战局优势影响的范畴,直接关系到重庆的安危。尽管随着日军攻势向贵州的延伸,重庆方面已出现惶恐情绪,并有了撤离流亡的声音。但在经历了河南战役、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之后,国民党当局已开始意识到退无可退,唯有倾力保住贵州,才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局已定的形势下,维持政治军事上的稳定。因此,在黔南之战打响之前,国民党方面在贵州已有了相对具体的战略部署,除由汤恩伯亲任黔桂边总司令部司令,调集了6个军的兵力,在贵阳和黔南一线布防外,早在1944年9月,国民党已将待建的“独山飞机场定为西南空军基地”。“年末,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汤恩伯、张发奎、杨森、谷正伦、张雪中、孙元良、周浑元先后到独山视察防务”。[4](P366)种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如何是不希望看到日军进占贵州,进而威胁陪都重庆安全的。在保卫黔南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作了非常坚决的抵抗,正是这种抵抗,粉碎了日军北上的企图,不得不在独山深河桥边止步,结束其在中国大陆疯狂的军事进攻。
其次,贵州独特的地形与气候,加上军民同仇敌忾,黔南各族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奋勇杀敌,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士气,令侵略者处处挨打、寸步难行。日军在黔南的处境已远远不可与在豫、湘、桂几省的情况同日而语,后勤供给既缺乏保障,复杂的黔南地形地貌又令队伍陷入盲人瞎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不断反击,即使没有军部的撤退命令,日军溃败的结局也是早已注定了的。一些文献曾如此描述黔南日军的情况:“孤军深入独山的日军,面对的是一座尚在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市废墟。士兵们身上穿的衣服,有许多是攻占南丹时,从军用仓库里抢来的,还有一些人只穿着夏衣。而黔南的12月已是冷风刺骨,不胜其寒的季节。既缺粮食,又缺衣物的日军,唯有从见到的老百姓身上抢劫衣物来穿,拆卸和焚烧房屋取暖,冒险到乡间觅食。这样既分散了兵力,也将自己暴露在了抗日军民的枪口面前。”而各族群众对日军的打击,就连当时的战地记者也有深切的感受:“黔南的克复,黔石关的大战固然极端紧要,而民力的发挥也收了特别的功效。”[7](P3)正如孙元良部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为战后出版的《黔南之战》书中提词时所写的:“军民合作为胜利之基础”。
第三,侵华日军虽有沿黔桂线威逼贵阳,剑指重庆的野心,但已不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军事实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和中国大陆抗日战争格局的演变,已经重挫了日军决策者的战略计划,面对黔南军民的坚决抗击,以分散方式收缩退出贵州,已成为当时日军的唯一出路。这同样是黔南之战中国军民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1944年底,由于失去了太平洋上的主动,除了陆地上所占领的东亚、东南亚各国外,日本已开始面临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危险。而在中国大陆,随着解放区的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华南纵队开始在敌后发动一连串攻势。1944年一年中,上述军队“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六万余人,俘获敌伪军六万余人,攻克县城四十七座(真正收复的十六座),攻克据点五千余处,收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二百余万”。[8](P213)加上这时美军先后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美空军拥有了更好的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日军通过“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与占领中国机场的行动,事实上已完全失去意义,如果再在黔南与中国军民展开激战,只会加速自己的失败。
对于黔南之战与黔南各族民众抗敌斗争的评价,既不能只着眼于战争的规模,不能只看敌我双方的伤亡人数;更不能以日军军部的某条后撤命令,或对战事部署的变更为依据。如果单纯以这样的视角给这场战事和黔南民众的抗敌斗争定位,极易造成某种错觉:似乎即使没有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军在突入独山、荔波、三都一线后,也会主动撤离。
发生在抗战后期的黔南之战,是中国军队在当地各族民众配合下,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场辉煌胜利,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时任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道藩,在黔南战后曾提词道:“驱逐倭寇出贵州,就是驱逐倭寇出中国的先声”。率部与日军在黑石关激战的29军师长王铁麟的切身感受则更具体:“苦战必胜,苦斗必生”。
黔南之战与黔南各族的抗敌斗争,体现了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国民政府军队与挟豫湘桂战役连胜之势的疯狂敌人殊死搏斗,黔南各族群众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手段与日军拼杀,甚至不惜与敌同归于尽。一些士绅在民族大义面前也挺身而出,配合军队和群众与敌人展开斗争。“上道乡某村的绅士石玉森君,痛恨家乡陷敌,决不甘作顺民,乃登高一呼,将全村壮丁武装起来,有组织的打击敌人。一日,敌军到该村搜索,乃与大战一场,终将敌兵杀死十一人。”[7](P4)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抗日战争整个战局的形势观察,黔南之战堪称正面战场的一个军事转折。黔南一战后,日军在中国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攻势,抗日战争逐渐转入反攻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座让日军最后止步的独山深河桥,也就成了这个转折点中有着某种历史象征意义的遗迹。据此,人们在挖掘和研究这段历史中,发出“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的感叹,也不宜指责为毫无依据。
[1]纪念77事变习近平在卢沟桥讲话[EB/R].新华网,2014-07-07.
[2](俄)斯·普·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史概要[M].北京:1980:440.
[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4]贵州省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独山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5]贵州省荔波县志编纂委员会.荔波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50.
[6]严正路.黔南新战地[A].黔南之战[Z].独山黔南文艺社,1945:90.
[7]何毓昌,贾耀恺.黔南战斗经过[A].黔南之战[Z].独山黔南文艺社,1945.
[8]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9](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黔南示范小城镇集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