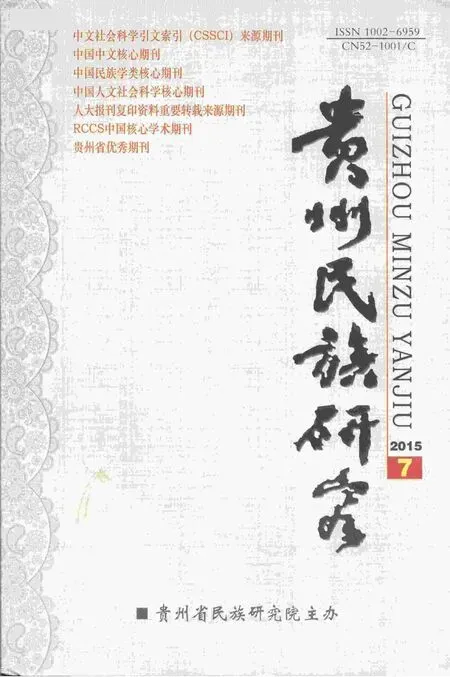跨文化视角下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研究
陆 晨 樊葳葳
(1.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武汉 430074;2.武汉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湖北·武汉 430081;3.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恩格斯指出:“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人类社会发展涵盖社会形态、经济程度、政治制度、国家政体、民族成分等多个方面,其诸多构成不是有序共进,而是交互重叠,民族与政治国家的发展也并不总是在同一时间线上,于是地理概念的国家划分成为跨境民族的产生的前提。[1]地理环境的稳定是跨境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我国边界线在陆地上共有30多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对边界和睦与邻国交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语境下,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三个概念内涵大致等同,不过其区分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三者概念指向侧重点不同,本文采用空间意义更浓厚的跨境民族概念。首先,“跨”所指的是居住在两个以上(含两个)国家,具有共同民族性,彼此相互认同的民族群体;其次,受居住地主体民族影响较大,但在语言、服饰、信仰、习俗等都体现出对他国相似民族群体的认同;再次,在地理概念上,现在或曾经有紧密的地缘联系。
一、基于跨文化视角的我国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现状解析
在现代语境下,跨文化视角常被用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群体的文化互动。跨境民族的跨文化对比群体为境内民族群体和境外民族群体。社会学角色定义认为人或群体在同一时刻扮演多个角色,故为角色集。跨境民族身份也不是单一的,是民族身份、宗教身份、国家身份的角色集合。
(一)跨境民族的语言身份认同现状
传统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一般以本民族母语为主要社交语言,兼顾使用与其混居民族的语言。我国大部分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属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情况,但语言习得的传承须以活态传递,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和相互交往来完成,这就增强了跨境民族语言身份认同的交往基础。随着我国国境边界的确立和民族识别的完成,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同时完成了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客观划定,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和民族划分标志之一推动着跨境民族身份认同。[2]首先,跨境民族存在着语言跨境的现实。我国有28个少数民族语言是跨境的,例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萨克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哈尼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佤族、京族等。换言之,跨境民族和境外民族的语言是同宗的,可以互相毫无障碍地沟通。其次,跨境民族存在双语或多语使用的情况。我国跨境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也会使用混居或相邻民族语言,例如跨境景颇族会使用傣语或者阿昌语。此外,受境外同宗民族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使用境外主体民族的语言。再次,跨境民族汉语使用水平逐年提升。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投入的增加和边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政策的执行,如今边疆跨境少数民族民众的汉语水平逐年提高。总之,作为跨境民族认同重要构成的语言身份认同在现阶段体现为求同取向,这更加利于我国边境稳定和交流便利。
(二)跨境民族的信仰身份认同现状
作为信仰重要表现形式的宗教交往是宗教社会化的重要过程。我国跨境少数民族一直以来有较高的宗教信仰热情,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身份认同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跨境宗教信仰社区的形成。信仰社区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地理区域,特指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因为共同的信仰,不局限于地缘,而同时涵盖血缘(亲缘)、物缘、神缘、语缘的信仰空间。信仰表达可以通过共同节日、共同祭祀、共同仪式等来完成。第二,跨境民族信仰体系多元化。[3]我国跨境民族都有独特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边界交往,信仰体系中也出现信仰融合和嬗变的因素,这成为我国现阶段跨境民族文化建设重点疏导的隐患。总之,跨境民族的信仰身份认同现状奠定了跨境民族内聚的基础,有利于民族团结,但跨境民族信仰的多元融合则需要成为我国跨境民族文化建设重点疏导的部分。
(三)跨境民族的政治身份认同现状
政治身份认同在国家语境下特指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跨境民族的政治身份认同由客观认同和主观认同构成,客观认同是由国家划定的身份归属,主观认同则是由于客观身份的刺激,对所系属国家身份的归属感。当前,我国跨境民族的政治参与涉及两方面因素,一是跨境民族的政治参与意愿,二是国家为跨境民族政治参与提供的途径和机会。国家归属认同的实质为对政治权利的认可与权威服从,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矛盾性,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往往意味着国家身份认同削弱,反之,民族身份认同削弱,同样意味着国家身份认同的加强。[4]政治参与度是衡量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准,国家身份认同较低时,政治参与度也较低,反之亦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跨境民族都具有越来越强的政治身份认同感,从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就可以看出。
二、跨文化视角下我国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三重困境
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相对于其他民族身份认同的困难根源于其地理区位和发展现状,我国跨境民族历史上虽然与主体民族有联系,但也多偏安于边疆,与国外的同宗民族却有着血缘、地缘、信仰文化等多重的联系。
(一)文化认同多元化所致的共感缺失
多元文化已经成为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动力,于该场域中分析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不仅着重本族文化的自然情感归属认同,更契合主流文化即中华文化的外力内化认同和其他民族文化的选择性认同。此种认同基础不仅可以纵向跨越历史,也可以横向跨越民族和国界,形成多元文化认同体系。一般而言,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同主流社会有较大差异,在整合过程之中会成为文化共感的主要障碍,形成共感缺失现象。[5]共感缺失在一定程度可称为国家离心力的扩大,文化共感缺失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立场、视角不同;另一方面,是主流文化显示优越性的沟通态度,同时也有两个文化群体持有者对于对方文化没有进行深层次了解而导致的刻板印象。世界各多民族国家都在努力消解由文化基础差异所致的跨境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文化认同差异摩擦,以成就跨境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文化的民族认同共感。
(二)跨境信仰掩护下的价值隐患
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长期与境外民族有着诸多联系,共同的宗教信仰身份认同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认同,以强烈的精神信仰认同成为其民族凝聚力。在跨境民族信仰的掩护下,民族情绪和不合理诉求对民族包容性形成挑战,造成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在我国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大环境下,区别于正常宗教宣传与宗教交流,以宗教为幌子的非常规边境政治文化渗透时有发生[6]。借用宗教促进友谊、加深理解的文化功能,宗教渗透试图通过信仰体系来消融异质性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其针对的对象非个人,而是政治制度、主流价值、社会整体、政权组织。[7]宗教信仰问题的背后往往是跨境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存在,这也是跨境民族问题发展恶化的根本原因,如果能够处理好跨境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则无论泛民族主义还是民族分裂主义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反之,一国如果长期漠视甚至有意限制跨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也意味着该国在将跨境民族逐步推离自身,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甚至会引发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动荡。
(三)大众传媒影响下政治身份模糊
如今,以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网络为载体的大众传媒,基本覆盖了我国所有疆界。大众传媒对边界跨境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已然成为边境地区民族接收外来文化、交流沟通信息的重要媒介渠道。大众传媒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监督、舆论导向的作用,作为受众的跨境民族群体不可置身世外,新大众传媒情境下,意识形态与文化构建对其身份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进入到新媒体时代,以电视、电脑、手机等作为终端的新媒介在方便跨境民族群体的同时,也带来了身份识别的困惑。[8]国内媒体利用现代技术对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意识进行宣传,同时境外宣传媒体也利用地域优势抢占宣传平台。例如,在中缅边界,可以收听、收看多个缅甸语节目。在跨境民族居住地,一些外媒利用边民的语言习惯制作具有特殊目的的节目,以达到模糊听众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的目的。在特殊边境环境中,大众媒体成为跨境民族政治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因素,如何有效减弱和消除境内外媒体宣传对跨境民族的消极作用成为我国跨境民族地区工作的重点。
三、跨文化视角下我国跨境民族身份认同路径探寻
跨境民族既是文化实体,也是政治实体,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面对新时期新情况,为了更好地加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应该从政府主导、跨境民族参与、社会力量支持着手,促进国家内部族群团结和社会秩序稳定,以达成我国跨境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共同发展。
(一)构建制度优势下的主流价值观,增强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向心力
主流价值观是指社会之中多数人认可的价值取向和标准。主流价值观的构建之于跨境民族是其身份认同向心力之源。首先,在国家制度中,教育体系、大众传媒等可以作为制度路径,将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培养与宣传教化相结合,其核心是价值观的调整与社会秩序相协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政策逐步将包括跨境民族在内的各边缘族群纳入国家一体化建设之中,共同构建同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通过制度建设服务跨境民族,使其真正感受制度的优越性,从内心接受和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服务的核心在于政治上对跨境民族实行村民基层组织自治,经济上给予政策倾斜和适当帮扶。我国多数跨境民族居住地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应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跨境民族区域经济,并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物质基础。再次,通过增强跨境民族参与主流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强化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跨境民族所处边境已逐渐全方位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突破原来的边境区域,融入到我国经济大潮之中。跨境民族在经济融合过程中信息、技术落后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对跨境民族的问题进行深层次改造,将其身份认同意识融入主流社会。
(二)发挥语言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塑造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力
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跨境民族群体语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语言反映民族交流、记忆历史与文化传承。共同的语言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在保证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自由的前提下,促进汉语的广泛使用,发挥语言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功能。一方面,以学校教育为主要手段,促进汉语在跨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例如,在云南跨境而居的阿昌族,越来越多地使用汉语,接受汉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汉语与本民族语言同时使用的双语模式,保留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进而增强跨境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认同意识。
(三)借用新媒体的宣传力量,提升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传播力
传媒的本质功能是国家控制和信息传播,而新媒体又使得大众传媒更贴近普通大众,恰当使用新媒体,发挥其统一化的影响力,可以很好地提升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传播力。首先,形成新媒体主流价值观宣传机制。在跨境民族社区,社会成员通过接受媒体宣传信息,了解和参与国家与社会各领域活动,认可社会主流价值观。其次,针对跨境民族地区使用跨境民族语言网站、微博、移动传媒等新媒体过少的现状,开发和制作一些好的新媒体节目,适应跨境民族地区受众需求。以跨境民族地区传统大众传媒原有部分为基础,拓展多种跨境民族语言使用的新媒介,贴近居民实际生活,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新媒体的影响力。跨境民族区域特殊的地理与政治环境,将会成为逐年倚重新媒体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
四、结语
跨文化视角下的跨境民族是一个特殊群体,对他们而言,跨文化传播应基于地域的、民族的基因和同宗同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的历史遗传。兼备边缘性与融合性、民族性与国际性、地域性与多样性、日常性与功利性的跨境民族识别多重特征,在文化全球化交流中必然会产生文化碰撞与冲突。当前多元文化下的多民族共存,其民族认同的实质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对于保持跨境地区长期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通过实践探索构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路径,确保兼顾跨界民族的同时享有民族特殊政策和国家一体化进程政策。
[1]赵廷光.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C].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1999.
[2]Gladney,Dru C.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98.
[3]杨得志.中缅跨境民族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4.
[4]栗献忠.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J].学术论坛,2009,(3).
[5]张兴堂.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6]何 跃,高 红.文化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境民族教育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7]杨得志.跨境民族问题类型化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4,(8).
[8]谷 禾.大众传媒与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塑造[J].云南社会科学,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