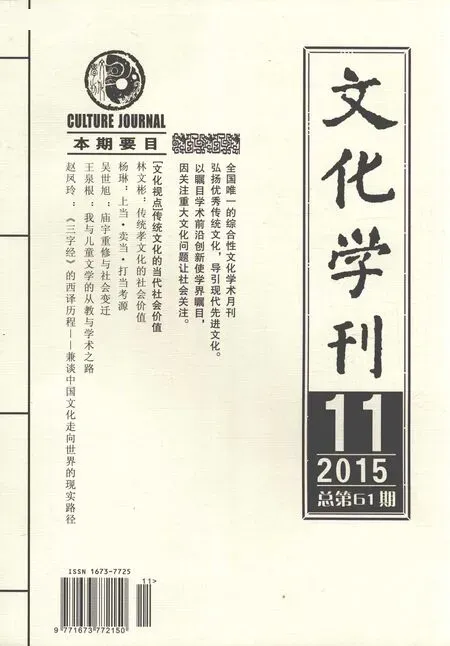“看不见的手”与“自组织原理”之比较
王小刚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5)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出版于1776 年,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与科学发现中1543 年哥白尼与维萨里在不同领域掀起革命等同时性现象颇为相似,由此似乎可以总结出人类心智与社会发展的同源性与必然性,此现象里也蕴含着一定的“看不见的手”与“自组织原理”。言归正传,《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圣经。正是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与“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西方无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方法均与东方有很大差异。东方注重整体性思维,追求全面与辩证,却失之肤浅;西方注重分析性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没有理想状态下的研究不可能有现在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体系。我们给予西方学术最多的评价词汇可能是片面、简化、任意假设、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思辨等,但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科学成为可能。我们说他们追求的是片面的深刻,但他们宁可以片面性来换取深刻性。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们不应仅满足于对自然、社会、伦理的懵懂认识,而应当用自己的理性来分析一切。西方学者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受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极大,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两种方法的呼应。还原论思想在自然科学中自德谟克利特开始已在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文艺复兴时期对原子论的发掘更是从各个领域全面贯彻推动了这一纲领。然而,西方一直也没有忽视整体性思维,在以物理学为主的自然科学哲学界,整体主义是目前研究科学理论结构的基本预设之一,在社会科学界和生物学领域,这一主张早已为哲学家所提出。至今为止,西方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传统一直是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此消彼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自组织原理”可是说是这两种思维方法的成果,两者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矛盾,于我们深化对经济、社会的认识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看不见的手
斯密认为,人人为己的利己心反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和形成自然秩序。斯密认为,虽然每一个人都在谋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但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却能自然地增进公共利益,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表述:“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在斯密看来,是因为自然秩序中存在一种自然平衡和调节的机制,使得人的各种动机和冲突的利益自然达到调适,这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由此而产生的行动必然在自己的利益中包括了别人的利益。[2]
二、自组织原理
自组织原理的基础是整体观与系统观。在康德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里,他承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目的,因思想将目的分为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并由此最早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康德认为,绝对目的论只是内在的目的性。他提出这种目的性不同于机械的单线的有效因的因果关系,可以称为有目的的因果性联系。这种有目的的因果联系,除包含一个前进的从属之外,还包含一个后溯的从属。举例来说,建造房屋是收取房租收入的原因,反过来说,收入房租又是建造房屋的原因。这种内在目的性使一个事物的各个部分与其整体之间保持有机的联系。由此,康德提出了自组织这个天才的猜测,他认为,从目的性看,一个事物是一个有组织的并且是自行组织的事物。从这种观点出发,他阐明了有机体与人造物的不同。简略地说,有机体不像机器那样只有动力,它具有自身内在的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使这个有机体自行运动、自己发展。
康德这个天才的猜测已为当代系统科学所验证,按系统论的观点,形成系统的组织方式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他组织,组织指令来自系统外部,另一类便是自组织,组织指令和组织能力来自系统内部。就整个自然界及其发展史来看,自组织的作用是基本的,它使自然界处处表现出伟大的自发生命力和创造力。
三、“看不见的手”与“自组织原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看不见的手”与“自组织机体原理”之间的区别是表面的、杂多的,而联系是深层的、相互的。
(一)区别
抛开研究对象与主题等方面的区别,两者的区别有三点。
1.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表明了斯密的个人主义立场及其在方法论上的还原论背景。在斯密那个时代,无论谁也不能回避牛顿的巨大影响,所以这机械式的、演绎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而自进化论出现以后,各个学科都深深打上了生成演化的烙印。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始,物理学中引入了时间,从而使以往线性的、可逆的经典科学注入了生命和演化,自组织原理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由于将历史等各种复杂因素引入科学,使其不可避免地采用整体观的方法。
2.理论预设不同
理论预设不同,这是两者间的关键性差异。“看不见的手”的预设是人性的利己心,人人都从相同的利己心出发,各种举动错综复杂,相互冲突和作用,产生了人们完全预料不到的结果,这就是完善的自然秩序。自组织机体的预设是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和孤立的系统,在开放的条件下,系统自身演化出与各部分之和完全不同的新组织。
3.结果不同
结果不同,这是最深刻的一点区别。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虽然从个体的利己心出发,其结果却消解了个体的作用,偶然性在这里不起作用了,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偶然状况对整个社会经济组织的形成与运行不构成影响。个人的利己心产生无意识的社会后果,其自由意志及偶然性在相互冲突中产生着对所有参加者来说是完全预见不到的结果,这个结果与偶然性无关,社会的进程丝毫不受其影响。而在自组织原理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偶然性的作用,甚至将其提高到了本体论的地位,在开放系统中,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正是偶然性不断地打破平衡,放大涨落,推向新的有序。
(二)联系
二者都是统计与进化的科学观的体现,却又都是某种决定论的反映,似乎统计与决定论是一对矛盾,其实近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表明二者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二者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在斯密的年代,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各种形式的自然神论、决定论与进步观开始向神学争夺理性的地盘,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表明,历史过程会调整和矫正人的观念和弱点,这就是说,存在一种为能动的行动者所察觉不到的历史强制力,因而它既是一种自然神论,也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无疑将严格决定论推向巅峰;自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提出以来,生成与演化、联系与发展的辩证思想便开始登上自然科学的舞台;在力学引入统计方法后,自然科学中统计决定论开始削弱严格决定论的理想,社会学也开始引入统计与概率的方法;达尔文进化论问世,无疑向各门学科渗透了进化的思想;量子力学的出现,动摇了以往各种决定论,发展出几率决定论;系统科学的横空出世,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洗荡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在自组织原理里,非平衡状态在非线性的机制下,通过涨落达到有序,通过超循环生成新机体。决定论与统计论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全新意义的历史决定论,决定与非决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分野越来越淡化,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必然性蕴于偶然性之中起支配作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超越时空的遥相呼应,二者都加入了历史的元素,一个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在历史决定论经过否定之否定而达到的更高阶段。两者在内在机理上是相通的,都有一个由低层次或无机体向新秩序或有机体的跃迁与进化过程,根据内在目的性原理,在二者的作用下,发生量到质的变化,都有一个事先无法预料的全新的有序状态产生,而且向着最高的目的——善的方向进化。可以说,现代系统科学的自组织原理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了更细化、更科学化的分析与阐述。
[1][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39.
[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第三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