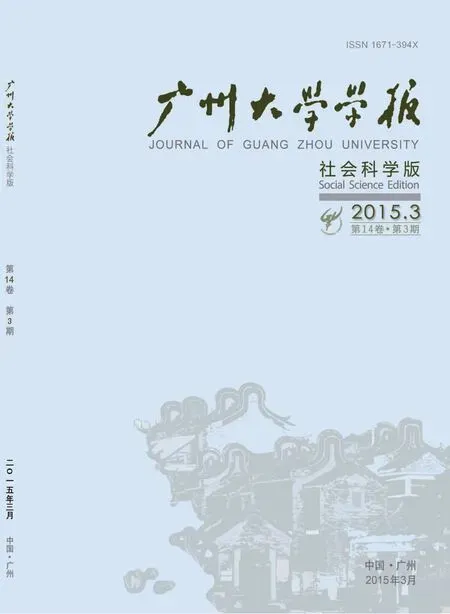论四库全书《诗类》五种提要之异同
谢炳军
(暨南大学古籍所,广东广州 510632)
《诗类》各提要生成之时间:以文津阁本的书前提要为最晚,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方竣工,其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修成已逾三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本文援引皆用是书,省称为《总目》)。(下文省称为《总目》)由乾隆第六子永瑢、纪昀主编,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撰就初稿,又逾八载之修补润色,定稿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然则文渊阁、文津阁本[1]225书前提要早出,《总目提要》之提要晚出。
一、五种提要异同例证
文津阁本书前提要的总纂官系纪昀、陆锡熊和孙士毅,总校官是陆费墀;《总目提要》主编系纪昀,其对提要之润饰,显足其才力,其对“国朝”诸儒之经业赞述不已,时亦有颂圣之辞。纪昀推崇汉学,抑贬宋明理学。有清一代,汉学派占据经术之绝对优势。《总目》之提要与书前提要之差池,足见其影响之巨大,兹对《诗类》《总目》之提要与书前提要的歧异,略举四例以资考论。例1:《总目》之《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提要[2]130:
二十卷,《序》二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御定。刻成于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制《序》颁行。《诗序》自古无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争毛、郑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诗》者,萌于欧阳修,成于郑樵,而定于朱子之《集传》。盖《集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又成祖虽战伐之余,欲兴文治,而实未能究心经义,定众说之是非。……是编之作,恭逢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道光经籍,研思六义,综贯四家。……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岂前代官书任儒臣拘守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
文渊阁本《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前提要同《总目》,文末标明日期、编纂诸官,其云“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3]7-8。
文津阁本《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前提要:
臣等谨案《诗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序》二卷。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臣王鸿绪等奉敕修刻成于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制《序》颁行。……数千年来言《诗》者可别白而定一尊矣。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下文省称为《荟要》)内容同文津阁本,文末所署日期系“乾隆四十年十月”[4]151。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下文省称为文溯阁《提要》)内容同文津阁本。所署日期为“乾隆四十七年十月”[5]87。
考五则提要,可察知其以下分异:
第一,书名同,卷数异。《总目》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下文简称文渊阁本)谓二十卷,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下文省称为文津阁本)《荟要》、文溯阁《提要》言二十一卷。
第二,有无修刻者。《总目》、文渊阁本无,文津阁本、《荟要》、文溯阁《提要》均言及王鸿绪。
第三,字数篇幅差池。《总目》详,文津阁本提要略。《总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揽《诗》学之良莠,称道清经解之昌明。而书前提要止步于辅广。
第四,剖判汉学、宋学异辙,并打上颂圣烙印。其一,《总目》、文渊阁本标举汉学,虽自谓“持其至平”,但未见其然,其剖判前代官儒甚力,有失公允,如谓前代著述未及此书之“万一”。其二,《总目》颂圣意图显著。文津阁提要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尚未有明彰之颂圣语气,及至《总目》歌颂圣上则昭然如昼,其比较明成祖朱棣与康熙之文化伟绩:成祖于太平之时未能研习经义、定《诗》学之是非,是以未有文化创举;康熙禀性聪颖,穷研六经,学贯四家,润色经业,文治煌煌。将朱棣援入《总目》之中,反映了作者歌帝颂清之政治立场。
此外,辨章学术之时,《总目》所论有未安之处。如谓“盖《集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平心而论,吕祖谦与朱子胥系穷探经业之大儒,并有儒雅大度之品性,他们系学术上之诤友,生活上之良朋,此于文献有征。吕祖谦、朱子始论《诗》皆宗《毛序》,《总目》之《诗集传》提要亦谓“朱子作是书时两易其稿”,第一稿系“全宗《小序》”,但后朱子与《小序》分途,改从郑樵之说,而吕仍主《小序》,然则并非俩人因学术相激而成《集传》。相反,朱子因吕氏信从己之《集传》初稿,而深感愧疚,如朱熹为《吕氏家塾读诗记》作《序》时云:“此书所谓朱氏者实朱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已经下世矣……”由此可以推断,朱氏、吕氏并非因争于才力而“相激”。
较之《总目》,文津阁书前提要之剖判《诗》学则为持平,其谓“是书之作博採《传》注兼用汉宋之说而取其精。数千年来言《诗》者可别白而定一尊矣。”是未有尊汉抑宋之门户之见。
例2:《总目》之《钦定诗义折中》提要[2]130-131:
二十卷,乾隆二十年,皇上御纂。……盖我圣祖仁皇帝钦定《诗经汇纂》于《集传》之外,多附录旧说,实昭千古之至公。我皇上几暇研经,洞周窔奥,于汉以来诸儒之论,无不衡量得失,镜别异同……于《诗集传》所释蝃蝀之义,详为辨证。并于所释《郑风》诸篇概作淫诗者,亦根据毛、郑,订正其讹。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见圣圣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诸臣恭承彝训,编校是书,分章多准康成,徵事率从《小序》……
文渊阁《御纂诗义折中》书前提要同《总目》。文末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6]4-5。
文津阁《御纂诗义折中》书前提要[1]596:
臣等谨案《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取圣祖仁黄帝《周易》命名之义为名,大学士忠勇公,臣傅恒等裁纂。盖《诗》义自朱子斥去二《序》,独寻微旨,一扫《传》会拘牵之说,我皇上鉴聚讼之失,标言志之准,融洽诸家,归于一是。分章间採康成,徵事亦搜《小序》,至于讽劝之大仍一以朱子为正。……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荟要》内容同文津阁,文末云“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4]151。
文溯阁《提要》内容同文津阁,文末云“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敬上”[5]87。
兹比勘五则提要之异同,可获知:
第一,《总目》之“诗义折中”前是“钦定”,其他四则提要之“诗义折中”书前是“御纂”,“钦定”意思是皇上亲自裁定的;“御纂”意思是按皇上诏命编纂。文渊阁本名同文津阁。
第二,《总目》与文渊阁本不言及编纂者,其他四则提要标明裁纂者系大学士忠勇公傅恒等。
第三,《总目》与文渊阁本未能反映皇上及编纂者之意图,其他四则提要则彰显是书编撰之意旨。《总目》因拘于门户之见,仅言及乾隆或学士对朱熹训诂的生疑及正朱讹误之功。《总目》提要的门户之见,还体现在只字未及乾隆所采之朱熹《诗》学,而书前提要却言及“讽劝之大仍一以朱子为正”。乾隆对朱子之学颇为赞赏,考之《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序》,乾隆谓:“自说《诗》者各以其学行世,释解纷纭而经旨渐晦,朱子起而正之,《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圣经,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正义》为正于春秋《诗》复命儒臣次第纂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故是书首列《集传》”[1]233,又案是书之《周南·关雎》,诗旨用的乃系《集传》之义,朱熹在《诗序卷二》中谓:“其诗虽若专美大姒而实以深见文王之德,序者往见其词而不察其意,逐一以后妃为主而不复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即认为《关雎》之主旨在于美文王。《诗义折中》中《关雎》之旨不用《小序》,而讲“《关雎》,文王之本也,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格物致知,心诚皆所以修身也”[1]596。意同朱子。这同《总目》提要“徵事率从《小序》。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卜氏旧传,远承端绪”不合,由此观之,可见《总目》门户之见深矣!
此外,是书按乾隆之意编纂,必然反映乾隆之政治意图,文津阁本简略地一笔带过,云:“皇上鉴聚讼之失,标言志之准,融洽诸家,归于一是”,论调平允。而《总目》提要却未及之,代之以颂圣媚上辞,云“圣圣相承,心源如一……作述之隆,后先辉耀。经术昌明,洵无过于昭代者矣”。
考稽此书诗旨,乾隆将“忠君事父”之思想注入诗解,解《汝坟》之旨曰:“《诗序》曰‘《汝坟》道化行也。’道莫大于五伦,而君臣父子为尤重,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故纣王暴虐,文王事之不敢逆,也不惟叛而已,且使天下之叛者皆服于己而已,复率之以事纣,故终文王之世,天下皆供纣之役,而且忘纣之暴,是文王以事君之道化天下而天下化之,故曰道化行也……文王服事商纣并有怙胃之仁,必如此而后天下化,必如此而后天下之为君臣父子者定”,由此可略见是书编撰之政治用心。
例3:《总目》之《田间诗学》提要[2]131:
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国朝钱澄之撰。……大旨以《小序》首句为主。所采诸儒论说,自《注》、《疏》、《集传》以外,凡二程子、张子、欧阳修、……楷二十家。……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徐元文《序》称其“非有意于攻《集传》,于汉唐以来之说亦不主于一人。无所攻,故无所主。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书之意。张英《序》又称其“尝与英书,谓《诗》与《尚书》、《春秋》相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即今舆记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所亲历”云云,则其考证之切实,尤可见矣。
文渊阁《田间诗学》书前提要同《总目》。文末云“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4]395-396。
文津阁书前提要:
臣等谨案《田间诗学》十三卷(按:下文内容同《总目》是书之提要,故省之)……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7]1。
《荟要》无是书提要;文溯阁《提要》内容同总目,文末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敬上”[5]87。
这四则提要除却卷数差异外,内容庶几相同。考钱氏之《田间诗学》,诗之旨时而采捃《小序》,时而捡拾朱熹,时而自行己意。钱氏《凡例》自云:“是编一以《小序》为断,去古未远,其世次本末虽未可全据,要不大谬也……《小序》者诗题下发端二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只此论之《小序》盖古《序》也,……朱子《集传》半尊毛郑,间出己意,明白易简,迥出于毛《传》郑《笺》之外确不可易矣而亦有过于拘泥者……吾之从朱犹之从毛郑二家取其是者而已矣!”由此观之,钱澄为学无门户之见,参稽众说,兼容并包,而又七易其稿,足见其治《诗》之严谨。然而,钱氏之学这个鲜明的特色,《总目》提要却当言未言,所言又有未安之语。钱氏所言系别家若有一言可采便录而存之,如《芣苢》,援引了刘向《烈女传》中蔡女作《芣苢》之事,而提要谓除毛郑朱外,钱氏采用二家学说,不合钱氏初心。
又《总目》称引徐文元与张英之《序》文,《总目》作者自行己意,因删削原文,或因误记,以致乖违。如徐氏原《序》为“非有意于攻《集传》也,凡以求其至是至当而已……无所主,故无所攻……”《总目》删省“凡以求其至是至当而已”一句,易致读者误读:有之,读者可晓钱氏对朱学之态度;无之,容易误导读者而认为钱氏攻朱学,而于朱无所取。又如《总目》将“无所主,故无所攻”误记为“无所攻,故无所主”。徐之前文谓:“朱子之作《集传》其意亦以为敛辑诸儒之说,而非一人之独见也。惟其先有诋诃《小序》之见,故其援引指摘时有不能无疑者,后人说《诗》若先有诋诃《集传》之见横于胸臆,则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心,有甚于朱子者矣。”故应是先无所主,所以无所攻。
此外,《总目》中“尝与英书”,张英《序》作“尝贻余书”;提要“与情事之疑信”后面省去张《序》之“而且列国之封域山川之形势变迁不一”,若加之,或能更好地理解《总目》中援引之《序》的文意。
例4.《总目》之《诗集传》提要[8]122-123:
八卷(通行本),宋朱子撰。……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序》末称时方辑《诗传》,是其证也。……《周颂·丰年》篇小序,《辨说》极言其误,而《集传》乃仍用《小序》说,前后不符,亦旧稿之删改未尽者也……
文渊阁提要《总目》内容同《总目》,文末云“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9]745-747。
文津阁书前提要云:
臣等谨案《诗经集传》八卷,宋朱子撰……朱子尝自谓“少年浅陋之说,久而有所更定”,陈振孙江西所刻万年本得于南康,胡泳伯量较之建安本,更定几什一。……朱子说《诗》去二《序》,而《集》中有广青衿之疑问句却用《序》说,后人惑之,要其涵濡讽詠务得性情之正,此
固律世之大防也。[10]293
《荟要》内容同文津阁本,文末云“乾隆四十年恭校上”[4]149-150;文溯阁《提要》内容同文津阁本,文末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5]79。
《总目》提要和文渊阁本同文津阁本相较,歧异颇大。《总目》着墨于批判朱子,而无暇言及《集传》之优点,后又以颇大之篇幅阐述各家对《集传》之校勘,意指其讹误之多,失却提要作为提要之本旨。书前提要简短,仅阐明了《集传》版本及朱子去《序》言《诗》的一个现象,然而亦未深究朱子《诗》学之基本问题。
《总目》因“《序》末称时方辑《诗传》”,遽断文津阁本的《诗经集传序》系初稿之《序》,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亦称“此序乃是其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11]591。以笔者考之,未见其然。此《序》收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名为《诗集传序》,文末标明时间“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又据朱子“以冠其篇”等言语,再者,此《序》文渊阁本名为《诗经集传原序》,而比它晚出的文津阁本去其“原”字,以正其讹误。然则此《序》确系朱子新稿之《序》。
《总目》称其为初《序》的一个证据系“无一语斥《小序》”,但需表而出之的是,此《序》之意不在探究《小序》,是以不斥《小序》;再者,换而言之,“无一语斥《小序》”并不侔认同《小序》,如同“无一语赞《小序》”的逻辑相类,并未能证实问题关键所在。
《总目》又指出朱子是书所存“同诗不同诗旨”之矛盾现象,这个是事实。朱子《诗》学顺应疑《序》之风而转帆,《诗》作前后俨然两物,束景南对此已研究甚详。文津阁本援引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说》一卷,朱熹撰。……其序《吕氏读诗记》,自谓少年浅陋之说,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于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者几什一云。”指出了朱子释《诗》前后踳驳之主因:朱子又不间断修正其《诗》说,以致多个《集传》版本行世。此外,考之《集传》及《诗经辨说》,“朱子说《诗》去二《序》”不侔朱子摈弃了二《序》,而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序》有取有舍。朱子对毛郑有同有从者,根据祝敏彻、尚春生等学者之统计,谓“朱熹《诗集传》从毛传的七十六处,从郑笺的八十六处,兼采毛传郑笺的十六处”[12]。
二、五种提要异同之原因
先简述《四库全书》编撰时的政治环境。
清廷自顺治洎乾隆,对明遗民、汉族知识精英硬软兼施,武攻文诱。武攻,即制造了一场场惨不忍睹文字狱:康熙时有两大惨案,一系庄氏“明史”案,二系戴名世《南山集》;雍正时有“查嗣庭案”、吕留良及曾静案等大案;乾隆朝,文字狱数量、规模上可谓登峰造极,九辑《文字狱档》庶几有八辑与乾隆一朝有涉[13]1。清廷认为“大逆不道”的违碍之书,直接危及清廷之治乱,而对文籍进行一次大检查,企图扑灭反清思想的火源,官方修书便成为堂而皇之之理由。乾陵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辑佚《永乐大典》的问题,正中清帝之怀,由是一场书籍大汇编的巨大工程启动了,同时,一场针对文籍的“大屠杀”运动亦轰轰烈烈地开机了。乾隆藉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文字狱亦被推上了高潮: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1774~1783年)的十年间,便发生了文字狱五十起[14]6。清帝对诗文中的“清”“明”两字极度敏感,以致“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如斯平常之诗文亦能断送诗人性命。《四库全书》之修纂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兹论述各提要异同之因素。
(一)卷数差异之原因
《总目》提要、各阁书前提要著录之卷数差池,概而言之,有三大主因:其一,乾隆下令对书籍的抽毁;其二,书前提要的纂写时间与书籍编成时间有分异;其三,《总目》提要编撰者未能如实著录书籍之卷数。
编纂《四库全书》对清廷而言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对古今文籍的大荟萃,系功在千秋的文化美事,亦系清廷重视文化之表现、笼络汉族知识精英之手段;二是通过检查所征之书籍,便于肃清异己思想,消灭打击对清廷心怀不满的力量,达到威慑征服的目的。这样一件既美化了自己,又打击了异己思想与力量的大事,乾隆朝做成了。这样工序浩大的工程,是文化任务,而对清廷而言,意义更在于政治上的需要。一旦皇帝发现进呈之书中有违碍的字句或书卷有悖己意,就会对负责人给予惩罚。乾隆四十七年,发现四库馆进呈原任检讨毛奇龄撰的《词话》内,有字句违碍,而总纂官没有签改,交部议处[13]37。是其明证。
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凡是当局认为有悖逆之意的书籍,皆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其间,有删削者,有销毁者,甚而有之,连宋代书写到抗金、明代书写到抗元等文籍,亦要删窜改写。仅在浙江省,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就进行了二十四次大规模的检查和销毁,全国范围内列入全毁的书目有二千四百多种,抽毁的书目有四百多种,销毁的总数在十万部左右[14]4。通过删窜、销毁以及抽毁等手段,书籍已离其真,面目皆非。
在如此修书之政治环境下,皇帝随时抽读《四库全书》,一旦发现有违碍之处,就命编修官修改。刊削之书的卷数,在最晚出之《总目》中体现出来。然则《总目》提要根据最后定稿时之版本卷数行文,原先书前提要记录的卷数已然不准确了,因原所采征之书籍的面目已发生了变动。这就造成了书前提要卷数与《总目》之卷数的不同。
卷数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书前提要的纂写时间与书籍编成时间的分异,有时书前提要已经写就,而当时编进去的书籍又有新的善本,编修者便用新版本。最早的文渊阁《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内容是二十一卷,《序》两卷。但其书前提要却谓二十卷,《序》两卷。北四阁最晚出的是文津阁本,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5年),距文渊阁本修成的时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近三载,与《总目》定稿的1789年,又差近四载。文津阁修正了文渊阁书前提要之讹误,将文渊阁本的“二十卷”正为“二十一卷”,又新作了书前提要。但《总目》之编撰,没有按文津本的书前提要修正文渊阁本之错误,亦未核查是书的总卷数,乃系照录了文渊阁书前提要致误。
卷数差异的另一个原因系《总目》作者并未如实著录书籍卷数。《总目》著录诸书,前后附卷多弃而弗录,偶亦有计入正卷者,体列不一,率非实录[15]86。其实,这亦无可厚非,《总目》亦系一个不小的工程,而《四库》又在被修改着,也要有所补充,纵穷纪氏之力,疏漏错误也在所难免。例子上的《总目》提要用的都是文渊阁的书前提要,除了文津阁的《诗经稗疏》之书前提要(卷数不同)内容同,其他的差别有颇大者,如《诗经集传》。
(二)内容差异之原因
从上举之例子看,文津阁本书前提要、《荟要》、文溯阁《提要》,此三者于内容上差别不大;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差别也大同小异。但前三者与后两者比较起来,有的存在较大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文字数量的多寡上,还体现在考镜源流之态度上,此从前面举的例子可见其崖略。其主因有二:一是受制于政治文化环境,阐发宋明理学之儒者退隐,在经术圈里的人数递减,经术义理派之影响力亦随之削弱了;为降低因文获罪的政治风险,学者型官员埋头于典籍,推崇毛郑,醉心于考据之学,汉学派于学术圈便势不可挡,占据经术主流;二是编撰者对几个提要取舍的标准系表彰汉学。
康熙、雍正、乾隆在政策上尊崇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康熙尊崇以汉族为主创造的中原文化,大力提倡学术,奖励理学[14]2。康熙推崇朱子之说,可以从雍正为《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作的《序》中窥见一斑。并且文字狱的罪由之一就是“诋毁程朱,倡为异说”。但是义理学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充其量仅系皇帝独有之理学,理学亦止步于斯。雍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序》云:“皇考授儒臣勒为是编,期以阐先王垂教之意、与孔子删《诗》之旨,学于是者,有得于兴观群怨之微,而深明于事父事君之道,从政专对,无所不能,则经学之实用著。”而在《御纂诗义折中》中,释诗亦将“事父事君”思想贯穿其中。这亦不难理解皇帝为什么大力地推崇理学,因为对他宣扬自己的思想最有利。古人对《诗经》意旨之解读,本身有经世致用之意图。皇帝正好用“诗教”去贯彻自己的思想。皇帝阐发理学,因其握有生杀予夺最为自由之权力,而学者却无思想之自由,是以理学在乾嘉学派面前退隐出了学术圈的舞台。
最先进入四库馆充纂修官的姚鼐,系以宋儒之学务本的学者,其弟子毛岳生的《惜抱轩书书录序》云:
桐城姚先生……以程朱为海内大贤,……先生尝云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词章,三者必有豪杰之士兼收其美……当乾隆间,考证之学尤盛,凡自天文、舆地、书数、训诂之学皆备,先生邃识综贯,诸儒多服,而终不与附和,驳难惟从容,以道自守而已,时纪文达为《四库全书》馆
总纂官,先生与分纂,文达天资高,记诵博,尤不
喜宋儒……[16]1-4
由此观之,理学派与汉学派之学术分歧,姚鼐尚义理,但亦不废毛郑,较之纪氏诸儒之“不喜宋儒”者,其治学态度尤足称道。然遗憾的是,四库馆臣之中,姚氏势单力薄,人微言轻,在汉学为代表的经术圈内不得志,是以所纂提要稿亦不为汉学派所重,并过早地离开了四库馆。梁启超谓“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17]19,所言甚确。为何汉学之劲风压倒理学而标榜推崇理学的皇帝却不加以禁止呢?主因在于皇帝推崇义理学,并非真心鼓励理学,“诋毁程朱”之罪亦未在汉学派间形成威慑力,尤其及至乾隆朝开四库馆之后,总纂官纪昀“尤不喜宋儒”,矛头直指程朱。文渊阁本的书前提要,明显流露出尚毛郑、抑程朱之学术风向,但皇帝却视而不见。梁启超云:“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分压倒”[17]19,此仅系表面现象。学者埋头古籍,从事考据之业,正系皇帝之真心。
在古代的中国,学术历来与官学、政治密不可分,清朝亦然,且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借编修《四库全书》之良机,乾隆把官员学者绑结成一串,编纂古籍,形成统一的官方的学术圈,汉学之风盛行,宋明理学喑哑了。而为何文津阁本的书前提要,如例文所见,较《总目》、文渊阁本提要持论平允呢?主因在于两阁的书前提要并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编修时间之前后,馆臣之变迁,均能生成书前提要之歧异,此可从例文所署日期不同,提要亦有所生异,知其根萌。
(三)援引错误、表述错漏之原因
《总目》提要中,援引或表述偶有错漏,虽无可厚非,但亦不可不谈,不可不为之纠正。出现错漏的主因显而易见,编纂者不可能一本书一本书地比勘核查,时间、精力亦有限,而经史子集所涉及的范围过广,难以面面俱到、处处留心。余嘉锡谓《总目》经“纪昀一手修改,考据益臻洋赡,文体亦复畅达,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覆检原书,无一字无来历,此势所不能也”[18]。并且纪氏被称“天资高,记诵博”,“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亦不如原书之矜慎者,且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逐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18],这正是例文中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在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几种提要之异同,既与提要编撰者的学术取向牵连,亦与其时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涉。《总目》作者力图以公允之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避免门户之见,然而,编撰者自有学术价值观,或倾于汉学或偏于宋学,胥于不自觉中失却寻绎“公理”之初心。
[1] 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 诗类 第二八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 经部 诗类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册 经部 诗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王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 金毓黻.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M].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6]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册 经部 诗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 诗类 第二九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 经部 诗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 经部 诗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 诗类 第二四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 祝敏彻,尚春生.论毛郑传笺的异同[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1).
[13] 黄裳.笔祸史谈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4] 孙立.清代文字狱[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 崔富春.四库提要补正[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
[16] 姚鼐.惜抱轩书录[M]∥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6.
[18] 余嘉锡.序录[M]∥四库提要辩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