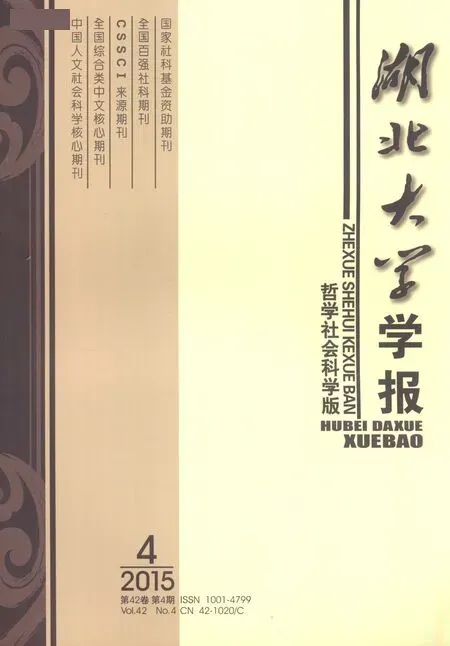“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
刘建明,徐开彬
(1.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天普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19122)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James W.Carey,1934-2006)在1975年发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从此,传播学者开始从仪式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传播活动,形成传播学研究不容小觑的支流。沿着这条支流顺流而下,依次呈现这些学术景观:传播的仪式观、仪式化或仪式性电视收视行为、媒介事件、仪式传播、媒介仪式等。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把传播与仪式相关联,从而拓宽了传播学研究视野,加深了人们对传播活动的认识。正是凯瑞突破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藩篱,开启了传播的仪式研究或文化研究传统。凯瑞以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意思就是“传播是一种仪式”。仪式通常指宗教的或世俗的人类社会性活动,属于神学、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范畴,与通常意义下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传播概念相去甚远,为何将它作为传播的隐喻?凯瑞没有做具体的、详细的解释。本文试图探寻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背后的逻辑。
一、“传播的仪式观”对“传播的传递观”的纠偏
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收录于凯瑞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凯瑞提出两种对立的传播观: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前者指“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后者指传播“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1]5~7,是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的社会交往仪式。凯瑞提出仪式观的出发点是纠正美国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盛行的传递观。虽然他“不否认的确存在信息传递式传播,但把它视为仪式传播的低级版本或否定”[2]。凯瑞倡导传播的仪式观,反对传播的传递观及其主导地位,与他对传递观的认识密切相关。他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传递观与社会模式“存在着某种紊乱”
由于对传递观的迷恋,使得人们总是把社会“看作是一张由权力、管理、决策与控制结成的网——也就是把社会视为一种政治秩序”。或者,“把社会看作是所有权、生产与交易的关系——也就是把社会视为一种经济秩序”。但是在凯瑞看来,“社会生活不只是权力和交易”,“它也包括了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与情感以及学术观念的分享——一种仪式的秩序”[1]21。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活不仅指涉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包括仪式化的其他社会活动。
2.传递观体现了传播的单向性话语霸权和功利性
现代(大众)媒介由于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单向信息传递,以及渗透大众头脑并施加影响的科学。在现实中传播作为一种说服活动广泛地被政府用于谋取政治利益,被企业用于谋取经济利益,企图实现“对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大人口的影响、控制”[1]28。凯瑞反感这种工具性的、实用性的和功利性的传播和话语霸权,在多篇论文中屡次主张能够体现主体间性的“会话”(conversation)文化。
3.传递观主导的传播学效果研究停滞不前
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确立至70年代初,其研究范畴一直聚焦于信息传递和接收活动,主要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围绕大致可预料的传播效果而进行,它总是“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因此,凯瑞主张传播学从“生物学、神学、人类学及文学”等学科知识材料中汲取营养,“另辟蹊径,以免像现在一样原地打转”[1]11。其突破口便是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与这些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凯瑞意识到传递观只注重传播的空间维度,而忽视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凯瑞响应了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观点。他们都认识到,传播同时存在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但他们更强调时间维度。威廉斯认为,传播不只是信息的空间传递,它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分享。凯瑞赞同威廉斯的观点,传播的仪式观也正是一种文化研究取向,因为对凯瑞而言,传播就是符号表述活动,而符号表述活动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深层目的就是维系脆弱的文化”[3]。文化在时间长河中形成和成长,历经时间,人们结为一体,团体维持着身份认同,社群源于时间上的连贯性。而传播所发挥的作用,正是社会关系的维系和传承。用仪式观来表述,传播就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1]7。
英尼斯区分空间偏向(space-bias)和时间偏向(time-bias)的媒介/社会,他认为空间偏向的媒介过度膨胀造成现代社会的不平衡,主张复兴时间偏向的媒介,抑制空间偏向的媒介,使二者平衡发展。凯瑞认同英尼斯关于媒介/社会的时空偏向二分法,略有不同的是,他使用空间连接(space-binding)和时间连接(time-binding)两个相应的术语。空间连接发生在书写和印刷媒介兴起以来的社会,特别是大众媒介繁荣的时代;时间连接的典型发生在口语文化时代,部落通过讲故事或其他具体仪式,使生活方式或共同文化代代相传。凯瑞主张传播是时间连接,认为传播发生于时间之中,传播跨时间而进行。由于仪式事关重复和循环,事关维系和保存,事关记忆和传统[4],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是一种仪式。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来,凯瑞一直呼吁传播学者重新反思传播即信息传递这一根本假设。他提议,将社会生活的循环往复,定位为各种过渡仪式和不同群体间交流共享意义的仪式。这对任何大众媒介研究而言,都是极有价值的起点,因为大众媒介并非中立的信息载体,它们在构建和传递各种符号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这些符号,社会认同和社会关系得以创造并为人们所理解[5]114。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代替了传统的讲故事和仪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神圣仪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社会纽带功能。
实际上,黑格尔对大众传播的仪式性曾有朦胧认识。他把清晨读报比作现代人的晨祷,用以对比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分野:传统人倾心于上帝,现代人忠实于国家,因为读报把现代人与国家事务联结在一起。黑格尔没有挑明传播是一种宗教仪式,凯瑞也没有把他列入传播的仪式观的思想来源。然而,把读报比作晨祷蕴藏着仪式作为传播隐喻的胚芽。凯瑞更明确地指出,“当我们审视报纸时,……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在那种场合下,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1]9。大众媒介的内容充满了陈词滥调,无足轻重,但是它们具有宗教仪式般的社会功能,对凯瑞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传播的传递观”的纠偏构成了传播的仪式隐喻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全面把握“传播的仪式观”,还需要理解传播与仪式的社会共性,以及传播活动的仪式特征。
二、仪式和传播都具有社会序化和凝聚功能
仪式属于多学科领域研究范畴,不同(学科)学者对仪式的认识见仁见智[6]7。解析传播的仪式观,关键在于理解凯瑞对仪式的看法。令人遗憾的是,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和《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这两篇仅有的论述传播的仪式观的文章①凯瑞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这两篇论文后,转而继续研究技术与文化、新闻与民主、美国新闻教育和大学教育等问题,对“传播的仪式观”再没做专门论述,也极少提及,以至于怀疑者认为,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会不会是凯瑞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它合理吗?凯瑞的得意门生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也是怀疑者之一,他在对晚年凯瑞进行专访时提到这个问题时,凯瑞的回答是:自己对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很高兴;既然在提出后得到广泛反应和认同,就没有必要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中,凯瑞并没有对仪式做具体解释。然而在其他论述中,凯瑞还是谈到自己对仪式的看法。《詹姆斯·凯瑞:一个批判性读者》一书,收录了凯瑞关于仪式的相关论述,其观点可归纳如下:
我们往往把社会秩序视为理所当然,把社会无序视为想象的产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类混杂多样,人性中存在冲动莽撞的一面,初始社会充满了混乱和偶然性,只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化,社会才得以序化。由于仪式创造了社会关系形式,从无序中建构了通行的社会规则,因此仪式成为人类文化的最佳体现。仪式原初的意义是控制无序状态、施加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文化是人类实践的总和,这些实践首先构成了传播。传播的深层目的是为了维持脆弱的文化,所以传播有助于社会序化。会话(conversation)是传播的具体体现,它要求身体实际在场。为了使会话继续下去,必须给对方留下反馈的余地,充分重视对方,因此会话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平等形式。在会话中理当注重措辞,因为措辞不仅反映我们的思维,也反映我们的身体状态。会话不仅希望得到反馈,而且必然会以克制和缓和的语气表达批评、疏离、反对和异见,并或显或隐地表明团结一心和彼此尊重,这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和凝聚力[7]314~315。
如果再简约一点,凯瑞的上述仪式观可分为两部分:(1)仪式是文化的最佳体现,而文化序化了人类生活,因此仪式也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序化。(2)传播是文化的首要因素,而传播具体体现为会话,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礼仪,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
传播的传递观着眼于信息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仪式观着眼于人们之间的符号互动活动及其仪式般的社会功能。在凯瑞看来,仪式和传播都具有社会序化和凝聚功能。这一点可以从传播的仪式观的思想渊源得到旁证。正如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所说,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追溯传播的仪式观的思想渊源就会有助于了解传播的仪式观的本质。
凯瑞把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作为传播的仪式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他指出:“传播的仪式观有着明确的宗教起源,而且它也从未完全脱离这一基本的宗教隐喻。”他把传播的仪式隐喻追溯到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7,其仪式概念主要借鉴了涂尔干的宗教仪式观念。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创造和维持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市民生活分为世俗的日常劳作和神圣的宗教仪式,前者是分散进行的,目的是获取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后者是集中进行的,目的是形成集体共同感。通过宗教仪式,分散的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共叙手足之情,同享道德准则,社会秩序从而重焕生机。宗教仪式强化了人际关系,加深了彼此间的情谊,稳固了人与社会的纽带。在宗教仪式中,人们的社会身份得以确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以创立和维系[8]。宗教仪式后来衍生出世俗仪式,包括正式仪式(如婚礼、葬礼)和非正式仪式(如见面时握手、寒暄,告别时挥手、说“再见”等)。世俗仪式也反映和构建社会关系,同样具有社会序化和凝聚功能。
凯瑞坦承受到杜威(John Dewey)等芝加哥学派社会思想的启发。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9]5。社会的本质在于传播,社会的存在离不开传播。芝加哥社会学派在对19世纪美国边疆和城市形成过程的研究发现,社区的建立与传播活动密不可分。由于居民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因此只有通过协商和沟通,形成某种意义的共同文化,才能彼此和谐相处。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ommunis,最早有“普遍”和“分享”的涵义。古罗马时期政治家西塞罗把communication定义为把握一件事情或者是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这样拉丁语中的 communication的意思就是沟通、参与[10]77。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共享(communion)、共同(common)等具有共同的词根,说明它们在古代已经具有同一性。传播原本寓含宗教仪式、社会团结、社区纽带之意,但在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后则强调出于控制目的而进行的货物、人、信息跨空间运输活动,从而丧失了长期以来与仪式、社会纽带的关联,变成与信息的准确传递相关联。其新含义强调说服技巧和社会控制,而不是社区形成和社会仪式[5]104。在现实生活中,传播被社团或个人广泛用于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传播的社会性就这样被政治性和经济性所取代。芝加哥学派重新发掘了传播的社会属性,敏锐觉察到传播具有仪式般的社会凝聚作用,把传播视作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的有效手段,因此备受凯瑞推崇,被他称为“在美国思想传统中对传播和大众媒介研究最有价值的观点”[3]。
三、人类社会生活的符号互动本质及其仪式性
在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之前,传播的含义已窄化为单纯的信息传递过程。凯瑞认为,这背离了传播的原义和应有之义,传播的含义应该更宽泛更复杂。他从人类本质特性这一高度思考传播问题,把人类视作符号动物,个人和社会实践都围绕符号活动这个中心而展开。人类社会生活就是符号互动过程,研究传播就应该研究符号互动。这一点,凯瑞受到符号论和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根据符号论提出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观点,人是一种符号动物,这些符号包括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科学、神话等等。其他动物通过本能和直觉感悟世界,它们也有自己传情达意的能力和方式,但停留在使用简单的“信号”(signs),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并使用这些符号进行沟通。凯瑞引用卡西尔的话说,“人类生活在一个新的现实维度中,这是一种符号的现实,通过这种能力机制,存在得以产生”[1]14。
作为凯瑞认同的思想来源之一[1]12,休·邓肯(Hugh D.Duncan)也认为:“在社会里人类传播就是试图创建符号,并相信使用这些符号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既存在于传播中,也通过传播而存在。传播就像食物和性一样是人类的天性”[11]。
凯瑞承认米德(George H.Mead)、库利(Charles H.Cooley)、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符号互动论学者对传播的仪式观的影响[1]12。米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在于符号互动。人们通过符号互动进行交往,他们总是在积极寻求与他人、环境的互动,以图发现意义。凯瑞认为,人类个体在符号互动中相联结,社会的存续依赖于这种不间断的相互表达。
库利着重探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他的“镜中我”概念(looking-glass self)表明,个人感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这种感知以及这些评价和态度,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它们决定这个人的自我成长和个性特征,这时他人就成了这个人的一面镜子。“镜中我”概念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及其有机的、稳定的联系,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
传播的仪式隐喻与戈夫曼的“场景社会学”(sociology of occasions)和戏剧理论密切相关。场景社会学研究人际之间的肢体语言和语言,戈夫曼使用“仪式”一词来比喻人际互动是如何被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强调日常面对面互动被结构化和表演化的程度。根据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人生是一场戏剧,人们在不同场景扮演不同角色。剧情和台词由剧本提供,剧本主要由传统、习俗、制度等事先规定,因此这些表演都是例行的、可预见的(重复性的)、形式化的和仪式化的。人们在不同舞台上的表演主要通过语言和肢体语言,实则为符号互动仪式,藉此维持彼此间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凯瑞认为,人类传播就是符号互动和文化共享仪式,具有人生这场戏剧表演的性质和功能。
传播的仪式观还受到文化人类学者的影响。文化人类学把仪式看作习惯性、重复性行为,拘泥于形式的行动,以及事关超凡价值(transcendent values,或神圣价值)的行动(比如圣餐仪式在基督教语境中被理解为与上帝进行直接接触)[12]3。“人类所有行为一定程度上都是仪式化的”[13]13,这主要是因为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对个体来说,文化基本上是既定的、现存的。当我们出生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栖身的社群中;在我们生命过程中,它继续维系或有所变更;当我们逝去时,它还会沿袭下去[14]57。因此,我们的言谈举止都会打上我们先辈创造的文化规范的烙印,不会轻易偏离这些文化规范。以传播为主体的个体行为,往往具有模仿性、重复性(可预见性)、表演性、形式化和超凡性(超验性)的特征,因而具有仪式化的特征。通过这些行为,社会认同得以确认,社会关系得以创造和维系。传播的社会序化和凝聚功能正是通过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符号互动而实现的。
凯瑞还把韦伯(Max Weber)、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学者的思想列为思想来源[1]12。韦伯认为人类是一种悬置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格尔茨把这些“意义之网”理解为文化,人类创造文化,又依附于文化。在韦伯关于科层制的政治文化中,不同科层之间的沟通具有程序化、制度化、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
传播是一种仪式,仪式也是一种传播[6]。赫伊津哈这样描绘中世纪末期西欧社会生活:“即使是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出行、劳作和探亲访友也必然在祝福、仪式、格言和惯例的环境中发生。”[15]1对于中世纪末期的西欧人来说,虔诚态度常常表现在各种仪式和言谈举止中,仪式等礼俗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社会认同和社会秩序的角色,也是日常传播的主要形式。
格尔茨通过对印尼爪哇岛和巴厘岛社会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探索人的行为如何表达意义。他分析爪哇岛一场葬礼仪式,认为“一个仪式并不只是一个意义模式;它也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14]202。他还分析了巴厘岛的斗鸡游戏,通过这种游戏,建构和维系了参与者和旁观者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按照传播的仪式观,斗鸡游戏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传播。
凯瑞的个人阅历和宗教信仰也有助于传播的仪式观的形成。他出生在美国罗德岛州一个传统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从小便成为一名天主教信徒,日常生活中充满各式各样的天主教仪式活动。他没有接受正规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渊博的学识是在进入大学后获取的。凯瑞的青少年时光在家乡浓郁的天主教氛围中度过:每天光顾天主教堂,与神父们聊天,有时随他们向生病的信徒发派圣餐,走访年长者,做通风报信的差使,游荡于当地咖啡店,与退休老人一起读报、谈论政治等等。这段奇特的经历对凯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很多东西都是在这种环境中习得的。这些直接的生活体验有助于凯瑞感悟,通过带有宗教仪式意味的社会(符号)互动活动,分散的人群最终形成了亲密的社区。
据凯瑞的学生昆廷·J.舒尔茨回忆,除了在私下场合,凯瑞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信仰。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2002年《媒介与宗教》发刊辞中,凯瑞说宗教“也许是传播中最被忽略的话题”,对此他深表遗憾和感伤;另一次是同年11月在全国传播学会的小组讨论时,凯瑞公开称:“宗教是我摆脱不了的东西,即便我曾试图这样做……天主教义在我的人生中已经生根。”[16]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古代信仰的世界观已经融入凯瑞的血脉,对他来说,所有的文化和传播活动本质上都是宗教(仪式)。
[附注]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Grossberg,L..The Convers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J].Cultural Studies,2009,23(2).
[3]Pooley,J..Daniel Czitrom,James W.Carey,and the Chicago School[J].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07,24(5).
[4]Strate,L..Understanding a Man in Time:James W.Carey and the Media Ecology Intellectual Tradition[J].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07,24(2).
[5]Packer,J.,Robertson,C..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Essays on Communication,Transportation,History[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6.
[6]Rothenbhhler,E.W..Ritual Communication: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M].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1998.
[7]Munson,E.S.,Warren,C.A..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8]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Dewey,J..Democracy and Education[M].New York:Macmillan,1916.
[10]周鸿雁.隐藏的维度——詹姆斯·W·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11]Duncan,H.D..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Order[M].New York:The Bedminster Press,1962.
[12]Couldry,N..Media Rituals:A Critical Approach[M].London:Routledge,2003.
[13]Grimes,R.L.,Husken,U.,Simon,U.,Venbrux,E..Ritual,Media,and Conflic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4]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5]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M].何道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Schultze Quentin J..Communication as Religion:In Memory of James W.Carey,1935-2006[J].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200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