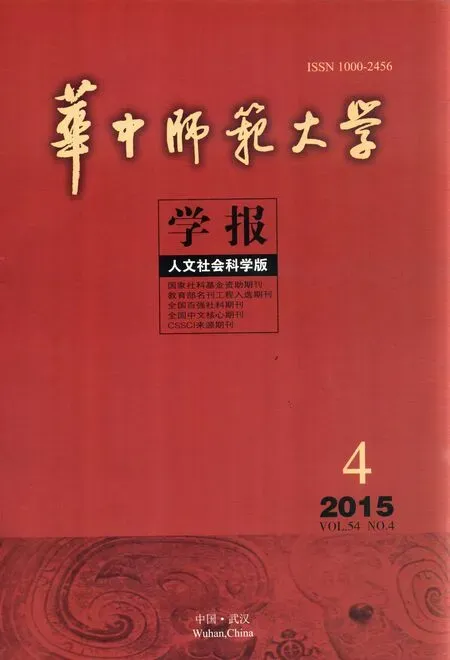“中庸”思维与杜亚泉的“新文化运动”
赵黎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047)
一、“中庸”思维与杜氏“调和”原理
关于杜亚泉及其文化“调和”论,学界已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了充分挖掘,积累了相当多的学术成果。有的文章侧重对“调和”论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新认定,有的偏重于对杜氏“调和”论意涵的重新阐释,有的则注重杜氏文化思想与五四新文化派的比较研究,这些成果为将杜亚泉研究引向深入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追问:杜氏“调和”思维的传统基础是什么?其“调和”后的文化愿景是一种什么状态?如何评价其新文化设想的价值或意义?等等。
近代以来,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文化出路”问题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持续思考的核心问题。面对“古今中外”的深刻矛盾,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均在其思想世界里描绘了各自的“新文化运动”地图,真可谓有一千个知识分子就有一千种“新文化运动”。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正是这无数“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与多数“最后的儒家”一样,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杜亚泉,有意无意地利用传统智慧以解决古今、中外的文化转换难题,杜氏的思路可以作为近代某类人文主义者心目中“新文化运动”的标本。
事实非常明显,杜氏操持的思维武器是多数儒生耳熟能详的中庸之术。何谓中?中,《说文》释,内也,从口。丨,上下通。段注曰:中者,“別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可见,“中”字本意中就含有空间上内外相通和时间上上下贯通的意思。《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可见它又含有中和、持中、合度之意。在传统文献中,“中”也是一个活性很高的搭配字,常见的复合词有“执中”、“时中”、“中行”、“中正”、“得中”,等等。何谓中庸?《尚书·洪范》一段“皇极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其中要义:“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当无偏,王道平平。”庞朴曾这样概括其意指,“正确的坐标既定,左偏都只能是不正确的。这个坐标,其政治术语曰‘王道’,其哲学术语则谓之‘极’。”①在他看来,这里的“极”十分关键,它就是中,意味着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仿佛是一架天平的指针,任何偏离准星的倾向都是错误的。这是作为方法论的中庸的要旨。
《中庸》的地位被历代儒生所看重,“《中庸》,群经之统会枢要也。”②“中庸”的价值,更被儒家所推崇,朱熹曾把它放在历代圣贤所传“心法”的神圣位置。“作为这一心法传承内容的‘中庸之道’……始终被理解为中国文化精神与灵魂的直接阐释……‘中’作为一个关键词或中心词的位置始终被保持着。”③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知识分子,杜氏身上自然被打上“中庸之道”的鲜明烙印。不过,受过科学训练的杜亚泉,却用现代科学知识对中庸之道的合理性进行了别样的解释。
杜氏把物理学上“力之对抗”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认为中庸之说具有充分的科学道理。他说“中”类似于自然界中两种相反力量的冲抵,“宇宙间发生种种之现象,无不有力之存在。不特有形之物质变动离合,受力之支配也,即无形之事功成败举废,亦莫不由力之作用。政治隆替,国家兴亡,悉缘于此。”④在他看来,自然界的规律同样适合于社会界,社会也需要两种势力来形成力量平衡,如此,现代政治中的多党制,政治争斗中若干势力的抗衡,就具有了正面的价值:“顾或谓政治进行,全赖对抗力之作用。有某种之势力,必有他种之势力以相与抗衡;有此方之主张,须有彼方之主张以隐为对待。”⑤同样的道理,这种“对抗”原理也可以移用到文化领域,无限多样的文化形式,需要在一种相互抗衡中寻找共同之点。具体到中国文化选择上,也就意味着要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所以其文化革新的第一个诉求就是在多种文化样态中求“中”。
他进而指出,中庸求“和”的道理,也符合物理学上“调节”原理。他说:“机械之运用,固赖原动力之牵引。然必轮齿含接,干轴贯联,交相约束,互为裁制,节其力之过巨者,调其力之不均者,夫而后力之所向,悉如夫意之所期,成物利用,不竭不匱;不然者,原动力虽如何强大,而轮与轮不密锲,轴与轴不停匀,无节制机以执其中,无操纵轮以均其势,未有不偾事肇祸者也。政治之力何独不然?”⑥他虽承认物理学上“二物不能同时并容于一地”的张力原理,但是他更认定在社会生活领域,两种主义、两个政党相对峙而存在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政治上的“民众主义”与经济上“专制主义”等就是如此,因此他进而得出这样几个“觉悟”,一是“天下事理,决非一种主义所能包涵尽净”,如果对社会没有“至大弊害”,即使几种要严重冲突的主义,也可以同时并存于社会,因为它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之间,收相互提携之效”;二是即使“两种极端暌隔”,但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二者多少具有互补之效;三是主义之争是人为造成的,并非天然如此,本身具有调和的可能。⑦他指出,这种“力之调节”原理具有多方面的现代启示,“一在养成对抗之秩序,一在造成对抗之形势,夫而后可立平民政治之基础,可树政党对峙之模型,故相因而不相背者矣。”⑧这种原理用之于政治革新,用之于文化改良,就是求“和”,在他的理解里,两种异质因素的“和合”状态应该是现代政治文化存在的常态。
最后,他把两种自然原理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认为“中”“和”的结果就是求“多”,就是追求事物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天下事决非一种主义所能包涵尽净。苟事实上无至大之冲突及弊害,而适合当时社会之现状,则虽极凿枘之数种主义,亦可同时并存,且于不知不觉之间,收交互提携之效……凡两种主义虽极端暌隔,但其中有一部分或宗旨相似,利害相同者,则无论其大体上若何矛盾,缘此一部分之吸引,使之联袂而进行,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翕合,即属此理。”⑨此话含义是颇为丰富的,就其主旨来说,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主义”之间,其实并不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其中有交叉关系、有互补关系、有并列关系等,“折中”的目的就是要把具有共性的东西更多地留存下来。
中庸之道的“微言大义”被历代儒生说得玄之又玄,神妙莫测,但站在现代角度其实可以数学或物理学方法进行简化处理。事物的两极如果分别为A和B,“中庸”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两极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A、B既然并非变动不居,其力量的平衡点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中庸的难处在此,妙处也在此。从排列组合的原理来看,两个因子的组排产生的结果一定不止两个,也就是说中庸最后得出的结果既不会是A,也不会是B,更不是AB的简单并置,而是远远多于AB的“第三方”,它可以是A而B,亦可以是非A非B,还可以是亦A亦B,等等。从思维上讲,它讲求的就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了,庞朴说:“中庸的所谓中,就是第三者;承认二分又承认中庸,也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分为三。”⑩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此看来,用中庸之道解决“古今中外”问题,客观上有促进文化选择多样性的可能。杜氏自己也曾明确表述调和论原理及其现代价值:“既知甲说,更不可不知反对之乙说,尤不可不知调和之丙说。盖近世思想发达,往往两种反对之说,各足成立,互相补救者,若专主一说,则思想易陷于谬误。”⑪显然,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二、“调和”之客体及其三种调剂形式
儒家中庸之道,向以解决矛盾为能事,庞朴曾将其效果概括为:“把对立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以此之过,济彼不济,以此之长,补彼之短,在结合中追求最佳的‘中’的效果。”⑫他认为中庸的A、B两极可以演绎为四种形态,即“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⑬,因此它的价值在于提倡以多抗一,和合包容,反对非此即彼的绝对二分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充满了辩证智慧的多元化思维形式。杜亚泉显然深谙此道,他把这种思维智慧用之于文化矛盾问题,为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等文化难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路。概括起来,他提出了对有关客体对象的如下几种调和形式:
一是以A补B型,此型主要适用于东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处理。为避免抽象谈论文明和进行文明比较,杜亚泉首先给文明下了一个具体的、相对的定义,认为文明必须“合社会之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而言之”,它是特定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状况与道德状态综合作用的产物,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必须有一个相对的、历史的尺度,不能把不同经济与道德状况下产生的文明放在一起强分轩轾。“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⑭在他看来,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发展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东方文明之经济是为满足人们“生活所需之资料”,而西洋文明之经济则是为满足“生活所具之欲望”;同样是满足,一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资料,一个是为了填满无限的欲海,欲壑既然难填,于是发展科学,想尽一切手段,开发出令人目眩的物质文明。这是两种文化产生经济背景的不同。而从道德方面言之,他坚持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动静虽然各有利弊,但以“力行”精神为核心的西洋文明,在近代化进程中逐渐优胜于中国文明。“十九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更由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与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奋斗主义、活动主义、精力主义,大而张之,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其尤甚者,则有……战争万能主义。”⑮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也有“重力行而蔑视理性”的天生缺陷,这种不足只有用素重理性的东方文明来弥补才能得以完善。他曾用了一系列生动比喻来描述这种互补关系,“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当以水及蔬疗之也。”⑯
二是以A济B型,这主要适用于“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处理。近代以来,中国曾因遭受列强欺凌而引进列强先进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这种反应也是自然的,但在杜亚泉眼里却产生了另外一种消极效应,那就是使中国也走上了一条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不归路。他把晚清以来人们奉为圭臬的“富强论”和“天演论”,统统划归为“危险至极之唯物主义”范畴,认为在这个“主义”的支配之下,“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⑰他认定“唯物主义”的危害在于,激起人类的竞争心、刺激人类的物质欲、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等。那么,如何解救人类?他以为根本在于用“精神主义之新唯心论”加以调剂,而这种主义的要义就是“理性”与“社会的感情”⑱。
当此之时,他亮出了自己的调剂武器,要用“适当的制裁”,平息这“爱与争”:
人苟有所爱,必有所争,此欧人所以有生存竞争之说也。如欲无争,惟有无爱,此释氏所以传爱根清静之旨也。然弱肉强食,既非人性所安,舍身饲虎,又非凡夫所愿。争既不可常,爱亦不能割,则奈之何?曰欲驰其争,宜平其爱。例如名与利,人之所爱也,则有权利义务之制限焉;好色,人之所爱也,则有一夫一妇之规定焉。是皆所以制裁其爱,使不得充分以逾其量。爱不逾其量,虽不能持此以息天下之争,然争亦可稍辑矣。⑲
其“制裁”物欲的武器,显然就是以“适如其量”为分寸的中庸之德,这种中庸之德曾被杜亚泉称为一种“理性精神”,“孔子言理性,叮咛反复于中庸之为德”。⑳在他看来,这种理性精神的特征是“和平中正”,它“本乎生理之自然,与夫心理之契合,又益之以外围时地之经验,遂形成一种意识”,因而具有广大的“势力”,它小而言之可以“应付事物、范律身心”,大而言之可以治国安邦平天下,“凡人类之各遂其生活,社会之获保其安宁,非仅恃乎军队之保障,政治之设施,法令之诏示,刑赏之劝惩已也,赖有理性焉,为之主宰是而纲维是。”在杜氏的理解里,这种中庸之德本身就是中国“精神文明”的一部分,依靠它可以弥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唯物”偏至之失。
三是A、B相因型,主要用于“新旧”或“古今”关系的处理。关于“新旧”之关系,杜亚泉曾以“新我”“旧我”为喻做过生动阐述:“吾人之所谓我,即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及将来之我,相接续而成者。故昨日所发之言,今日践之,昨日未竟之事,今日成之,此现在之我,对于过去之我,所当负之义务也。”在他看来,新与旧的关系是暧昧不清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逐渐递嬗的关系,“故新旧递嬗之间,其由两方对抗竞争,一方渐绌,一方渐伸,而后取而代之者,历史上虽不无其例,而其多数则常由旧者之多行不义,至于自毙,新者乃得有自然之机会,起而承乏其间。”具体到文化领域,新旧相因就不能不是演化发展的常态,“文明之发生,常由于因袭而不由于创作”,变革的前提是继承,没有继承也谈不上变革。
他因而坚持,新旧差异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曾以戊戌时期到五四前后文化演变为例,证明新旧的这种历史性和相对性。戊戌之时,新旧所指非常明确,“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然而经过数年的时势变迁,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现代文明在现时已无维持之法”,“中国固有文明……根本上与西洋现代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东西文化的差异性在日益减少,“新”、“旧”的情形发生了不小的位移,“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而在另一方面,西洋、东洋与中土,各种思想在相互碰撞中也逐渐渗透融合,很难再分出中西新旧,“吾国民之所谓新思想者,岂能脱离其固有之东洋思想,惟吸收几分之西洋思想而已。而所谓旧思想者,又岂能全然墨守其固有之东洋思想,以排斥西洋思想?”要之,新与旧是相互渗透的,是陈陈相因的,需要用以新调旧的办法逐渐转化旧事物。
三、“调和”主体及其三个“主义”
客体是主体施行的对象,上述A、B两种客体的相补、相济、相因,因而也就不是两个客体的自然并置,而是主体有意图的文化行为。具体到“古今中西”关系,杜亚泉坚持主体应该为“我”、为“今”,客体应该为“西”、为“古”。首先,输入西方外来文明,必须以中国固有文明为根底,相合处则纳之,凿枘处则修之,“救济之道,正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同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线索,一以贯之。”以中国文明为红线、以西方文明为散钱,这个比喻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施受关系。他甚至把这种以我为主、统筹其他的特征,视为“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若何之摧毁,已示世人以文明统整之可以成功”,并倡言要把这种消化异质文明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其次,处理新旧问题,必须站在“新”的立场,对“旧”的因素加以扬弃,“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所谓“刷新”,当然是主体有目的有选择地更新。此外,他还系统阐述了如何用“精神”的手段,实现“经济”的目的,“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用“科学的手段”、“力行的精神”,来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方法手段是外“借”的,目的结果却通向自我,这里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明了的。
杜亚泉以中庸思维处理中国的现代性难题,提出了不同于复古派也不同于西化派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实施方案,提出了中西转换中的以中化西原则和古今转化中的以新化旧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可以用三个“主义”来概括:一是“协力主义”,它是一种综合协调的艺术,涉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精神与物质等各种关系的平衡,“农业国与工商国,为物质上之协力;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为精神上之协力。一方面发展自国之特长,保存自国之特性,一方面确守国际上之道德,实行四海同胞之理想,则所谓国家的和平主义是矣。”
二是“接续主义”,它主要涉及政治文化新旧关系的处理。杜氏曾对“接续主义”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全面阐述:
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所用其接续乎?若是则仅可谓之顽固而已。夫使吾侪之先民,不为吾侪谋开进,则吾侪今日,犹是野蛮之国、狉獉之民耳。今日之国民,既享用前代所遗留之文明,则开发文明,实所以继承先志。……故欲谋开进者,不可不善于接续。
他不仅主张把这种“主义”推广到个人、家庭、团体等各层面,还提议将其运用于文化、教育、道德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如何才能在文化实践中这种新旧“接续”呢?他以新旧道德转换为例进行了说明。他不认为新旧道德冰炭不容,反而认为旧道德中含有不少与民主共和兼容的因素,因此“实无根本改革之必要”。在他的分析里,道德有“体”有“用”,是体用的复合体,“体不可变而用不能不变”,“变”些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变其不合时宜者一二端可已”,具体而言约有三件,一是“改服从命令之习惯而为服从法律之习惯”,二是“推家族之观念而为国家之观念也”,三是“移权利之竞争而为服务之竞争也”。
三是“多元主义”,这是前两个主义的自然结果。如前所述,杜亚泉秉持的中庸之法,本身包含有反对非此即彼简单思维的朴素辩证法精神。庞朴先生曾将中庸的结果概况为四种状态,“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争于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这说明,“中庸之道”追求的既不是“此”,也不是“彼”,而是彼此排列组合后的无限“多”,包含的是一种对二元对立思维有着天然抵制的多元主义精神。杜氏对这种多元主义有着清醒的自觉,“世界事理,非一种主义所能包涵,且知两矛盾常有类似之处,而主义又或随人事时代而转变,则狭隘褊浅主奴丹素之见,不可不力为裁抑。”为了实现多元主义的文化鹄的,他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两种不良倾向,其一是动辄排斥异己的独裁主义倾向,“世界事理,如环无端,东行之极,则至于西;东行之极,亦至于东。吾人平日主张一种之思想,偶闻异己之论,在当时确认为毫无价值者,迨吾所主张之思想,研究更深,而此异己之论,忽然迎面相逢,为吾思想之先导。”二是唯我独尊的极端主义倾向,“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世界事理,无往不复,寒往则暑来,否极泰生……社会之成立,由利己心与利他心对抗调和之故。故不明对抗调和之理,而欲乘一时之机会,极端发表其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祸乱者也。”在他看来,只有用理性的态度,经过冷静的比较,将相互矛盾的两种主义放在一起,求其同而存其异,才能达到“永久和谐”之境界,“对于相反之主义,不特不宜排斥,更当以宁静之态度,研究其异同。夫如是,则虽极矛盾之两种主义,遇有机会,未必终无携手之一日,即令永久不能和谐,亦不至相倾相轧,酿成无意识之纷扰也。”显然,杜亚泉的中庸思维里面含有丰富的现代思想质素。
四、杜氏“新文化”思想的价值及问题
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期,由于世界观不同,方法论各异,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各有自己的“新文化”设想,杜亚泉的“新文化”设计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客观讲,它深受儒家思维惯性的濡染,是一个偏于守成的文化改良方案,因此对此持同情态度的往往是那些文化上趋于“保守”的知识群体,如国粹派、甲寅派、学衡派等。在这些人眼里,经过“调和”处理的“新文化”愿景,既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文化,又不是生吞活剥的西方文化,而是将古今中外因素充分化合后产生的“第三种文化”。显然,这种文化并不是不分主次的杂拌,而是以我为主、化古化欧的积极“拿来”,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时代特征。应该说,这种文化愿景和变革策略,与全盘西化等激进现代性方案相比,也显得更为理性和务实。这些改革思路,即使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不小的启迪价值。
而在思维方法上,杜亚泉用现代科学眼光,解释中庸思想的合理性,并将之运用于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无疑是对中国思维传统的一次更新,也是中外思维形式的一次对话和嫁接。他提出的处理中外、心物关系的“协力主义”,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接续主义”,以及处理思维问题的“多元主义”等等,不仅包含了丰富的辩证因素,也含有开放包容的现代意识。他提出的文化观念,对新文化派的文化观念而言,是一次有益的对话和补充;其所采用的稳健建构策略,对五四新文化派激进文化遗产,未必不是一种必要的纠偏和匡正。当今之世,新文化前驱所设想的美好愿景并未最终完成,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新文化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更为丰富,不但要面对“古今中外”问题,还要面临两种新文化思路的整合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杜氏善于利用传统智慧、整合各种资源的“调和”思想,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
在今天看来,杜氏的“文化调和说”于情于理并无什么错谬,为什么其在近代中国却遭遇了被冷遇的命运呢?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厘清,然从儒学方法论的角度讲,这恐怕也是不能得“时之中”引起的,也就是说是其对中庸之道的使用出现了偏差。任何思想的价值都包含时代与超时代两种因素,按照儒家辩证法,超越历史与拘于历史一样,均非“时中”表现,故未得中庸真味。可惜的是,中道思想融进血液的杜亚泉,在文化改良实践上并未真正进入儒家境界。从超历史的角度而言,杜亚泉的文化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旦临近到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接踵而至了。近代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是中庸思想已经蜕变,成为一种阻碍历史变革的惰性力量。鲁迅说在中国要想开窗,必先喊推墙;胡适说在中国要做五十步改革,必先提出一百步设想,这些话虽是谑语,但多少道出了近代的现实。晚清以来,各种改良不绝如缕,但因始终严守中庸之道,致使改良限于局部修补,始终未见大的起色。不仅如此,旧势力占尽先机,反将新因素销蚀殆尽,因此直到五四先驱才有“思想革命”的“最后觉悟”。他们终于发现,“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也,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折中主义”看阻碍文化变革的主要因素,甚至当作比顽固派更为危险的东西,“折中二字,是新旧杂糅的代名词,就是把旧材料用新法制组织的代名词,或是旧材料新材料并用的代名词,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上最流行的思想和主义。”反对讲究妥协、调和,反对新旧杂糅的“灰色革命”,以免革命成果被折中主义断送。“人们对于社会上的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发现了它的毛病,非‘改弦而更张之’不可,那就应该明目张胆地鼓吹革命:对于旧的,尽力攻击,期其破坏,消灭;对于新的,尽力提倡,期其成立,发展。这才是正当的行为!”所以在旧因素有着巨大历史惯性的条件下,一味讲折中,因为新旧因素的过于悬殊,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新不仅不能平衡旧,反而可能被旧的东西吞没。所以新文化派提出,“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是很有道理的。
杜氏对“中”的把握也有失准确。按理说,中庸之道的“中”,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地变了,情势变了,天平两边的事物也变了,两极之间的准星即“中”,当然需要进行及时调整。两极已变,而准星不变,这就不是“中”,而是一种“偏”了,这是中庸的微妙之处。所以传统思想不仅强调“时中”“适中”,而且强调“权变”,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有人对此加以发挥道,“执中而不知随时权变,反而等于固执一偏;因权变而时执一偏,倒是真正的用中……是孔门为学之道的顶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凡事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可刻舟求剑、固执一偏。在杜亚泉时代,“中”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实践证明,新的力量太弱小,旧的势力太强大,“中庸”已经抵挡不住旧势力的冲击,“中”的方法只能给旧势力造成更多空间,“进化的公例,总是新的胜于旧的,这一层,他们都未想到,一味地折中调和,得过且过。”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洪流般的革命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派对折中论调的批判是击中要害的,“不问时势之适否,不问事理之是非,而惟持一中立调和之态度,成则居其功,败则不任其责。其所主张,虽或有近于是者,然要皆折中两间,非自心之确有所见者是也。”包括杜亚泉在内的折中派受到新文化派的猛烈抨击是可以想见的。
杜亚泉文化思想还有一个不能周延的矛盾,一方面他承认,某种道德文化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若夫新道德之特色,则无习惯团体之障碍,故人民得以自由发展其理想,完全使用其知识,日新月异以合乎社会之进程。是说也,未尝无充分之理由。特其所陈,多以欧西社会为根据,与吾国状况,微有不同。”然另一方面,却也认为在不根本改造文化土壤的前提下,照样可以用中庸之术对之进行切分和平衡。这就有一点耽于妄想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看得透彻,也来得彻底,“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也就是说,要想建立现代道德,必须先把阻碍新道德生长的文化土壤除掉,不破不立,非如此不足以建设新文化。“旧者不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五四新文化先驱这席话不免有些绝对,但确实击中了近代中国文化变革难题的要害。
另外,和其他折中论者一样,杜亚泉也认为中国向以“精神文明”见长,西方以“物质文明”为胜,并从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西洋文明“显著之破绽”的结论,进而产生“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之类的文化自信,最后誓要用中国的“精神文明”之胜弥补西方“物质文明”之失。这就更是一个淆乱的认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既非东西方所专,也非中西方所长,按照胡适的话说,一切文明里面都有物质和精神两种成分,一只蒸汽锅炉、一部摩托车,里面包含的复杂精细的智力就是精神的部分,所以他批评折中论者为“有夸大狂的妄人”,此话虽显尖酸刻薄,但也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既然对中庸的两极子虚乌有,那么一切所谓“调和”“救济”也就无从谈起了。
注释
②[宋]黎立武:《中庸指归》,《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0册,第718页。
③陈赟:《中庸的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7页。
④⑤⑥⑧高劳:《力之调节》,《东方杂志》13卷6号,1916年6月10日。
⑭⑯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3卷10号,1916年10月。
⑰⑱伧父:《精神救国论》,《东方杂志》10卷1号,1913年7月1日。
⑲高劳:《爱与争》,《东方杂志》13卷5号,191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