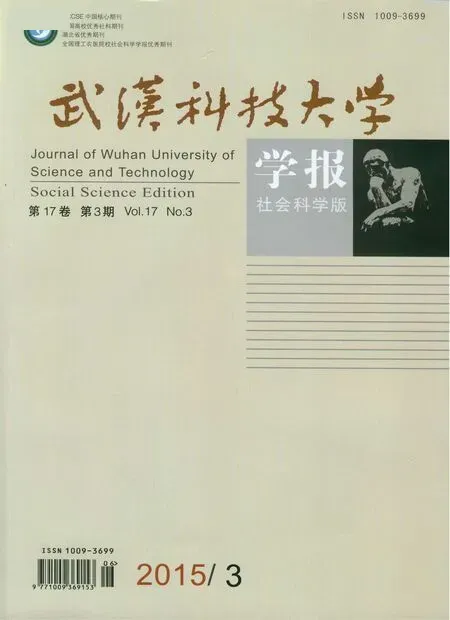《管子》“天道人情”中的职业伦理思想研究
孙 长 虹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管子》“天道人情”中的职业伦理思想研究
孙 长 虹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管子》认为职业分工是“天道”和“人情”所决定的,实质是把职业分工看作是不同道德禀赋的结果,赋予职业分工以道德上的因果联系,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统一。“天道人情”既承认职业之间的差别,又强调各种职业的不可或缺性,是一种有机的职业分工伦理。在职业劳动上,《管子》不仅强调道德的作用,还强调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命令以及经济手段等多种方式,促使人们履行职责。《管子》注重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体现了对人性和道德规律的深刻洞察,对当代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管子》;天道;天道人情;职业伦理;职业分工;道德
在人类发展史上,职业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职业伦理思想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生产与发展。在我国传统社会,由于家庭(或家族)同时作为职业共同体存在,因而,职业伦理往往与家庭伦理、政治伦理交织在一起,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管子》一书被罗根泽誉为“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1],其中蕴涵着比较完整丰富的职业伦理思想,深入发掘《管子》中的“天道人情”思想,探讨其中的职业伦理蕴涵,对今天的职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天道人情”中职业分工的伦理内涵
(一)“天道人情”为职业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
《管子·君臣下》云:“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在《管子》看来,神异圣明的人做王,仁义睿智的人做君主,威武勇猛的人做官长,这既是天经地义,也是人之常情。《管子》认为人的道德禀赋在职业分工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才能、道德水准的人应该担任不同的职位。并且,“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管子·君臣下》),天道和人情是确立君臣上下的职分以及礼制的依据。《管子》为职业分工以及等级制度寻找到了神秘乃至神圣的支撑,即“天道”;把职业分工看作“物之理”,上升为自然律,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传统天命观在职业分工上的体现。它同时主张分工要符合“人情”,把神秘的“天道”与世俗的“人情”联系起来,强调二者在作为职业分工依据上的内在的一致性。《管子》的这种观点与古希腊柏拉图主张的德性与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的对应有异曲同工之妙。柏拉图认为德性主要包括智慧、正义、勇敢和节制四种,智慧、勇敢和节制分别对应的是君主(统治者)、武士、平民,认为不同职业或地位的人应该有不同的道德德性,正义是贯穿于各个职业之中的。这种中西方职业分工上道德要求的不谋而合,说明随着文明的发展,不少思想家都已经看到不同职业应该有不同的道德要求。
《管子》强调天道,体现了传统的天命思想。传统天命思想并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以德作为基础,天人合一思想中最关键的是天人合德。“天道人情”中职业分工上的道德依据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它摆脱了没有因果必然性的随机性、偶然性,把职业分工以及等级地位看作是不同道德、才能禀赋的结果,赋予其道德上的因果联系,这种导向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传统社会的人才选拔标准,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天道人情思想中,一方面,通过“天道”赋予职业分工以超越性的来源,为人们确信并遵守提供一个超验的依据;另一方面,强调“人情”符合并引导人们关于职业分工朴素的认识和理解,为人们遵从职业分工、安分守己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可能。正是由于职业分工上的道德要求,天道的神秘性与人情的世俗性结合在一起,既合乎天理,又合乎人情,具有了合理性的蕴涵。从根本上看,注重道德要求,乃是更注重人情的表现,虽然《管子》为其职业分工找到了天道作为支撑,但是,其落脚点是人情,在超越性与世俗性的关系上,更注重世俗性,超越性是为世俗性服务的。《管子·轻重丁》云:“此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可以看出《管子》对神秘的天道之类事物的看法,是以其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来利用的,体现了一种功利主义态度。在《管子》看来,超越性或神圣性的东西只是为现实的东西提供形上的依据,提供终极的前提或理由,在实践中则专注于世俗的功用,往往把这种神圣的来源给抛开了,这样,就从神本转向了人本,这也是我国传统思想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二)《管子》中的职业分工体现为有机的职业分工伦理
马克斯·韦伯第一个把“有机”的概念应用到伦理上。他认为,在某些宗教看来,职业分工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构成部分,对于基督教和印度宗教而言,“种种职业或种性莫非神意所定,而且每一种皆被赋予某些神意或非人格性之世界秩序所指定的、特定且不可或缺的使命,因此,每一种职业也都承担了不同的伦理义务。准此理论,职业与种性的分化可拟之于一个有机体的各个构成部分。以此方式出现的各种权力关系即被视为神意所定的权威关系。准此,任何对这些权威的反抗或甚至大声疾呼地要求(除非出自那些具有适当身份者),皆被视为违逆神意,因为这些行为代表了被造物的自大与傲慢,是会摧毁神圣的传统的”[2]。韦伯认为某些宗教理论为现实的职业分工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在基督新教中,由于职业分工被赋予了上帝的权威,从而产生了职业平等的观念。韦伯认为儒教伦理中并没有“有机”的职业伦理思想,而是一种纯粹人格性的特征。
其实,《管子》也是把职业分工放在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环境中看待,只不过,在《管子》看来,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有所不同,重要性也不同,比如《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在《管子》看来,不同等级或职业的人在有机体中的作用不同,君主相当于人的心脏,具有更关键的作用,这样,基于有机体各个部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职业之间并不一定是平等的关系,即不同职业的重要性也不同。虽然如此,但并不妨碍《管子·小匡》中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把士农工商等职业看作国家的基石,认识到不同的职业劳动对于社会的不可或缺性。
《管子》朴素地看到了职业劳动的重要性。《管子·揆度》曰:“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当然,这句话的最早出处不是出自《管子》①在《吕氏春秋》以及《淮南齐俗训》中记载为神农之语,说明《管子》之前已有此语。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89页注释)。,《管子》引用此语说明对这句话持肯定赞赏的态度,这表明《管子》朴素地看到了个体劳动哪怕是最卑微、最普通的日常劳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虽然看到了日常劳动的价值,但是《管子》的职业分工是以承认等级差别为前提的,并不认为不同的职业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管子》没有赋予不同的职业以同等的地位。
当然,相对于印度宗教的各个种性之间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管子》从“天道人情”出发,认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这种思想其实在本质上已经打破了等级的命定观念,蕴含着不同等级之间相互流动的逻辑可能性,特别是为较低等级的人向较高等级流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具有卓越才能和道德禀赋的人确实有成为“士”的可能,《管子·小匡》记载,农之子弟,“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农之子弟优秀者理论上是可以上升为士的,并且确立了举贤制度,“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管子·小匡》)。《管子》尚贤选能,为有德行和才能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现实路径。这种流动性使得整个社会的职业分工更像有机体,其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交流、沟通和流动。在传统社会里,下层向上层的层际流动渠道始终存在,一方面,这种流动具有伦理性,为具有卓越才能者提供了一条上进之道,体现了一种公平合理;另一方面,层际流动缓解了社会各个阶层主要是上下阶层之间的紧张,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天道人情”与西方基督教中的“天职”观念比较类似
在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天职”观念,也是把职业分工的依据追溯到神秘的力量,即上帝那里。“天职”观念是在宗教改革中首先由马丁·路德提出的,马克斯·韦伯对其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阐述。他认为,“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3]。与世俗的职业观相比,新教的“天职”观念不可避免带有超越色彩,即职业劳动超越了谋生的高度,成为上帝许可的唯一的存在方式。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任何职业都具有伦理内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世俗社会中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增添上帝的荣耀,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这样,不仅产生了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而且还形成了高度自律的道德履行方式。但是,它面临着假如上帝不存在,道德如何可能的根本性困境。
与西方基督教“天职”观念相比,“天道人情”思想虽然有宗教性,但是并不强烈,它更注重职业劳动的工具性价值。在职业劳动中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中实际上往往把超越性的东西给抛弃了,注重的是职业劳动的世俗价值和意义。
二、“天道人情”观念下职业道德的履行
《管子》既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也不忽视经济、政治、法律和行政手段在职业道德履行中的作用。也就是说,《管子》既注重道德自律,也强调道德他律,它采取的是多管齐下的方针,促进职业道德的践履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谐。其中,对下层体力劳动者它更注重他律,对上层统治者则强调自律。
(一)《管子》强调对职业劳动者加强管理和约束,提出了“四民分居”思想
《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一方面,《管子》主张让人们保持淳朴的心智,有利于听从政府的命令,专心劳动,安伦守分;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家庭共同体来学习职业技能,约束人们履行职责。《管子·小匡》又云:“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在《管子》乃至整个传统思想及社会中,家庭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场所,也是职业技能及职业道德养成的重要场所。家庭(或家族)既是建立在祖先崇拜基础上的宗教共同体,也是建立在权利和责任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并且,经济、政治、法律上的株连措施,把家庭成员紧紧捆绑在一个责任共同体之内,家庭的这种共同体性质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利益休戚相关,成为一个统一体。在传统社会中,实行家长负责制,每个家庭的家长是人格化的责任主体,家庭成员都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都是责任主体的一分子。这种以家庭为主体的责任方式类似于有机体,每个部分都对整个有机体负责,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功能替代作用,有机体的一部分出现问题,绝不会造成系统的崩溃,其他部分会代行其职责。与此类似,在家庭统一体中,也形成了责任统一体,绝不会出现机械的责任方式,即个人只负责自己的那部分,别的部分出现了问题却置之不理,更不会出现无人负责的情况。因而,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共同体乃至统一体这个责任主体,更类似于有机的责任伦理,而不是机械的、直线性的责任对应方式。
(二)《管子》强调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命令以及经济手段等多种方式,促使人们安心劳动、履行职责
《管子·版法解》云:“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所谓三器,就是号令、刑杀、禄赏,《管子》主张用行政命令、法律手段以及经济方式治理国家。《管子·轻重丁》中记载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五衢之民,衣衫褴褛,桓公问计于管子,如何使帛布丝絮之价格下降,管子的计策是把路旁树枝砍掉,使没有树荫,从而使五衢之民不在路旁嬉笑闲谈,而是回家去耕田织布,行令不到一年,物价真的下降了,百姓也有衣服鞋子可穿了。由此可以看出《管子》灵活采用各种方式对过多的娱乐玩耍进行限制,其目的是促进社会生产,使民众富裕起来。在《管子》看来,民富则国强,政治统治者不是要搜刮百姓,而是要让百姓生活富裕,这样才能有利于统治;政治统治和民众利益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关系。这既体现出《管子》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管子》高明的治国理念,这种观点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蕴含着深刻的真知灼见。
运用各种手段促使人们辛勤劳动,表明《管子》看到了权威在职业道德规范中的重要性,道德必须被赋予权威,否则,职业道德就会成为奢侈之物。权威可以通过外在的经济、法律、制度等手段予以保障,但是归根到底,权威还是应该来自于规范内在的合理性,因而,《管子》非常注重权威的内在性,即注重命令的合理性。
与孟子、荀子等诸子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点不同,《管子》并不空谈人性善恶,而是从“人情”,即从人性之趋利避害出发制定命令,使人们遵循命令。《管子·禁藏》云:“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形势解》又曰:“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因而《管子》主张制定命令要从“人情”出发,符合人欲利恶害的需要,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和遵从。“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民之所恶也。……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管子·形势解》)。可以看出,与空谈“德性”的儒家传统观念不同,《管子》超越了抽象的人性善恶二分法,深刻地看到了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注重对人趋利避害本性的引导,有利于实现其规定的职业道德要求。
在《管子》看来,人们进行职业劳动,履行职业职责,更多的是出于自利观念,因而不必对其奢求、奢谈利他观念,而应该赋予其职业劳动以合理性。《管子》从人情出发,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等有形的制约手段来保障职业道德的履行,这种职业道德实现方式无疑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实效性,与西方的功利主义非常类似。
(三)从“天道人情”出发,《管子》强调上层统治者的道德自律
《管子》特别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认为君主的德行是实现统治的必要条件。《管子·心术下》曰:“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认为君主必须要公正无私地治理天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管子·君臣下》云:“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认为君主有德行,就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德行成为实现其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体现了传统的德治思想。《管子》强调君主道德的自我修养,预设了君主有道德反省的能力,这表明《管子》主张和注重精英伦理,这也是传统思想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同时,《管子》看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正相关的关系。《管子》认为,上层统治者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责任,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比起普通民众重要得多,因此,对他的道德要求当然比普通民众高得多。上层统治者应当具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一点无论在什么社会中都是合理的。上层统治者作为社会政治、文化中心的标杆,其行为具有典范作用,其对道德的侵越,影响不仅仅是在其职业群体内部,更会对全体民众的道德情感造成侵害和不良影响。《管子》看到了这些,无疑具有合理性,不过,在上层统治者的道德实现上,《管子》主要强调依靠其自身的道德反省,对于君主而言,整个国家都是自己的,加强道德修养有利于统治,明君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有可能身体力行,而昏君则未必。《管子》过多地把道德实现寄托在君主自身,预设了道德主体自省的能力,忽视了道德主体的差异性,无疑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因而这种道德实现方式并不具有可靠性,是或然的、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四)加强对下层体力劳动者的教化
虽然《管子》强调上层统治者的自律,下层体力劳动者的他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忽视对下层体力劳动者的道德教化,相反,《管子》非常注重他律与自律的结合。《管子·牧民》云:“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把礼义廉耻看作是国家的根基,高度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管子·权修》云:“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主张通过教化使社会规范成为人们认可和遵守的习俗,一旦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
在关于下层体力劳动者的道德教化方式上,《管子》特别注重上行下效的道德教化方式。《管子·法法》云:“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认为人民是以君主作为行为的榜样,在上位者,必须要修德,以身作则,做好榜样,才能起到好的示范作用。通过上行下效的教化方式,教化成俗,潜移默化,使人们遵守道德要求和君主命令。如若君主没有德行,则上行下效,礼义尽失,则影响到统治者的政权安危,正如《管子·形势》云:“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管子》这种上行下效的教化观点,建立在预设君主的道德自觉能力基础之上,认为其天然具有道德禀赋,而下层劳动者则缺乏道德自觉性,仅仅是从“人情”出发的一种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可以通过引导而遵从道德的要求。这种观点与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强调在上位者、君子的道德主导作用,认为劳动者处于道德追随地位。
《管子》注重上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的道德修养要求,对下层体力劳动者则强调因势利导、上行下效,这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社会需要。涂尔干认为:“在低级社会中,因为社会组织都非常简单,所以道德就具有同样的特征;与此相应,对纪律的性质进行清楚明确的阐释,既没有什么必要,甚至也不可能。道德行为这种同样的简单性,很容易使它转变成习惯,并机械地实行;在这些条件下,上述自动形成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困难。”[4]同理,我国传统社会中,因为社会分工十分有限,生产方式简单机械,所以职业道德要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职业道德要求也就十分简单,只要去做就可以了,农民努力耕田,手工业者努力做工,士兵作战勇敢就足够了。因而,传统职业道德理论并不复杂,道德规范相对简单,比较容易转化为习惯,或者说较容易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并机械地实行,因而,对下层体力劳动者来说,职业道德的履行并不复杂和困难。而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由于其权力和职责的广泛性、重要性,其行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因而对其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也是符合其职业特点的。
三、结语
《管子》的“天道”为职业分工寻找到了神秘的来源,同时又立足于“人情”,注重对人性的因势利导,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和约束人们安伦守分、努力生产,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从而能够辅佐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功。
与宗教道德相比,《管子》中的宗教性比较淡薄,不过,在管子执政时期乃至后来传统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却没有出现整个职业生产领域道德失范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管子》对不履行职业道德的人实行严厉打击。《管子》主张“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子·乘马》),对缺乏职业基本道德素质的人限制其从事这一职业的权利;强调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以及道德教化等多种手段,规范劳动者的职业行为,因而,人们往往不敢违反职业劳动要求。其次,“四民分居”形成的是“熟人社会”以及“熟人伦理”,造假的成本和代价太高,使得人们不愿造假、不敢造假、无法造假。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有很强的地域性,形成的是“熟人伦理”,职业伦理也包含在其中。“熟人社会”中,造假容易被发现,一旦发现,信誉随之扫地,甚至失去安身立命之所,代价太大。对职业的责任感也就是对熟人的责任,不管是从情感出发,还是基于再生产的考虑,遵从职业道德要求成为一种习惯行为乃至习俗。再次,“四民分居”乃至整个传统社会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单位,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主人翁意识,都是责任主体,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责任伦理,对自己的产品具有很高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意识甚至使得生产者关心自己的声誉甚于自己的生命,主观上不存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条件。
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道德失范状况令人堪忧,毒牛奶、毒馒头、地沟油、毒胶囊等安全事件频频爆发,审视传统、面向世界,大力推进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实现职业生产领域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职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责任机制,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对人们的职业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而这正是《管子》中所多次强调的,是其职业道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管子》中的很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职业道德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1] 罗根泽.管子探源[M].长沙:岳麓书社,2010:3-4.
[2]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81.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4.
[4] 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1.
[责任编辑 彭国庆]
2014-08-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3AZJ001);福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一般项目(编号:2014B008).
孙长虹,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B82
A
1009-3699(2015)03-028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