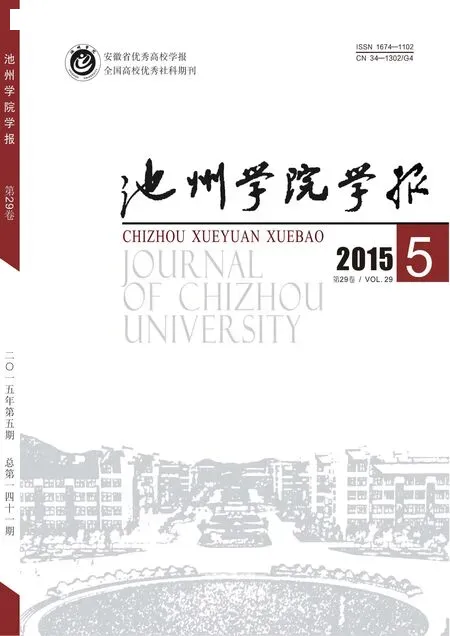明清徽州胥吏与宗族社会——以家谱为中心的考查
程源源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明清徽州胥吏与宗族社会——以家谱为中心的考查
程源源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胥吏是中国封建时期长期存在于官场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胥吏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缺乏有效监管使胥吏操权柄、谋私利的情况非常普遍。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强大,宗族通过家谱中的凡例、家规家训等,极力反对胥吏为非作歹;同时,对“良吏”充分褒扬。宗族的压力使徽州胥吏任职表现较好。对明清徽州胥吏的探讨,有助于认知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
[关键词]明清时期;胥吏;宗族
胥吏制度作为古代官僚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明清时期,一方面胥吏的权力扩大,“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皆付之胥曹”[1];另一方面,对胥吏的歧视也日益加深。关于明清胥吏的研究,大多都是在探讨“胥吏为害”这一方面,本文从徽州家谱资料的记载入手,对徽州的胥吏作一考查,并探讨宗族控制与胥吏任职表现之间的关系。
1 关于徽州胥吏
胥吏地位卑微胥,指的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押解官府物品的杂事;吏,指的是在官府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负责文书事务,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文案工作。他们没有特权阶级的社会地位,但明清时却有很多人愿意做胥吏。因为做胥吏有诸多好处。首先,作胥吏就可以免除自身的其他种种差役,获得一个免役的权利。其次,胥吏的社会地位毕竟要高于一般百姓,更重要的是,胥吏可以收取“例费”,按不成文的陋规,胥吏每干一件稍涉钱财、或由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要从中得到点好处,算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手续费”。再次,胥吏毕竟是步入特权阶层的一个门道,明朝规定,胥吏在服役供职一定年限后,经考核无过错,即为“考满”,可获得作官出身。
赵吉士在《徽州府志·吏才》里说到:“若吾乡则殷实之家借以庇风雨,计其上下班役之期,糗糧而往往惴惴焉,惟恐有意外之失,而巨豪大蠧绝未有焉,其或邀半绾之荣者,恶可以不忘之。”也就是说在徽州充任胥吏的,大多都是殷实人家,借此躲避赋役,作恶多端的胥吏是非常少见的。
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中,对徽州胥吏不为大奸的原因有说明:“书吏操纵之弊,是处皆然,徽俗则否。充是役者,大都钜姓旧家,藉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前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滑,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2]。殷实之家的成员往往为了获取社会地位、保护家财、逃避徭役等目的而充胥吏。他们由于本身家庭富裕,不以获取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徽州胥吏没有“大憝巨滑”,不是因为其本身良善,而是因为徽州聚族而居,宗族势力强大,为奸作恶之徒,不能容于乡里。
2 胥吏在家谱中的形象
2.1以警世的形象出现
《吴越钱氏七修流光宗谱》中:“子弟一入衙门,其心术即化为枭獍,其行径即化为鬼蜮,以祖宗父母之身而效奔走于呼叱,受辱于鞭笞,可痛孰甚焉耳。其人方哆然自视为得意,舞弊挟诈,见事生风,倚三尺之威以恣其渔獐,敛万人之怨,莫厌其贪婪,即使其乘强横之运,以暴致赢余布旅,踵而灰飞烟减,造物之于此辈报应甚显且速,必然之理也,上堕累世之门户而汙玷于祖宗,下遗无穷之罪孽而降殃及孙子,人世之大耻大辱孰有甚于此者乎,若夫习优伶之为下流,投营伍之为败类,虽罪有轻重,要之同为倡优隶卒,乡党不齿,有一于此众,可斥之不许入谱。”极言胥吏之害,以父母之身受辱,这是不孝的典型;不知廉耻,渔肉乡民,谋一己之私;声名败坏,有辱门风,贻害无穷,并以不得入谱这一家谱中最严厉的惩罚,警示族人不得为胥吏。从中也可以看出,对胥吏的歧视有一部分是针对这个职业本身的,觉得胥吏是“身入贱籍”,以父母所给之身供人驱使,这种对这一职业本身的歧视,无疑也会影响人们对胥吏个人的评价。
《程氏族谱》对胥吏的规范相较而言要和缓不少:“生平荣辱所关实在乎品行,端则人遂从而敬之,品行不端则人遂从而忽之。凡我族中如有子弟,奔走衙门、武断乡曲、或害人、或骗人,与一切自轻自贱而坏乎名节者,宜同声共击之斥其非。”主要从品行不端这个角度来考量,名节败坏,可群起而斥之。一方面,不提倡族人为胥吏;另一方面,即使为胥吏,也要小心谨慎,不得坏自己一世名节,不容于乡里。
徽州地区健讼之风盛行。家谱对这一现象大多是禁绝的态度,不少家谱的《家训》专有“禁家讼”,“禁诉讼”这一条。胥吏对诉讼这一司法活动的影响是很大的。被告如果向其行贿,案件开审可能就被故意延迟,负责记录被告供述的胥吏可能会在笔录上作某些变动,胥吏还会把尽可能多的人扯进案件中,以图勒索钱财[3]。《吴越钱氏七修流光宗谱》中,“书曰敦叙九族,敦者聊之以情,所以合疏也;叙者秩之所以礼,所以聊远也……。尝怪世之惯斗者,在家人则分不遵,偏不惮卑屈以下胥吏,世之健讼者,在家人则铭铢不让,偏不惜资财以殉请托卒之,家不和而行道皆传为议讪,内无助而邻里得肆其欺凌,岂不深可痛哉?吾故为敦叙之说,而尤以禁讼为谆匕者,盖重有所感也夫。”对整个宗族而言,遵守礼仪,讲求敦叙之义,宗族内的矛盾,由房尊、族长定曲直。对在族内斤斤计较却对胥吏耗财奔走请托的,“深可痛哉”,作者有感而发,可见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
2.2以家族榜样形象出现
胥吏任期5年届满之后,是有资格进入官场的。通过“考职”,会被授予品级或任以适当官职。“杜由吏员授山西氓州衙知事,升四川都护衙经历,”“熷以书字见重于王直,指超桼府掾,后考中正入品,恩免省祭径授山东郯城县县丞,升辽东广宁前衙经历”[4]。“汉,字大川,号蜜齐(大谱载密巷),尚富公长子,新安衙吏,授北京太仓衙经历,转虎贲衙经历,父母及妻皆膺锡命,升授青州府莒州同知,致仕后侍父黄山桥居焉”[5]。“宜墇,字子道,号养齐,谦公次子。善经先型,事兄如父,好读书,愽通典故,由掾史授汾水县典史”[6]。在徽州的谱碟里,此类记载不乏其文。
在家谱的世系记载中,有功名的人其生平事迹毋庸置疑会被较详细的记录下来,大部分普通人只会记录其生卒年份、婚嫁对象。对有功名人的突出,既是彰显家族地位的需要,也有勉励后人读书仕进,以这些先祖为榜样。胥吏作为官吏群体的一分子,也是有这一殊荣的。
《棠樾鲍氏三族宗谱》世系中载:
琛,字以重,行正二十,洪公次子,能立事。洪武初以良家子选充县掾吏,差往婺源办事,城中夜半失火,延烧甚炽,有司欲开城门救,而守御官坚不肯,公曰:“苟延烧官库及官府交书,谁任其责?若开城门,有罪某请当之。”由是城门遂开,民得运水入救。明日事闻上司,嘉公识权变。又当持有分司按临至境,遇疑狱不能决,公为剖析轻重,深合事宜,分司曰:“曹吏中有斯人耶!”因得举保,赴京授兴武衙知事……,晚年康健,抚孙成立,劳苦而有功,尤人所难者。生元至正甲申,卒明永乐壬辰,享年五十有九。
这段记载,生动的展现了鲍琛的机智善断,识大体,是不可多得的吏才。
“鲍义,字公尚,礼佳公子,洪武中举充郡吏,于时乡里群小结党为害,赖公悉力扫除族党”[7]。作为地方官与平民连接点的胥吏,不止是上传下达、作刀笔文案工作。他们身为本地人,对外来不知民情的地方官影响是极大的。这一影响不仅仅只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方面。
3 胥吏与宗族关系
家谱记载中有不少胥吏家境殷实,有的甚至是非常富裕。“汪童讳容,永真公长子,少读书,永乐十一年以税粮满千斗,有司举保,历政都察院十七年,除山东曎县丞”[8]。因纳粮千斗而为县丞,家境富裕可以想见。有的胥吏出生于富裕商人家庭,胥吏鲍琛之父鲍洪“尝偕从兄君茂贾江汉,多获资利,增置产业”。
虽然徽州不少胥吏是“钜姓旧家,藉蔽风雨”[9],但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普通人家,程楚琦“为科差命子彦达充府吏”[10],因没有缴纳赋税而让其子充任胥吏,鲍添佑“四岁而孤,值家事不给,备历甘辛”[11],家境贫寒,可见一斑。屡试不第而为胥吏的也不乏其人,“曰煦,字淑和,时贵公三子。读书未遇,由掾属例授九品咨选”[12]。
胥吏中存在父子相承的现象。“民佑公,字彦达,楚公子。幼明敏立事,洪武初因田粮充吏,未几南北对迁,遂调西安府,计四年。适苏州太守悯其情以侍亲,放回后因程彦超事连及,公提京问戍二十年,道至桃园苏溪巡检司,以六月十六日寅时卒。同事程彦超质地葬之,人称佳兆云。生至元庚辰九月二十日卯时,年四十八”[13]。尽管程民佑为胥吏的历程十分坎坷,但其子仍为胥吏,“贵得公,字士恭,民佑公三子。俊逸多能,洪武初充府生员,除巡检二年,升泉州典史”[14]。不少胥吏虽不是父子相承,但也或多或少与胥吏有关。有父亲德高望重,为乡先生祭酒的,“膺仕者冠服,孙曾林立,人谓积厚之报”[15],其子“尊父训为繁阳掾,考满当除,高尚不仕,优游田亩,内行淳备”[15],虽为掾吏,但德行情操,仍然不坠家声。
家谱记载中,胥吏的行为更多的是从宗族的角度出发,对宗族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添佑,字思敬,行敬三十,凤公五子。四岁而孤,值家事不给,备历甘辛,稍长赘稠里汪氏,为复亨公婿。勤慎无失,往厚遇之。居十余岁,携妻子归宗室,为子孙计。声起乡闾间,未几太守陈公廉其才德,强为掾,守法清慎,丁内艰服,阕擢周府郎官,劳心茹苦恪其厥职,考满还乡,志存邱壑,家居终老焉[16]。入赘汪氏数年后,偕家归本宗。这种行为是宗族所提倡的,体现了宗族凝聚力的强大。
纂修族谱是实施教化,规范族众行为的重要手段,而其中家训、家规的教化作用更为直接。《绩溪璜上程氏续修宗谱》家训以“有一等不安分者入衙为隶卒、为书吏,舞文弄法,连累本宗,为祸不小。至于为优戏、为人奴、为僧道,皆系下贱,概不入谱。”把同为“贱籍”的胥吏、优伶、奴隶、僧道相提并论,在家谱里是惯常出现的。胥吏舞文弄法,有损宗族声望,对宗族的影响很大。因此家谱对胥吏从严要求,防患于未然。
族谱为达到以榜样励众的目的,对任职有良好表现的胥吏记载详备。“贵得公,字士恭,民佑公三子。俊逸多能,洪武初充府生员,除巡检二年,升泉州典史。在任四年,有政声”[17]。“积善公字庆余,任甫公之子也,仁甫公性严毅,训子义方,公委曲承顺,得其欢心,至其立心制行,耿介刚直,不肯随俗,俯仰尝博览经籍,尤谙法律,永乐中以掾吏给由,上京考授八品冠带”[18]。对这些已有品级或官职的胥吏,他们大多本身非常胜任胥吏这一职位,对法条律令非常熟悉,且不乏“良善之家”的子弟,品性刚直。家谱对他们的记载,以褒扬的口吻记述的,可见胥吏对宗族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4 结语
胥吏作为古代地方行政中的重要部分,不可或缺。但在徽州地区,虽然存在对胥吏的歧视,但宗族对胥吏的态度,更多的是警戒,在百陈其害中,是希望充任胥吏的族人内心警钟长鸣,知有可不为。宗族一方面规范胥吏的行为,一方面对作恶的胥吏施以惩戒。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宗族势力面前,胥吏的行为得到较好的规范。考查胥吏与宗族社会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明晰明清时期的徽州基层社会状况,也有益于我们认知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问题。
参考文献:
[1]谢肇淛.五杂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78.
[2]许承尧.歙事闲谈[M].合肥:黄山书社,2001:601-602.
[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5.
[4]徽城杨氏家谱:卷5[O].明崇祯3年刻本.
[5]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10[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6]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7[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7]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13[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8]程启东等纂修.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6[O].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9]许承尧.歙事闲谈[M].合肥:黄山书社,2001:601-602.
[10]程启东等纂修.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2[O].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11]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8[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12]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5[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13]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2[O].程启东,等纂修.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14]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2[O].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15]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2[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16]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8[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17]程启东.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2[O].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18]孙家晖.古筑孙氏家谱[O].清嘉庆17年刻本.
[责任编辑:余义兵]
作者简介:程源源(1993-),女,安徽无为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主要从事明清徽州地区的社会生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94);国家社科基金(11BZS035)。
收稿日期:2015-04-17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18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074-03